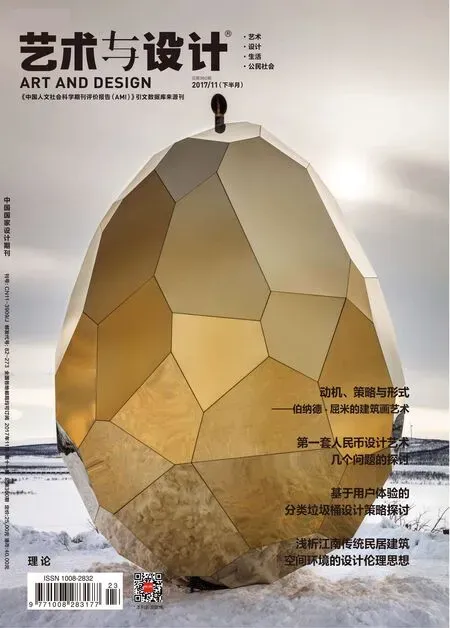四川唐代道教造像的三个特征
肖晓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四川唐代道教造像的三个特征
肖晓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从北魏至唐代,道教造像体系也渐渐有了南北之别。当北方还在承接周、隋之余续时,南方川蜀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格的造像体系。从现在的遗存来看,北方多为造像碑,单体造像虽有,但不成系统,而南方则继承了北齐、北周以来石刻造像的形态,并向大型化、系统化发展。就题材而言,北方多以老君为主,而南方的造像题材多以天尊为主。这些都说明了至唐代时道教因其自身的发展使得道教造像产生了地域特色。
道教造像;四川;唐代
从现存唐代道教造像遗存中,大部分的道教造像出现在川蜀地区。而四川地区历代都是道教兴盛地区,四川省大邑县鹤鸣山就是东汉末年李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所在地,也常被后人称之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至唐代,安岳县苑大乡的玄妙观,丹棱县唐河乡的龙鸪山,蒲江县天华乡的长秋山,剑阁县城边的鹤鸣山等地,以及仁寿县高家乡牛角寨,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道教造像龛窟群。本文以造像题材为研究对象,对四川唐代道教造像研究提出一孔之见。
一、天尊的泛行
所谓“天尊”,在《上清灵宝大法》中是如此解释的:“男仙高曰天尊,女仙高曰元君。”按照陶弘景编写的《真灵位业图》道教神仙谱系中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是道教的最高尊神,都成为天尊。但是,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天尊并不局限“三清”,而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天尊能够分出无数化身。《云笈七籖》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载:“天尊亦有十号:第一曰自然,二曰无极,三曰大道,四曰至尊,五曰太上,六曰道君,七曰高皇,八曰天尊,九曰玉帝,十曰陛下”。
尽管传统文献中对唐代官方崇拜老子(老君)的记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通过对唐代四川地区道教造像的梳理,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天尊已经成为造像题材中最常见的主神。
现将唐代道教造像的题材总结如表1:

表1 唐代川蜀地区道教造像题材统计表①
表1中,共有20龛天尊造像,而老君像只有5龛,当然这其中还有道佛合龛并未算在内,如果按照《云笈七签》中的说法,其他如长生保命天尊等冠以天尊之名的造像也算做在内的话,那么天尊的数量将会增加至26龛。这说明,其一,在唐代的川蜀地区,天尊作为主神出现的频率之高。其二,作为官方所提倡的老君并未在这一时期的川蜀地区占据主流,官方提倡与民间认同,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
把天尊当成至高神来供奉可以上溯到两晋时期盛行于南方的上清派,《茅山志》卷十中以元始天尊为至高无上的神。而此时,北方则以张陵的天师道和寇谦之改革的新天师道为主。其把老君当做道教的至上神。继而,南朝上清派著名道士将道教凌乱的神仙谱系整理成系统。他的《真灵位业图》将上清虚皇道君,应与元始天尊放在了第一个等级。而把太清太上老君放在了第四位。另唐释玄嶷《甄正论》中说:“近自吴蜀分疆,宋齐承统,别立天尊,以为教主”。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元始天尊的地域问题。六朝时期,四川主要是受南朝统治。此时的道教信仰最主要的是受到流行于南朝的上清派的影响。
至隋代,其道教神祗系统主要与南朝道教有关。最高的神仍是元始天尊。《隋书·经籍志》中说:元始天尊“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所度劫天仙上品,有天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皇真人、五方五帝及诸仙官。”
在刘宋以前,受张陵创立的天师道的影响,川蜀地区认为老君是最高尊神。之后又受到上清派的影响认为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神祇。巴蜀地区,大约是在周、隋之际最终承认元始天尊为道教的最高尊神。入唐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因唐宗室尊崇老子而改变。我们可以从川蜀地区的道佛合龛中看出来。一般佛道合龛的造像皆为元始天尊居中,老君居左,释迦居右。若是老君、天尊同处一龛,则天尊居左,老君居右。而左方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最尊崇的方位,将天尊置于中和左也就说明了当时道教仍将天尊当成是最高神。
二、道教女真的加入
在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道教经典中,道教对于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已经趋于完善,但是直至唐代的道教造像者才将其他的神祇引入到道教造像的镌刻体系之中。例如,《唐代川蜀地区道教造像题材统计表》中所列的长生保命天尊、六丁六甲神、三清等。尽管这些神仙仍比道教经典中的神仙谱系的范围要小,但亦可认为它们反映了道教有意识地将造像题材逐渐扩大、丰富的态度。
唐代四川地区的道教造像与北朝以及同时期的北方造像的主要区别之一便是造像之中女性形象的出现,这些女性形象多作为胁侍出现在主神像之侧。如四川省绵阳县西山玉女泉和子云亭隋唐道教摩崖造像第三组第4龛玉尊龛主像胁侍两边又增加了一位女真。头戴莲花冠,项下有一新月形短璎珞。又如四川省安岳县黄桷乡玄妙观道教造像11号龛“老君龛”左右两侧也各有二胁侍一女真等等。隋唐以后,女仙不单单指道教女性神祇,而是逐渐成为女神、道教及民间信仰的女性神祇的统称,甚至对貌美的女性也可称之为女仙。
为什么唐代四川地区道教造像中会出现女性形象?笔者认为是佛教菩萨女性化的影响以及道教女真数量的增多所导致的。因为佛教本土化的深入,菩萨女性化已经在隋代初步定型。道教造像或学习菩萨而选用在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女性神仙,也即女真来代替佛教中菩萨的位置。而唐代道教造像中女真的出现也预示着道教造像系统化的基本定型以及世俗化的开端。
唐代,女真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各个阶层都有女性加入到奉道的行列,新的女真谱系最终在唐末时期由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整理而成。在多个领域也反映了女真对于唐代社会的影响,道教造像仅是其中的一例。我们这里提到的女真有着两层概念:一是奉道的女性;二是女冠仙化之后的女仙。据已有的文献记载,奉道的女性已经深入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文章提出唐代奉道妇女的社会阶层:(一)封建士大夫阶层:1、皇宫贵族女性;2、上层贵族女性;3、下层官吏妻女;4、宫女入道;(二)社会下层:1、平民女性;2、婢女奉道;3、妓女奉道。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参与奉道,其结果是,致使唐代女冠和女冠观的大量出现。盛唐“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唐六典》中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上述道士的数量有些相关问题仍在讨论之中,道士和女道士的数量皆指“正名道士”。政府的统计显示了盛唐女道士的数量比男道士还要多,这至少说明了唐代女道士的群体规模。在唐代,也有天师夫人入道并被尊为女仙的情况,如孙天师智凉妻女皆入道并被尊为仙真。唐代众多女性尊师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并被女仙传记纳入仙籍,同时这说明了唐代女性修道者的活跃。
唐代女真的广泛出现,引起了道教造像者的注意,以至于引入到道教造像的体系中来,对于造像工匠及赞助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无意识的引起了道教造像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即世俗化。唐代时期,尚属世俗化的早期,女真的出现是早期世俗化的表现。这一时期,女冠大量出现,且女冠奉道的原因又兼多种多样,在某些情形下,女冠又被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者创造出精彩的小说故事,女仙或女冠们不再对仙界企慕和追求,转向了世俗的享乐与渴望,转向了人之情感的表达,出现了仙性淡化,人性增强的趋势。此时,人们不再从宗教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情感角度出发叙述故事,不再从宗教所设定的圣洁——非圣洁区分标准,而从人的情感标准出发去使用意象。
三、系统化的造像体系
系统化的造像体系出现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道教经典的广泛编撰。我们现在知道道教经典编撰在魏晋时期有一个初步的高潮,也就是灵宝经的编撰。此一时期的道教经典已经初步建立了道教的经典体系。而至唐代时,道教经典的编撰则又进入了另一发展时期。因为受到佛道之争的影响,尤其是关于《老子化胡经》所引发的争论,道教摄取佛教经典中的教理、教义,并制作种种经典来对抗佛教,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道教经典。二是道教多种神仙的出现以及神仙体系的初步奠定。道教是一种多神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率先规定了道教的初步的神仙谱系。其将道教神仙归入到一个有着等级概念的体系当中,并初步有了“三清”的概念。而到了隋唐时期,是三清作为最高神地位的奠定时期,也是道教神仙谱系继续编订时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唐代杜光庭的《道门科范大全》一书,其基本确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三是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我们知道在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最开始的“道无形象”阶段,之后逐步有了道教造像碑的制作,但仍然是汉代画像石艺术的演变,道教神仙形象只是造像碑整个图像体系中的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讲,魏晋南北朝的道教造像艺术尚未真正的独立。直至隋唐时期,道教造像艺术才真正的独立,有了道教独特的造像艺术语言,有了自身完整的神仙体系。而这些体现在隋唐时期道教造像艺术之上,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体造像的出现,道教徒可以通过直接造作神仙的单体造像而不是通过其他的图像语言来表达信仰。另外就是系统化的造像的出现。这是道教造像艺术在题材上的进步,因为道教神仙有着各自的功能,而民众在供奉神像时,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因此在造作造像时也会有针对的选择神仙。
现存的唐代长江流域道教造像以“组合”式造像表明了制造者已经对系统化的道教造像有了初步的要求及兴趣。这时期石窟造像的配置,与前代造像碑中流行的三尊像不同,在主尊像的两边除胁侍像外,还增加了真人,一般为五尊,与当时佛教造像中流行的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的配置相似。有些龛窟受佛教造像中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的影响,出现了一天尊(或老君)、二胁侍、二女真、二力士,一铺七尊、十一尊的造像配置,有些还增加了八个、十个,甚至十二个护法神。在一些佛、道混合龛中,造像配置更加灵活多样,往往佛教造像与道教对称排列,如四川仁寿县龙桥乡千佛寺4号龛以一弟子、一菩萨与二真人对称,后壁刻天龙八部。渣口岩10号龛配二弟子一菩萨与三真人对称,后壁刻八部众与二仙真。而8号龛则阵容庞大,以道教形象为主。虽然前排是二弟子一菩萨与三真人对等,但后排上、中部却是道教个神、护法神、仙真共十四身对八部众,且为两侧错落排列。
系统化的造像体系的出现是道教造像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系统化的造像体系也对道教教理、场所空间等作出了新的要求。依照前文所述,道教神仙谱系的扩大影响了道教造像体系的形成,但这也是道教造像体系对道教神仙谱系所提出的要求。另外,系统化的造像体系也对道教的场所空间作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来讲,场所也即环境,包含了由造像所组成的整体环境,其中有造像设计者的思想,蕴含了独特的宗教观念。关系到造像的宗教语境,也关注到宗教信仰者心理环境的再现。我们在唐代道教遗存的描述中发现了包含了两种道教造像的模式,二者把道教的教义、教理充分的表达出来,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供养人的存在。在第一种模式中,造像的设计把道教造像与建筑环境结合起来,启示着一种特殊的象征环境的存在。其基本元素(即建筑与造像)根据道观设计者的观念,使得造像与环境彻底的融合起来,营造一种便于道士观想、修炼的场所。在第二种模式中,供养人们放弃了建筑环境,造像仅仅依托于野外的环境,仅为供养人提供一个祈愿的场所。这两种模式有时独立有时相互转换,都不曾在历史中消失,道教通过二者而实现他们的礼仪与象征意义。因此,宫观场所的意义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其为我们了解道教造像的礼仪与象征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唐代以前,道观中的神仙塑像甚少,唐玄宗时期(713-756)曾命全国各大宫观皆塑老子像,并在太清宫塑玄宗像立于老子之侧,自此道教宫观中供奉雕塑的神像逐渐盛行起来,促使了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事实上,宫观神仙塑像的增加也与宫观场所的功能演变有关。就道教造像而言,宫观仪式场所的普及性远远超过石窟仪式场所的普及性,所以信徒们的持续热情往往是通过再塑造来体现的。因此,直至唐代,道教宫观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与石窟造像并行于道教造像发展过程之中。建造道教宫观的流行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系统化造像系统的产生。宫观在唐代时已经成为道教徒们最主要的宗教仪式场所,而宗教仪式场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即是供道教徒们朝拜。而道士们在建造宫观的时候自是有自身的一种诉求,他们希望通过对神仙塑像的布置以及宫观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来传播道教的教理和教义,并最终让世俗信众们笃信道教。
综上所述,道教造像艺术发展至唐代,已经出现了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造像艺术的重要区别之处。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与道教本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天尊的出现以及系统化造像体系的发展。这其实与道教经典中对三清概念的发展是相关的。虽然在唐代老子像的制作仍然是主流,但天尊的出现已经表明道教不管是在经典还是在造像中均已透露出对三清以及道教整个神仙谱系发展的努力。另外,道教造像艺术中女真的出现应当是唐代道教造像艺术最具特殊性之处,它表示了道教造像艺术世俗化的可能性。■
注释:
① 此表根据胡知凡的《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胡文和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汪小洋的《道教造像艺术研究》等书制作。
[1]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
[2] 赵娟宁.唐代妇女与道教[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3](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百官三·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52.
[4](唐)张说,张九龄等.大唐六典·尚书礼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89.
[6] 胡知凡.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96.
[7] 汪小洋.中国道教造像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16.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Taoist Statues in Tang Dynasty
XIAO Xia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Taoist statues also gradually appeared north-south difference. When the North was still undertaking the heritage of the Zhou Dynasty,Sui Dynasty,Southern Sichuan area had developed into a strict statue system. From the present remains,North was more statue tablet,although there existed monomer statue, did not form a system, While the South inherited the pattern of image creation by Stone-carving since the Northern Qi Dynasty,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large-scale and systematic form. As to subject matter,North to Supreme Venerable Lord mainly,While the South of the statues of more than Primus. All these indicate that Taoism in the Tang Dynasty owe to its own development made the Taoist statues produced geographical features.
Taoist statues; Sichuan; Tang Dynasty
检 索 :www.artdesign.org.cn
J32
A
1008-2832(2017)11-0143-03
Internet :www.artdesign.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