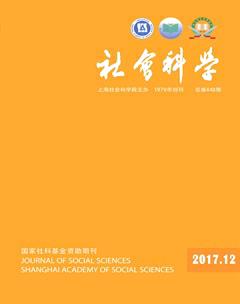心与目之辩
摘 要:王阳明尊心贱目,反对放纵目光向外逐物。主张真正的视乃心视而不应当单单以目视,心视发窍于目才有目视。目被心所主导、统摄,心感应天地万物,目亦以“感應”方式与天地万物交接。物我一体而无内外,理乃不可见者,道必体而后见。透过王阳明对心、目关系的思考,我们既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思维方式,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心学之内涵。王阳明自觉以心抑制目,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对先秦以来自觉压制视觉思想的呼应,使中国思想彻底远离视觉思想;另一方面,也深化了汉代以来确立的味觉思想,并影响着明代后期的文化思潮,尤其深刻地影响着与视觉关系颇为密切的绘画理论之“心画”走向。
关键词:王阳明;心;目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115-09
作者简介: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 (上海 200241)
从比较哲学看,不同的文化对“目”与“心(思想)”的理解各异。或以心(思想)随目,或以目随心(思想)。以心(思想)随目,即将视觉理解、规定为心(思想)活动之基本样式。比如,以视觉对象——形、色——规定为对象的本质,并将此作为心(思想)追求的对象;以视觉活动的基本特征(如主体与客体拉开距离)作为心(思想)活动的基本要求(距离性、客观性),等等。以目随心(思想),即自觉化解目活动的基本特征,比如化解其向外追逐物、与物自觉保持距离、追寻对象的客观属性,等等。以心(思想)随目与以目随心(思想)对应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式。
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其著述中大量涉及对“心”“目”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些直接表达“心”“目”关系,有些将“目”与其他感官放在一起而和“心”对立。显然,批判“贵目贱心”而自觉走上“贵心贱目”之路向,此乃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趋向。因此,从“目”与“心(思想)”关系入手,对于理解王阳明的思想,对于理解中国思想传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心目贵贱
先秦儒者通过区分“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抑制“见而知之”而挺立“闻而知之”;汉儒通过“耳舌之辩”而以味觉(即作为“心之窍”的“舌”)进一步抑制视觉,统摄听觉①。宋儒区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抑制、超越“见闻之知”,将视觉、听觉同时超越,而归向以“心”(心本身而非心之窍)之“所体”为基本内涵的“德性之知”比如张载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闻见之知”(或“见闻”)狭而“德性之知”(或“德性所知”)无外。“不萌于见闻”表述的是,两者乃不同类的“知”。。王阳明所展开“心目之辩”, 较之横渠,更自觉地高扬“心”而抑制“目”,无疑是儒家这一传统的自觉继承与推进。
《传习录》载:有一学者病目,戚戚甚忧。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这里的“目”指作为躯体一部分的器官,并没有直接涉及“目”的活动,如如何看,及所看者何等。但“贵目”所包含的对躯体的看重其实与向外逐物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它与“贵心”形成了对立的价值取向。“贵目”,还是“贵心”,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重要论题。
就《传习录》整个文本看,与“心”相对的“目”当然不仅仅指器官本身,同时也指视觉活动,以及基于视觉活动而衍生的一种思想方式。具体说就是,视觉的展开以物我距离的拉开为前提,基于视觉活动而展开的思想活动亦以自觉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为特征。王阳明反对的不是张目去看世界这种纯粹官能活动,而是反对以视觉为基础、以物我自觉拉开距离的思想活动。事实上,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这种以物我二分为基本特征,在外物上求理的思想方式一度为王阳明所欣赏,并付诸实践。阳明自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王阳明全集》,第120页。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欲践履朱子的“格物”观念,但在实践中却理解为“格看”。
将“格物”理解为“格看”,这显然误解了朱子。朱熹以敬格物,求“内外之理合”。朱熹确实拒绝将外物销融入内,试图保留住外物的独立性,以此保留住通达万物的路径。不过,格物之实质与玩味、理会一样,它不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外物,也不是追求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其目标是使物成为自家物事。因此,朱熹原则上拒绝拉开距离去做纯粹的看。当然,朱子没有提供一套“看”的指南也并没有提供一套“格物”指南。其以“格物”为先而展开的为学与成德工夫被误解并不让人奇怪。
阳明坐亭中,始终保持与竹子的距离,竹子是竹子,阳明是阳明,惟以眼光联结彼此。如我们所知,阳明之前的中国思想中视觉曾经一度凸显,但随即为听觉所抑制,并最终与听觉一道为味觉所统摄视觉、听觉、味觉之争的具体过程,请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因此,阳明之前的中国思想中没有形成积极的“看在阳明, “看”是“直视”:“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王阳明全集》,第115页)”的精神传统,并无“纯粹的看”之追求,亦无以“看”为主导的经验规训与思想规训。此时阳明之所求,为“理”,其中既包含“所以然”,也包含所当然。前者乃狭义的“真”的基本内容,后者乃狭义的“善”的基本内容。阳明撇开自家之身心,单单去“看”,既求不得真,也求不得善。阳明坐亭中七日格竹而不格心,终至于劳神成疾。
阳明践履“格物”说失败,经历“龙场悟道”而终于明白自己“格看”问题之所在。他说:“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全集》,第120页。以为物在心“外”, 撇开自身单单求物,逐物随物,不知归止,非罔即怠。外物格不得,只能格自家身心。endprint
阳明顿悟后,其格物不再只以眼光去看物之究竟,而将重心放到了“在身心上做”。认识自家身心不能拉开距离去看,了解自家身心之善恶更不能如此。“格物”不是與自家生命无关的认知活动,而被理解为“诚意”的工夫。“意”之“诚”是“格物”必要的精神准备。以“诚意”去格物,物在“诚意”中展开。此物非身心之外、客观独立自存自在者,而是与“诚意”相关涉者。如此,王阳明言物不再就物论物,而是就心论物,所谓“心外无物”是也。王阳明岩中花树之典故即是“心外无物”最好的诠释。“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全集》,第107-108页。王阳明这里特别用“看”来解释“心外无物”道理。“未看”是物我未遇之状态。此时花与人保持距离,花离开人,人离开花,花是花,人是人。如此,花“寂”,汝心亦“寂”。“寂”的意思是具体意义未曾显现。具体说即是,花无所谓真、不真,无所谓善、不善,无所谓美、不美。汝心中也不会有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呈现。王阳明所说“看花”之“看”显然非拉开距离地向外“看”,而是身心上做了工夫(诚意等)之后、花与人彼此交融、相互关涉地“看”。至于“看”到底如何展开,我们在王阳明的另一处说法中可寻出端倪。他说:“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王阳明全集》,第122页。“寂然不动”对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感而遂通”对应“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时的“所看”不在心外,“看”不是拉开距离、客观地“看”。花(物)不在心“外”,也不仅仅在心“内”。花不离人,人不离花,二者通过“看”而“感”,原未曾显现者便在彼此相感中显现出来。“看”只是表达花与人之间相遇而相互感应,“明白”则表达花与人之间相遇而彼此通达。由“看”而“感”则心花齐放,心与花之真、善、美等具体意义遂呈现出来(明白)。
二、心之视,发窍于目
“看”是(一种)“感。”人与物的本然关系,不是耳、目、口等感官与声、色、味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之灵明与天地万物之灵明之间的感应关系。二者之间的感应通过心发窍于耳、目、口等感官而实现。“目原是明,耳原是聪,心思原是睿知。”《王阳明全集》,第109页。“人心本自悦理义,如目本悦色,耳本悦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悦。”《王阳明全集》,第32页。“原”“本”是王阳明所理解的理想状况。“目本悦色”建立在“目原是明”基础之上,即人有能力看清楚事事物物之形色相貌,有沟通、联结物我的桥梁。“悦”表达的是“目”与“色”之间谐和的关系。当然,“目”与“色”之间的谐和不是通过“看”来实现,而是二者之间相互感应造就。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相互感应关系,乃在于“目”由“心”统摄。相反,“心”随“目”转,即放纵“目”之欲而逐物,人欲蔽心累目,则目不悦色,耳不悦声,心不悦理义。由“悦”至“不悦”,物我和谐关系不再。“不悦”表明心物一体关系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物我分,心理二。
不放任耳目,不追随耳目而逐物,就是要将“心”作为耳目的主宰,所谓“心统五官”也。阳明以君臣分职为例来说明这个关系,他说:“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王阳明全集》,第22页。人君所谓“端拱清穆”是指“心体”独立而不为五官活动所移易。保持住心体之独立性,也就护持住了心的尊严与主宰性。相反,五官诱导心,心逐声色,即不成其为心体。王阳明据此反对“多闻多见”,他说:“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王阳明全集》,第51页。阳明继承了横渠“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二分法,以及德性之知超越见闻之知的思想。并且将德性之知理解为良知,更自觉地以“心”超越“见闻”。“良知”与“闻见”,前者为“本”,后者为“末”。“闻见”指向外在的对象,多闻多见,心即外驰,务外好高则心逐物、溺于物,故阳明斥之为“第二义”。从闻见方向转向良知,即从务外转向德性之良知,这才是孔门正道在孔子,“多闻”高于“多见”,而并未完全弃绝“多见”,更未弃绝“多闻”。不过,由“多见”向“多闻”之转向确实显示出思想由客观外在向内在转换的倾向。阳明一概斥之为“务外”,显然与孔子思想有出入。。王阳明多次申说此义,如:“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王阳明全集》,第71-72页。致良知与求之于见闻乃不同的精神路向。阳明称良知为“主意头脑”,唯一的知,这并不意味着,见闻与“知”绝缘。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而可使其发用于见闻,见闻可视为致良知之功。由此二者可谓一事。不过,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由见闻寻良知便入歧途。更危险的是,求见闻之知而撇开良知。因此,阳明首先反对“专求之见闻之末”,其次反对“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前者“失却头脑”,后者以“致良知”与“求之见闻”为“二”。先致良知,确立起良知主脑地位,由良知视听而发窍于耳目,由此而有见闻,这是阳明对良知与见闻关系的基本定位。“心统五官”之“统”义为“统摄”。具体说就是,心乃视听言动展开的根据,即所谓“心是能视听言动的”。心能视听言动,无心则视听言动皆不能。不过,离开耳、目、口、鼻四肢,视听言动亦不可能。“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王阳明全集》,第90-91页。我们通常认为,视听言动乃耳、目、口、鼻四肢之活动。王阳明却让我们看到了视听言动的复杂性。将视听言动理解为耳、目、口、鼻活动,是将其限定为生理性活动。心的活动乃精神性活动,将其视为耳、目、口、鼻活动与心的活动之结合,则将视听言动理解与规定为生理性、心理性、精神性相统一的活动,这种见识无疑相当高明。endprint
心如何能视?在阳明看来,人与万物原本一体。具体说,人的良知构成了一体之“体”,即良知构成了一体之“理”。而在实际构成上,人与天地万物同为“气”,故彼此相通。万物以良知与气而为一体,此体非混沌,而是象人一样富有生机者,其表现就是体皆有“窍”。众窍之中,人心之灵明为最精。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王阳明全集》,第107页。以良知(理)为根据,以“气”为构成,王阳明的这个看法实质上与宋儒是一致的。万物一体而有窍,则众窍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一体表明,“看者”与“被看者”之间不再有内外,此乃“心视”的基本特征。“心视”也就是作为最精之窍的人的灵明与天地万物灵明之间的相互感应而相互通达。以观花为例,人的灵明与花的灵明在感与应中一起明白起来,人“明”花亦“明”,花“明”人方“明”。此“看”不是拉开距离而展开的“目”之“看”,而是“心”之“视”。由此说“目视”,其实质是“心之视,发窍于目”。
王阳明认为,作为身心一体的有机部分,耳目活动应该有益于此统一体及自身。耳目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为耳而害耳,为目而害目,遂使耳目不成其为耳目。对于如何能使耳目活动有益于自身,阳明认为,必须使耳目活动接受“礼”的范导才可能。耳目自身不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必须由“心”才能做到非礼勿视听言动,才能成就耳目自身。简单说,在心的主导之下而发的视听言动才是真正的视听言动,才能有益于耳目,成就耳目。阳明曰:“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王阳明全集》,第36页。“心”非“一团血肉”,是说,“心”并非如肝、胆、脾一样的脏器,而是精神性的“一身之主”。心主宰目,心视便由目来执行与完成,此谓“心之视,发窍于目”。 这里的“窍”指的是外在的通道与表现,而与中国先秦以来五脏与五官对应的“心窍”之说关于五官与五脏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心窍”说,最终确立“舌”为“心窍”,可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王阳明将“血肉之心”(生理性)与“神明之主”(精神性)相统一的“心”分判为“二”。作为精神性的“心”,其窍被理解为“多”,如目、耳、口、鼻、四肢,而不是“一”(如《黄帝内经》中的“耳”或“舌”)。不同。王阳明身心分说,明确将先秦以来“血肉之心”(生理性)与“神明之主”(精神性)相统一的“心”分判为“二”,此乃王阳明的创造朱熹以“知觉”说“心”,由所知觉而说“道心”与“人心”,并未言及“血肉之心”。陆九渊开始以理说心,他强调没有“二心”,但并未明确言及“心脏”与“心”的关系。。 “视”皆是“心”之“视”,而不单单是生理性的“目”之“视”。“目”之所以“能视”,乃在于人有此人性能力。在此人性能力不受损毁情况下,目皆能视。心与物不二,或曰,心与物无内外,则心之“视”活动中,我与物亦不二,亦无内外。这样物我无隔、无距离之视也就消除了所谓的以物为外,以眼向外看的精神趋向。真正的视乃心视而不应当单单以目视,心视发窍于目才有目视,这就彻底远离了视觉思想。
心明则目明,理明则物明。心明,良知明,即道明、理明,即对事事物物之理灿然于胸,知得来,做得来。反之未必是,理不可见,目明,见物而不必见理,理不必见,则心未必明。不过,在阳明看来,良知之不明与目之不明,其问题是一致的,即都在自身而不在外。具体说,良知之不明,乃由于其被“气拘物蔽”,只要去此蔽,则良知可复其明;目之不明,乃自目被遮蔽而病,治疗目病才可复目明。“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王阳明全集》,第46-47页。“目”之“明”是指看得清楚,“不明”是指眼睛看不清楚。“求明于其外”是做眼睛之外的工夫,比如,关注并创造外物之可见的条件(将物带至光亮之处,使其以“形”或“色”的方式存在等),以求得其明。按照通常看法,眼睛能不能看清楚问题不在外物,而在眼睛自身,故曰“明岂可以自外而得”。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服药调理来治疗目疾,正如通过为善去恶的工夫来去除心上之“气拘物蔽”。对于心、目之病相似之处,阳明进而论道:“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王阳明全集》,第124页。心体着念如眼中有尘沙,有尘沙(哪怕是金玉屑)则满眼昏黑,有着念则心体不明。去除心中留滞之念则心明,去除眼中留滞之物则目明。
以心(“良知”)主导“目”并不意味着心会提供现成的内容给“目”,同时“目”也不会自具内容。唯有心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应过程中,“目”才具有现实的对象。阳明曰:“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王阳明全集》,第108页。“体”指现实的“对象”与“内容”,“心”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其现实的对象与内容,“目”以“万物之色”为其现实的对象与内容。“能视听言动”的“心”包含着活动的能力,是活动的根据。能力与根据首先指的是可能性,现实的心以“感应”的方式与天地万物交接。心之视,发窍于目。心在感应,心之视也在感应,即目也在感应。在心与天地万物感应过程中,视听言动也就获得了现实的内容。由“感应”关系,万物相对确定的“形”被隐去,确定性较弱的“色”凸显目对应形与色,先秦时,随着“目”的凸显,“形”亦成为当时的思想范式。但是,随着视觉被抑制,“形”被超越,“色”则相应被选择与目对应,此在“五色”“五味”“五声”说中有明显表现。相较于“形”,“色”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容易随着个体生理、心理状况而变化。洛克把颜色归为“第二性质”,认为它具有主观性,正基于色的以上特征。。“感应”同时也将“目”与“色”结为一体,离开“万物之色”,“目”亦无其明。endprint
良知与造化诸物相互感应而使天地鬼帝诸物由“幽寂”而“显明”,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甚至夸张地以“生”“成”等字眼来表述良知的功效。所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王阳明全集》,第104页。“从此出”是说,造化诸物出现之根据为良知,良知灵明则有造化诸物,良知被蒙蔽则无此物。
三、无内外者不可见
在阳明看来,灵明充塞天地间而万物一体,一体而无距离,无距离即无隔,无隔则无内外,无内外则能合一。“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王阳明全集》,第124页。我的灵明与天地鬼神及万物间相互不可离却,彼此相互依存。与对象相互依存是“心”展开的基本方式。
王阳明并不否认“物”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对于他来说,与人无涉的物并不具有明确的意义(“寂”)。王阳明关心的是与人之“意”相关涉的“物”。所谓“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王阳明全集》,第47页。心之虚灵明觉即本然之良知,而其现实性上之应感而动即为“意”。尽管为应感而动者,但“知”为“意”之体,故“意”乃良知主导下自觉的精神活动。基于良知的主导性与意的自觉性,“意”之所用,原本自在之“物”即成为人所参与、介入之“事”,如事亲、治民、读书、听讼皆是。从“物”说,每个物都与特定的“意”相关涉,“物乃意之用”表述的就是“意”对“物”的主导与内在关联。有意则有物,无意则无物,就此说,“物即事”,“物”不在“意”外,不在“心”外。对于“意”如何“在”,王阳明这里用的是“应感而动”,也就是说,并非是“意”的单向投射(如此,投射而生者则为“意”之“所生”),而是“意”与“物”之间双向互动。“应”是说“物”非“意”所生。“应”而有“感”,“应感”表达的是两者之间互动而共在的关系。王阳明有时也用“感应”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如:“理一而已……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王阳明全集》,第76-77页。“物”之“有”是“感应”的前提,“有”而无人,则为“寂”;有人与之感应,则“有”即为“在”,不仅物“在”,意也“在”。二者共在,物我由“寂”而共“明”。就此说,物不在“心外”,也不在“心内”。
物非客观物,物不在心外;理乃以“诚意”“成德”为旨归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之理,理亦不在心外。王阳明坚决反对将物、理设定于心外,他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王阳明全集》,第44-45页。就王阳明所追求的“理”来说,离开“心”而在的“理”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效用,或者说,只是空洞的形式,而算不上是真正的“理”。以“孝”之“理”为例,“亲之身”是“孝”之“理”落实处,但“孝”之“理”不在自心外的“亲之身”,而在“自心”。因此,“孝”之“理”不会随“亲之身”之在而在,也不会随之没而没。有孝心,“亲之身”在而有理,“亲之身”不在,其理亦在。以理在“亲之身”,在“亲之身”寻理,此即析心与理为二;在吾心里寻“孝之理”,此谓“合心与理而为一”。从今日视角看,作为“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的“天理”不是纯粹客观物。“所当然”为人所制作,她依“心”而在,而不像现代科学追求的“公理”那样描述的是对象自身的客观属性。这里所说的事事物物得其理是说,这些事事物物本身并不具有“天理”。事事物物有其“所以然”,而无“所当然”。事事物物之“所以然”惟有与“心”“合”,才得与“所当然”结合,才可能“得其理”。王阳明强调在吾心处寻理,将“格物”理解为做“心理合”的工夫,这无疑有其合理之处。
理之凝聚为“性”,理无内外,性亦无内外。性无内外,则“学”不必资于外求。资于外求者乃以为义有外,乃以为性有外。阳明反对“以反观内省为务”,认为如此则“修身”二字足矣,而不必正心,不必诚意,亦不必致知,不必格物。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要落实在事事物物上,而这是仅仅求之于内所无法完成的。“以反观内省为务”意味着遗外。阳明承认“格物”乃《大学》实下手处,他进一步发挥道:“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王阳明全集》,第76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落实于“物”,无视“物”也就谈不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阳明看来,“遗外”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我”,在于“自私”,在于“不知性之无内外”《王阳明全集》,第76页。。不能求之于外而遗内,亦不能求之于内而遗外。“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王阳明全集》,第76-77页。人有私意,形体与灵明隔,我与物隔,有隔则有距离,有隔、有距离则有内外,有内外则有二。“无内外”“合内外”“无隔”“合一”,此乃阳明心学的基本思想方式。“心外無物”“心外无理”“性外无物”“性外无理”“理无内外”“性无内外”“学无内外”,“心与理一”“知行合一”“本体与工夫合一”,反对“隔”“内外之分”“理为外”“物为外”“义外”,反对“务外遗内”,反对“心理为二”。
视觉活动的展开总是以人与对象之间距离的保持为前提。理、物都不在心外,则人与对象之间无距离,无距离者不可见。阳明强调“无内外”“合内外”,这从学理上拒绝了视觉的放纵。在阳明的观念中,肉眼不可见者可以心感应、以心视,由“感应”(或“应感”)而保持着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通达关系。
四、道必体而后见
“心统五官”并不限于五官活动时,事实上,儒家一直强调在“未发之中”做工夫,即在未睹未闻时保持诚敬之心。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见。”《王阳明全集》,第37页。在不睹不闻时就要做工夫,即以“戒慎”“恐惧”之心主导,使耳目未动而心纯是天理,以保证目睹耳闻不随物而转。endprint
“道即是良知”《王阳明全集》,第105页。,道、良知无内外,故以拉开距离为前提的视觉不能“见道”关于“道”是否可“见”,思想家们有争论。比如,庄子认为,自然感官不能接近道。所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但经过“坐忘”等修行工夫,我们可以“闻道”。“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阳明对此有高度自觉。他说:“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王阳明全集》,第75页。道与人拉开距离而为二,此时不可谓“见道”。非“体”之“见道”以“我”与“道”拉开距离为特征,阳明称之为“讲之以口耳”。只有讲之以身心,实有诸己,道与人一,道得人“体”,此时乃真正“见道”。“体道”之“体”指人与道相互交融,人在道中而道以人显。道得人自觉去“体”,则道在人身中显现,由此显现处方可谈“见”,此即“道必体而后见”。“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全集》,第72页。,“天理即是良知”《王阳明全集》,第110页。。良知于其发用之视听言动,于其发用之思皆能自知,故在良知上体认天理乃为明白简易之途。良知无内外,欲拉开距离去“看”,亦不能见天理。
在阳明,物我一体乃本然之态,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就现实性说,物人相感才能真正成就“一体”。“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王阳明全集》,第79-80页。持守良知,任其发用,自能感应生民之疾痛。人人有良知,物物有良知,各任其发用,公是非,同好恶,则人而己,家而国,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中之天地万物、古今圣愚皆不“在外”。欲知天地万物,不可张目求之;欲知生民疾痛,惟务自家之良知。去其昏蔽,现其纯良,廊然大公,自照照物,皆如青天白日。
以心去看,即以良知去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之“视”以消除内外之分为前提,它始终拒绝着距离性的观看,而追求破除了物我之隔,物我合一之“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王阳明全集》,第106页。在天地万物与人构成的一体中,人的节律跟随着天地万物的节律,天地开,万物露,则人的众窍也随之开显。耳目之睹闻被当作良知之妙用,睹与闻都被良知化,由此確保所视皆能合乎礼(或“理”)。阳明对此说得明白:“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王阳明全集》,第119页。非礼之视是目无主宰,逐物溺物。以心主宰目,则所视皆可得正。
从修行角度说,从务外转向自家身心,确立“良知”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展开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之展开,须就心理上展开,但理不可见,理之发见处——文才可见。因此,工夫只能由“可见”而至“不可见”。王阳明说:“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王阳明全集》,第6-7页。“博文”为“约礼”的工夫,就可见处用功,以达于不可见之理。此即上文所说“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阳明未弃“目”之“见”,目可得见者乃不可得见的理之发见处。通过做前者的工夫,后者才能够落实。王阳明于此将前者归为“下学”:“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王阳明全集》,第12-13页。上达只在下学中,由“下学”而上达,此是不二之选择。其在下学中上达,即将“目”之“见”纳入心或良知主导之下(此谓“正目”,即“非礼勿视”),并由此寻求“目不可得见者”。
五、贵心贱目的历史流响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王阳明的著述中,“目”或者单独列出,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贵目贱心,见道与体道等,或者与其他感官及其活动一起列出,如:以见闻表述与良知之知相对的知,以耳、目、口、鼻四肢一起表述与心相对的“身”,以目色、耳声,口味一起表述人的欲望,等等。尽管以不同方式出现,但“目”始终被放在与“心”相对的重要位置。这表明,自觉超越目及其活动乃王阳明心学建构的基本任务。
从中国思想史看,先秦耳目之争,耳胜出,继而,秦汉耳舌之辩,舌胜出。由此确立了味觉思想之主导地位。舌为心之窍,心以味觉的方式展开,此乃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如上文所论,阳明将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应作为心的基本活动方式。“感应”实质是相互契入、无距离彼此融合的交接方式,这是“心之窍”的“舌”(味觉)的典型活动方式。贵心而贱耳目,可以看作是对以上思想历程之再次重演。由此可说,阳明对心的活动方式的论述,正是对味觉思想的深度强化。心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凸显了“是非”这种道德关怀,不妨说,王阳明的心学乃道德化的味觉思想。
味觉思想包含诸多维度。品味中通过味来识别品类(类的寻求),进而推演其根据(故的寻求),此为认知维度。品味中以闲适之心赏其情态、悦其情态,无辨识之心,无利害之心,此为审美维度。品味中审识其是否合乎人的价值规范,是否合乎人的目的、意志,由此有利害之选择、有善恶,此为品味之道德维度。王阳明自觉展开“心目之辩”,将“目”视作与“心”相对的、向外驰求的思想路线。随时警惕“目”所隐含的道德意义,比如,可能造成“心与理二”“物我之隔”“内外之分”等,从而极大丰富了味觉思想。endprint
王阳明确立的贵心贱目精神趋向随着王学的广泛传播而影响到其他领域。不离心言物,亦不离物言心,此在中国绘画中表现最为明显。真正的画作被理解与规定为经过画心消化过的物象,即经过心记忆、消化、心意化的物。画象不可单归于心或单归于物,实乃山水人物与画家之心灵交合者。莫是龙、董其昌提出画之南北二宗说“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此条见于莫是龙《画说》,同见于董其昌《画旨》,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是莫是龙提出,而董其昌大加提倡,遂流行于世。,并对苏轼之看法大加赞赏莫是龙认为,南宗始于王维,所谓“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荊、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引自潘运告编著《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又见于毛建波校注,董其昌:《画旨》,西泠书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9页),后者论画之“善画者画意不画形”思想被理解为区分南北的标尺。“画意”为南宗宗旨,“画形”为北宗宗旨。“画意”与“画形”之分又被邓以蛰准确地归纳为“心画”与“目画”之争。通常认为,绘画以形色创造意象,与视觉关系密切。但是,“贵心(意)”而“贱目(形)”的绘画思潮却在明代油然兴起。究其原由,一方面,以“象”论“画”(超越了以“形”论“画”)说奠定了中国绘画创作与欣赏之基调与方向,从而抑制了“目”的凸显关于中国绘画史上由以“形”论“画”,发展至以“象”论“画”,参见贡华南《心(画)与目(画) ——中西绘画中的视觉及其位置》,《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另一方面,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在明代的盛行无疑直接促进了绘画理论“贵心(意)”而“贱目(形)”之自觉关于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如朱良知《试论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因此,这股绘画思潮可视作王阳明贵心贱目说的自然流响。
(责任编辑:周小玲)
Abstract: Since Wang Yangming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heart (心) rather than the eye(目), he opposed letting the eye catch external objects without limitations. Instead of merely looking with the eye, he proposed that a true vision was seeing through the heart which mean the heart presupposes seeing by the eye and the eye was domina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heart. Both the heart and the eye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universe by means of “sensing”. Things and self constitutes an organic whole which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its inner nor outer. Unlike the invisible “Li”(理), “Dao”(道) can be seen only after we experiencing it. Based on Wang Yangmings insi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eye, we can master his own mode of thinking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as well as understand his philosophy of heart deeply.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Yangmings works, especially he restraining the eye and impelling the heart consciously, can be regarded as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Yangmings theory is a correspondence to a pre-Qin tradition that philosophers should consciously suppress visual thinking, which makes Chinese thought thoroughly far away from visual th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Wang Yangming not only intensifies a gustatory tradition established since Han Dynasty but also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ultural though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a painting theory called “Xin Hua”(心画) which closely related to visual relationships.
Keyword: Wang Yangming; the Heart (心); the Eye(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