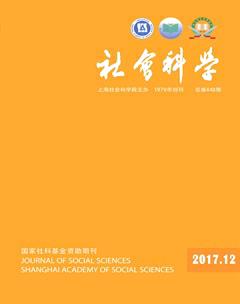论“听”与“圣”的关系
摘 要:在“圣”达成的过程中,“听”展现为一种能力,它具体表现为能听、会听、善听等多个面向。一方面,具备高超的“听”的能力,是成圣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凡为圣者,皆在“听”上达到至臻境地。“听”既是一种“德性”,又展现为一种“德行”,圣者在“听”上具备完善的“听德”。这不仅体现在成圣之后,也内在于主体通由“听”而成圣的过程中。“圣”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形态,具有正面价值,“听”于是在成圣的过程中体现为一种价值诉求,对其不断地追求与努力,使得主体在“听”上呈现出不同的人格境界。要达成一言出,而天下莫不听从的效果,需以“天下”为听之对象,以公正为依据,信任为内在要求,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同时也是由“听”而“圣”的方法。
关键词:听;圣;先秦;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124-09
作者简介:伍 龙,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后 (上海 200234)
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形态已逐步隐退,但人们在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上,却始终没有停止自觉的追寻。当前,伴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期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受人尊重的人。于是,新时期理想人格如何培塑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任何现实的问题都可以从历史的思想积淀中寻找可供借鉴的资源。“圣”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形态虽已隐退,但其实质的内涵,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驱动性与吸引力,却并未完全隐退。“听”作为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圣”联系最为密切的认知方式,与“圣”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立足先秦思想的资源,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圣”,在当下培塑理想人格,提供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一、“听”:“圣”的一种能力
“听”之于“圣”首先展现为,个体在达成“圣”的过程中,所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其具体表现为能听、会听、善听等多个方面。
“能听”涉及“听”的发生,即听者能听得进去,能通过耳或其他媒介将听的内容迎接到主体的认知过程中,促使听的产生。“能听”和听之“德性”有关:唯有塑造、培养耐心聆听的品德,才能具备“能听”的能力。圣者因具备高超的“听德”,所以“能听”,即对于各种声音都能合理地予以吸纳。
“会听”涉及“听”的方法,即听者懂得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践行“听”的行为。在“听”的过程中,听者往往容易受到自然性等方面的影响,从而无法正确践行“听”的行为。要想做到正确的“听”,必须秉持一定的原则,坚持一贯的态度,运用相应的方法,如兼听、衡听等。可以看到,要想正确地践行“听”,需经过一番努力,这既涉及对于“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自觉,也关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了解、掌握以及运用关于“听”的正确方法。
圣者在“会听”方面,具体展现为娴熟、自如地运用“听”的方法,几近完美地践行“听”的行为。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圣者能灵活自如地运用相应的“听”的方法来践行“听”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完善的“听”的行为背后,是圣者对于“听”的方法深入而透彻的掌握。换言之,前一方面涉及的是,圣者在践行“听”的行为时所展现的实践智慧,即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促使“听”完美地实现。要知“实践智慧不仅考虑普遍,而且考虑特殊”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2a10-15, in 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p. 1030.。它“指向具体事物,同时也意味着普遍原则与特定情境的沟通” 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后一方面则关涉对“听”的方法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对“听”的方法有了深入而透彻的把握,圣者才能运用实践智慧,正确践行“听”的行为。
“听”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又具体表现为一种“善听”的能力。所谓“善听”是指圣者善于运用“听”的方法,完成“听”的行为。这里的“善”一方面体现为上面所提及的实践智慧,即善于将方法与情境结合,促使“听”的行为完美实现;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一种积极、自觉的态度,即圣者因对于“听”各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都十分了解,故而能积极主动地促使“听”,由“听到”向“做到”转化。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听”的作用才真正得以发挥和落实。
“听”的能力所表现的上述不同面向,促使圣者在“听”的方面达至“聪”的境地。在先秦时期,一般认为,“目”追求的是“明”的状态,“听”则要趋向于“聪”的境地。“视思明,听思聪。” 《论语·季氏篇》。“目贵明,听贵聪。” 《管子·九守》。如何算是“聪”呢?“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 《管子·宙合》。顺乎中正之道地去听,对听闻的内容,依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审查和反思,便是“聪”,否则便是“不聪”,便会“缪”。“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 《管子·宙合》。
圣者作为一种至高的理想人格,在“听”上自然已达至了“聪”的状态。换言之,“聪”可以说是“听”所能达成的至臻状态。“聪,察也。” (汉)许慎,(宋)徐铉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0页。“圣,通也。”(汉)许慎,(宋)徐铉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0页。圣即圣。因此两字都从“耳”部。其中“察者,覆審也。”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339页。从“圣”的“通”之意反观“聪”,可以看到圣者在“听”上所达成的“聪”具体表现为,圣者在“听”上达至了“至察至明”的通达境地。立足于“能听”、“会听”、“善听”来反观“聪”,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内容。事实上,“听”的能力所展现的三个面向本密不可分,在相互关联的同时,呈现出“聪”所具备的品质。endprint
首先,“能听”是基础,涉及“听”的发生,唯有外在的内容被“听”进去,才能谈及“听”的其他阶段。其次,“会听”是手段,涉及“听”的方法,它为践行“听”,促使“听”的内容向实际行动转化提供指导。没有“听”的方法,便无从论及“听”的实践智慧。最后,“善听”是目的,关涉“听”的最终实现,以及将听到的内容,积极转化为富有成效的行动的过程。“善听”既以前两者为基础,又是前两者努力达成的方向。立足于三者的关联,可以看到,“聪”不仅是某一方面达成与呈现“听”,而是贯穿于“听”的整个发生、发展以及最終实现、完成的过程。换言之,包括能听、会听、善听等多个方面在内的“听”的能力,都应达成“聪”的状态,它不仅体现在“能听”的阶段,具备高超的“听德”,而且展现为灵活、自如地运用听的方法指导听的正确实践,故而,“聪”又与“听”在实现过程中,主体应具备的实践智慧紧密相关。基于此,“聪”体现出多面而丰富的意义。
“听”作为一种“圣”的能力,并非仅仅指向成圣之后,从成圣的过程来看,“听”作为一种能力,所蕴含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已经为个体不断培养和趋近“圣”这一理想人格助力。具而言之,“能听”是培养个体耐下性子聆听、听取外在的声音,使得“听”的内容能够进入听者的认知过程,促使“听”的发生,这一过程即是培养“听德”的过程。个体在此阶段已经通由“听”在塑造自身的品德,并不断培养起高超的“听德”。“会听”则要求听者不断地了解和掌握“听”的方法,并能灵活地运用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听者亦逐步对“听”的方法所具备的意义和价值予以自觉,从而将其自觉运用于实际行动。如何才能运用方法正确地践行“听”的行为,是“善听”所涉及的问题,在不断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主体逐步获得了关于“听”的实践智慧。与此同时,听者也对“听”自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自觉。
可见,在运用上述能力(能听、善听、会听)的过程中,听者不断成为一个具备高超“听德”,能耐心而全面地迎来“听”的内容,对“听”的方法既有透彻的了解、掌握,又能积极、主动、正确地将其运用于实际行动,指导“听”的行为的实现和完善,充分掌握了“听”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并对“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有充分自觉的人。这样的人在“听”上即趋向于“圣人”的状态。换言之,正是对“听”的上述能力的掌握和运用,个体才得以不断地向“圣”这一理想人格迈进。此外,从“圣”的字型来看,“听”是“圣”最为基本而原初的重要能力 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由此看来,“听”的上述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成圣的内在要求:要成为圣者,就应具备完善的“听”的能力。可以说,“听”的能力的培养和煅造,成为了“圣”达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二、具备“听德”的“圣”
“听”作为“圣”具备的一种能力,同时造就了其高超的“听德”,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圣者既有高超的听之德性,又展现出完善的听之德行;另一方面,在不断由“听”达成“圣”的过程中,借助“听”,主体得以具备完备的“听德”,从而成“圣”。前者体现出“听德”是“圣”的内在品质与要求,后者则展现出在由听塑德,进而成圣的过程中,“听”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听”作为“圣”的一种能力,首先表现为“能听”,而“能听”简而言之即指能听得进去。进言之,是指能由“听”将外在的内容,迎入听者的认知过程,这一点即与“听德”相联系。圣者作为理想的人格形态,其在“听”上具备高超的“听德”,无论是称赞的、肯定的意见,还是批评的、反对的声音,都能通过自身的理性判断,被合理地吸纳。“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 《韩非子·难言》。真挚、恳切的言语,多是忤耳、逆心的,唯有圣者、贤者才能合理地由听予以吸纳。圣者所具备的高超“听德”,从来源上确保了“听”之内容的全面和完整,从而为“听”的正确践行提供基础。可以看到,这里的“听德”涉及两个方面,即德性和德行。圣者正是因为在“听”上具备很高的德性,才能对听之内容予以合理而全面的听取。与之相应,这一正确的“听”的行为因其内在德性的支撑,使其展现为一种德行。
不仅是听的发生(能听),而且运用听的方法践行、实现听的行为(会听、善听),都彰显着圣者所具备的“听德”。如前所述,“听”的方法,涉及听的态度和原则,以及具体的“兼听”、“衡听” 对“衡听”与“兼听”,《荀子》一书有较为丰富而深入的阐述。参见伍龙《论荀子哲学中的“听”》,《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都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了判断和筛选,并最终被最大限度的广泛听取,从而使得听到的内容在转化为实际行为后,能最大可能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圣者能灵活地运用“听”的方法,完善地践行“听”的行为,他能运用一定的标准对“听”的内容进行判断,并实现“兼听”和“衡听”,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义,这些“听”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德行,彰显着圣者所具备的“听德”。
与“听”作为一种能力存在一样,“听德”并不仅仅是在“圣”这一理想人格达成之后,才具备的一种品质。在“圣”不断达成的过程中,“听德”一样起到着重要的作用。在不断修己之德性,善己之德行的过程中,个体才能不断地趋近“圣”这一理想人格。具体来说,当我们面对不同的声音时,因为自然性的驱使,总会对肯定的、赞扬的意见有所偏爱,而反感于批评、否定的声音。在克服这一自然性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了解并掌握了“听”的标准,且对标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有所自觉;另一方面,我们会主动地运用这样的标准,兼而听之,避免偏听偏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努力做到“兼听”和“衡听”。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个体将自己的自然性不断向社会性归正,促使自然性更好地存在。进言之,个体得以在博弈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使得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仅仅服从于自然性的动物性存在,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在世。其次,个体对于“听”之标准,即礼义、正道都有了了解和把握,对其所具备的意义和价值有了充分的自觉,进而运用这一标准对“听”的内容进行判断和筛选,真正做到正确的兼听和衡听。第三,“听”并不仅仅停留于“口”之上,即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仅仅表现为听取并予以口头上的承诺,而且通过将听到的内容贯彻于实际的行为,最终落实“听”的作用和意义,如此便实现了从“听”到“言”,再到“行”的转化。这一意义上的“行”,以“听”为依托,又将“听”行为本身予以推进、扩展,安置于更为广泛的行为中。不难看到,上述三点都促使个体不断由“听”达成“圣”:博弈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对礼、道等标准予以了解和把握,做到兼听、衡听,实现言行一致等。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地由“听”修习自己的德性,完善自己的德行,促使人格状态向“圣”趋近。endprint
三、价值诉求的“听”和人格境界的“圣”
“听”在一般情况下,被理解为一种认知途径和手段,而“听德”之“听”则更多地展现为一种道德能力。 参见伍龙《论“听”与“德”的关系 ——立足先秦视域的考察》,《应用伦理研究》2016年第1期。相较而言,“听”在与“圣”的关联中,则呈现为一种价值诉求。
“圣”作为一种最高的理想人格,一直是中国古人不断追求和趋近的目标,孔子便被后人视为“圣人”的典型代表,他既有深厚的仁德,又在各方面趋近智慧之境,“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基于此,“圣”被赋予积极而正面的价值,“成圣”则被视为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地趋近和获得正面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听”展现为一种价值诉求,它是获得“圣”这一具有正面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亦贯穿于个体对“圣”这一理想人格状态不断诉求,并积极趋近的过程中。
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希望成为在德性和德行上有修养的人,通过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趋近理想的人格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圣”作为最高的人格状态和精神境界,无疑具有指向性和目标性。基于人的这一自发自愿的内在要求,“成圣”就展现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同时,“听”又是成圣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这一过程便表现为个体自觉、主动地运用“听”达成“圣”。因为自觉、主动,所以,“听”的行为也变得更为可靠而富有成效。一方面,主体会积极运用“思”的能力对“听”的内容,依据一定的标准予以取舍;另一方面,主体也会将“听”的方法运用于“听”的具体行为,并进一步促使“听”的内容向实际行动转化。
不难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听”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认知手段,同时还成为了追求“圣”这一目标的途径,于是,“听”呈现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诉求,即要通过“听”来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诉求“圣”这一具有正面、最高价值的理想状态,它并非来自于外在的强迫,而是出自于内心的追求和趋向。立足于“听”的作用来看,个体之所以通由“听”来修德,培养自己能听、会听、善听等能力,从而向“圣”靠近,乃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个体,不断地追求和获得“圣”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帮助个体逐步向“圣”趨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听”本身也被赋予了价值内涵,成为一种具备正面意义和价值的行为。具言之,作为通向“圣”的途径之一,它为个体成“圣”提供了可能,听者可以通过“听”来修己之“听德”,不断煅造德性,完善德行,自觉“听”的标准,收获“听”的智慧,这都体现着“听”的正面价值。“听”在帮助个体成圣这一点上,同时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当我们反观当下,这一问题的思考将可能面临一个困境:现今是否还存在对“圣”这一理想人格,自觉自愿地不断追求?换言之,当下,是否还有一个所谓的“圣”的人格理想,在指引着人们不断地向其靠拢,以此为目标引领人们不断在人格上努力前行?这便涉及到“后圣贤时代” 所谓“后圣贤时代”,是指“圣贤”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和价值目标,被人们自觉自愿追求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当下,依然会涉及到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等问题,故而,以“后圣贤时代”这一名称来指示,当前时代在这一问题上的特点。的成圣问题 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如果“圣”的追求在当下已经不再可能和必要,那么“圣”与“听”关系的讨论将失去现实的意义,由此相关论述的必要性亦将受到质疑。,涉及到当下我们如何培养理想人格的问题。一方面,现今,“圣”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和至臻的理想人格,随着历史的发展已逐步隐退。与古人迥异,他们树立了一个孔子那样的圣人,作为生活中的楷模,让有志者不断地趋近和奋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以“圣”的内在、本质的意义为指向,不断地修习自身的德行,完善自身的行为,使其成为具备德性的德行,进而在修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格水平和精神境界,让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彬彬有礼,有人格魅力的人,依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换言之,从人的自我要求来看,个体总是希望成为一个在精神层面和行为举止上,更完善、更优秀的人,这样的修习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自然相处的同时,也帮助自身更好地在世。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虽然没有了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圣”的概念,也没有树立起一个如“孔子”那样的圣之楷模,但人们依然在实质层面上,有一种向“圣”靠拢的自发要求,故而在这样一个后圣贤时代,一样有成就圣贤人格的问题。只是这个“圣贤人格”的追求过程,已不再像古代所说的,成为像孔子那样的人,而是转变为更为广义的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培养和树立理想人格的问题。“与古代要使人成为圣贤、成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对新时代,人们如何塑造理想人格这一重要问题,冯契先生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应,提出了“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
借助这一理论,“听”与“圣”的关系得以呈现更为丰富的内容。首先,如前所述,通过“听”,我们可以不断塑德,进而提升德性、完善德行,并逐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塑造理想的人格状态。“听”在这里作为一种路径所提供的可能性,并非虚无缥缈,玄乎不定,而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因为“听”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认知行为,经常被我们使用和实践。我们常能通过“听”迎来外在的“声”,并对其加以认知。在践行“听”的过程中,更好地认知自己和外在世界,由此向“圣”靠拢。这一靠拢具体表现为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状态,包括内在人格和外在行为。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提升精神境界,塑造理想人格的途径和方式,“听”是切实可行,亦是触手可及的,它具有实践层面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前者源自“听”作为一种日常的认识方式,常被人践行;后者则因为“听”在展开过程中,具体的实践方法。所以,通过“听”而成就理想人格,亦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endprint
其次,在通过“听”而成“圣”的过程中,显然内蕴着一个“由听塑德”的环节。从结果上看,圣者应具备高超的德性和德行;从过程上来看,要想成为圣者,需要在“德”上下功夫,修习德性,完善德行。“听”作为一种行为,在不断践行的过程中,同时也为听者在“德”上趋近完善,进而为“塑德成圣”提供了契机和可能:个体在不断修习听之德性的同时,也践行着听之德行,这从“德”的角度促进个体成圣。冯契先生在构建“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考察培养实现这一人格的基本途径时,冯先生便指出“实践和教育相结合是培养自由人格的根本途径”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311页。。他进一步认为“实践是人和自然、主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并非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地将外在的环境、自然等对象化,从而由自在走向自为。“听”作为一种行为,首先是实践的。在践行“听”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通过“听”将外在的自然之声,人为之声,以及声所造就的环境,迎入到自我的认知过程中来,通过不断地消化和理解,完成“由听塑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并非是被动地听取,而是主动地“听纳”,即主体积极主动地运用“听”来“塑德”,逐步塑造理想人格。因为如前所述,对于广义的“圣”的追求,是每个人内心的愿望,为了达成这一理想人格状态,主体的行为是主动而自觉自愿的。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实现的亦是外在自然、环境的对象化,而主体本身也逐步由自在走向自为。
“圣”展现的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且呈现为一种人格境界。从这一意义出发,“听”又与境界的提升相关:在不断修习“听德”的过程中,个体也达成了不同境界的“听”。在最初阶段,听者可能需要耐住性子去听,克服某些自然性,并将其向社会性归正,但是随着“听”的行为的不断展开,听者对于“听”的意义、价值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自觉,对于“听”的方法有所探索和把握,于是,听者不再是克制、强迫自己去听,而是逐步自觉、自愿地去“听”,更为理性地将听的方法运用于听的行为,促使“听”的真正、正确地实现。可以看到,从强迫、克制到自觉、自愿,听者提升着自己“听”的境界。待到至臻于圣的时候,则一方面“不勉而中” 《礼记·中庸》。,即不用勉强地去听(如克制自己的自然性去听等),便可自然而正确地践行听的行为,达成听的效果;另一方面,从抽象方法到具体行为的过程中,圣者亦能灵活地将两者结合,促使“听”的实现。在“圣”之境界中,听者可能已忘却了“听”之方法的规定,包括相应的标准、态度,以及具体的措施,但其听的行为皆能正确,符合标准,达成“听”最好的效用,这便体现为“听”上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的状态。
纵观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在个体通由“听”向“圣”迈进的过程中,听者自身的精神境界也在不断提升。虽然要达成最高的“听”之境界相当艰难,但个体在践行“听”的过程中,正逐步地提升着自身的德性,包括人格状态和精神境界等,完善着自己的德行,向着这一目标趋近。可以看到,正是通过“听”这一实践行为,一些准则和规范,如耐下性子去听,将听之方法与听之行为结合等,才最终“习以成性”,形成了人的品德,这也是冯契先生在“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論中强调的。 参见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实质上表现为“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言论、行动、社会交往中贯彻理论,以至习以成性,理论化为自己内在德性,成就了自己的人格” 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的过程。
最后,由“听”而圣的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反复,循序展开的过程。在不断地通过“听”来修德性,善德行,从而提高人格境界的过程中,听者总是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干扰,比如自然性的驱使、影响,总会对赞赏的言辞有所偏爱,总想不顾具体情境地聆听美妙的“乐”。有时,自然性能因为理性的作用,得以克服,并被归正,但有时,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即自然性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压倒社会性,占据上风。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个体不断地通过“听”来修习自身的德性。德性的提升本身呈现为一个过程,德行的完善需要逐步实现,这都决定了“听”的行为需持续性的展开。事实上,也唯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够在不断运用“听”修德的过程中,逐步成圣。冯契先生也指出:“人的自在而自为不是说一旦归于自然就完成了,它是不断地反复的,人的才能、智慧和德性是不断提高的,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运动。”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而这样反复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源自于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个体自身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后者(世界与个体的具体、真实的存在状态)是前者(反复的过程)的本体论根据。也正因为如此,“听”要真正成为成“圣”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就需要听者在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中,持之以恒,坚持不断,这是个体通由“听”锤炼出的意志力,它同样是成“圣”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
可以看到,借助冯契先生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听”与“圣”的关系得以在多个层面丰富地呈现。这一方面体现出冯先生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听”作为趋近广义“圣”(一种理想人格状态)的一种途径,所具备的有效性。理想人格状态,既是指达到人格的自由,实现真善美、知情意的统一,又是指实现个体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由听塑德”的过程,促使主体德性不断提升,在化理论 这里可以具体理解为“听”的具体方法。为德性的过程中,成就自由的人格。“听”外在之声,包括自然之声和人为之声,所获得的美感、享受,以及实现的与他者的和谐共在,帮助主体逐步实现真善美、知情意统一的理想人格。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并非总是被动而为,“听”更多地展现为“一种主动的赋予创造性”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的实践行为。通由它实现的是,“听”之主体在迎接不同之“声”后,形成的在“听”之层面的个性,这一“个性”帮助主体不断地达成理想人格,在转化外在之声的过程中,由自在走向自为。endprint
四、圣而后天下听之
“听”可以被理解为听取、聆听之意,由此出发,其展现为认知途径、道德能力和价值诉求,但同时“听”还可以被诠释为“听从”、“服从”。前一种意义使得“听”一方面成为达成“圣”的重要路经,另一方面成为“圣”所应具备的重要能力。后一种意义,使得“圣”在达成之后,其所言之语,所践之行,都极具说服力和规范性,使得他者愿意听取,进而听从,并以此为楷模和目标,不断趋近。当“圣”和“王”相结合,即王者亦是圣者时,其所言之命令,皆会被听从、服从。消极地说,若不听从这样的言论,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 《管子·霸言》。圣者之言辞一出,听之则国家长久,不听则有亡国的危险。并非仅仅是出于消极后果的被动压迫,而且因为圣者自身具备的高超德性和德行,使其在道德意义上成为了模范,个体出于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和追求,自觉自愿地向这一目标趋近,付出努力。听者一方面对不听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有所了解和警觉,另一方面也是发自内心的甘愿听从,并积极效仿。基于此,圣者能达成“远不不听,近无不服” 《管子·霸言》。的效果。如果说,前面所言及的“圣”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理想人格状态,那么,这里的“圣”则与政治实践相联系,从“圣”转变为“圣王”,所以,“听”的意义也从听取、聆听扩展到了听从、服从,从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里亦涉及到前面所论及的问题:当下的时代已不再有“圣”这样一个角色设定,即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如孔子那样的圣者,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物,让人们学习和趋近,但不可否认的是,如在“听”和“德”的关系所提及的那样,当一个人在通过“听”不断提升了自己的德性,完善了自己的德行后,其所说之言,所践之行,则具有不同寻常的说服力和范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因为如此,个体才要不断的锤炼自己的“听德”,包括德性和德行两个方面,从而在提升自我品性、品行的同时,使自己具有话语权和权威性。所以,由此出发,虽然不再有“圣”之具体人物的设定,以及由此而引来的追求和努力,但是从个体自身角度来说,依然存在一个提升自我之“德”,从而使得自己之言、行,能够被人“听”的维度。
那么,听者应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达成“圣者之言”呢?首先,需做到“合而听之”。“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 《管子·君臣上》。个体在听取内容的时候,不能任由自然性的驱使而偏听偏信,应努力做到“听”意义上的“合”,因为“合而听之,则得失相辅,可否相济” 黎凤翔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5页。。唯有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才能权衡各种得失,为正确而理想的决策提供保障,这一内涵与前面所提及的“兼听”相通。这里予以“合”的对象应指向天下,换言之,“合”并不仅仅是指多听几个人的意见和声音,而应以“天下”为怀,广泛听取百姓的呼声,兼顾天下民众的利益。“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韩非子·奸劫弒臣》。一个圣明的君主,以天下百姓的呼声为自己听的内容。事实上,也唯有如此,圣者才能做到“无所不闻”,从而在“听”上达至超凡的境界,“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 《管子·九守》。。通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个体不再局限于自己之独耳,而得以扩展到天下百姓之众耳。如此一来,天下百姓所听到的声音,都能被我听到,听者于是做到“无所不闻”,这个时候的“听”已趋向于“聪”的状态,“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 《韩非子·法定》。。
以天下为听的对象,展现“听”之内容广博性的同时,其行为本身还应遵循一定的态度,这便是“信”。其具体表现为,在“听”的过程中,听者应从内心给予“听”的对象以信任,《管子》已有鉴于此。圣者是对天地四时之“道”有深入把握的人,“唯圣人知四时” 《管子·四时》。,因顺乎天地之道而行,故其行为皆“正”,在用人方面亦能知人善任。如何可知君王已进入“明”、“圣”之境了呢?“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 《管子·四时》。。这里的“听信”,一方面是指在选贤举能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另一方面,要求听者应对听之对象报以“信任”的态度,“即听其言,又信其事,所谓为圣” 黎凤翔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8页。。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听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只是“听”,但并不“信”,那么,面对言说的对象,听者将可能报以一种敷衍的“听”。唯有加入了内在的信任,才能促使言说者更为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将促使听者更好地通过“听”,收获更多真诚的意见。
从君臣关系来看,这种“信”亦具互动性,即不仅君上应“信”其臣,而且臣下应“忠”其君,唯有如此,臣子才能获得君主的信任。否则,将导致其言不被听,危及国之社稷。“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夫事君者无二心。” 《管子·匡君大匡》。此外,圣者以天下为怀,达成“无所不闻”的“聪”之境地,在“听”的层面呈现圣人之境,这种以“天下”为听之对象的态度,内在地涉及“公”,展现出“天下为公”的气象。“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管子·内业》。圣者之所以能够一言出而天下定,乃是因为其言以“公”为基础,即所说之言,建立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之上,这体现出“公正”。这里的“公”,可以说是“合而听之”、“兼听”、“衡听”等方法在“听”的过程中运用的结果。换言之,“合”天下之声音而听之,兼而听取广泛的意见和建议,都是为了实现“听”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基于此,不僅圣者之言能为天下听之,而且其行亦极具说服力和范导性,让他者自觉自愿地向其靠拢。
《尚书》中曾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周书·泰誓中》。天之所听,乃源自民之所听。换言之,听取百姓的声音,实际就是在听天之呼唤。百姓之声,指向天下民众之生存疾苦。作为圣者,在自我修身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以个体的完善为目标,同时也应心怀天下。遵从天之召唤而行,在这里即表现为遵循百姓的声音而行:唯有广泛听取百姓的呼声,才能在言说、行动时,得到百姓的听从、服从与拥护,“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将听民而已矣” 《韩非子·显学》。。所谓“先听天下,而后天下听之”。进言之,这里的“天听”更多地与“天道”相涉,是由“听”接续、体味、把握天之大道。与之相对,“民听”则更多地关涉“人道”,是通过听取百姓的呼声,体察民情、事理。从“民听”到“天听”,体现的是人道与天道的相通、融贯。从这一理解出发,天道的体察,不再那样神秘,而是在听取民声,体察民情,体味人道的过程中迎来。由此亦可发现,“听”不仅与“德”、“圣”,而且与“道”存在密切关联,“听”也由此而彰显出其形上意蕴。 “听”与“道”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当另做文单独述之,此处不赘。endprint
綜上所述,通过“听”个体不断地趋近“圣”的状态。当我们将“圣”做广义的理解,放在当下时代,具体予以考察时,不难看到,“听”作为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其所具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听之主体不断地把握“听之道”,一方面正确地实践“听”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和获得智慧。在冯契看来“智慧使人获得自由” 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这具体表现在“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上。由此可见,主体通由“听”达成“圣”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听”获得智慧的过程,个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自由,包括劳动自由,人格自由等,最终成就理想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将“听”之理论转化为“听”之方法,又将这一方法最终内化为自身的“听德”(包括听之德性与听之德行),从而实现广义的“圣”,即所谓的“理想人格”。于是,“由听成圣”的问题同时可以理解为“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听”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
(责任编辑:周小玲)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heng”, “Listening” as a kind of ability which express many aspects such as can listening, know how to listening and good at listening.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skill of listening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become “Sheng”.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e people who become “Sheng” will have the perfect skill of listening. “Listening” also reflects a kind of virtue. Stand on this point, “Sheng” will have a perfect virtue about listening which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heng” , but also embodies in holiness. “Sheng” as a kind of ideal personality which has the valuable, so listening becomes a kind of value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Sheng”. The constant pursuit and efforts to make the people reflects different realms of personality in “Listening”. To reach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people say, all the world will be object to listen to, people should listen the world firstly, basic on the justice, trust a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get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is is also the way to reach the “Sheng” through the listening.
Keywords: Listening; Sheng; Pre-Qin; Ideal Personal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