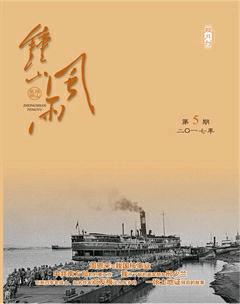周恩来与我国核事业
吴跃农
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标志,我国核事业开始快速发展,不断走向成功,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运载导弹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电站建成,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和国力,这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革命英雄浪漫气概淋漓尽致的展现,更是周恩来务实谋划、全盘部署、亲抓核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有力推动核事业创建和大发展的结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核工业、研制原子弹任务,周恩来在核科技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恩来的感召力
周恩来在西柏坡时就设法鼎力支持钱三强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1949年初,钱三强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资上困难很大。
1949年3月18日,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电,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任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为副团长,特意点名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为团员。
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制造中型回旋加速器所需要的电磁铁及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从这件事可见周恩来对发展我国核事业的决心坚定果断,也表明周恩来慧眼识才,十分了解研制原子弹的人才是中国科学家——钱三强们。
而科学家也为周恩来的眼界、胸襟所折服。当钱三强还在法国留学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革命活动的事迹,他从那时就对周恩来产生了钦佩和景仰之情。钱三强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北平解放后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向各界人士作形势报告,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中肯,手无片纸,侃侃而谈三四个小时,给钱三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十分重视国家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机制上予以保证和促进。为此,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任命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随后接管了旧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以及旧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以此为基础,1950年5月19日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组建起来了。
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待遇和良好科研环境,为着理想和信念,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
1950年赵忠尧、朱光亚、邓稼先回国;1951年张佩林、杨承宗回国。之后,1955年至1965年,有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核物理学家李整武、粒子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林、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实验物理学家张文裕陆续回国。
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彈、氢弹元勋,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的邓稼先以及何泽慧、赵忠尧、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十余位顶尖核科学家。
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人才是关键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地质资源等情况,仔细了解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
周恩来告诉他们,毛泽东、党中央将要开会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请做好汇报准备,主要汇报三项内容:一是关于我国近年来原子能科学的准备情况;二是我国科学家所了解的国外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情况;三是我国要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增强感性认识,到时还要请李四光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来进行探矿模拟表演。
周恩来对发展核事业的关键点把握得十分精准,铀矿的普查和勘探是最基本的,这是发展原子能的物质基础、必要条件,因此,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意见有着重要参考意义。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只有在李四光那儿得到基本可行的答案后,才有可能落实。
这天西花厅下午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他和科学家的谈话情况,就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参加人员和时间以及会议开法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告知可在15日下午3时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信中特别强调说:“李四光有午休习惯,晚上开会李四光身体吃不消,因此三点后开会较适宜,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会上,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
会议当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决定对高等院校的教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卫生部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可以再略予提高,最高者可以超过行政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还可以提高,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主席。对于其中提高工资后家庭生活仍有困难者,可以再给予补助。
在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后,周恩来问钱三强: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干部的培养?比方说,明年就能用上。钱三强等建议集中核物理方面的人才在北京大学创建技术物理系。
周恩来支持了这个建议,对于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等尖端科技人才,周恩来视为宝中之宝,倍加珍爱和关怀。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恩来提出要使懂原子能的专家归队,发挥其特长。
为此,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创办与核工业有关的科系或专业,并点名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上海复旦大学的卢鹤绂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同时,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专业。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到200名。endprint
1958年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又分别开办了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对培养我国原子科学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了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干部的中心。
周恩来还问计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表示,研制尖端核武器,一是要有尖端的人才,要成龙配套,二是要进口一些尖端的资料设备,三是要舍得花大钱。周恩来表示,一是要发挥好现有科学家的作用,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二是要以老带新,科学家要培养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三是要号召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为此,周恩来亲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带着留学生名册找到科学院干部局郁文,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中,挑选一些适合转方向的留学生转到原子能有关专业学习。最后选定了300余名,他们后来都在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反应堆、核化学和化工、铀矿地质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培养自己的科技工作者队伍
1956年4月和1958年9月,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的两个文件,调配相关人员充实到原子能科研和核工业开发建设的队伍中。他还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职工或划拨单位。
与此相应,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有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1956年5月29日,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凝聚人才的方案。
之后,聂荣臻将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授权聂荣臻与各部门商调需要的人才。任新民、屠守纲、梁守春、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当年还分配了100余名大学生进入导弹研究院,随后又有蔡金海、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调入,组成了以钱学森为领队的中国发展导弹的第一个技术骨干队伍。当年10月,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院长。
在争取苏联援助时,为了谈判人员的职阶对等和打破苏联谈判的障碍,周恩来向中央军委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建议,国务院新建统管原子能事业的专门部委。同时科学院系统为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吴有训分别为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大发展阶段。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我国的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些高端科研机构的成立和运行,就是为了大力引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和核军事工业的发展。
有了专业技术组织,有了相关管理部门,还必须有领军型專业人员。周恩来说:“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人才。”
周恩来对相关人员的调配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祚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
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
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周恩来想了许多办法,国家也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从国内增派留学生学习核物理专业,到1959年,全国发展到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27所。二机部也从1958年起开始筹办大学,还筹办了一批中专、技校,大量培养新生力量。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二机部又多次派科技人员到苏联进修、实习、参观考察,还派出140余名高中级科研人员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中了解、学习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这些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有关学科的带头人。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基本上满足了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需。
在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下,1958年夏,反应堆和加速回旋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
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
懂知识分子的人民好总理
周恩来常常教育周围的干部要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应视科学家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还要在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他们。
1956年元月,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因为“知识分子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56年6月间,也就是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之后,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提高,其中教授、研究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几,最高工资由原来的253元提到345元。1956年7月,国务院还转发了相关部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及这个文件的《通知》,提出了对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明确意见和措施。endprint
知识分子待遇的落实,使他们在工作上产生巨大的动力。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整个原子弹研制、试验系统工程“龙头”的三次方,更为艰难的氢弹的理论设计是更为复杂的整个氢弹研制、试验系统工程“龙头”的三次方。邓稼先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总体设计后,1963年转入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周恩来最清楚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他指示二机部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实验的关系。1965年2月,二机部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立即得到周恩来的首肯。
后来,正是由于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使氢弹设计方案成功并付之试验。
周恩来在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态度。特别是在那个“文革”动乱的特殊年代,他出面全力保护知识分子。1966年9月,二机部一批专家被抄家,家属受株连,引起专家们的不安,当年国庆节,周恩来安排钱学森、邓稼先等6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登上天安门观礼,以此宣布科学家在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科学家受冲击的危险在增大,然而,周恩来总是想尽办法,在最大范围内给予有效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会议,为了钱学森等一批知识分子能排除干扰干好工作,他宣布,七机部“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杨)是政治保障,他(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周恩来本人知识渊博,但他十分重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在抓尖端核技术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弄懂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不厌其详地听取科学家对一些技术难点的讲解。
在“两弹一星”事业发展时,每次开專委会,周恩来总是嘱咐多找一些专业人士参加,以便全面听取各种有益意见建议,他还不时提出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他尤其重视不同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或有道理的反对意见,而又一时验证不了难下结论,他都不急着拍板,而是暂时休会,要求大家回去把问题搞清楚后再复会讨论决定。只要听到不同意见,哪怕这个意见来自普通科技人员,他也会立即加以考虑,用来对照研究自己原来的决定,他曾不止一次当众宣称:“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
周恩来这种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使科学家们非常感动。当他们听到总理把不同的意见巧妙地集中起来,分析比较,得出比争论各方更为高明的结论时,对周恩来更加由衷敬佩。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依靠自己的科学家队伍,建成了完整配套的核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一次又一次成功,攻击性核潜艇胜利下水,卫星上天高奏《东方红》,导弹发射呼啸天宇,我国建成了一支积极有效的核防卫力量。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