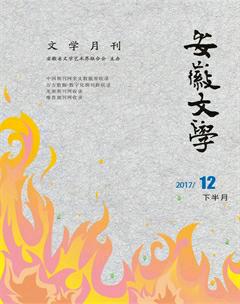钟求是长篇小说《零年代》人物刻画刍议
吴延生
摘 要: 城乡二元结构小说始于“五四”时期,兴盛于当代,因为农耕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城市文明的冲击。很多作家关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凸显的矛盾,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温州作家钟求是创作的长篇小说《零年代》,却以特殊的视角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通过刻画生动的精准的形象加以研究,在挖掘文本价值的同时以彰显其社会价值。
关键词:当代小说 《零年代》 人物形象分析
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的小说创作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肇始于“五四”后的乡土田园小说,激活了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创作激情,首先带来他们审美视阈的拓宽,如老舍以幽默的笔墨,在北方都市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建构自己的市民艺术世界;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目光将都市与乡野加以比较,以古朴之风反衬出都市的堕落。而到四十年代,则有赵树理、孙犁等作家们继承和发展了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在小说主题深度的开掘上、抒情笔墨的运用上,彰显出大家风范。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转型的变化、城乡矛盾的凸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小说创作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如陕西的贾平凹;贵州的何士光;山东的张炜;河北的铁凝;河南的喬典运;江苏的汪曾祺、高晓声、赵本夫,等等,他们或从人际关系层面,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或从精神层面解剖人性的弱点;或以土地情结层面,关注在农业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城市文明的撞击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对当下诸多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追问。而来自浙江温州的钟求是,在创作了如《谢雨的大学》、《未完成的夏天》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之后,在2009年9月,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零年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人文原创”系列之一)。他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小说创作的路数下,没有被束缚住,而是标新立异,他没有像吴组缃在193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菉竹山房》,隐喻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一次张望;也没有像施蛰存在193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阳》,隐喻主人公遭遇都市文明后向乡村文明的退缩。如果说这些小说的主题追求的是人的发现,那么钟求是的《零年代》则是在新的城、乡矛盾异常激烈的时代,描写被社会挤压到最底层的小人物拥有的对人的尊严、对生命的尊重的“新质”的追求。正因如此,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温州市委宣传部和温州市文联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当年十月份在京举行,雷达、吴义勤、李建军、贺绍俊等一批专家、学者到会,给予了《零年代》以较高的评价,可见其影响。笔者从人物形象刻画的视角细加寻绎,解读其价值。
二、生动的人物形象
受主题思想制约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如何生动准确,则成为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方面作者要把他对自然的观照、人生的感悟、社会的理解,渗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借以揭示主题,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读者在小说文本阅读过程中,通过审美期待,在检阅人物的生活轨迹,纵向地透视人物的成长历史;通过审美判断,去考察人物的生活逻辑,横向地直射人物性格的发展特征。这就决定了作家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读者负责,担当起塑造人物的大任,如此才能不愧作者的天职,赢得读者的青睐。而作家认识生活的精度和把握生活的深度,是塑造人物、刻画人物的前提。如第一部分所言,钟求是挂职来到山村,瞄上了绝大部分人都已下山,只有老夫妇和小狗的破败的小山村。对此,作者进行体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文本中的林心村,以及吸引来林心村的人物。“对真正伟大的小说家来讲,无论是以悲剧的方式叙述,还是以喜剧的方式反讽,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1]8钟求是并不是伟大的小说家,但肯定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怀着敬意写出他们在人生旅程中的纯朴善良,即使在人生的困境和不幸中,他们也没有空洞的牢骚,没有恶意的诅咒,没有苦涩的泪水,有的却是坚韧、奋斗。“爱是文学的根本。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把对人和生活的爱,当做一种稳定的心情态度和世界观;他们不仅自己心疼自己笔下的人物,而且能让读者也喜爱甚至心疼他们。”[1]142作者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刻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赵伏文曾是城里宗教局的小公务员,他热情、善良、固执,性格中有点“迂”。小说开头诗意地写到他和林心好上了,当他得知林心的生母可能在巴梨镇时,他独自去了巴梨,并且通过文字慢慢想象出林心被遗弃的过程。为了寻找,赵伏文带着林心爬到山中的一个叫“林心”的村子,在这里他们有了故事。之后,林心去医院证实怀孕了。赵伏文坚持“拿掉”。可到了医院后,林心却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在忙着成婚的间隙,因为阴差阳错的故事,林心拒绝和赵伏文成婚。赵伏文每天只是远远地站到马路对面看看林心的身影,不敢上前解释,显出他的“迂”。再后来林心死了,赵伏文丢弃城里的工作,怀着救赎的心理,带着林心的“纸灰”去了他们感情的原点——林心村,又一次显出他的“迂”。在村子里,遇到了在城里打工被骗回山上生孩子的王云琴。后来,王云琴又去了城里寻找孩子的父亲。赵伏文热情地看管并抚养清明这孩子。在和王云琴结婚并发展出几个孩子后,乃至到城里生活,小说没有显现出赵伏文阳刚的一面,特别是把四个孩子送人的细节更多地表现他的固执乃至“迂”,显然也还有生存的无奈与无助,直至又回到山上,走向生活的终点,无不表现其“迂”。赵伏文受过高等教育,传统文化的规约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规避。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他选择了后者。对他的刻画,分明有作者的“天真”烙在人物身上的痕迹。作者用意在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的天真阀,我们对其认知一向是与人的精神、思想、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被物质生活所决定着,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精神领域有那么一点点让人愉悦的天真之气。[2]”
活在作品上半部分的小学音乐教师林心,是个专情偏执的女孩,性格中有些“疑”。她小时候被母亲遗弃,带来她的任性和多疑。和赵伏文恋爱后,她是个专情者。她怀孕后,在医院准备流产,瞬间又决然要保护孩子,并且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这同样是她专情的表现。实际上体现出作者对生命关注的理念。楠溪江游览,林心和赵伏文从竹排上掉下水,赵伏文那不经意的一脚踹在了林心的肚子上,让林心偏执地认为他是有意为之。她的多疑之心破灭了彼此的爱情。后来,轻信父母的话,去了医院,被拿掉了孩子。从而断绝了她所有的希望。最后她任性的悄然飘出窗外。做为小学教师,林心也应该有良好的修养。然内心世界其实是封闭的,一旦情感上找到对接点,便会撞出火花;可一旦她认为别人有意要熄灭这火花,这个情感丰富的女性便会极端地走向“单纯”,以致采取极端的方式“封闭”自我。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出现的王云琴,是个纯朴善良的打工妹,性格中有些“傻”。她是林心村的姑娘,后来在城里被一位叫方哥的人骗了,无奈地回到村里,生下一个唇裂的孩子。她把孩子托付给赵伏文又独自去城里寻找骗她的人。三个月后,她回到了山里终于和赵伏文结婚了。之后,主要写了她的生育史以及母性的善良。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全家到城里后,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进了KTV,赚取辛苦钱;为了养家糊口,她干起了代人受孕的事,结果上了当,还落下了病根。她傻得让人心酸!后来在丈夫的劝说下,她同意把四个孩子送人。她傻得让人心疼!最后带着病体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山上,过上了起点的生活。她傻得让人心焦!云琴这个山村姑娘,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显得朴实、天真、单纯,这是她“傻”的根源。
在人物刻画中,作者有意识地在比衬层面凸显人物、鲜活人物。“在小说世界,人物既是有着独立性格的个体,也是在文化中形成的个体。他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表现着他的性格,他行事的逻辑是由文化提供和决定的,他的性格也是在与群体的对照中映现出来的。”[3]这一点,作者做得非常好。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击碎人的心灵。他们用自己的屈辱和心酸行走在社会底层的狭小的空间,一步步迈过生活的困难,顶过生存的艱难,维护生命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作者把人写“活”了。“人对于人是最有兴趣的。人们之所以那么着了迷似地阅读小说,主要是被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吸引。”[4]《零年代》的创作,正说明了小说中的人物必须富有生气,必须开出生命之花,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而人的生命和灵魂,具体地说总是表现为性格。只有写出性格来,人物形象才是栩栩如生的。
三、结语
《零年代》以全新的视野再现了现代城市文明进程背景下的乡村文化面临的考验。作者采取了冷静的审视态度与反思现代文明内涵的视角,站在时代的前沿,以诗性的抒情、理性的思考、哲学层面的价值观演绎,建构文学对社会大任的担当,引发人们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生态、城乡和谐等问题的忧患之思。在人物设计上,没有描写一般的打工族,而是塑造了社会底层不被人看重的另类小人物。“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轻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把人当做人看待。现代意识的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积极创造条件。”[5]而作者本着“现代意识的核心内容”,对这样的底层人物不是人生的怜悯,而是出于人性的敬重,赋予一种人文关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他通过实践诠释其追求。因而,他不是感性化地去表现人物,而是诗意地来呈现人物,这就大大出乎同类题材之上。所以,它是近年来难得出现的一部好作品。“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上的薄弱之处,扬长避短也是正常不过的反应,不应该成为指责一个作家的理由。可一个作家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显示的功力却无法不让人将之纳入对其艺术造诣的整体评价。”[6]虽然有些遗憾,但并不影响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肯定。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8,142
[2] 岳雯.天真与世故的较量[J].天津:文学自由谈,2010(4).
[3] 钱雯.小说文化学理论与实践[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2.
[4] 裴显生.写作学新稿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498.
[5] 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62.姚晓雷. 世纪末的文学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