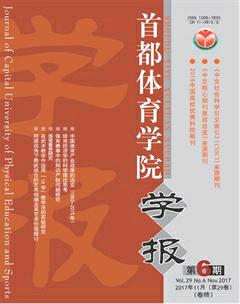武舞相融中“剑”的舞台艺术探寻
余梦露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影像资料法、对比法,以武术和舞蹈的融合作为切入点,对以“剑”为道具和创作元素的舞蹈作品进行分析,以此探索从“武之剑”到“剑之舞”的舞台艺术价值。认为: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下和现代多元的舞台呈现语境中,剑的舞化过程就是对舞剑过程的审美再造过程。探讨“剑”在舞蹈表达中叙事性的功能转变,“剑”在舞台呈现中的表意性艺术传达,“剑”在艺术表现中的传统意象,为武术与舞蹈的嫁接和融合寻找更多的途径和可能性。
关键词:武术;剑;舞蹈;艺术传达;舞台呈现;武术表演;舞台艺术
中图分类号:G 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6-0525-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mage data and comparison, taking the combin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danc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dance works which take "sword" as props and creative elements are analyzed, so as to explore the stage art value from the "Wu sword" to "sword dance". It concludes that under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odern multi stage presentation context, dance process is to process the sword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narrativ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sword" in the dance expressi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sword" in the stage present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sword" in artistic expression, so as to find out more way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grafting and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 and dance.
Keywords: martial art;sword;dance;artistic transmission;stage presentation;martial art performance;stage art
武術与舞蹈伴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相互吸收、借鉴和促进。在众多舞蹈风格种类中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气、神”韵味的便是武术中对“剑”的提炼、吸收与融合。剑的武、舞属性都离不开人体运动的本质媒介,剑在武与舞的千年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属性与表达功能;因此“剑”作为传统器具的代表,它的文化价值已经超出武术与舞蹈本身的核心价值,它以具象的道具形式,来强化身体所承担的武术与舞蹈的表达功能,最终结合武术与舞蹈的特征,造就出不同表达形态下的剑器语境。 在当下艺术创作的多元时代,舞蹈艺术的创作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功的剑舞佳作,例如《醉剑》《垓下雄魂》《霸王别姬》《大漠孤行》《梅·砺香》等都是我们探索“剑”的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武术和舞蹈的艺术融合作为文章切入点,运用影像资料法、对比法对以上经典舞蹈作品进行归纳与分析,以此来探索从“武之剑”到“剑之舞”的舞台艺术价值。
1 “武之剑”的历史渊源
“武之剑”就是武术范畴概念中的剑。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武术的主要功能是技击,随着时代的变迁,武术也衍生出了健身、娱乐、教育功能[1]。“武之剑”实质上就是以技击为出发点和存在意义的剑器属性,对“武之剑”的探究也就是一种对于武术中“剑”的身体运用的探讨与研究。武术作为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印证出它的文化根基”[2]和传统哲学思想。“武”代表着勇者无畏、仁者无敌的胸襟与气概,它以身为径,以技为形,以道为旨,以“径”与“形”的相合,明悟造化为一种“武道”的文化精神。 “剑”作为中华民族的典型传统器具,在当今已不具备攻击性的实用功能,但在久远的上古时期,舞剑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表演形式,而且承担着防御、制胜的格斗功能,它与铠、矛、戟形成古代典型的兵器形式;因此,“剑”的起源其实伴随着“武”的发展自行演变而来,由此不难看出,剑的早期功用是伴随着古代的部落征战而形成的。据《黄帝本纪》《管子》等记载,远在我国的黄帝、蚩尤时期,就发明了剑器,可见其是剑的雏形[3]。而剑作为一种防身自卫的工具兴起于商代,后来随着春秋战国的战乱,“剑”无论在割据战争,还是在自我防御的功能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它传统的历史地位。
“武”与“舞”自古有之,并在各自的文化价值传承中大放异彩。此二者虽属各不相同的技艺门类,但它们之间一直有着紧密联系。“武舞同源”,这早已为史学家们所证实。从 《山堂肆考征集十五舞者》《山海经·海外西经》《史记乐书》中的记载都不难看出武舞同生、武舞同源的紧密关系。武术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书中的武术指的是军事技术[4]。而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武术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其自身运用实践的发展,武术从最初的技击格斗转变为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自卫护身的文化形态。武术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武术具象形式的开始,剑作为典型的传统兵器,自然形成了练武形式;因此,魏晋南北朝武术形式的出现,剑的竞技、攻击功能便开始转向了一种传统体育文化形式,随之形成了一种文化属性。武术产生的过程也是武舞交融的过程,《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武舞性质的舞蹈,而这一曲名舞在唐代时传入了日本,现在日本传统乐舞中的《陵王》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武舞。endprint
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技艺”,意指刀、枪、剑、棍的使用技术和方法,这种“技艺”最早根源于狩猎与战争。在武术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习武之人更多的是通过这种行为活动来获得强大的精神修为,并以此来获得武之精髓。在隋唐时期,一种具有组织性的习武团体形成,它的普及性涉及到不同阶层的群体,同时武术还作为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之一,使得“武之剑”的传统概念,在隋唐以后正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形式。
剑作为一种战争防御器具,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被古代文化分解出了另一种艺术形式,即“剑器”。其作为民间习武组织使用的器具形式之一,形成于宋朝,民间练武组织相应出现了“锦标社”“英略社”“角抵社”等武术社团。剑作为典型的武术项目,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从隋唐以后,剑便逐渐脱离了竞技与防御的本质属性,进入到传统武术文化中。剑文化的形成,始终伴随着古代朝代更替、征战的过程,也是在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商品的快速流通,最终形成了当前的武术传统的“剑文化”。当前舞台上剑的表演,是一种去掉武术内涵中的攻击属性,转入一种具有视觉美感的艺术表现方式;因此,舞台上所呈现的剑舞是一种艺术门类下设的呈现手段,无论是舞蹈中的剑,还是武术表演中的剑,都与上述所说的历史脉络中的剑的属性、功能相区别。因此,在现代视野下的剑文化已经作为一种身体运动方式同古代技艺性的攻击目的大相径庭了。例如“闻鸡起舞”的祖逖、“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成”的阮籍、“十五好剑器”的李白,还有诗人杜甫笔下的“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裙底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以上情况表明,作为武技的剑术更趋向健身性、艺术性,日益与体育、文娱活动相结合[5]10-11。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剑术则以“套路为主要形式”,并具有“轻盈敏捷、优美潇洒、气势流畅、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还发展出众多的风格流派等。
2 “剑之舞”的传承与发展
“剑之舞”顾名思义就是指剑器之舞蹈,也就是从舞蹈的角度来研究武术中剑的运动方式、审美方式,最终转化为具有舞蹈属性、以剑为道具的剑器艺术表现形式。“舞”作为“人体动作的艺术” [6],是以人体本身作为物质载体,并经过提炼、组织、美化的人体动作 [7],其本质是表现思想、表达情感 [8]。舞蹈作为人类身心形式的身体反映,其体现出了一种叫做文化身体的媒介,因此作为同一根源下的身体表达形式,“剑”自然具备了进入艺术鉴赏性的文化范畴,即剑法、身法与舞蹈中的路线、韵律具有同质不同形的表现特征;因此,在由“武”进入到“舞”的过程中,自然是一条相互借鉴与传承的捷径。虽说以纯身体的动能追求为存在的武术与以情感意象为存在依托的舞蹈,在社会功能、文化价值、传播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它们有着诸多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个最根本的相同之处,即此二者都是以人的身体为物质媒介和传达方式,而这个最根本的身体媒介又可以使得武与舞之间相互借鉴、吸收、促进和发展。另外,舞与武同样以身体为呈现媒介,但二者的呈现方式各不相同,却又相互关联。舞蹈与武术同样来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实践。“人类曾经以狩猎为生的时代,斗兽舞也是武舞的一种,在周代铜器的猎壶上,在汉代石刻的画像上,还留下了此类斗兽题材的图画。由于表演狩猎跳舞,而有模拟兽类动态的舞蹈形式产生” [9]。由此可见,舞蹈与武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舞蹈在身体语言的诉说中抒发情感、展示生活。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舞蹈便已成为了超越语言的一种交流方式。
因此,由“武之剑”到“剑之舞”的过程中,必然进行了表达规律的方法的转化,也就是由竞技规律的动态模式向视觉美感的身体运动模式的转移,当这种转化进入宫廷之后,便形成了当前的文舞和武舞、健舞和软舞。这些不同类型的舞蹈称谓,都是相似属性的文化形式相互沟通与借鉴的产物,因此,舞蹈这门艺术门类之所以区分出不同的艺術风格、审美风格,其实质是文化门类多样性之后的再生产。而“剑之舞”所言的剑形成于舞蹈的过程中,伴随着舞蹈艺术门类多样化的过程。在两汉之际,刀剑既是武器,又是舞蹈表演时所用的道具和舞具,特别是对剑的使用更为普遍 [10]。伴随着逐渐成熟的汉代舞蹈,在形式、种类、风格等方面的定型,剑在此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舞蹈道具的方式,进入到舞蹈艺术领域。尽管汉朝之前也有执剑而舞的情况;但由于武舞不分家的粘合性,汉朝之前的传统舞蹈与武术健身并未形成鲜明的专业界限,因此,才有舞武不分家的历史现象。
汉朝作为舞蹈艺术第一个爆发时期,舞蹈便脱离了传统武术竞技中的身法与审美方式,进而进入到社会思潮所影响的汉代艺术的审美形式。从汉朝开始,剑逐渐退出了军事舞台,但在民间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11]。“剑,既是具有某种高雅气度的标志,又可防身御敌。执剑而舞是人们寄情抒怀的一种手段。《剑舞》有舞单、双剑和独舞、双人舞之分,山东汉画像石上有二人对刺的场面。四川彭县汉画像砖上,也有一人抬脚踏鼓、执双剑而舞的形象” [12]。剑作为古代人们防身、作战的工具及身份的象征,产生于商朝晚期,剑身及剑鞘的不同规格也分别具有不同含义。“剑”本身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具有不同功能,拥有攻和防的特质,以及大众审美与娱乐需求。剑的使用逐渐由严谨的剑术发展为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套路,拔剑起舞的历史在唐朝便已有记载;但为数不多的史料也显示出剑舞的存在一直未形成系统,只是零星出现在浩瀚的历史中,直至戏曲发展旺盛的清朝,也预示着剑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代表性道具,而剑术的发展带给舞蹈的灵感从未停止向前。由此可见,剑舞开始脱离技击手段,而逐渐转化成为一种艺术化的身体与道具形式,并且最终在唐朝的剑舞系列中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剑舞表演艺术家。《公孙大娘舞剑器》就是唐代剑舞的最高典范,也是古代剑舞艺术舞台表现形式的巅峰,它标志着剑舞以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脱离于武术的表达范畴,第一次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独立的舞蹈形式。可以说从唐朝开始,剑已经由身体表达的共性特征的交叉模糊状态逐渐形成了具有艺术表达特色的“剑之舞”。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剑舞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梅兰芳创造的《霸王别姬》中的双剑舞,使得剑舞艺术得到改造,为剑舞艺术的发展独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13]。endprint
3 武舞相融中“剑”的舞台呈现
武术与舞蹈同作为身体运动方式的一种,通过节奏、道具,以及观赏价值等相区别,而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武术中的精华逐渐被拥有自身发展轨迹的舞蹈所采用。这种采用就是在具有武术元素的呈现方式中融合舞蹈所独具的艺术审美,以武术的形神劲律和器械道具为艺术转化支点,进而“再造”和创作出具有明确舞蹈语言和表演特征的舞台化艺术形式。舞台艺术作为现代行为下人为塑造的一个密闭空间,它通过灯光、服装、道具等舞台要素的结构、重构与解构,形成一种可被抽象化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具有典型性、抽象性,同时具有夸张且浓重的视觉效果,将舞台这一观赏视觉空间演变成了具有虚拟性的真实空间,最终将舞台的效果升华成一种艺术的表现范畴。而艺术是文化的高级表现形式。剑术向更高级发展,增加文化含量,从而使其艺术得到升华 [5]147。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剑在诗、书、舞、画、乐等众多艺术形式中都有表现,而这些表现也使得剑脱离了其本质之技击特征,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艺术形式。此艺术形式的最终形成便是武舞相融中剑的“再造”和创作,也是对武术进行合理、有机的舞化,而舞化的结果与最终的舞台表演相结合就实现了武术的舞化呈现。舞化后的武术在舞台上的表现依然具有武术带来的观感上的“精、气、神”,而且更多了些许韵味,因而也归于一个已有明确划分的舞种。
剑的舞化过程其实就是对舞剑过程的审美再造过程。当今,以剑为道具编创的作品在舞台上有很多,有关武术题材的舞蹈作品层出不穷,这也更加明确了武舞同源的历史语境;因此,在摄取武术中剑的相关资料,以及行业标准的前提下,同时结合舞蹈中美的属性的传达,最终创作出一大批成功的剑舞案例。诸如古典舞《醉剑》《大漠孤行》《垓下雄魂》《霸王别姬》《梅·砺香》等舞武相融的作品,都是我们探索“剑”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通过剑之舞化的研究提升舞蹈艺术作品的创作手段与能力。剑作为武术中的一种运动形式,“剑术”特点包括身法轻快潇洒,剑路灵活多变,剑法丰富流畅,有“剑似飞凤”之美誉。无论是训练,还是作品表演,对剑的使用早已被认为是“剑舞”的一种。舞蹈领域研究者对剑舞展开了探索,随之舞台上以剑为道具的舞蹈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为了继续发扬剑舞中的武术精神,当前把对剑与舞融合的探究纳入到以科研教学为主的大学课堂中。由此可见,剑、舞相融背后深远的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
3.1 “剑”在舞蹈表达中叙事性的功能转变
对“剑”的使用曾经体现于现实生活中,当前舞蹈中的“剑”在舞台艺术上主要体现在叙事性。例如张家炎编导的舞蹈作品《醉剑》通过把一位将军的思绪寄托于“剑”,表现其报国无门的悲哀之感。酒与剑在一定时期,成为人物情感发泄之物,而“醉剑”本身便把二者合二为一,借酒浇愁之势拔剑起舞,利用剑的形态特点结合舞蹈特性,在穿、刺、跃、翻、腾中划破时空,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古籍中的场景与角色此时的心境。编导对于题材的选定决定了剑的作用无可比拟。如果选择徒手舞蹈,缺少了能最直接传递信息的工具,其含义反而让人捉摸不透,而“剑”的功能性从古代生活延续至当今的舞台,并没有丢失其存在于生活中的最初功能,因舞中“将军”这个角色的衬托,使得剑在舞蹈中的功能仍然是以杀敌、防御或与文献资料中描述的舞剑为主,其抒情与点题之用是有形的传统遗存,也是剑舞对“剑”历史功能的保留。再如,张建民编导的《垓下雄魂》更是将剑的功能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体现于在虞姬剑舞绝唱之地,把“剑”直接搬上舞台更能使剑舞古今之间相互贯通;其二,为表现楚汉争霸情境,人人佩剑的设定仿佛能透过舞台艺术窥探到舞蹈作品力图表现的战事场面。而剑给舞蹈带来的功能性提升不仅体现在能够模拟舞蹈主题要求的场景,更多的是倾向于为舞蹈本身服务,在叙事功能方面,“剑”本身具有的攻击性胜过大篇幅的身体对人物性格的模糊表达,群舞挥剑更是带来一种徒手无可比拟的气魄,也通过对剑所存在位置与出现时机的安排,依次亮剑,使得意味性较强,不仅延长了肢体所能到达的物理空间,而且明确了人物的身份和心境。这部作品使得“剑”再次成为表现其叙事功能的灵魂,与服饰、情节相匹配的剑在保留其刺杀功能的同时,通过群舞编排也被当作表现人物气魄与性格的道具。这种功能性表达更加倾向于对舞蹈语汇的开发,在舞蹈叙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 “剑”在舞台呈现中的表意性艺术传达
把剑术转化为剑舞,跳出生活走向舞台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剑”在舞台中的呈现带来的观感或许已经剥离了一些传统武术需要达到的对抗性技艺,但对其精华的继承能否足够支撑剑舞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品?艺术性从何体现,又该从何处追寻?舞蹈作品《梅·砺香》与《垓下雄魂》相比,这部作品更具有舞蹈特殊的艺术性,其拓展了“剑”这一道具带来的表意功能,用剑突出表现人们对“梅”的赞美,这份寓意已突破一个实体框架,剑不再是一把作为人们展现威猛善战与防卫需求的实体,而成为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和象征。作品 中鲜艳的红色剑穗便是对梅花的艺术性转化,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与再造,也帮助群舞在整体构图中形成一个可供想象的艺术空间。在舞者手中翩翩飞舞的剑穗来自生活却早已超越了生活对它的限定,这不仅是舞蹈的价值,而且是剑舞艺术性的体现。整部作品对“梅”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绽放的表现,又蕴含着剑舞的艺术性转化。“剑”在这类舞蹈作品中的艺术性表意作用,充分允许舞蹈赋予它更多样化的气质。这也开拓了剑舞的发展态势,不局限于物质本体表达,而是以道具的身份随着舞蹈的艺术需求,转化为表意工具,在其艺术性增加的同时也带给作品本身更多滋养。
3.3 “剑”在艺术表现中的传统意象
剑舞作为完成舞台表演所需要的技术,经历了一系列蜕变。古典舞本身融合了武术、戏曲运动特征与审美风范,这使得剑舞归于其中成为必然。剑舞对武舞相融的诠释完全符合中国化审美意象的追求,这种意象是作品形象,是一种传统道具在舞台上的象征功能。以意象为旨,以传统为根,通过剑之舞化的过程,将剑所潜在的审美意境通过完整作品充分地表达出来,最终形成了舞台化、舞蹈表演范畴下的剑的审美意象。而较之融合了芭蕾元素的古典舞训练体系,剑舞对剑法的追求更能完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存,握剑而立、中正挺拔、人剑合一,当这一情景出现时,传统意义的龙的传人的精神形象便得到充分体现。在这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意象的继承和发展也切实地体现出了历史文化延续的意义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剑舞最具特色与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东方舞台气质。从运动原理角度看,如要把剑舞好,必须由中段发力至末梢才有足够能量使规格大小不一的剑灵活运转,而中国舞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必须秉持自身特色,无论是武术套路、太极,还是剑舞,都要求气沉丹田、以圆型运动轨迹为主,节节传导发力。而剑舞的运动特征使得舞者必须遵循规则,以富有中国味道的运动形式在舞台上完成好每一个舞步,即使是相同的动作,剑舞与徒手而舞也截然不同,何况剑舞自身的刺剑、劈剑、挂剑、撩剑、架剑、点剑等剑法各具特色,使得剑舞极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并且在与芭蕾、现代舞等同台演出时能够凸显中国特有的东方气质。
4 结束语
剑舞作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我国最具特色的舞蹈之一,应把握剑舞的运动规律与艺术特征,并且逐渐形成更加完善的训练体系与可作为编创素材的动作语汇。开发更多以剑舞为元素的舞蹈作品,促进舞蹈融入更多可被舞化的元素,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舞蹈展示出来。
参考文献:
[1] 胡平清.武术教育的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6:2.
[2] 肖亚康.武以载道:武学与道家思想关系探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2.
[3] 邢金善.中国传统剑文化考论[J].南方文物,2010(3):93.
[4] 李北达.中国武术理论与舞蹈实践: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材丛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9.
[5] 董有为.剑术[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
[6] 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1.
[7] 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率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1.
[8] 袁禾.舞蹈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27.
[9] 常任侠.中国舞蹈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4.
[10] 季伟.汉代乐舞白戏考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70.
[11] 张军.中国古典舞剑舞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3.
[12] 王江萍.中国古典舞蹈风貌与发展流变[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84.
[13] 李英,杨愛华,吕宏,等. “剑舞”考论[J]. 体育文化导刊,2004(10):8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