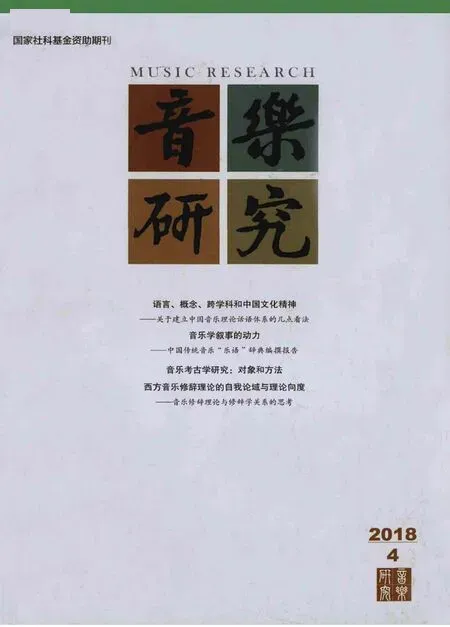表述·认知·语境
——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研究
文◎朱腾蛟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威廉·福利(William A.Foley)在围绕观念与语言的谈论中,将两者总结为“物体”与“容器”的关系。他认为,交流在于找到恰当的词语表述某种观念,就如同为“物体”(观念)找到“容器”(词语),沿着导管(写),或通过空间(说),把这个盛满的“容器”送至听者,听者要把这个“物体”(观念)从这个“容器”(词语)里拿出来。①William Foley.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195.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如何找寻合适的“容器”,以及听者能否从“容器”中顺利地取出“物体”,是交流之关键所在。
在“物体”(观念)和“容器”(词语)之间,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学)研究者似乎都面临着 “挑战”。“如何感受音乐”,又“如何言说音乐”,可以说是所有音乐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其间存在着的某种悖论,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将其称之为“语言中心的困境”(linguocentric predicament)。
笔者在对民间歌唱表演的研究中也曾遭遇同样的问题,转瞬即逝的“声音”、内化于身体而难以观察的歌唱行为、缺乏准确的表述方式,均成为民间歌唱表演的描写与研究中的“难题”。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lan Merriam)曾指出“以往的研究对于声乐技巧的探讨不像对器乐技巧的探讨那么频繁……声乐技巧确实为区分音乐风格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标准,但是问题在于寻找更精确的习语或更精确的测量方式”②Alan 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108.。而科妮莉亚·菲尔斯(Cornelia Fales)则认为,“我们从所有的音乐现象中都能听到音色,它提供给我们大量有关声源与发声位置的信息,但是我们却没有语言去描述它,也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用隐喻或类比的方法去表述音色提供给我们的感受”③Cornelia Fales.“The Paradox of Timbre.”Ethnomusicology,Vol.46,No.1,2002.p.56。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寻找对于歌唱表演的精确的描述性习语,还是借以科学的测量手段进行的量化研究,似乎都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无论是“感受音乐”还是“言说音乐”,在某种层面上都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上述问题也绝非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所“独自面对”的“挑战”。那么,音乐的实践者(局内人)又是如何感受和表述音乐的呢?他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语言中心的困境”?这一问题指引着笔者将目光转向局内人的表述,试图在对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的研究中有所启示。
一、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的多样性
基于上述思考,并在参与课题的工作中,笔者对于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工作,共梳理出四百余条相关习语,④本文所收集习语,主要依据自己的田野考察,以及所有卷本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还包括相关辞书、专著、文集与期刊论文等。主要涉及发声方法(真声、假声、气息、共鸣腔的运用等)、润腔手法(颤音、滑音、倚音等)、表演中的互动方式(对唱方式、多声部歌唱中的互动关系、帮腔、歌唱与乐队的合作形式等)以及板式唱法(起板、收腔等)等方面。本文主要聚焦于与表演者的歌唱实践直接相关的习语,而曲体结构、音调旋法、宫调、唱词等其他形态方面的习语暂不作为本文论述的范畴。同时,笔者在研究中以习语的原生性、口传性与地方性为原则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通过这些习语切入民间歌唱表演者的音乐认知、审美观念与表述逻辑。
通过对于上述几个方面习语的初步梳理,笔者有以下思考:
1.局内人的歌唱分类观
在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中,存在许多成对或成组的习语,这些习语所反映的是歌唱表演者的歌唱分类观念。例如,发声方法习语中的“大本腔/二本腔”、“苍音/尖音”(花儿)、“老音/夹音”(丝弦老调)、“开口音/闭口音”(陇南影子腔)、“阳面/阴面”(苏州弹词)、“本工嗓/背工嗓”(河南坠子)、“柔口/刚口”(甘肃小曲戏、兰州鼓子)、“阔口/窄口/泼口”(扬州清曲)、“直磨/直作”(景颇族的载瓦山歌)、“茨玛/茨惹”(红河哈尼族山歌)、“上相格/上相作”(阿昌族民歌)等;润腔习语中的“干疙瘩/水疙瘩”(京剧)、“颠腭儿/咳腔儿”(凌源影调戏);帮腔习语中的“头杠/二杠”(都湖高腔)、“接口帮/复韵帮”(东河戏)、“搬尖声/打莽筒”(南溪号子);板式唱法习语中的“闪板”(弱拍起唱)/“顶板”(强拍起唱)(豫剧)等。这些都是一系列成对或成组的习语。
局内人对于歌唱进行分类的维度,既有基于音色差异的分类(如苍音/尖音),也有对表演中身体状态的区分(如颠腭儿/咳腔儿)。就其类型划分的目的而言,也各有不同,如广东粤剧中以大喉、平喉、子喉、苦喉等不同唱法塑造性别、性格、年龄各异的角色;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苏州评弹以“火功”和“静功”(或“阴功”)分别代表激烈火爆与细腻含蓄的两种说表风格;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5页。土家族的南溪号子以“搬尖声”与“打莽筒”区分高音区与低音区的帮腔形式;⑦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0页。江西都湖高腔以“头杠”和“二杠”区分高腔帮唱中鼓师一人的帮唱与其他乐手的集体帮唱;⑧《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420页。湘西苗族山歌中的“索补加”(高腔)与“索补斗”(平腔)分别对应着山野与寨内两个不同场合的歌唱风格;⑨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内部资料),第137页。而甘肃小曲戏的“柔口”与“刚口”则分别用于演唱才子佳人与英雄豪杰两个不同主题的内容。
对于不同歌唱方法的类型划分,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尝试。但实际上,从上述习语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基于歌唱的音色与身体状态的不同,还是出于角色、音高、内容、场合等方面的需求,局内人都是有意识地区分不同唱法,并加以运用,这是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多样的、地方性的分类维度都是我们在歌唱的类型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我们在研究中表述不同的唱法时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真声、假声、真假声转换、滑音、颤音等词汇。笔者曾对不同地区的假声唱法进行比较,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通过听觉和歌唱实践意识到,同样是假声的发声原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的假声在音色和发声上存在不少差异,假声唱法内部也包含多种类型,但笔者却一直苦于不知如何用语言准确地表述这其间的差异。通过梳理这些民间的习语,笔者发现实际上在这些习语中就包含了对于这样一些单一唱法内部差异的描述习语,如真声包含了本音、炸音、霸腔、膛音、箭音、横喉声、内喉声、将音、沙喉、宽音、沉音等不同类型,假声则包含尖音、窄咙、细嗓、犟音、顶音、夹音、子音等称谓。这些不同的习语指向的其实就是彼此间音色、共鸣腔、发声方法的差异,例如“膛音”与“炸音”同为真声的发声方法,前者强调运用丹田之气与胸腔共鸣,声音低沉洪亮,后者则强调爆发力,粗犷而带沙哑的声音。因而,回归唱法的“局内表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细节入手对唱法本身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能让我们对这些唱法的“再表述”更为准确,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比较”的研究视野。
2.歌唱习语的使用范畴
从笔者梳理的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的使用范畴上来看,主要有个体表演者、乐种、地方和跨地域四个层次。(1)个体表演者的唱法习语,如京剧老生谭鑫培的嗓音被誉为“云遮月”,即初唱时仿佛力不从心,略带沙音,嗓音好似蒙上层层翳障,宛如月初被云遮,但愈唱则愈为响润,云散则月光皎洁,让人听了有豁然开朗之感。“云遮月”不仅成为“谭派”之精髓所在,也成为行内所推崇的一种嗓子,而余叔岩、杨宝森的嗓音也曾被形容为“云遮月”。这类习语还有马师曾(粤剧)的“乞儿喉”、陆云飞(粤剧)的“豆坭腔”、徐云志(苏州评弹)的“糯米腔”、祁莲芳(苏州评弹)的“迷魂调”、郑城界(正字戏)的“瓮仔声”、畅金山(秦腔)的“闹音”、靳伟(秦腔)的“敏腔”、杨森(彝剧)的“绒音”等。(2)单一乐种中使用的特殊习语,往往体现了这一乐种的某一典型特征,如蒙古族长调的“诺古拉”、纳西族“窝热热”的“则流客”、鄂西土家族山歌的“打喔火”、青海回族宴席曲的“打颤”、潮剧的“痰火声”、湖北兴山山歌的“闪音”等。(3)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乐种间共享的习语,在体现地方性歌唱风格特征的同时,也反映了不同乐种间的相互吸收与影响。如湖南地区的长沙花鼓戏、辰河戏高腔、武陵戏、常德花鼓戏和阳戏均是将真假声转换的唱法称之为“金线吊葫芦”,即以金线吊葫芦这种植物的形状比喻歌唱中真假声的快速转换,不露断痕。⑩《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1981年版,第21、764、924、1569、1846页。(4)有的习语则是被不同地域的乐种相互吸收,如“疙瘩腔”就在评剧、拉场戏、滇剧、二人转、京剧等剧种中均有使用,并在京剧中又发展出干疙瘩与水疙瘩两种不同的类型。⑪汪人元《京剧润腔研究》,《戏曲艺术》2011年第3期,第9页。
因此,对于歌唱习语使用范畴的考察与甄别,让我们不仅对个人和乐种的歌唱风格特征有所把握,同时亦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唱法及其习语在不同剧种与地域间的时空流变。
3.同音同形而不同义
“嗖音”“嗽音”与“擞音”三个习语不仅读音相同,而且所指的唱法形态也较为相似,均是代表一种颤音的唱法。但是,若对三个习语本身做进一步分析,便会发现三者背后人们对于唱法的认知和理解是不同的。“嗖”是一个象声词,形容迅速通过的声音,“嗖音”在江西兴国山歌中是指歌者在演唱拖长音时,通过喉头的快速上下颤动发出的碎音效果。⑫王宇扬、伍润华《江西兴国山歌的歌唱艺术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 年第1期,第25页。“嗽音”是在声音流畅进行时,特意地连续制造障碍,气息突然短暂停滞,随后造成气息冲破障碍之感,这种控制的破裂声形成颤音,常给人以像咳嗽的感觉,所以称之为“嗽音”。⑬龙旎《戏曲声乐音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擞”的原意是用通条插进火炉,抖落炉灰。“擞音”则是唱者为了婉转动听,往往增加一些乐音,但仍保持原来的节拍速度,唱时通过下腭的活动辅助产生颤动。⑭夏征农、陈至立编《大辞海·戏剧电影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版,第211页。可见人们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类唱法的,而且三种唱法间也存在着形态细节上的细微差异。类似的情况,亦如“膛音”与“堂音”,两者均是指运用丹田之气演唱出的一种低沉、宽广、粗壮、有力的真声,但前者是说明这种唱法以胸腔为共鸣,后者则来源于今称戏曲演员声音洪亮、四座皆闻者为“响堂”,意为声音在空间中送得远,人们听得清。对于这一类“同音同形而不同义”的习语,我们若不加以区分和细究其因,而是将其“一视同仁”的话,便无法体会到人们对于唱法本身的多样理解与认识。
二、从表演到表述:歌唱习语中的认知方式
习语如何产生?为何对于歌唱表演人们有如此丰富多样的表述?这些问题与人们对歌唱表演的认知方式有关。从习语本身的含义出发,笔者发现大多数歌唱表演习语并不以呈现歌唱形态的特点为目的,而是描述了主体在歌唱或聆听中的某种感官体验与状态。例如,“颤音”这一客位习语所指的是一种声音形态的快速连续波动,但与其相对应的民间歌唱习语“麻音”(湖南民歌)、“闪音”(兴山山歌)、“绒音”(彝剧)、“嗖音”(兴国山歌)等,则均侧重于描述歌唱表演与聆听中的体验。因此,可以说歌唱实践者在“唱”“听”“对”“搭”过程中的体验是认知歌唱表演的主要形式,而这也体现于人们对于其表演特性的命名之中。笔者将从本体体验、听觉体验与通感隐喻三种体验方式,探讨歌唱习语产生的认知基础。
1.本体体验
本体体验,又称为深部感觉、动觉(kinesthetic sense),是人们在运动或静止中对于自身身体不同器官的位置与运动状态的感知。歌唱实践者在歌唱中对于身体歌唱器官的控制与认知,是其产生多样歌唱风格的基础。与之相关的歌唱习语在笔者的梳理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并能从中看出不同的几种情况。
以歌唱中共鸣腔体的运用及其位置命名的习语。鄂西土家族称唱山歌为“喊歌”,讲究“喊歌要三音”。所谓“三音”,即“膛音”(胸腔共鸣)、“腮音”(咽腔共鸣)、“顶音”(头腔共鸣);⑮高鸣《鄂西高腔山歌演唱的声腔特色和润腔特色》,《大舞台》2010年第11期,第138页。花儿“老把式”常将“苍音”(真声)与“尖音”(假声)也称为“心音”(胸腔)与“头音腔”(头腔、脑后腔和口腔);⑯张连葵《朱仲禄“花儿”演唱艺术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6页。再如戏曲中的“脑后音”或“脑后摘音”(头腔)。
以发声器官的运动状态命名的习语。如安徽大鼓的“卧嗓”、山西高平鼓书的“后闷嗓”、广东潮剧的“横喉声”,均是挤压声带以发出沙哑且刚劲的声音;安徽淮北花鼓戏的“啃音”、辽宁凌源影调戏的“颠腭儿”、评剧的“腭音”均是通过上、下腭的运动产生的颤音效果;康巴藏区的“昂叠”、安多藏区的“昂合”、卫藏地区的“缜固”,均有“喉咙拐弯”的意思,是藏族歌唱中一种独特的装饰性唱法。
还有一类歌唱习语较为特殊,它们并非直接描述歌唱中身体的运动状态,而是以自己的身体结构或状态隐喻某种歌唱表演中的形态,这种认知方式被称为“具身经验”或“缘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⑰〔智利〕F.瓦雷特等著,李恒威等译《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或“内身隐喻”⑱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例如,在吉林的汉族小调和满族萨满神歌的演唱中,经常使用倚音、波音、滑音、小颤音等润腔方法,尤其是在同音进行中最后一个音符或在拖长音时,使用前倚音和波音,这种润腔方法突出了旋律的棱角,民间称之为“肩膀头”⑲《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吉林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13页。;京剧中的“错骨不离骨” 是演唱中灵活处理节奏的一种特殊演唱方法,演员为表达角色的情绪,刻意把唱段中的某些词句放慢,给人跟不上板的感觉,而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原有节拍的轨道;⑳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滇剧的“秃腔”(又叫“秃头腔”)是一种若断若续、声断情不断的唱法,即每个字演唱者只唱第一个音,后面的小腔由伴奏代替。
2.听觉体验
对于人声音色与音质的听觉体验,是人们认知歌唱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歌唱表演习语中,包含着大量表述音色和听感的习语。如花儿的“苍音”“尖音”,田歌的“娇音”,秦腔的“犟音”“闹音”,晋剧的“拔嘹子炸音”,赣剧的“朱沙音”,常德花鼓戏“揢揢腔”,京剧的“刚音”,彝剧的“闷音”,粤剧的“霸喉”,等等。这类习语中的听觉体验也常与情感体验相关联,如豫剧的“恸声”(“恸”意指极度悲哀的情绪),其音色如放声恸哭,富有强烈的戏剧效果;㉑郭克俭《豫剧演唱艺术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而京剧中的“哭音”和“笑音”,实际上就是将生活中哭与笑的发声状态与音色运用于演唱之中来表现相应的情绪。㉒同注⑪,第8页。此外,人们时常将对歌唱的听觉体验与自然生态中声音联系在一起,对此笔者将在第三部分具体阐述。基于听觉体验的歌唱表演习语在中国传统民间歌唱中非常普遍,因而在此不再过多赘述。
3.通感之喻
“通感”,常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但同时它也是一种认知方式,是通过从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映射而形成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㉓王志红《通感隐喻的认知阐释》,《当代修辞学》2005年第3期,第59页。这种认识方式或修辞手法的基础是人类在感知活动过程中多重感官相通的现象,即心理学所称的“联觉”(synaesthesia),在表述中则常运用隐喻、转喻、明喻、借喻等修辞手法。在歌唱表演习语中,以视觉感官映射听觉感受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晋北道情艺人将演唱中的强拍起、弱拍收的演唱方式称为“红起黑收”。另外,在曲调进行中,利用特色乐器渔鼓垫奏强拍造成的弱拍起亦很普遍,艺人们称之为“补黑”㉔《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下),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1291页。;鄂西北兴山山歌有一种以真声与气声相结合的快速颤音唱法,这一独特的唱法在音色上呈现出虚实、明暗间的对比,因而被称为“闪音”。㉕周方跃《鄂西特性三音歌的演唱》,《黄钟》2001年第4期,第27页。以事物的视觉形象比喻歌唱的习语就更为普遍了,如梅花大鼓的“楼上楼”,豫剧的“拐头钉”“燕尾腔”,昆曲、豫剧中的“橄榄腔”,蒲州梆子的“箭音”,等等。
此外,除视觉外,亦有少量触觉之喻的习语,如蒙古族长调的“陶勒根绰伦诺古拉”(意为“绸缎般的柔软”)、河北梆子的“硬上弓”、陕西地区戏曲中的“硬音”和“软音”等,而味觉之喻的习语则比如粤剧中的“苦喉”。
通过上述习语,我们或许会发现,基于体验与认知的民间歌唱表演习语对于“言说音乐”而言,并不那么“客观具体”和具有“普适性”,甚至有时是某种抽象的表述,但它们在某一特定人群的交流中却十分有效。这不仅因为人们对于歌唱表演的体验具有某些层面的共性,更是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相关。
三、语境化的民间歌唱表演习语
通过体验认知歌唱表演,是歌唱习语产生以及主体在歌唱中进行交流的基础,而这样的认知与表演活动是无法脱离其社会生活与历史语境的。笔者在此将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对作为“语境化的符号”㉖萧梅《中国传统音乐“乐语”系统研究》,《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92页。的歌唱习语做进一步的阐释。民族音乐学领域对于符号学理论的关注由来已久,梅里亚姆就在其著作中专设一章为“作为象征行为的音乐”,他总结了“在人类体验中呈现”音乐作为符号的四种方式:(1)音乐艺术是表达意义的符号;(2)音乐反映情感与意义;(3)音乐反映其他文化行为、结构和价值;(4)广义上,音乐可象征人类的一般行为。㉗Alan 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p.229-258.
美国民族音乐家露丝·斯通(Ruth M.Stone)将符号学的研究总结为三个规则(rules)或分析层面(levels of analysis):(1)语法规则(syntactic rules),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的关系,或位置与位置之间的语法,例如可以运用语法规则描述音乐的ABA的三段式结构及其段落间的关系。(2)语义规则(semantic rules),即符号与其所指(designatum)之间的关系,也即解读符号所指涉的含义。(3)语用规则(pragmatic rules),人们对于符号的使用,符号之于社会生活的功能,以及在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她指出,“尽管符号学给出了分析的三个维度,但大多数艺术领域的研究,包括民族音乐学,都未能真正超越语法规则的层面”㉘Ruth M.Stone.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8.p.81.。内特尔也认为,“从语言学中得出模式和方法的音乐学分析学派,认为符号和符号代表的事项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符号系统的结构那样重要,通常不研究所分析音乐的特定本质,也不研究音乐与生成音乐的文化之间的关系”㉙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与概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纳蒂埃(J.Nattiez)的音乐符号学研究则是把视角投向了语义和语用的层面,他提出内在层次、创作层次与感知层次的符号学三重分析模式,并探讨了符号的结构分析与文化语境。㉚参见汤亚汀《文化·符号·语义·认知——纳蒂埃〈音乐与话语,关于音乐符号学〉述评》,《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Peirce)在其研究中强调在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全面系统地思考和理解符号,“符号过程”(semiosis process)是其理论的核心,即将包含语言在内的符号分为“征象”(sign)“对象”(object)与“释象”(interpretant)三个部分。“征象”是我们对符号的物质性的感知,不是物质性本身,而是物质的心理征象;“对象”是对此物质性之所指的感知;而“释象”,人类学家迈克尔·西尔弗斯坦将其解释为基于符号受指体(entity signaled)和符号发出体(signaling entity)之间关系的性质,即被交流之意义的性质。㉛Michael Silverstein.“Shifters,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Basso,Keith.and Henry Selby(eds.),Meaning in Anthropology,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76,pp.11-55.笔者认为,实际上“释象”是对“征象”与“对象”之关系的社会文化语境做进一步的再阐释与升华。由此,三者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生态网络。㉜参见纳日碧力戈《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40—50页。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就人们对于歌唱表演的直观体验与感受进行了阐述(即“征象”的层面),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主要从“对象”与“释象”的层面分析歌唱表演、习语与语境之关系问题。
在“对象”的部分,皮尔士进一步将其划分为“象似”(icon)、“标指”(index)与“象征”(symbol)的三种类型,它们所指涉的是符号与其所指的三种不同关系。这不仅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三分法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对歌唱表演习语做语境化的类型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将讨论的“符号”并非习语本身,而是习语所代表的歌唱形态以及人们对于这一形态的感知,通过歌唱形态与其所指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局内人对于唱法进行命名,从而形成习语的内在逻辑。
所谓“象似”,是指符号与其所指在形态上具有一致性或类似性,例如照片、地图、拟声词等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在歌唱表演习语中,拟声唱法即是这一类型的符号,例如纳西族歌舞“窝热热”中女性演唱的 “则流客”是一种模仿羊叫的快速颤音唱法,与男声部发出的强悍粗犷的吼声相结合,并形成音色上的鲜明对比;㉝黑力《浅谈云南纳西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兼谈对纳西族歌手培养问题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83页。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的长调有“哈日嘎”与“沙格莎”的演唱技巧,前者模仿泉水声,而后者则模仿鸟叫;㉞笔者采访内蒙古苏尼特长调歌手呼日乐巴特尔,时间:2012年8月14日。评话、弹词等曲种运用口技技巧来模仿各种鸟兽声、战斗声、市井声等唱法,称为“音响”。㉟上海艺术研究所等《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4页。
“标指”,则是指符号与所指在形态上并无一致性或相似性,但在符号所属语境中,两者间具有某种逻辑关联性或连续性,这种关系并非随意的,而是可以由甲推乙的推论或联系过程,将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感知与对另一事物的感知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对于符号的心性层面的建构。如豫剧花脸的“燕尾腔”,将真声唱词、假声翻高八度拖腔的唱法与燕子尾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㊱郭克俭《豫剧演唱艺术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朝鲜族盘索里的“缠声”,这种装饰性唱法和嗓音技巧则被认为是缠绕丝线的声音;㊲宁颖《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皖西民歌中高亢嘹亮、尖锐辽远的高腔唱法,被人们比喻为“蜜蜂钻天”;㊳刘蓉惠《汉族民歌演唱的用声与润腔特色》,《中国音乐》2005年第2期,第142页。阿尔麦人的喉颤音唱法,被称为“嘎吾斯嘎果”(意为“有波纹似的唱”),即是让人们联想到了水面的涟漪。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下),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981页。“标指”的特殊性在于,符号与其所指的逻辑关联性是在特定语境被人们所建构的,因此我们也只有在语境中方才能理解这层联系。
“象征”则是指符号与所指间既无一致性和类似性,也无逻辑关联性与连续性,而是一种约定俗称的关系。如大本腔/二本腔、阳面/阴面、阔音/窄音、老音/夹音、本功/背功等均是指真声与假声,这是局内人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命名与分类。
上述符号(歌唱形态)与意义的三种关系,可以说是民间歌唱表述习语产生的内在逻辑所在。如果再往“释象”的层面延伸,便会对这些关系的语境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歌唱习语的产生是基于实践者对其所生所长之地的感悟,体现出的是歌唱、表述与其生态环境、自然景观、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提炼”。
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歌唱习语。戏曲中的“虎音”“鹤音”“猿音”“鸟音”,民歌中的“蜂音”(广东壮族)、“则流客”(羊咩颤,纳西族)、“玛莫巴君”(母羊向山下跑时的叫声,藏族)、“蜜蜂钻天”(皖西民歌)等,皆可见其与动物的关联。“棉花腔”(祁剧弹腔)、“糯米腔”(苏州评弹)、“亚亚葫芦腔”(淮海剧)、“橄榄腔”(昆曲)等则来源于人们对植物形态与特性的认知。而“翻天云”(桑植民歌)、“云遮月”(京剧)、“雨加雪”(桂剧)、“海底翻”(绍剧)、“隔山拖”(赣西北民歌)、“过山垅”(长沙山歌)、“爬圪梁”与“钻山沟”(二人台)等,是人们将日常所见所想之自然景观与对歌唱的感知体验联系在一起。 此外,歌唱与生态的联系也常被赋予某些宗教意涵。在藏传佛教的吟诵中,将使用同一组音高和节奏型,不断反复地演唱的,一字一音的吟诵方式称为“顿”。“顿”的字义原为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名,每“顿”面积大小不定,大者可播种青稞百余克,小者播二三十克。从宗教吟诵移植到藏戏的“顿”,具有对土地净化与经文吟诵祝祷的双重意义,“顿”在藏戏中最大的作用是在正剧之前为戏剧演出场地净化,以期正剧的演出顺利。㊵参见魏心怡《藏戏“阿姐拉莫”前演“顿”之音声考源、仪式象征及其意义》,《大音》第12卷,2017年出版,第84—86页。
与生活生产相关的歌唱习语。湖南祁东渔鼓的“坛子音”是在一个音上做快速的颤动,就如敲击腌菜坛子的回音;㊶《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398页。湖北渔鼓将甩腔的演唱称为“扣子”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版,第550—551页。;正字戏演员郑城界的演唱有“瓮仔声”之称;㊸《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东卷》(下),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2274页。西北花儿将假声尖音亦称为“尕刀子音”㊹同注⑯,第105页。等。这些习语与日常的生活用具相关。五音戏中将一种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唱腔起唱形式称为“旱地拔葱”,又将一种快速唱腔突然转慢的演唱方法称为“老牛大摔缰”,形似绷紧的缰绳实然摔断的情景;㊺《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469页。河北梆子的“夯音”是通过气息强烈冲击声带,从而发出短促、浑厚的强顿音,如同劳动砸夯似的大咳一声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河北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39页。等。这些习语则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经验。
通过对于皮尔士符号学三元观的解读,以及在歌唱习语研究中的运用,笔者认为,皮尔士的理论并不在于解码符号,也不是描述符号本身,而是在于揭示存在于人类认知与表述中的“关系体系”,即物质性及其感知(“征象”)、意义(“对象”)与语境(“释象”)的关系。而对音乐的感知、音乐意义的阐释以及文化中音乐的研究,也正是民族音乐学长久以来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这也可作为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民间习语进行分析、分类和阐释时思考的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在对歌唱习语的基本形态类型(发声方法、润腔手法、表演互动方式、板式唱法等)与歌唱认知方式(本体体验、听觉体验与通感隐喻)的分析的基础上,从皮尔士三元观的角度,对习语、歌唱表演与其语境之关系和类型进行阐释。在这一过程中,局内人对歌唱表演的表述及其内在逻辑,让笔者对音乐学研究中“如何言说音乐”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寻找精准的语言本不应该是言说音乐的目的,言说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其目的应在于唤起信息接受者对于音乐的某种真实体验(过往的/当下的、内在的/外在的体验等),并引发其对音乐语境的认知,从而实现音乐实践者、描写者与信息接受者三者间体验的“共频”。借以文章开篇处引用的威廉·福利的“隐喻”来说,“物体”(观念)的传递与接收才是言说的目的,而非“容器”(词语)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