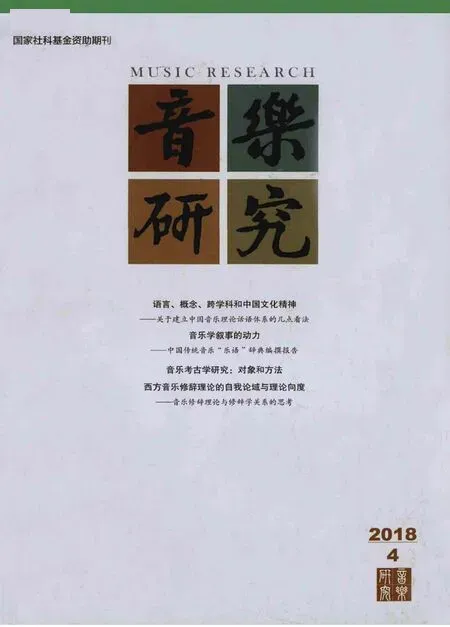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和方法
文◎方建军
一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总称为音乐遗存。音乐遗存分为遗物和遗迹两类,这里仅就音乐遗物略加论列。音乐遗物主要有四类——乐器、乐谱、音乐文献、音乐图像,它们是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又以乐器的研究为大宗。乐谱目前发现较少,出土音乐文献虽然较为散见,但数量并不算少,二者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音乐图像的数量相对较多,有时能够提供其他三类音乐遗物所无的内容。
这四类音乐遗物各有自身的特点、优长和局限,它们之间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时常相互牵连,相互依傍,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出土乐器大多数是古人使用的实用乐器,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乐器埋葬于特定的出土单位,大多情况下,它都有伴出物,具有一定的考古学环境,而不是孤立的存在。各种随葬品与乐器的共存关系,使乐器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参照系。在这方面,它比文献孤立记载一种或一件乐器要全面和丰富得多。
乐器在古代社会的应用处于动态之中,经过埋葬之后便转入静态之下,以往使用它的主人已不复存在,如何制造、如何演奏、演奏什么以及当时的具体表演情形等,均难以获知其详。并且,出土乐器一般都为古代宫廷和贵族阶层所拥有,通过它只能了解这些特定阶层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文化,而属于民间层面的乐器则较少发现,这是出土乐器自身的局限。
古乐谱虽然是弥足珍贵的音乐考古材料,但由于古乐谱在早期(公元前)尚不多见,后来则由于记录载体难以保存的原因,故目前发现很少,估计其地下潜藏也不会很多。但即使如此,它仍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并且还可参考传世古乐谱对出土乐谱进行研究。不过,传世古乐谱如同传世音乐文献那样,不应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黄翔鹏主张将传世古乐谱的研究称之为“曲调考证”①参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等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前言”部分。,应是比较合适的。
古乐谱是我们了解古代音乐作品具体构成的重要资料,甚至是唯一的资料,这是它自身的优长,但由于古乐谱使用的文字和符号与现今所见传世乐谱差异较大,加之有的乐器演奏谱存在定弦上的判定问题,所以对它的识读解译存在较大困难,研究结果也是仁智互见,甚至是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古乐谱记录的音乐作品缺少精确的节奏、节拍和时值,因此对它的解译复原就会存在一定的分歧,有时同一首乐曲,不同的研究者所译,表现在音乐形态上就具有明显的差异。
音乐图像出自古代美术家之手,他们对于当时音乐事物的描绘,各有自己的侧重,不一定都是从音乐专业的角度来创作。由于创作意图、图像主题、画面布局和艺术手法的不同,以及制作材料、工具和技术的限制,图像内容会有不同程度的省减,有些只是写意而非写实,有些则有所夸张,或具有象征性,甚至想象成分,不可能全部是现实音乐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古代乐队的组合,乐器的形制、件数和尺寸比例,弦乐器的弦数,吹管乐器的管数或指孔数等,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图像乐器虽然不是实物,但它是实物的形象再现,有的再现可能是比较真实的,有的可能只是轮廓式的,有的则可能是错误甚至虚构的,这都需要加以具体的辨析。如在中国出土的汉画像石和唐代壁画中,常见有乐人双手握持一小型乐器置于口边吹奏的形象,对此有埙、笳、贝等不同说法,但都是从外形所做出的猜测。对于此类不具备观察条件的轮廓式模糊图像,应以暂且存疑为是。
失真的音乐图像,不仅在考古发掘中见到,而且在传世的古代音乐图书和考古图书中,也存在图像不确甚至图像有误的情况。如宋代陈旸《乐书》所绘的埙、于等乐器,即与出土实物的形制不符。又如宋代吕大临《考古图》收录的编钟,所绘图像不确且无比例,这些都是应予注意的。
验证音乐图像的正确性,需要用一定数量的同类图像资料加以比较,同时,还需以图像和实物加以比较,以实物为验证图像的标准。当然,有些乐器图像虽然在出土实物中尚无所见,但恐不能简单认为即图像有误,还应参考古代文献记载并耐心等待新的音乐考古发现。
音乐图像资料能够反映出不同品种的乐器,有些乐器品种迄今并无实物出土,恐怕今后也不会有大量发现。音乐图像中的器乐表演形象,有的描绘一件乐器,或展示一件乐器的演奏状态,有的反映出几件乐器的组合及其演奏情景,有的则是古代乐队的整体描绘。因此,音乐图像对于乐器的研究,不仅关注乐器个体,还应包括乐器组合和乐队构成。
音乐图像有时反映出一定的乐器组合,有的可能是整体乐队,有的可能是乐队的局部,有的甚至是写意,即所描绘的乐队只是象征性的几件乐器,不一定是古代现实生活中的乐队乐器构成。如中国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礼器,有些上面刻画有所谓宴乐图像,但其中只见编钟、编磬和建鼓等少数几种乐器,很少看到琴、瑟类弹弦乐器和吹管乐器,但不能据此便认为古代宴乐演奏不使用弦乐器和吹管乐器;而图像描绘的场面,也不一定必然是宴乐表演。从考古发现看,既有仅随葬编钟、编磬的墓葬,也有包含多种乐器随葬的墓葬,乐器的应用场合则不一定仅限于宴乐。
相对于立体图像的散置状态而言,有些平面图像(如壁画)反映的乐器组合或乐队构成则较为可信。但是,墓葬中出土的乐俑,其摆放或出土位置有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不一定就是古代现实音乐生活中的乐队排列和组合方式。有时由于乐俑的出土位置被扰乱,发掘者在整理和发表材料或在后期布展时,将乐俑以主观意图加以组合,容易给人造成古代乐队或乐舞排列组合的错觉,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与古代文献对于音乐的描述相比,音乐图像具有较为直观的特点,是古代音乐活动和音乐器物的形象化和视觉化。音乐图像虽然不如出土乐器那样具有无比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但往往能够提供较为广阔的音乐表演场景,有时能够表现出某种音乐活动的整体或局部整体。与出土乐器相比,它有表演者甚至观赏者,以及表演的场面和环境,有乐器或乐队的排列组合,表演者(奏、唱、舞)的姿势、姿态和服饰,反映出乐器的配备、安置和演奏方式,器乐演奏与其他表演的关系,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长。
出土音乐文献是古人对当时或之前音乐活动和音乐事物的描述和记录,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体现出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传世文献会发生遗失乃至毁灭,如六经之一的《乐经》即已失传。古代文献流传至今,经过多次传抄、刊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修改或窜乱,从而产生一些讹误,有时甚至包含有作伪成分。而出土文献往往能够提供传世文献所无的内容,弥补传世文献之缺,有些则可纠正传世文献的讹误。
出土文献有关音乐的记载,常能提供音乐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上下文语境和音乐事象的关联性,而不是孤立地记录一件乐器或一部音乐作品,这是它明显的优长。
不过,应该看到,出土文献犹如传世文献那样,主要记述统治阶层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其中的音乐事物,自然属于统治阶层所有,而民间音乐则缺乏记载,这方面它与出土乐器具有同样的局限性。此外,出土文献里面专门记载音乐内容的书籍或篇章目前发现较少,而有关音乐的记载通常都是较为分散零碎,往往穿插于其他出土文献之中,需要做专门的梳理和分析。
二
音乐遗存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集中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的音乐遗存进行断代研究,可以形成音乐考古学的分期研究,从而出现石器时代音乐考古、青铜时代音乐考古,或某一国家和地区特定时代的音乐考古等。如中国的商周音乐考古、隋唐音乐考古,欧洲的史前音乐考古、中世纪音乐考古等,就是按照考古资料的时间范围而形成的分期研究。
音乐遗存分布于较广的地理范围之内,都属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因此,从空间视域看,音乐考古学还能够从事分区或分域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音乐考古学有以国家和地区为限的,也有以洲际为限者。如中国音乐考古、希腊音乐考古、埃及音乐考古、美索不达米亚音乐考古、斯堪德纳维亚音乐考古、地中海国家音乐考古、东亚音乐考古、欧洲音乐考古和南美洲音乐考古,等等。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还可进一步再行分区研究,如中国东周时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按当时的国别和族属分为周音乐考古、楚音乐考古、秦音乐考古、三晋音乐考古、吴越音乐考古和巴蜀音乐考古,等等。
对于上述四类音乐遗物进行专门研究,可以形成音乐考古学的分类研究。②方建军《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黄钟》1990年第3期。集中研究出土乐器,可以形成古乐器学或乐器考古学;对出土乐谱进行研究,可以形成古乐谱学;对出土音乐图像进行研究,可以形成“古乐图像学”;对出土音乐文献进行研究,能够形成“古乐铭刻学”③“古乐图像学”和“古乐铭刻学”的名称,系李纯一先生提出。参见李纯一《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其中,有的音乐遗物还可做进一步的分类研究,如目前学术界对编钟、铜鼓、口弦(jew's harp)、里拉(lyre)等的集中研究,已经形成音乐考古学乐器类研究的分支。
音乐考古学的分期、分区和分类研究,既可以各自独立开展,成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也可以同时交叉进行,形成综合性研究。在从事音乐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时,可以在同一时期再进行分区和分类研究。例如,要研究中国东周时期的编钟,似可将其分成春秋和战国两期进行研究,每一期再做分区或分域研究,每一区域又可单独进行编钟的类型划分,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综合。分区和分类研究,也可大体参照这样的分期研究模式开展。
三
相对于传世的音乐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的音乐遗存,犹如一系列需要读解的“地下音乐文本”④方建军《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音乐考古学的研究资料,本身即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而各种音乐文化物质资料之间,也具有多方面的联系。不同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与相关的学科领域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认识和解释音乐考古资料的内涵,就不可能运用单一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而必然要涉及诸多的理论、技术、方法和学科领域,以此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综合运用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术的普遍特点。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为音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及时学习和吸纳有关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只要能够达到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即可法无定法。
由于音乐考古学试图重建考古实物所反映的某一历史时期人类音乐行为及其发展规律,所以必然要涉及较多的学科领域,以多学科知识或多学科协作的手段,来达到和实现研究的目标。总体来看,在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或涉及的学科领域中,考古学和音乐学应是最基本的两种,二者需要科学有效的结合。音乐考古学所应用的考古学方法,主要是考古类型学,当然也涉及考古地层学、考古学文化、古文字学、古人类学、实验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等;而音乐学方法则主要涉及音乐史学、乐器学、音乐声学和音乐人类学等,并通过乐器测音、音乐遗存的复原和模拟实验等特殊方法,来探索古代人类的音乐行为和音乐文化的构成。
鉴于音乐遗存来源的考古学性质,我们不能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处理音乐考古资料,或者仅从音乐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它,那样就会使音乐遗存与考古学割裂或隔绝。音乐遗存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遗迹通常是遗物的出土和存在单位,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必须掌握与之有关的一切考古资料。诸如音乐遗存出土的地层、年代(时代)、考古学文化、共存物、墓葬情况(墓主、国别、族属等)、器物组合、人种分析等,都是音乐考古学研究必备的资料,需要与音乐遗存联系起来加以通盘考虑和分析。
就出土乐器而论,只关注乐器本身,仅掌握单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密切追踪相邻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如对于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就涉及古文字学、乐律学、音乐声学、音乐史学、冶铸学和化学等。因此,单纯从某一学科出发,只能认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而集聚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则有可能较为全面地认识和分析音乐考古材料。
在关注乐器本体的同时,还应通览和把握与之共存的其他出土物品。也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既将音乐考古材料与一般考古材料有所分别,同时又需将音乐考古材料与一般考古材料加以整合。这是因为,出土乐器与一般考古发掘品有所不同,它是音乐制品而非一般生产和生活用品,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考古材料,应该将其抽绎出来予以特别对待。同时,音乐考古材料又与一般考古材料具有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因而不能将其与一般考古材料绝然分离,而应厘清考古发现情况,将其纳入考古材料的整体系统之中来关照。
基于这样的认识,出土乐器的研究方法,似可归纳为由外部形制、内部结构再到音响性能的三层递进模式:
外部形制——内部结构——音响性能
这种三层递进模式,也可表述为出土乐器的表层、内层和深层研究方法:
表层研究——内层研究——深层研究
出土乐器的三层递进研究模式,是由外到内,由视觉观察到听觉判断,由仪器测量到人脑分析的过程。
仅进行表层的乐器外部形制学(包括纹饰)研究,普通考古学即可胜任;乐器的内部结构与音响之间的关系,乐器的材料性质、化学成分和乐器形制的断层扫描等内层范围的考察分析,需要由音乐考古学者从事实物观测,并与有关学科的学者密切合作;声学特性、音乐性能和音乐分析等,则主要由音乐学术背景的音乐考古学者来完成。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是案头工作、田野工作和实验室工作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结果。
在对音乐遗存进行考古学观察的同时,还要参考传世古代文献记载,以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对音乐考古材料予以阐释。这就是王国维倡导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⑤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葛剑雄主编《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因此,音乐考古学应将历时研究(diachronic study)与共时研究(synchronic study)结合起来。目前主要还是集中于音乐遗存的历时性探索,而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则较为欠缺。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文化具有多方面的联系,因此不仅应将音乐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察,而且需要将其纳入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横向空间维度来审视,这样才能纵横交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进行音乐考古学研究。
考古发掘揭示的音乐遗存,由过去的动态而处于静态,使用它的原主人业已消逝于历史之中,我们只能“睹物思人”,并尽可能运用考古学环境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关联分析。因此,在从事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分析时,不能仅限于就物论物,而应联系到物背后的人。
由于考古发现的音乐遗存属于特定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进行必要的考古学分析之后,还要将其纳入音乐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来考量。如果游离于音乐历史之外,不关心音乐考古资料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不考虑资料的人文属性,这些资料就徒成自然形态的物质。从此而看,音乐考古学应由纯物质层面的研究,进入到文化的、精神的和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音乐考古学应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体现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综上所论,音乐考古学对出土乐器的研究,实际应主要包括形制、音响、文化三个方面,其中的乐器形制研究,包括三层递进模式的外部形制(表层)和内部结构(内层)研究。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基本遵循由个体、群体到总体的研究路径,即由个别到一般、由小的综合到大的综合、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过程。音乐考古学的个案分析是群体和总体分析的基础,也是一个必经的研究阶段,但仅有个案分析,就会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此,在个案分析之后,还应进行群体和总体的综合分析,以此来考察不同音乐考古学文化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探索古代音乐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