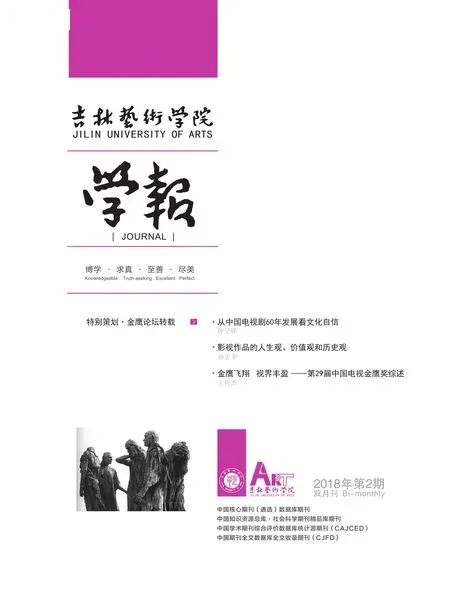作为一种美育实践的高校抗战历史剧
周珉佳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756)
对于剧作家来说,历史就是一种强大的、真实的创作动机,剧作家能够通过创作历史剧表达深刻的哲学寓意和现实价值。同样对于现代高校来说,站在当代文化的高度观照历史,用一种现代意识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淬炼,创作古今汇通的历史剧,创作动机也是极富有现实意义的——这既是高校美育实践的重要机会,也是检验当代大学生历史观的一次大练兵。
从宏观的社会历史区段来说,大学生创作者较为集中地选择了抗日战争历史时期进行叙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难以忘却也不应忘却的,70多年来承载这一沉重“历史记忆”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层出不竭,构成我国现当代文艺大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铭记历史,抗日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也成为展示民族形象、传播民族文化传统意识的绝佳载体,因此,表现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日战争也是高校原创话剧的一大重要生长点。
一、高校抗战历史剧的地域性
抗日战争举国齐心,但是不同省份及区域的抗日形式、抗日氛围及抗日文化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中融入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区域人文性格,凸显出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化景观。东北的历史文化并不算悠久,与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三秦文化等相比,东北地域文化无论是传统历史时长、自身发展积累、文化艺术形态、文化艺术作品和研究成果等,都显示出明显的单薄和滞后。尤其是在近代不断遭受战争的影响,现代性发展受阻,再加上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闭塞,使东北地域艺术文化的表现题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通过创作校园戏剧的方式展现东北近现代经历战争的特殊历史图景,能够对东北地方文化历史的传播注入一剂强心针。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导演系主任陈晓峰就是看准了东北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突出风格,与职业编剧何苦合作,创作并导演了《南门客栈》这部校园话剧。陈晓峰说:“我们希望做一个全新的抗战题材剧目,东北民众的质朴幽默为我们提供了灵感,用喜剧的手段,从不同角度展现那段历史,然后给观众带来更深层的思考。”[1]《南门客栈》张扬起东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将喜剧文化对大众的亲民性和东北地域文化中深沉冷静的一面结合起来,生成了颇具东北历史文化气息的风格体征。这部抗战题材校园喜剧,不仅对青年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还能够让观众在欢乐之余产生对这段抗日历史的思考。
从这部话剧的幕起,编剧就将20世纪80年代东北话剧(《田野又是青纱帐》《庄稼院里》《榆树屯风情》《大荒野》《北京往北是北大荒》等)中的经典化意象运用进来——风雪、老树、群山、寒冬……令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东北的民风和民俗。人物台词中囊括的地方特产、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承载着东北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反映了东北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言语表达习惯、伦理道德表达方式等,呈现出创作者的文化自信和生活经验。[2]同时,主人公叶娜兰和胡两刀二人转式的对话展示了当时东北地区的复杂甚至有些惨烈的历史大背景——“长春早改名叫新京了啊,溥仪那小子,啊不,康德皇上都登基坐殿好几年了。大清国完了,是气数尽了,找日本人当爹算什么玩意?”“不是鬼子杀人放火,就是胡子打家劫舍。”话剧《南门客栈》虽然表现的是伪满洲国东北抗联时期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但是每个人物背后都背负一段特殊的过往。编剧何苦说,“这是一个用很欢乐的形式展现一个很宏大很悲观的主题,这是我们想做到的一个审美情绪。虽然这个主体是很宏大很沉重的,我们仍希望用这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南门客栈》对戏剧结构和戏剧节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的戏剧矛盾也是复调式的——家国相连,有国才有家,有情更有义。关东浪、一丈红共同经营一脉胡子,情深意重,二人是为了与东北抗联组织接头才来到南门客栈;而关东浪与南门客栈女老板叶娜兰是娃娃亲,叶娜兰十几年来孑然一身不接受其他人的感情,也是为了等待与关东浪重逢,叶娜兰的痴情使这个四角情感线绵密感人;厨子胡两刀对叶娜兰痴心一片,只为付出不求回报;再加上保安队队长赵大嘎子对叶娜兰垂涎已久,共同形成了《南门客栈》充满了喜感和动人的情感线。这种借助于情感线索表现宏大历史战争的手法借鉴了电视剧《闯关东》和《二炮手》,同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伟大的英雄“部队”,他们在十四年的时间里,艰苦抗击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南门客栈》这部话剧一方面用具有东北特色的喜剧风格展现了东北民众质朴、机敏而幽默的独特性格;另一方面,也用这种风格基调彰显了千千万万东北民众面对民族存亡时的大无畏气概,那种举重若轻的家国情怀和态度就是这部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的真正价值所在。这部既表达了“意义”又有“意思”的剧作,在表现小人物方面有突出的成绩,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独特的性格特色。对这样一部现实主义剧作,陈晓峰导演运用了传统舞台手法,力图让故事以朴素直白的面貌呈现出来,只在最后一幕最后一场借用了电影里面的慢放,帮助剧目最终高潮的完成。尽管东北地域文化与大众文化产生越来愈多的交集,但是专属于东北的历史文化是带有传承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的校园社团原创话剧就承担起重返历史,重现历史,重新诠释红色题材的重大责任,清洗一直以来“抗日题材”的滑稽和反逻辑性。
北方望南国——厦门理工学院“厦理巴人”话剧社的原创话剧《陪楼》也是一部表现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品。作品充满了浓厚的闽地风情,将厦门鼓浪屿的特殊风情和历史有机地融合进去。编剧袁雅琴在竭力宣传鼓浪屿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大力传播了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阶级的差异、人物身份的差异以及经历的差异,使中国民众产生了向度并不统一的想象,对待同一问题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过程是艰难、惨烈和充满曲折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则是迟缓滞涩的,其中经历背叛、流血、死亡与涅槃重生,因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在被侵略、被欺侮、被损害、被迫觉醒的历史过程中辗转建立起来的,具有程度不统一、节奏不一致的特点。
当然,这其中还有人性的作用力。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极善和极恶都是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产生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金陵十三钗》都是描写在战争绝境中的人性之光,而《陪楼》的主旨也有类似的意义,都是表现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生存状态,夹杂着情感、矛盾与正义,最终用小小的光焰点亮更广阔的黑暗之地。在《陪楼》中,龙家老太爷不畏日本人的威胁,怒火冲天高喊:“我死后变成岳武穆、戚少保,领天兵天将来杀尽倭寇!日本鬼子,我来了!”说完冲出去一头撞柱而死。龙老太爷代表了抗战中的一众小人物,他们为了自我尊严而拒绝苟且偷生,更是为了民族同胞而牺牲自我,生命的价值在特定的瞬间升华。在不可想象的混乱和动荡中,人性的遮蔽外衣全都被扒掉,呈现出最真实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也是中国人在抗战中民族意识的最直接体现。
主人公阿秀本是一个连“民族意识”为何物都不知的底层婢女,她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成长为一个民族意识突出的人物,她对待战争的态度夹杂着对龙家的报恩、对二龙的爱情、对地瓜的鄙视以及对日本人的痛恨。作家在阿秀的成长中传播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且以阿秀作为一个中心点辐射出更广阔的人物景观,各个人物都呈现出个性和立场:龙博山、阿敢叔和二龙,都为抗日战争贡献出了自己的绵力;日本人攻占厦门,鼓浪屿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一时间涌入了11万难民,龙家拿出衣物粮食支援难民,甚至连凤海堂的陪楼都已经成为难民营避难所,龙家几代人都将抗日作为己任;地瓜成为汉奸,阿秀视其为渣滓和忘恩负义的败类……袁雅琴将最激烈的情节矛盾和最惨烈的现实都集中在凤海堂龙家,十分符合戏剧舞台的要求,更能够凸显民族大义和小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泰民安的今天,回顾这段抗战历史,青年学生更要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民族意识传播、民族文化继承与国家观念认同,这些都需要在新时代中不断被重视。
《陪楼》这部戏也呈现出十分浓郁的闽南特色。本来,厦门作为万国租界,它的沦陷和中国民众的抗战就不同于其他普通的沦陷区,再加上鼓浪屿是个相对封闭的小岛屿,它独有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承使其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更具个性的方面。鼓浪屿在2017年申遗成功,使其历史文化更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袁雅琴书写鼓浪屿的历史,既表现了她的文人自觉,又体现了当代作家的文化自信。闽南是一个地域风格十分鲜明的区域,首当其先的便是建筑艺术风格。在小说中,龙家正是搞地产的侨商,在鼓浪屿小岛上建别墅。“凤海堂”表达出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的诗意与豪迈,既渲染闽南特色,又张扬东南亚、欧洲风情,更能体现出居住者对于美学的感悟力和格调品味。在《陪楼》中,厦门鼓浪屿这个曾经的万国租界是如何形成的,它遭遇了哪些坎坷,小岛上的人们最终走向何方——这段沧桑的历史在校园话剧舞台上被重新言说,再现了鼓浪屿的温婉、寂静、从容、迷离。对于厦门鼓浪屿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地方文化宣传。鼓浪屿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符号,曾几何时,它已升华为诗人的扁舟、琴者的圣地、行客的天堂,而《陪楼》在作者细腻的文字里铺染开温婉的鼓浪屿情调,同时也揭示了沦陷时的动荡不安和抗日时的狂风暴雨。
“厦理巴人”学生话剧社有意将宏观的大精神和大理念具象成为一个个形象的小故事,将传播历史文化这样的大工程分解成一个个有效的分子,从小处着手服务于地方文化发展与宣传。经过了排练与演出《陪楼》,学生对剧本时代背景的了解与感悟更为深刻了,对人物性格的揣摩更为真切了,对闽南文化的认识更为详尽了。总之,该剧带来的文化熏染不亚于一堂历史文化素质课。
再从东向西——重庆是西南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进入近现代,这座城市的红色文化又异常浓郁。重庆大学缙云剧社的原创话剧《重庆往事·红色恋人》尽管不是抗战题材戏剧,但是它对共产党人抗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与抗战历史剧是异曲同工的。刘国鋕与曾紫霞这段爱情因理想而孕育,为理想而升华,最终又为理想而割舍,是历尽风霜洗礼却依旧熠熠生辉的红色爱情。编剧王宏亮抽取《红岩》中的重要线索情节,再结合重庆大学的真人真事,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审美的艺术形式,书写了这段革命史视角下“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的恋人往事,在祖国的西南方张扬起校园历史剧的独特魅力。
二、高校抗战历史剧的共性问题
尽管上述几部作品的创作和演出都较为成功,但是就宏观角度看,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剧社在处理抗日战争历史题材的话剧时,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
首先,高校剧社因创作经验有限,创作目的性又太强,创作思路的局限性比较大,尚未从民族矛盾升华至伦理人性层面,所以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有比较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甚至是妖魔化的特点。例如《南门客栈》中的核心人物关东浪,他是一个落草多年的绿林胡子,凭着心眼正直、枪法硬气走江湖,杀过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也灭过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和欺压百姓的“二鬼子”。关东浪具有东北土著强大而乐观的性格,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可以面对一切艰难和困苦。当然,这个人物塑造得过于理想化。面对日寇入侵,处处是狼虫虎豹,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天不打跑这小日本子,我就一天不想这成家的事儿!”只想着国恨却不会再爱的性情,也辜负了叶娜兰和一丈红的深情,从伦理人性的角度来说,关东浪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失真了。再如《陪楼》中对日寇的表现处理方式也比较肤浅和滑稽。日本侵略者的愤怒、霸道与残暴、冷血有其特有的表现方式,比较成熟理智的做法是在戏剧舞台上通过台词的节奏和音调、舞台动作的力度来表现,而非单纯的歇斯底里。日本人侵略中国疆土,奴化中国人民,其处理方式也不见得是全然不带智慧的,所以不能把日寇形象塑造得过于扁平,甚至是小丑式演绎。这个问题在很多抗日题材的电视剧、电影以及舞台剧中都出现过,归结起来就是编剧和演员们只是呈现了一个“符号”,而非塑造一个“人物”。
实际上,在小说创作领域,职业作家们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新世纪抗战小说对比之前的战时小说和十七年小说,更注重表现中国抗战故事中的人性和情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展现中国民族形象的同时,也注重传播这段历史文化的超越国族情感的价值意义。北京大学陈晓明先生在《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中国抗战小说缺乏对时代、对民族、对人性的反思,希望中国作家全面检讨对历史的认知态度,尤其是对邻国日本的认知和理解。[3]随后,学术界出现了李西阳《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抗战叙事”与现实焦虑》、赵国乾《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新探索》、张韶闻《中国抗战文学中的日本战俘形象》、张鹰《英雄话语与悲剧形态——长篇小说<亮剑>的美学拓展》等文章,也都是分析讨论这一问题。一般的高校剧社没有结合小说创作经验而创作,多数仅仅是完成了“讲一个抗战历史的故事”的任务,对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表现得不够,因此也没能在剧作中完成从抗战到建立“大民族意识”的任务。
其次,剧中“战”与“反战”的意识不明确。早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直观表达战争所激发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控诉日寇的凶残与丑恶,促使中国作家投入到战时文学的创作洪流中去。战时小说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英雄主义,激发鼓舞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年抗战小说歌颂和怀念曾经的国家英雄,缅怀牺牲的战友和同胞,歌颂战争的伟大,强调政党领导的正确性,为新生的革命政权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一阶段的创作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昂扬的乐观主义基调消解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层面,反战意识薄弱。进入新时期,抗战小说延续了以上两个阶段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却不再一味地歌颂战争,着重呈现人物复杂性和事件多面性。这一阶段的创作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冲破阶级性和党派性的历史观,对前两个创作历史阶段有明显的超越。重要的一点是,还原国民党抗战事实,反战和平意识凸显。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于抗战文学出现了来自民间的人物形象和解构的图景,最经典的作品当属莫言的《红高粱》。而在历史剧领域,无论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历史剧创作潮流以及著名的重庆“雾季公演”,还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矛盾意识都是围绕着“战”与“不战”。但是,如果将视野投向中西方战争文学的对比研究,就会发现,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大冈升平《野火》、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等战争历史题材作品,都明确地宣扬了反战意识。世界经典战争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在于其明确的反战态度和对人性本身的思考,以及对战后永久性伤害的描写。战争对人的伤害并不止于战争结束,它对人的精神压迫、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都有长久的影响。国内的抗战文艺作品比较专注于描写战争历史现场,而对于后续的、外部的、潜在的战争影响则挖掘得很不充分,对于民族文化的辐射思考比较欠缺,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也往往浮于表面。
如果国内高校历史剧能够在创作中与世界经典战争文学形成对话,便可以纠正夸张的民粹主义与英雄情结,跳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二元对立视角,从而进入到更为开放的交流空间,抛开狭隘的历史局限性,站在大民族文化传统意识传播的基准点上,传播健康、正直的民族文化观。1939年底,德国最富盛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因战争流亡瑞典,其间创作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具有鲜明反战意识的剧作,然而,同样描写战争和历史,布莱希特却并没有描写正面战场,也没有直观表现血腥、暴力与死亡,而是通过一个妄图发国难财的女人来斥责战争。国内高校抗战历史剧可以学习和借鉴《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叙述视角和书写方式,使创作不止步于给观众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抗战历史现场,而是超越了以往单纯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从而增加了浪漫主义、怪诞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的表达。
最后,高校剧社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舞台驾驭能力还有待加强,对剧场性的理解方式也可以更加多元化。现实主义的还原和浪漫主义的写意应同时充分运用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完整表现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重庆往事·红色恋人》的导演利用富有历史感和美感的诗意舞台,以营造阴森恐怖的生存境遇以及这段爱情的凄美。同时,校园剧社因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应该尽量调整对“战争伤害”的表现手法。情感的输出方式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而不局限于用近乎自然主义的写法描写血腥、暴力和死亡等伤害场面。刺激视觉和听觉等感官而形成的情绪是最为初级的,因而也是十分短暂的。对暴力伤害的叙事表达发生转变,连带着对汉奸和日寇的描写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低能的咆哮、无差别的杀戮、单一的残暴等特性表现应逐渐减少,情感输出方式富于变化,甚至是陌生化。剧场舞台设置如果富有象征意味,就可以通过某种特定的具体形象表现或者暗示某种观念、哲理或情感,甚至可以通过意识流等先锋手段辅佐完成戏剧的主旨表达。
高校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镇,青年大学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优秀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的文化使命。高校师生创作抗战历史剧,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逐步显现出它的美育实践与文化育人的功能。大学生是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又是文化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因此,以文化育人为目标、以创作抗日战争历史题材话剧为手段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富有战略意义的。抗战历史剧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创造价值;是建设学生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实践机会,具有重要的应用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