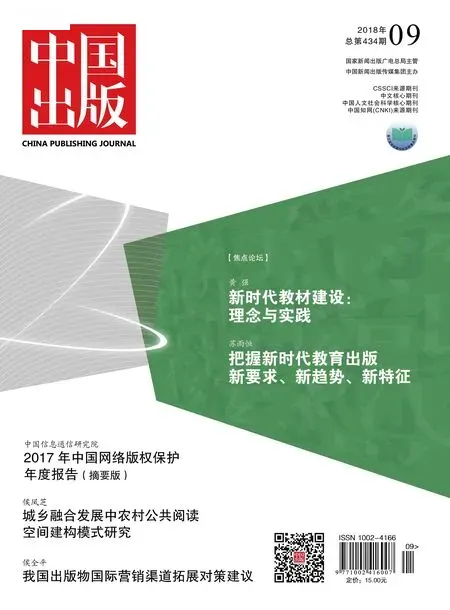论著作权转让的变动模式
——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五十九条
□文│吉 利 顾晨昊
著作权重复转让引发的纠纷一直是我国司法审判的难题。近年来,版权交易蓬勃发展,各地版权交易中心、在线版权交易平台兴起,著作权交易将越来越频繁,制度的完善也日益重要。2014年《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五十九条规定:“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的,使用者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专门登记机构登记。未经登记的权利,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有意建立著作权转让登记的公示制度,并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是否应当建立著作权转让的公示制度、以及著作权转让公示的效力应当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还是登记生效主义,业界都有争论。本文从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的法理出发,结合著作权自身的特性,对著作权转让公示的必要性、公示的效力、著作权登记的公信力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完善我国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的构建。
一、著作权转让公示的必要性
由于物权是一种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权利,具有绝对权、支配权和排他权的特性,因此物权的权利变更须经公示,才能让当事人和第三人直接从外部知悉它的权利状态。[1]从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角度而言,物权有公示的必要。
知识产权与物权具有绝对权、支配权和排他权的共性,为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和市场交易安全,也有公示的必要。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大多数种类知识产权的变动均需经过公示。
公示制度在著作权“少有建树”或备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著作权的权利初始取得采用自动取得原则,即创作完成时自动享有权利,无需履行任何手续,甚至也无需让任何人知晓。但是著作权的自动取得原则也并非与生俱来。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产生的初期均规定作品获得保护的前提条件是登记。而国家设立登记制度是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鼓励发表作品是基于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只有作品发表且作者表示了此愿望之后才予以保护,单纯地发表并不足以给作者带来这种保护。[2]只有在受著作权人格权学说影响较大的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才采用自动取得原则。自动取得原则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权利产生通行的方式,是因为《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均采用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为实现国际贸易达到这些国际条约的要求,成员国不得不修改或制定相应的国内法。
但是,国际公约采用自动原则,不宜看作是对作者人格权理论的全盘接受,否则就消弭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差异。我国《著作权法》采用自动取得原则是继受国际条约的结果。在我国的法律史上,并不存在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著作权人格理论,直接套用其理论解释我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妥适。著作权之所以能够采用自动取得原则是因为其自身客体的特殊性以及《著作权法》的事先安排。
首先,著作权的客体具有非简化的特征,即著作权法的调整对象在其所在的物质载体之外是不可能进行简化的。在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中,申请人必须描述其保护的对象和所主张的权利要求,但是在著作权中,作者向相关机构所提交的就是剧本、曲谱、图书等对象本身,而非其描述。[3]当然,这一点随着作品登记制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在作品登记中,通常通过登记有关作品创作的原始信息,如作品名称、作品署名、作品是否发表等信息代替对作品内容的描述。但这也表明,就权利初始取得而言,著作权并不能建立像专利权、商标权等其他种类知识产权一样的财产权登记制度,只能依靠客体的作品登记制度对著作权的权利取得作辅助证明。
其次,从著作权的制度设计上来说,《著作权法》已经通过“思想、表达二分法”“合理使用”等制度在权利产生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作出了合理平衡,著作权的自动产生不会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著作权的转让不会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权利的取得是否需要经过公示与权利的处分是否需要公示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物权法》中,非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其权利的产生也无须进行公示,但是在立法上对该权利的处分都作了限制以保护第三人,如日本与法国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德意志法系国家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处分。在实践中,著作权重复转让的纠纷也反映出著作权交易市场中第三人利益保护的现实问题。
因此,不管是从著作权自身绝对权、支配权与排他权的权利属性而言,还是从保护市场交易安全、保障权利人利益的客观需求而言,著作权转让都有公示的必要。虽然著作权权利的初始取得无需公示,但那是因为《著作权法》已经合理平衡了著作权的初始取得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著作权权利的处分依然会引起第三人的利益冲突。由于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不可转让,相较于一般物的转让而言,著作权的转让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纠纷,因为在没有公示的情况下,其他人很难知晓作品的署名人或创作者已非作品的真实著作权人,从而避免重复交易。因而,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并不违背著作权的自动产生原则,而是其权利属性的内在要求和著作权交易现状的客观需求。
二、著作权转让公示的效力与立法选择
公示的效力,是指公示对权利变动所发挥的作用。在物权法中,公示有公示对抗和公示要件两种效力。根据公示对抗主义,法定的公示方法为权利变动发生法律效果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即当事人只要达成权利变动的合意,就发生权利变更的法律效果,但是非经公示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公示要件主义则要求权利的变更只有经过公示才具有法律效果。《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即采公示对抗主义。
就规制重复转让而言,公示对抗主义在立法上无法有效遏制出卖人一物数卖。公示对抗主义下,自合同成立之时权利已发生变更,出卖人已失去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与处分权。但是出卖人无权处分并不意味着其不会处分。在此种情况下,权利变动后出卖人既没有丧失对标的物的实际占有,也没有办理权利移转登记。如果市场上物价波动较大,出卖人见利忘义,那么出卖人极有可能一物数卖,进行重复转让。此时,由于未经公示,前买受人无法对抗后买受人,而出卖人属于无权处分,但是后买受人却可以基于无权转让获得所有权,并且是较前买受人更优的法律地位,这在理论上难以自洽。[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法律明文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情形下,还不进行登记的买受人也不值得过多同情。[6]但是这无疑在法律之外强加给买受人一个“强制”登记的自觉义务,而在登记对抗主义下,买受人本可根据交易风险和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登记,即便买受人判断失误或心存侥幸,也不能成为法律不予保护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后买受人较先买受人获得权利的理论依据依然难以自足。为解决对抗主义下后买人获得所有权的理论依据,物权法学界提出了债权性双重让与学说、相对效力说、物权性双重让与说、公信力说等不同观点,但理论上均欠严谨。[7]
由是观之,从解决重复转让的现实问题出发,转让登记对抗的公示制度并不是有效的方式。而公示生效主义却并不存在以上的问题。根据公示生效主义,权利必需经公示之后才发生变动的效果。在权利人与受让人签订合同之后公示之前,权利人即便将该物转卖第三人,也属于有权处分,后让人完成公示即可取得权利,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逻辑问题。因此,在解决重复转让的问题上,不管是理论之严谨,还是实际操作之简易,公示生效主义都优于公示对抗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我国的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不宜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因为登记生效主义会对私法自治进行过度干预,影响交易效率,增加交易成本。[8][9][10]
就物权变动模式而言,“任何一种物权变动模式,绝非真理,而是特定国家基于自身传统、民族个性、社会现实做出的选择。”[11]公示生效主义与公示要件主义各有利弊,如何取舍端赖于制度构建的目标与价值取舍。从价值层面看,公示对抗主义重在倡导交易自由;公示要件主义重在维护交易安全。[12]但是公示要件主义强调交易安全时并非剥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仅仅是为其设定合理的边界。就交易效率而言,公示对抗主义也不一定就优于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下,权利变更无须公示,简化了交易程序,确实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是未经公示的物权变动即便公示也不具有公信力,又会增加第三人的征信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效率。[13]因此,就交易效率而言,公示对抗主义并未较公示生效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从交易自治来看,公示生效主义也仅仅是进行了合理地限制,并未过度干预。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的构建目标在于在现行交易自治的基础上提高交易安全,因而交易安全的价值目标应当优先于交易自治的目标。
三、著作权转让登记的公信力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不应采登记生效主义,因为我国目前的著作权登记尚不统一规范,著作权登记无法进行实质审查,难以保证登记的名义人是真实的权利人,著作权的登记制度没有“公信力”,因此并不适合采用登记生效主义。[14][15][16]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即便构建了转让登记对抗的公示制度,也不应当赋予其公信力。[17]这种观点既混淆了作品登记与著作权转让登记,也误解了公信力的制度内涵。
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制度还未正式建立,所以著作权转让登记表征真实权利的概率还无从谈起。而目前已经建立的作品登记制度与著作权的转让登记制度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登记制度并非版权或著作权登记制度,其登记的对象是作品的创作信息,而不是一种权利。我国实行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作品自愿登记制度。从性质上而言,作品之登记并非是一种权利之公示,因为著作权的产生无须公示,其不过一种证据,证明自己是作品创作者的一种方式。作品登记机关无须也不可能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审查,因为即便登记之作品的创作信息真实,也并不意味着该作品必然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认定其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不是作品登记机关的职责。而登记公信力保护的是第三人对处分人享有处分权的信赖,只有当登记簿显示处分人享有处分权,但登记错误时,公信力才发挥作用。[18]
也就是说,登记公信力之赋予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该登记须是一种权利登记,是一种公示手段。其二,登记公信力仅保护涉及处分权信赖的记载事项。而作品登记并非权利登记,登记也并非一种权利公示,作品登记簿显示的作品名称、作品署名、作品是否发表、作品创作完成日期、作品首次发表日期等属于不涉及权属状况的事实记载,并非登记公信力所保护的对象。作品登记的公信力自然无从谈起。作品登记制度没有公信力是因为该制度本身并不涉及公信力的问题,而并非因为作品登记证明著作权真实权利人的概率较低。
与作品登记不同,著作权转让登记的对象并非作品,而是权利。著作权转让登记权利表征之真实率与著作权转让公示变动模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并没有有效的统计数据表明著作权登记的权利表征之真实率过低或远远低于物权登记的权利表征真实率,也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要求权利登记之真实率达到何种程度才能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恰恰相反,登记公信力的适用前提就是存在登记错误,其实质在于排除登记错误对善意第三人的不利影响。[19]如果公示的权利与实质权利完全一致,则无采取公信原则的必要。[20]并且,就立法模式而言,权利变动的区分标准,是是否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作为权利变动发生效力的必要条件,所涉及的是权利变动公示效力的问题,而公信力涉及的是第三人是否应当受到保护、是否保护善意信赖物权表征方式的问题。[21]公信力的制度基础,在于节约物权的信息成本,并通过在物权保证方式传递的物权信息错误时,仍对善意第三人视为正确的方式实现。[22]公信力的制度内涵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是否赋予登记公信力在于是否承认登记的善意取得。
同时还需注意的是,意思主义与形式审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没有严谨的论证证明意思主义与形式审查有着不可切断的逻辑联系。[23]而试图通过实质审查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登记错误也是不可能的。审查成本应当与通过审查获得收益相当,过度审查会导致对私法自治的过度干预,也会影响交易的快捷。一般而言,登记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应当确认登记申请人为现登记权利人,而且该申请人有书面表达的登记意思,有正当的权利变动的原因,并正确记载新的登记权利人。至于债权行为的效力问题,不应是登记机关的审查范围。
综上所述,作品登记制度是否健全、转让登记反映真实权利的概率、作品登记或转让登记采形式审查或实质审查与著作权转让登记采对抗主义或生效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是否赋予登记公信力也与登记表彰真实权利的概率无关,而在于是否保护善意第三人。从减少信息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保障交易安全的角度而言,公示应当具有公信力。虽然在理论上,奉行公示对抗主义的日本民法一直否认对抗主义下登记之公信力,但却通过《日本民法典》中登记错误之对抗理论、预告登记等规则的完善对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作了充分的保护。[24]我国的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尚在起步阶段,异议登记、更正登记、预告登记等各项制度尚付阙如,在这样的情形下,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已实难保全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果再否认登记之公信力,则公示制度将形同虚设。
四、结语
著作权转让公示的必要性源于著作权与物权具有绝对权、支配权和排他权的权利属性特征。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维护第三人的权益,著作权的转让应当予以公示,与著作权初始权利的自动取得原则不相违背。就公示的效力而言,著作权转让变动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著作权法中保护善意第三人规则的完善以及对交易安全或交易自治价值目标的偏重。与作品登记制度是否统一规范、著作权转让登记反映真实权利的概率、作品登记证明真实著作权人的概率、作品登记或转让登记的实质审查或形式审查无必然联系。在我国著作权异议登记、更正登记、预告登记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尚付阙如的情况下,著作权转让登记的对抗主义模式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也无法实现提高交易安全、增进交易效益的制度目标,著作权转让登记制度将形同虚设。就规制著作权重复转让的现实问题而言,登记对抗主义在理论上难以自足。因而,不管是从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保护第三人的制度构建成本而言,还是解决著作权重复转让的现实问题而言,我国应当建立著作权转让登记生效的公示制度。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注释:
[1][2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胡开忠等.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布拉德·谢尔曼,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英国的历程(1760-1911)[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11][13][23]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9]黄玉烨,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7]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版)[M].陆庆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李雨峰.版权登记制度探析[J].知识产权,2008(5)
[10]文杰.我国版权登记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完善——从版权“一女多嫁”谈起[J].出版发行研究,2011(5)
[12]渠涛.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研究与中国的选择[J].法学研究,1999(5)
[14]董美根.论版权转让登记的对抗效力——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59条[J].知识产权,2016(4)
[15]李杨.著作权公示的制度解读及效力重塑[J].电子知识产权,2008(5)
[16]陈爱碧.著作权重复转让中的权属认定[J].知识产权,2017(9)
[17]唐艳,苏平.论著作权转让与登记制度型构——兼论对民法物权理论的借鉴与扬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8][19][21][22][24]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