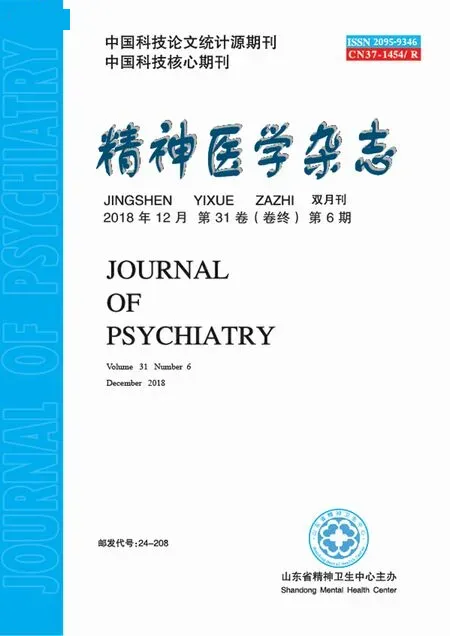嘌呤能系统在精神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卢 喆
任何原因导致的神经递质系统功能改变以及与其他系统相互关系的不平衡都可能表现出精神活动的异常。除了公认的单胺类神经递质、谷氨酸/γ-氨基丁酸神经递质系统之外,嘌呤能系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系统,参与了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发展[1]:腺苷与腺苷受体(P1受体)结合后,IP3、cAMP、Ca2+等第二信使水平发生改变,调节了神经递质或神经肽的释放;ATP受体(P2受体)分为P2X和P2Y两大类,ATP与P2X受体结合后,通过配体门控离子通道(Na、K和Ca)调节快速反应,ATP与P2Y受体结合后,则通过G蛋白激活第二信使系统,从而调节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释放。
1 嘌呤能系统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证据表明ATP和相关核苷酸可以作为神经递质,ATP水解产生的二磷酸腺苷(ADP)、腺苷一磷酸(AMP)和腺苷(ADO)也参与了细胞间的信号传导。这些核苷酸的功能受一组酶的调节,包括外核苷三磷酸二磷酸水解酶(E-NTPDases)、核苷酸焦磷酸酶/磷酸二酯酶(NPP)、碱性磷酸酶(ALP)和外蛋白-5-核苷酸酶(e5NT或CD73),这些酶催化完整的核苷酸分解产生ADO。除此之外,ADO也可以由S-腺苷高半胱氨酸(SAH)的裂解产生。神经末梢的转运蛋白可以吸收ADO,并通过腺苷脱氨酶和黄嘌呤氧化酶(XO)产生下游产物尿酸(UA),UA水平的升高加速了嘌呤能转化并减少了腺苷能传递。UA等产物作用于突触前和突触后神经元以及胶质细胞膜中的特异性受体(嘌呤能受体),可以影响其他神经递质的活性,包括多巴胺、γ-氨基丁酸、谷氨酸和5-羟色胺,这些递质都参与了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除此之外,嘌呤能系统也是中枢神经系统与外部系统(如免疫系统、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
嘌呤能受体根据其生化和药理学特性,可以分为P1和P2受体。P1受体是代谢型受体,对ADO敏感,可细分为A1、A2A、A2B和A3受体,分布在多个脑区域中,包括前脑、纹状体、基底神经节以及多巴胺能和谷氨酸能神经元。除A2B受体之外,A1、A2A和A3受体对其配体具有高亲和力。A1和A3受体的激活能够抑制cAMP的产生,与之相反,A2A和A2B受体激活则刺激cAMP的产生。由腺嘌呤核苷酸分解代谢形成的ADO优先激活A2A受体,而由特定核苷转运蛋白释放的ADO则激活A1受体。P2受体分为P2X和P2Y受体,可以被核苷二磷酸和三磷酸(ATP、ADP、UTP、UDP或UDP-葡萄糖)激活。P2X受体是ATP门控离子通道受体,包含七个受体亚基(P2X1-P2X7)。P2Y受体是代谢型受体,可以分为P2Y 1、2、4、6、11、12、13和14亚型,它们在接受ATP、ADP、UTP和UDP-葡萄糖的刺激时的激动特性不同。
嘌呤能系统参与神经发育和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如细胞增殖分化和神经元-胶质细胞的炎症等。P1受体能够调节突触的可塑性和神经递质释放,P2受体则与胚胎神经发育密切相关,任何嘌呤能系统功能的紊乱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2]。
2 嘌呤能系统与精神分裂症
ADO在谷氨酸能和多巴胺能的信号传递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正因为如此,ADO被视为是一种参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CH)病理生理机制的重要神经递质[3]。A1受体的激活抑制了谷氨酸和多巴胺的释放,同时减少了NMDA受体诱导的离子电流,与之相反,A2A受体的激活诱导了纹状体和皮质区谷氨酸的释放,多巴胺D2受体的激活则能够降低谷氨酸释放,这三种受体互相聚合可形成A2A / D2或A1 / A2A二聚体。由于ADO对A1受体具有更高的亲和力,而且A2A受体的活化降低了A1受体对激动剂的亲和力,其中低或高的ADO浓度分别抑制或促进谷氨酸释放,因此A1 / A2A异聚体的出现可能是一种转换机制[4]。
A2A受体缺陷的小鼠在解剖学(脑室扩大)以及行为的改变(惊吓习惯的减少和前脉冲抑制)与SCH患者相似[5]。通过药物抑制ADO激酶,ADO水平升高,可以使SCH动物模型的精神病性症状改善;在过度表达ADO激酶小鼠的纹状体中移植ADO释放细胞,可以使其恢复对苯丙胺的运动反应性,当ADO释放细胞移植到海马体内时,则可以逆转认知功能的损害[6]。此外,与健康人群相比,SCH患者死后,其纹状体中的外核苷酸酶活性降低及ADO水平降低[7]。虽然这些关于ADO受体表达的数据提示SCH患者的ADO功能降低,但对此还应该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约50%的SCH患者中并未观察到A2A受体表达的减少,提示这种状态可能仅存在于SCH患者的某种亚型中[8]。据此,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就是SCH的发病可能是由A1受体和A2A受体活性之间的不平衡引起的。有研究表明,SCH患者的纹状体中A2A受体蛋白和mRNA的表达降低,而A1受体的表达没有发生改变[8]。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在一些SCH患者中观察到A2A受体表达的上调,这可能提示,不同患者间ADO功能减退的补偿和适应机制或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反应不同[9]。腺苷脱氨酶(ADA)22G/A基因型的活性低于G/G基因型,其表达可能与较高的ADO浓度有关,有研究发现SCH患者的这种基因多态性频率显著降低[10]。尽管ADO参与SCH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但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证实A2A受体多态性是SCH的危险因素,但A1受体和ADA的遗传变异是可能的SCH候选标志物。
研究表明,丙氯拉嗪和三氟拉嗪对人体P2X7受体活性起到了变构和负调节的作用,据此,可以推测抗精神病药能够通过抑制P2X7受体来起到治疗效果[11]。在动物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通过药物阻断和遗传沉默P2X7受体,可以减轻SCH动物模型中的SCH样行为,这些数据提示P2X7受体可能参与调节SCH的症状[12],然而,编码P2X7受体基因多态性却与SCH的发生无关[13]。
嘌呤能系统为SCH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项开放式临床试验表明,氟哌啶醇联合双嘧达莫(一种ADO摄取抑制剂,增加突触间隙中ADO浓度)治疗的患者与单用氟哌啶醇治疗的患者相比,联合用药组患者的阳性症状有较大改善[14]。另一项联合别嘌呤醇(ADO代谢降解抑制剂)治疗难治性阳性症状患者的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15]。但是,当双嘧达莫或别嘌呤醇单一用药时,均未对SCH患者起到治疗作用[16,17]。
3 嘌呤能系统与双相障碍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ADO通过谷氨酸能系统在兴奋性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的相互作用中起重要作用,用于治疗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的锂盐直接靶向腺苷能系统,抑制了外核苷酸酶活性,阻止了ADO的积累[18]。A2A受体与BD的部分症状相关,拮抗A2A受体和敲除A2A受体分别增加了运动动机和目标导向行为[19],此外,A2A受体拮抗作用与咖啡因的唤醒作用相关,但是A2A受体敲除所产生的效应是大脑区域特异性的,纹状体中A2A受体敲除影响了习惯的形成和精神运动活动的增加,而纹状体外或前脑中A2A敲除时表现为活动减少。在动物模型中,A2A受体激动降低了苯丙胺诱导的运动活动和行为不安,相反,A2A拮抗作用既增加了小鼠的运动行为,也克服了多巴胺受体拮抗诱导的运动活动减少[19]。
嘌呤能系统的调节与严重的情绪变化有关,已经在BD的个体中发现遗传表达以及外周和中央生物标志物的改变。有遗传学研究也已经显示了BD中的嘌呤能靶点,例如,有研究发现编码线粒体DNA的SNP与BD诊断以及BD受试者的脑pH相关[20]。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显示,躁狂患者的cAMP,蛋白激酶C(PKC)和细胞内钙水平存在改变,这一发现证实了BD中ADO受体下游信号传导功能失调[21]。此外UA也涉及了BD的病理生理学,特别是冲动性和兴奋寻求行为,UA水平也与特定的性状特征相关,包括驱动和去抑制,这两者在躁狂发作中都很常见[22]。在急性躁狂发作中可以观察到UA水平升高,表明嘌呤能转化增加,且外周UA水平与中心水平呈正相关[23]。在不同研究中,这些标志物的水平与症状严重程度和躁狂症状的改善呈正相关[24],但至少有一项研究并未得到阳性结果[25]。近期一项荟萃分析证实了BD患者的UA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且BD患者的UA水平显著高于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相关的回归分析指出,年龄和性别的变化可能会减轻BD受试者和MDD受试者的UA差异;不同双相期的比较显示,与抑郁期的受试者相比,躁狂或混合发作期的受试者的UA水平增加,但是这种差异很小,相关的敏感性分析表明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研究间的异质性所致;此外,双相缓解阶段的受试者和躁狂或抑郁阶段的受试者之间并没有发现明显差异;这些结果提示UA作为双相情感障碍状态标志物的证据是弱的[26]。
嘌呤能系统为BD提供了一系列潜在的治疗靶点,并且针对嘌呤能系统的药物制剂的临床试验已经有了阳性结果,最近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别嘌呤醇治疗BD的临床潜力。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显示,与双嘧达莫组和安慰剂组相比,别嘌呤醇(600 mg/d)合并锂盐组显著减轻了BD患者的躁狂症状[27]。使用别嘌呤醇(300 mg/d)作为锂盐和氟哌啶醇的佐剂的类似试验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28]。但有一项研究发现,在经历急性躁狂发作的BD患者中,别嘌呤醇组(较低剂量,300 mg/d)和安慰剂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这项研究并没有排除各种情绪稳定剂和抗精神病药的影响[29]。一项4周、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显示,与安慰剂相比,使用别嘌呤醇(300 mg/d)作为丙戊酸盐的附加治疗,显示出显著的抗躁狂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呼应,该研究还发现了较低的UA水平与终点症状改善相关[30]。最近对腺苷调节剂与安慰剂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也支持这些药物作为双相躁狂的辅助药物,特别是别嘌呤醇[31]。
4 嘌呤能系统与抑郁障碍
MDD是由急性或慢性压力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异常激活所致的糖皮质激素水平改变有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激素的释放都受到ADO受体的调节,例如,ADO激活A2受体增加了肾上腺皮质酮的合成,而且拮抗A2受体可以阻断这一作用。A2A受体过表达促进了皮质酮水平的改变,增强了突触可塑性和糖皮质激素导致的记忆障碍,这些证据表明A2A受体特异性参与控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并且调节糖皮质激素的活动[32]。抑制性A1受体和兴奋性A2A受体的激活能够促进谷氨酸能和单胺能系统的突触调节功能,并且与突触可塑性和神经保护作用相关[33]。
神经元A1受体表达增加对转基因小鼠的抑郁样行为有急性或慢性的改善,而A1受体敲除的小鼠则表现出相反的效应,表现为抑郁样行为的增加[34]。慢性不可预测压力(CUS)模型,是一种MDD的动物模型,与皮质酮水平升高、海马回路异常、情绪改变以及记忆能力下降有关[35]。在CUS模型中,使用选择性拮抗剂KW6002阻断A2A受体和A2A受体的基因缺失对MDD的预防及治疗均有效[36],这表明A2A受体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生物标志物。
ATP浓度的轻微失衡便可能导致大脑中广泛的信号变化,并且可能导致行为改变,在社会压力诱导的MDD动物模型中,反复社交失败的动物表现出脑ATP水平降低,通过转基因阻断星形胶质细胞释放ATP可以诱发社交失败小鼠的抑郁样行为,在补充ATP后则产生了抗抑郁样作用(强迫游泳试验中的不动时间减少)[37]。
P2受体的过度活跃与MDD的发生相关,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P2受体拮抗剂(PPADS)具有一定的抗抑郁和抗焦虑作用[38]。小胶质细胞上的P2X7受体激活能够促进其释放与抑郁行为相关的炎症标志物[39],P2X7受体拮抗剂则产生了抗抑郁(强迫游泳试验)和抗焦虑样作用。除此之外,与野生型动物相比,P2X7受体敲除的小鼠在重复强迫游泳试验中显示出较强的恢复能力[40],这种抗抑郁效果可能与白介素-1β释放的抑制有关[41]。在基因研究中,P2X7低转录与MDD相关,且在自杀者的研究中发现了较低的mRNA表达[42],一些研究结果将rs2230912(P2X7受体基因,Gln460Arg)多态性与临床结果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多态性可能与MDD的严重程度相关,而不是与MDD的风险相关[43],但这些发现均表明P2X7受体基因在MDD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潜在的关键作用。另一种可能具有治疗重要性的受体是P2Y1受体,该受体由星形胶质细胞表达,可以促使星形胶质细胞中的钙通量改变以及促进突触前多巴胺和谷氨酸的释放[44]。
嘌呤能系统生物标志物包括ATP代谢酶(例如XO,ADA和CD73)、黄嘌呤、UA及其代谢产物。早期的研究显示脑脊液中的嘌呤代谢物次黄嘌呤和黄嘌呤水平与抑郁症状相关,较低的黄嘌呤水平与抑郁症状相关,这与单胺能系统的激活有关。一项研究发现,与健康受试者相比,MDD受试者的血清ADA和XO水平显著升高。在该研究中,ADA水平升高与疾病的持续时间呈负相关,且在抗抑郁治疗后ADA水平升高,提示ADA水平可能是MDD的生物标志物。此外,XO水平随着抗抑郁治疗而降低,表明MDD中的嘌呤能系统功能失调受到了药物干预的影响[45]。一项关于治疗和未治疗MDD患者UA水平的荟萃分析显示,与健康对照相比,MDD个体的UA水平显著降低,还指出UA水平受治疗状态的影响,而不是MDD这个诊断,从而提出了UA水平可能是代表MDD的状态标志物,但这种关联中涉及到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以及症状严重程度和UA水平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46]。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嘌呤能系统的各种成分参与了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该系统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嘌呤能信号传导与其他神经递质、神经调节剂、神经肽和神经营养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更为精细的分子机制需要进一步被阐明;(2)需要探索嘌呤能系统的可靠的外周生物学标志物。尽管研究提示UA水平在不同精神疾病中有差异,但受到较小样本量以及未能严格控制的混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果;(3)将嘌呤能系统基础研究所取得的结果转化为临床应用,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