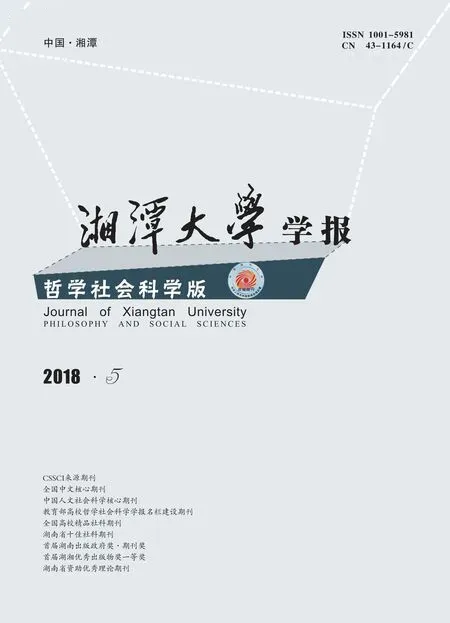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探微*
谢 芳
(衡阳师范学院 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8)
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期发表的《王夫之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一文,即揭示了王船山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共同伦理维度就在于“皆奖自由而恶干涉”(勇立,1906);民国时期学人郑行巽《王夫之之经济思想研究》一文重点分析了船山经济思想中重民生之伦理维度;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李守庸出版《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被称为是“使王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成果(肖箑父,1989),该著在融通王船山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王船山的货币观、财富观等的分析,探析了他在理与欲、义与利、公与私等方面的伦理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王船山经济思想中蕴含着的深厚的伦理关怀及其历史地位。王船山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丰富,货币伦理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实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在王船山著作中并没有直接提出“货币”这个概念。但笔者梳析王船山相关著作发现,其中反复提到并深入论述的“金钱”“百物之母”等概念之基本精神与现代性概念“货币”几乎通义。王船山立于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科学地分析了货币(金钱)的“百物之母”的媒介本质,指出了货币是一种具有手段善价值的经济现象,货币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无论何种形式的货币都不具有目的善价值,也不应该成为人们追逐的终极对象。同时,王船山前瞻性地洞悉了货币的价值幻相、货币与人性迷失之间的关系以及纸币形式下的诚信风险,并提出解决对策。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王船山的货币伦理思想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方面研究成果更是少见。据此,本文试图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关注。
一、货币的本质:“百物之母”特性下的“价值幻相”
我国古代,货币现象很少引起思想家的理论思考,这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货币使用频率还不够高,另一方面源于货币在传统社会履行的职能主要为简单的流通手段,尚未成为财富或者其他标榜身份地位的象征。到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货币越来越频繁,货币履行的职能越来越复杂化,甚至使人伦关系也越来越扑朔迷离,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思想家的兴趣,开展了从货币起源、发展到货币本质的理论审思。王船山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刻地分析了货币起源问题,并在探讨货币形式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触及到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即货币的价值幻相问题。
王船山突破了古代关于货币起源的“圣王创制说”,试图从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寻找货币起源的根据。他说,“古之税于民也,米粟也,布缕也。天子之畿,相距止于五百里;莫大诸侯,无三百里之疆域;则粟米虽重,而输之也不劳。古之为市者,民用有涯,则所易者简;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则所赍以易者轻。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无,而授受亦易。至于后世,民用日繁,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输于国、饷于边者,亦数千里而遥;转挽之劳,无能胜也。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1] 111通过对比“古” “今”经济发展之现状,王船山揭示了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扩大的道理。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产品也非常简单,商品交换是非常简单的物物交换。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物交换变得不可行,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交换媒介,通过这种商品可以全面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于是国家因势所趋制定了以金钱为代表的货币。王船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条件下交易量和交易范围扩大而造成的交易困难。我们可以看到,王船山从唯物主义视角,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探寻货币的社会起源,并认为“民之所趋”是“国之所制”的逻辑和历史的前提。与传统的“圣王创制论”相比,王船山的货币起源论凸显出了不同的伦理维度,“圣王创制论”着重强调 “仁治”或者“仁政”,意在强调权力对经济的外在作用力;而王船山的货币起源论则强调人们在商品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对“交换媒介”的“共同认同”,这种“共同认同”逻辑地蕴含着一种伦理约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到底是什么或者货币本质的问题上,王船山有更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货币的伦理本质是 “百物之母”,即货币与一般商品的关系是一种“以与百物为子母”的关系。[2] 1055所谓“百物之母”即指用以权衡其他物品的价值标准,这道出了货币具有手段善的价值本质。但随着货币性能的扩展,它不仅成为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标准,而且成为了财富的普遍象征和代表,即 “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2]1058货币作为财富代表的这种外在的价值性,因而具有了增值的本性,继而成为经济主体相对独立地、不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而追求的对象。这就意味着在商品世界里,货币处于价值世界的最顶端,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价值标准,并最终抹杀了不同商品之间的异质性,成为人们信仰和追逐的对象。
王船山前瞻性地洞悉了货币由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张对社会“正在形成”的价值导向作用。他指出,货币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或者价值符号,并不是货币本身具有高价值,即“非宝也”。只是因为它们有“可宝之道焉”,即“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唯然,而可以经久行远者,亦止此而已矣。”[1] 111-112金银铜铅充当货币源自于它们稀有、难炼、难铸等特殊的物理特性。金属货币本身“非宝”,却在经济生活中成为了一切价值的代表和衡量标准,这就潜在地揭示了货币容易让人们形成一种观念上的“价值幻相”。
王船山接着从历史上货币形式的不断变化来进一步说明货币的“价值幻相”本质。他说,“且夫金银之贵,非固然之贵也。求其实,则与铜、铅、铁、锡也无以异;以为器而利用则均,而尤劣也;故古者统谓之五金。后世以其约而易齐也,遂以与百物为子母,而持以求偿,流俗尚之,王者因之,成一时之利用,恶知千百世而下,无代之以流通而夷于块石者乎?”[2] 1055社会最终选择金银等贵金属充当货币,淘汰掉了铜铁等贱金属,因为金银具有“约而易齐”的特性,可就其实用性而言,甚至比不上铜铁,那怎么知道在以后的千百年里,不会有别的东西充当货币,而金银却如同卑贱的石头一样呢?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价值幻相”本质,如同马克思所言,货币在流通中“只执行虚幻的金的职能”。[3]106船山的此种论说在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地位。
二、货币与人性迷失:“天下益汲汲于金钱”
王船山积极地肯定了货币的经济功能,商品因为货币这个媒介能够及时、顺利地进行交换流通,因而不会出现商品堆积、国家财政短缺的情况。而且指出商品能不能转化为货币是“民日以贫”还是“民日以富”的根本原因,“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纴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民贫而赋税不给,盗贼内起,虽有有余者,不适于用,其困也必也。”[2]1058-1059
但在肯定货币带来“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的经济繁荣景象的同时,王船山对货币可能带来的人性异化也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货币成为价值标准继而成为财富的象征后,人们生产或者交换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社会出现“金夺其粟之贵”的异化现象。[2]111人性贪念之恶被激发出来,出现了疯狂违法开采金矿以攫取金银的现象,甚至出现“烧药为金”等制造假钱的丑恶现象等;[2] 1055自此形成了天下人造假的风气,连君主都受其迷惑,“自汉武帝惑于方士,而天下惑之”,[2]1055“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盖为伪金以欺天下,鬼神之弗赦也。”[2]1055总而言之,货币从衡量价值的手段变成了实现价值的目的,人们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金银货币,以至于严刑酷法也无法阻止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天下益汲汲于金钱,徒以乱刑赏之大经,为败亡之政而已矣。”[2]112
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拥有货币的多寡便等同于拥有财富的多寡,是衡量国家、家庭、个人贫富的标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船山认识到了,以追求货币形式的财富创造和利益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社会发展伦理道德的。但王船山亦深刻地洞悉到,货币作为衡量社会财富的权威标志,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追逐私利的人性驱使着人们无限地追求货币,竞相追逐金钱。一方面对金钱的过度索求,使个人的生存价值变为可以用数字来计量的货币价值,消解了人存在的崇高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转化为冷冰冰的纯粹功能性的交换过程,在金钱万能的价值观下,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能做出来,此乃“乱刑赏之大经”,亦“为败亡之政”;另一方面,货币作为“百物之母”的原初作用发生异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货币本身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真正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货币由原本的手段或者工具价值变为了目的价值。这种货币经济一旦形成,将突破时空乃至等级身份的限制,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统一价值的衡量体系,必将导致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被货币的抽象等价性消融,进而危及到封建的统治政权。无疑,这也是王船山批判人们汲汲于金钱的一个重要伦理维度,自然也使他的货币理论裹挟了无法解脱的局限性。
三、纸币形式下的“道德风险”:“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1023年),也是第一个终止纸币流通的国家(明1426—1435年)。关于宋朝纸币出现的前因后果、意义以及不同时代纸币的形式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宋朝开始流通的纸币体系为何在明宣德年间突然崩溃?有研究学者主要从经济学视域寻找缘由,其中以张彬村为代表,他指出,纸币短暂退出历史舞台主要根源于明朝实行的“不兑换纸币”和“保守退缩的发行”政策导致。[4]28-40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错误的货币政策只是导致纸币体系崩溃的契机,而不是其内在根源,错误的货币政策契机之下更有深层的伦理逻辑。王船山则立于社会历史现实考察的基础上,从伦理视域揭示了宋明纸币短暂引退历史的深层逻辑。王船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来,不复能行于天下。”[1]112一个“欺”字,深刻地道出了宋明以来纸币形式遮蔽下的社会“道德风险”,即全社会自上而下的“诚信缺失”是纸币体系崩溃的深层伦理根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纸币作为一种自身没有价值的价值符号,“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3] 106由此可见,一种真正进步意义上的纸币的产生不外乎两个条件:即“公认”和“法定”,从其前后两者的顺序来讲,“公认”应该是“法定”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即“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中产生的”,[3]104可见,纸币是一种以“诚信”为基础而由国家发行的货币符号,或者说纸币与其说是一种“法定货币”,更不如说它是一种“信用货币”。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说,信用货币产生直接的逻辑前提并不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由商品经济所决定的信用关系的水平。”[5]21-29
王船山正是在对宋朝纸币的历史考察中深刻地揭示了纸币形式下的“诚信风险”。
第一,纸币由于其“可造”、“速裂”、“可改”等特性,因而成为“官骗商”、“商骗民”的主要手段,人们之间互相欺骗并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作伪”的逆道德现象。他说,“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1] 112交子作为一种货币符号是用纸张和墨等原料做的,只要具备这些原料,就可以任意制造出来;纸币还不能作为财富来贮藏,因为纸币是依靠国家强制发行流通的,一旦国家改变货币政策或者发生朝代更替这样的大变动,原来通用的纸币就会变得一钱不值。这种权力垄断下的纸币体系不仅隐藏着严重的经济风险,比如通货膨胀,更隐藏着严重的“道德风险”,比如“欺骗”盛行。
第二,纸币成为政府解决财政短缺的一种逆经济手段。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国家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根本手段应该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方式来获得。发行纸币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交换,促进经济顺畅流通,提高商品经济的效率。但宋明时期纸币由最初的弥补“钱荒”之用,到最后成为统治者赤裸裸地剥夺百姓财富的财政手段,不但没有提高商品经济的效率,相反抑制了商品经济的高效发展。船山批判说,从宋到明,统治者利用纸币“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忍为此,亦不仁之甚矣!”[1]112船山的这一批判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自宋以来至明清时期,历朝都采用通过强制性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方式,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样纸币的“通货”作用已退居其次,而国家的财政利益则摆到了决定发行纸币数量的首要地位了。
王船山对货币经济现象展开的伦理审思,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他充分肯定了货币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手段善价值,同时又非常深刻地洞悉了纸币形式下隐藏的人性迷失和道德风险。船山对货币经济发展的前瞻性预测,为更深入地认识货币与人性、货币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对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值得关注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