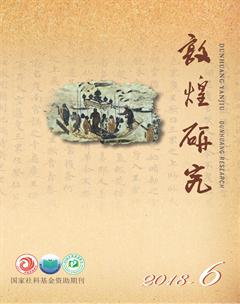新疆龟兹研究院院藏彩绘泥塑调查简报
吴丽红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对龟兹研究院院藏彩绘泥塑造像进行初步整理。院藏保存较好的可辨识的造像共44件,有代表性的15件,按其特点分为五类:彩绘泥塑头像残件、彩绘泥塑身躯残件、彩绘泥塑手残件、彩绘泥塑花饰,动物与须弥山等归为其它类。
關键词:彩绘泥塑;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佛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6-0032-06
新疆龟兹研究院保存着出自龟兹石窟的文物,包括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马扎巴赫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温巴什石窟、阿艾石窟等9处石窟清理发掘和采集到的珍贵文物。
一 彩绘泥塑入藏情况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相关要求,新疆龟兹研究院展开了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把院藏的这批文物做了初步整理并逐一分类,有泥塑、陶器、木简、木器、钱币等。总计完成整理654件(套)可移动文物,尤为突出的是146件(套)彩绘泥塑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2件。
院藏彩绘泥塑有数次大批量入藏。1982年库车文管所时期入藏的库木吐喇石窟大沟区第7窟后室清理发掘的出土品。1984年库车文管所时期入藏的库木吐喇石窟大沟区第41窟前廊清理发掘的出土品[1]。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维修施工时入藏的谷西区中段清理发掘的出土品。1990年入藏的为配合克孜尔千佛洞第一期维修工程对谷西区中段与东段窟前堆积物清理发掘的出土品。1994年入藏的森木塞姆石窟群第32窟堆积物及后甬道清理发掘的出土品;2000年入藏的克孜尔千佛洞谷内区加固工程所涉及洞窟进行了部分考古清理发掘的出土品[2]。
龟兹石窟所出的不少彩绘泥塑及壁画于上世纪初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院藏彩绘泥塑就显得尤为珍贵。本文试对彩绘泥塑残块作进一步整理,并对它们的年代、形象、位置以及风格特点等做初步讨论。
二 彩绘泥塑的分类整理
院藏彩绘泥塑按其保存现状基本可辨识出头像类残块34件(套)、身躯残块51件(套)、四肢残块30件(套)、饰品残块23件(套)、小动物残块4件(套)、须弥山残块5件(套),较好的可辨识的造像共44件,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15件,按其特点分为五类:彩绘泥塑头像残件、彩绘泥塑身躯残件、彩绘泥塑手残件、彩绘泥塑花饰,动物与须弥山等归为其它类。
(一)彩绘泥塑头像残件
1. 总登记号:XQ0032。彩绘泥塑佛头(图1-1),高21厘米、宽17厘米,质量1.45千克。佛发浅浮雕,螺髻施蓝色,左端残。面部保存基本完好,面敷白粉,脸部丰满。眉、眼墨线勾勒,眉间有白毫,鼻脊狭长挺拔,鼻端略残,唇填朱砂红。左耳残,右耳尚存。左脸部颜料剥落,下颌部有几道细小裂纹,头背面有一凹槽。1974年克孜尔新1窟出土。
2. 总登记号:XQ0035。彩绘泥塑头像(图1-2),高18.5厘米、宽15厘米,质量1.960千克,头像大体完整,左眼、鼻、上唇略残。卷发浅浮雕着黑色,额间阴刻三道皱纹,双目微阖,口部略张,牙齿外露,面目狰狞。左眼、鼻、上唇、左颧骨修复,面部的红泥及木棍为后来修复时抹装。头像背面修复部位有裂纹。面部施白粉,大部分脱落。1994年出土于森木塞姆第32窟。
3. 总登记号:XQ0042。彩绘泥塑供养人头像(图1-3),高8.5厘米、宽5.2厘米,质量0.21千克,五官俱全,带帽,面敷白粉,多已脱落,额际、颈部残留石绿。额间浅刻两道皱纹,鼻脊高耸,嘴角内抿。武士形象。红色泥及木棍为后来修复抹装。头像背部修复平整。1994年森木塞姆第32窟出土。
(二)彩绘泥塑身躯残件
1. 克孜尔第130号。贴壁的彩绘泥塑像(图2-1),长23厘米,宽12.2厘米,厚5.6厘米。薄裙衣纹为蓝色,裙带系在左腰处,泥塑臀部向左侧凸起。背面抹平,现已加固。1990年克孜尔第90—19窟出土。
2. 克孜尔第22号。上半身残块(图2-2),长22.1厘米、宽16.1厘米、厚11.4厘米,头及胳臂残失,肚脐以上胸像,阴刻线纹胸衣,胸衣外缘刻有连珠纹,表面残留白粉、红色、黄色。连接头部和下肢的木骨架脱落。1974年克孜尔新1窟出土。
3. 总登记号:XQ0390。彩绘泥塑佛残躯(图2-3),长14.5厘米、宽8厘米,质量0.70千克,佛像上半身,翻领通肩袈裟,阴刻衣股自右向左披覆,头部及胸以下残断,身体表面敷红色。塑像背部平直,中部留有连接头部及下半身的木棒。1974年克孜尔新1窟出土。
(三)彩绘泥塑手臂残件
1. 总登记号:XQ0349。彩绘泥塑左手残块(图3-1),长13.5厘米、宽10厘米、厚5.5厘米,手做伸展状,五指完整,大拇指打开,四指上敷泥塑花朵,掌内肌肉纹理清晰,面敷白粉,手掌部分多已脱落。
2. 总登记号:XQ0436。手眼残块共有10只,其中3只左手、7只右手。彩绘贴塑左手残块(图3-2),长16.5厘米、宽9.5厘米、厚0.5厘米,手做伸展状,掌内肌肉纹理清晰,掌心墨绘眼睛,柳叶状、单眼皮、有瞳仁和眼白,面敷红色多有脱落,贴敷泥皮。
3. 总登记号:XQ0409。彩绘泥塑左手臂残块(图3-3),长68.5厘米、宽9厘米,手做伸展状,五手指前半部残失,掌内肌理清晰,胳膊健硕,带臂钏、腕镯,露出稻草骨架,面敷白粉多有脱落。
以上三件均为1984年库木吐喇第41窟出土。
(四)花饰
1. 总登记号:XQ0460。彩绘泥塑花条饰(图4-1),四条,均为六朵,用泥片塑出圆形的花瓣,花心微凸为白色,花瓣分别为红色、黄色、淡绿色、白色,贴敷泥条上,现已加固。
2. 总登记号:XQ0466。彩绘泥塑花饰品(图4-2),两个耳坠用白色花朵连接白色串珠组成。一个圆形红色花心外有两圈白色连珠纹组成的花饰。其余十个花骨朵含苞待放,两朵红色,八朵白色。
3. 总登记号:XQ0381。泥塑浮雕花,长12.5厘米、宽11.5厘米、厚2.5厘米,四层花瓣,层层叠放,花心为白色,花瓣有红色、粉色、绿色、黄色。
以上三件均为1984年库木吐喇第41窟出土。
(五)其它
1. 总登记号:XQ0370。泥塑龙头残块(图5-1),长10.5厘米、宽6厘米、高5厘米,仅存头部,张嘴瞪眼,形象生动。面敷白粉。
2. 总登记号:XQ0084。泥塑小鸟,长5厘米、宽7.9厘米、高1.6厘米,一只做工比较粗糙简单的小鸟,没有脚部,翅膀用阴刻线简单表示,鸟头直立。面敷白粉,脱落处漏出红色底色。体内留有插棍。
3. 总登记号:XQ0385。泥塑山形残件,长26厘米、宽25厘米,一大三小乳突组成的山形泥塑,在大乳突顶部及小乳突之间均有小孔。表面残留有红色、黄色和白色。
以上三件为1989-1990年克孜尔谷西区出土。
三 对彩绘泥塑的认识
根据上述分类整理,笔者就彩绘泥塑的时代、形象、位置以及风格特点等提出以下初步认识。
(一)彩绘泥塑年代
以上出自克孜尔新1窟、第60窟、第90-19窟和森木塞姆第32窟的彩绘泥塑头像、身躯残件及动物造像等,在造像风格及雕塑方法等方面有相似特点,它们大体是同一阶段的作品。其中“新一窟”的开凿年代大约为7世纪中叶[3],而克孜尔石窟开凿的衰落期在8世纪中叶[4],由此推测这批彩绘泥塑的时代大概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
彩绘泥塑手臂残块、花饰都出自库木吐喇第41窟,库木吐喇第41窟开凿年代为9世纪中叶[5]。第41窟洞窟多半塌毁,塑像也已毁坏,正壁现存低坛,坛上可能有塑像,手眼残块是在窟内堆土中清理出来的,大概就是低坛上塑像的一部分。据此推测这批手臂残块及花饰的时代为9世纪中叶及稍后。
(二)彩绘泥塑形象的辨识
在彩绘泥塑中除了佛、武士及一些动物形象比较明确外,其它一些残件通过参照壁画及塑像,可对它们的形象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1. 举哀形象的彩绘泥塑头像(图1-2)。双目微阖,口部略张,牙齿外露,面目狰狞,面部表情作痛苦状的人物,推测是涅槃图中出现的举哀形象。
2. 天人形象(图6:克孜尔第80窟后甬道右侧壁)。下身着裙装和上身着胸衣残件以及配有臂钏、腕钏的手臂残件一般都是天人形象的组成部分。粘有小花的手应该是天人中飞天形象的一种,其在壁画中是一手托花,一手撒花,在泥塑造像里是举臂撒花。连续排列的小圆花、项坠和耳坠应是天人佩戴的饰品(图7:库木吐喇石窟第21窟券顶菩萨)。
3.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第41窟窟内清理出来的手残块数量较多,手做伸展状,有的在手心绘眼,有的没有。手心墨画一眼,能辨识的有3只左手、7只右手。另外还有一些手姿略有变化,如呈握姿状、自然弯曲状等。从手的数量和姿势,推测主尊可能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三)彩绘泥塑原位考
中心柱窟内大多在主室正壁塑出菱形山峦,保存尚好的可见克孜尔第13窟、第171窟等。山峦间插塑动物和禽鸟[6],上述山形残件以及动物形象应是正壁菱形山峦上的一个部分。
龟兹石窟有些洞窟在中心柱窟后室正壁,凿出涅槃台,台上塑出涅槃像,前壁雕出或砌筑荼毗台,如克孜尔第197窟,森木塞姆第11、第32窟等。前述举哀形象可能影塑在涅槃像周围,龙头则是荼毗台上所放置棺木的前端装饰。有的在中心柱窟后室前壁荼毗台下方布局“八王分舍利”题材,如克孜尔第27、第175窟等,武士和马头彩绘泥塑应是“八王分舍利”题材中的内容。
(三)彩绘泥塑的艺术风格
这批彩绘泥塑残件有犍陀罗、汉风以及龟兹本土的艺术风格。犍陀罗艺术风格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佛头及佛衣上。佛头呈波状,额际宽阔,眉、眼墨线勾勒,眉間有白毫,鼻脊狭长挺拔。通肩佛衣,上身衣纹在胸部右侧呈波谷状,下身衣褶较深,累叠并行在两腿间,衣褶随体型而变化。这些都是犍陀罗造像常见的表现形式。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在龟兹地区现存两处,一处在库木吐喇第7窟[7],一处在库木吐喇第41窟。库木吐喇第7窟千手观音的手眼残块与第41窟的略有不同,其在手心上阴刻眼睛(图8:库木吐喇第7窟残件),与第41窟在手心上绘出眼睛异曲同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是8世纪下半叶在汉地出现的,如龙门石窟东山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龛,体具千臂,掌中各有一眼[8]。龟兹地区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造像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龟兹石窟洞窟形制有其独特性。在中心柱正壁塑出菱形山峦,山峦间插塑动物,形成“帝释窟”说法背景。这一题材在印度的表现形式更多侧重故事细节,如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帝释窟浮雕,其画面人物众多、形象繁杂[6]112-116。龟兹地区则比较简洁凝练,用壮观的菱形毗陀山的形式来烘托说法意境,使这一主题更为突出。中心柱窟后室正壁凿出涅槃台,台上塑出涅槃像,前壁雕出或砌筑荼毗台,涅槃台及荼毗台雕塑多已不存,仅在壁面可见若干固定塑像的圆形小凿孔。在后室狭小空间内以涅槃台和荼毗台相对应来表现佛传题材,这是龟兹石窟的独创。
以上是对龟兹研究院藏彩绘泥塑造像的初步整理和认识。这批彩绘泥塑造像不仅是龟兹石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新疆地区古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民族宗教及文化变迁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致谢:本文蒙北京联合大学陈悦新教授和龟兹研究院赵莉研究馆员的指点和修改,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刘松柏.龟兹研究(二)·库车古代佛教的观世音菩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706.
[2]杨淑红.龟兹石窟新出文物精品集萃[M].新疆文物,2005(2):98.
[3]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7-176.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20.
[5]王卫东.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1-22.
[6]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17.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213-214.
[8]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