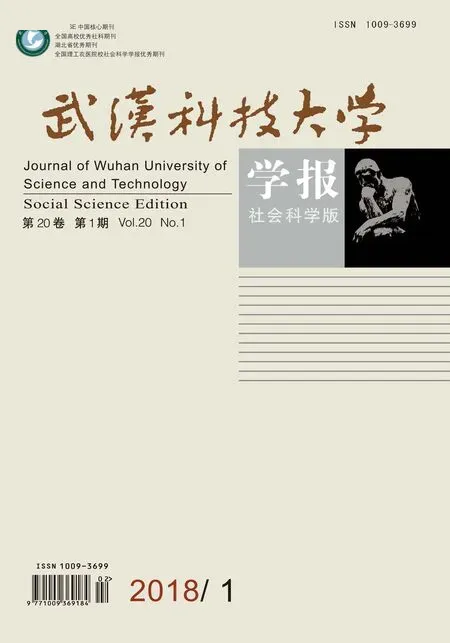“精神”内质结构的哲学透视
尤 吾 兵
(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精神”之谜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生命科学和精神病学等诸多学科探索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却很难给出一个全面、准确的答案,对于“精神”一词含义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有人把对“精神”的研究形容为一个“黑洞”问题。黑格尔就说:“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1]1“精神”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它似乎是一种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存在,很难被直观把握、精准透视,但它又确实存在着,而且之于人又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是人的本质体现。马斯洛曾深刻指出:“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2]人不仅仅是具有肉体的生命体,更是具有“精神”的生命体,“精神”甚至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标志,也是人成为世界主宰者的根本标志。要想走进神秘的、隐性的“精神世界”,需要对“精神”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清晰的概念可以揭示出事物本质属性,为人们认识事物和研究问题奠定基础。概念的分析主要是哲学学科的任务,而且在哲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就说过:“在哲学中,如果想不用概念立论,那就没有参加谈论的权利。”[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精神”的本质内蕴
在哲学学科中对于“精神”的研究最科学、最理论化的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常把“精神”“意识”“思维”等看作同一意义的概念。《辞海语词分册》对“精神”的解释就有:“与‘物质’相对。唯物主义常将其当作‘意识’的同义概念。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4]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里也常常体现这种思想,如在解释“意识”“思维”时,“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5]38-39,“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5]45。把“意识和思维”均是当作具有相同意义来使用,而在解释“精神”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把“精神”同“意识、思维”一样都看作是人脑的产物,具有相同性,“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6]。“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5]426,“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在有机体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5]407,这些论述都可以看出马恩思想常把“精神”与“思维”“意识”看作是同义概念。因此,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精神”的内涵时,会出现以“意识”“思维”等作为替代词,其意义指向都是限定在同义范围内使用的。
虽然马恩著作里没有给“精神”下过一个明确定义,但不同于以往的哲学,马恩著作里多处对“精神”内涵进行阐释,深刻揭示了“精神”的本质属性。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的观念和思想的结晶。马克思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7]81,“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525。“精神(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一定社会背景、风俗文化、经济状况以及人的经历等影响,其不是“天然之物”,这些是透视“精神”实质的主要因素。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是人脑的机能,只有人脑才会产生出“精神”。恩格斯鲜明点出了“精神”的来源——主要是人脑的功能。因为人脑的特殊结构,人脑可以对外在世界产生反映,进行思考,所以恩格斯曾比喻说人脑可以绽放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精神(意识)”,“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9],再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意识)”是对客观世界存在产生“反映”,从而在主观上形成“映像”。也就是说,“精神”既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飞来之物”,是人脑通过对输入信息加工制作而形成的对于外在客观事物的“成像”。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112“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8]525。列宁也认为:“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11]这些都说明“精神(意识)”在实质上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反映”而形成的思想结晶,从而科学地回答了“精神”的本质。
二、哲学视域中“精神”内质结构的分层
现代医学对疾病检查的手段越来越精密,如CT检查方式,它可以深入、分层扫描病灶成像,准确揭示疾病产生的原因。为更深入认识“精神”的本质,我们也可以模仿CT检查法对“精神”的内质结构进行分层级透视。
应该看到,在对“精神”本质的理解中,对关键词“反映”的理解是认识“精神”本质的“钥匙”。这里的“反映”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摹写”,即对客观世界信息的简单输入而成像。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讲究的“发展、创新、实践”等可知,“反映”活动应是包括“摹写”和高于“摹写”的“抽象”以及更高的“创造”的统一,如列宁就把“反映”看作是“感知、抽象、形成规律等”一系列的过程,“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的过程”[12]。马克思也指出“观念”“意识”的东西不是外在事物简单搬挪到大脑,需要在大脑中进一步加工、组合、改造。现代心理学在对“意识”的结构分析中,也是把“知(由认识而理性智慧)、情(情绪情感)、意(意志、观念、信念)”作为其主要的构成部分,因此,这里的“反映”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对信息简单感知——“反应”、对信息抽象加工——“反思”以及对信息创新重构——“升华”。
人作为现实存在,在生物学意义上会表现出对外部事物作出需求“应答”,马克思认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13]这种本能感受性主要表征为“反应”,人在这一阶段主要凭借感觉认知世界,人的精神主体性也主要表现为摹仿性,即人会凭借感觉去感性地认识外在事物,产生出诸如感应、喜恶、情绪和情感等表现。“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8]211。马克思主义不是把人对事物的“反应”看作低级层次加以贬斥,而是把这看作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8]334-335。相对于一般存在物,人除了有感性,还有理性的特殊的存在,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统一体,也就是说,人不仅仅会对外在事物作出简单“反应”,还会表现出对其进行抽象和概括化思考——“反思”,以使外在信息的本质变成头脑中的“思想”。“人的意识不仅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还能够自觉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深刻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14]。正如黑格尔所说:“本质自身中的映象是反思。”[15]可见,“反思”不是存在直接、简单产生“反应”,而是进一步认识世界,探究世界本源,关照自我、改造自我,从而使人体现为具有“理性”的动物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人自身进行反思,才能深刻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6如康德所说:“人是这样一种东西……是天赋有丰富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有某种道德素质的理性生物。”[16]另外还应看到,人不仅是一个现实的、理性存在,还应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即人在接受、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还会对现实作出更深层的“反映”——创新、重构信息,可以称为“升华”,即对所面对的事物的本源进行形而上的追问,追问自身生存终极目的性,马克思就认为人的活动“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17]。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需要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系统来指导自身解决矛盾。生命的终极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追求自由的实现,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的信仰,这应是生命的最高追求。“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8],这其实就是说明人在面对生命的终极目的意义问题上,需要在现实社会中建构“信念、信仰”系统,来回应自身超越自我这一终极期待和希望。
三、“精神”内质结构中“三个世界”的划分及思想资源佐证
从对“反映”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外在世界通过人脑的“反应”“反思”和“升华”几个主要流程“进入”人脑后不断积淀,便形成了人的“精神”,这是对“精神”进行的“分层”剖析,其实也是对“精神”的结构层面以及各个层面包括的内容的展现。因此,我们可以说,“精神”主要是以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产生以“情绪情感”“理性”和“价值信仰”为代表的“映像”,三者构成“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们在逻辑关系上由内至外分为三个层面,其中“情绪情感”可看作是“精神”的最外层,第二层是“理性”,内核应是“价值信仰”。依据这样的认知,复杂的“精神”结构很明显可以划分为“情感世界”“理性世界”和“意义世界”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可以得到中外思想家观点的佐证。
在西方传统文化里,“精神”的意义多指向“灵魂”说。如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是生命的本源,是精神存在的体现,“‘何谓灵魂’的一个通用(普遍)定义:这是凭形式为之表现的本体(实是)。事物之所以成其为一实是者,就凭它这个怎是。”[19]86亚里士多德意思很明显,就是说灵魂是生命的“本体”,生命只有凭借“灵魂”才能体现为现实存在。亚里士多德还对“灵魂”进行了分类,他把“灵魂”主要分为“欲望灵魂”“感觉灵魂”和“理智灵魂”三种,其中“理智灵魂”最高级,“感觉灵魂”次之,“欲望灵魂”最低,这种分类很明显是从“灵魂”结构层面来划分的,与前面对“精神”的“三分法”有很大程度的契合。另外,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分类更能看到前面“精神”结构分类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人的“本体”,“人在本性上是求知的”,所以体现人本性的“灵魂”的呈现要通过追求知识实现。那么可追求的“知识”有哪些呢?亚里士多德把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进行了等级分类,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感觉的、理智的和最高的,其对象分别是个别的、抽象的和普遍的知识,那种最高的、最普遍的知识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和“神学”。“灵魂”通过这三种知识来塑造,很明显可以分别称作“感觉灵魂”“理智灵魂”和“信仰灵魂”,这完全契合“精神世界”三分法。
谈论对“精神”的研究,不得不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精神”不是抽象静态的,它是一个自我运动、辩证发展的理念,精神自身变化是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发展演化的过程,最后精神自身会自我实现,达到自由阶段。黑格尔对“精神”的一个定义就是:“精神以自然为它的前提,而精神则是自然的真理,因而是自然的绝对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1]10对于自我运动和发展的“精神”(黑格尔这里的“精神”主要是指向人类整个“精神”),黑格尔对其进行了分类,将“精神”按发展过程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类。主观精神指个人内在的精神,即是指个人意识,在这里“精神”和“意识”是作为同一含义看待,其实黑格尔也有很明确的表达,“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20]。客观精神则是指主观精神显现于外,与外部产生联系的精神,如法的、道德的、家庭社会的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等。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是在思维的最高阶段上达到了自由境界的地步。绝对精神发展自我认识历程有三个阶段:艺术、宗教和哲学。在三种精神的分类中,黑格尔着力对主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发展进行了精致的研究,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这里分析的“精神”。他认为个人精神的发展就是“从最初的与动物意识无本质区别的所谓自然灵魂直到成长为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能力、企图使外部世界服从自己以实现其自由意志的所谓自由精神的发展过程”[1]16。这样他把个人精神的自我演变又细分为三个阶段:灵魂阶段、意识阶段和精神阶段。在灵魂阶段,他把灵魂自我发展分为自然灵魂、感觉灵魂和现实灵魂,其中黑格尔花了很大篇幅探讨感觉灵魂的特点,如感受性、主体性和习惯性等。黑格尔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宣示“感觉”在“精神”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也可以说黑格尔把“感觉、感性”的东西看作是精神在这个阶段所包含的重要内容,这与前面我们把“精神”结构第一部分称为“情感世界”很容易对应起来。黑格尔把个人精神自我演变的第二个阶段称为“意识”阶段,这一阶段,精神作为意识是“使它的这个现象与本质同一,是把对它自身的确定性提高成为真理”[1]260。意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经历“意识本身”“自我意识”和“理性”三个阶段,而理性阶段,黑格尔认为这是意识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为了精神”[21]。理性能够确信自身的规定是事物的本质规定,同时又能认识到这即是自己的思想,理性在精神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意识阶段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把以理性作为意识核心的说法,也可以佐证我们前面对“精神”结构分类的“理性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最后,黑格尔把个人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称为是“精神”(这个精神应是狭义的称谓)。这个阶段是精神朝着它自己本原回归的阶段,是精神扬弃一切外在性和异己性达到自由发展的境况,这个历程会有三个步骤:理论精神、实践精神和自由精神。理论精神是认识活动,如直观、表象、记忆和思维等。实践精神是克服冲动和任意,追求普遍的满足——幸福的过程。自由精神是精神发展的最后阶段,是精神能够思维自己、认识到普遍规定——自由的概念,并努力去实现它,这一阶段同样和我们前面把“精神”结构分为“意义世界”异曲同工。
中国文化一直致力于“精神”体系的构建,用来指导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冯友兰在谈论人生精神境界时,把精神境界分为“本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22]298四个层次。自然境界是最低级的存在,功利境界比自然境界稍高一点,更高的是道德境界,最高的是天地境界,这里把人的精神境界从低级向高级划分了清晰的层次,在本质上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精神”发展过程的四个阶段。虽然冯友兰把精神境界细分为四种,但这四种和前面分析的“精神”结构中的三个“世界”可以对应起来。冯友兰认为,“在这四种人生境界中,前两种都是人生的自然状态,后两种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22]299也就是说,前两种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来自人的天然性,这两种境界中的人,一般依自我本能、社会习俗和感情用事,这种境界人的“精神”是处于原初发展阶段,也可以称为其“精神世界”处于“情感世界”位置。在后两种境界中,道德境界中的人是指已经脱离了对世俗物质利益过度或不适宜的追求,自身的行为已经规范化、理性化,达到较高完满境界,这个阶段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觉解”(冯友兰语),“觉解”就是能够理性认识自我,脱离感性、世俗的约束。按冯友兰的意思就是,“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里上升到‘智性的世界’。哲学家如果在智性世界中生活,他也就是超越于人间世”[22]300。而天地境界中的人,是那种对人生能够彻底“觉解”,能够认识自己不再是社会中的“小我”,自觉把自己融入了一个大全整体中的“大人”。一个人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这样做,这样使他处于在精神上超越人间世的境界,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达到“天地境界”。很明显,冯友兰把人生境界的高级阶段划分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和前文厘定的“精神”结构中“理智世界”“意义世界”相对应。
四、“三个世界”包纳内容的哲学透视
“精神”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能够得到很好的佐证,那么,三个“世界”里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情感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层面,是“精神”直接表现在外的层面,“情感世界”的流露反映一定的“精神”面貌。一个人情感丰富、多愁善感,“感时花溅泪”,我们常会说这个人“精神”柔弱,意思就是如此。情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意识,是生命自然原初表现和存在方式。“讲人的存在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因为情感,且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23]。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情”是外感于物而产生的,是由外在事物、事件而引发的。《汉书》有“情者,见物而动者也”,《荀子·正名》中提出“六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中医传统文化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亦称“七情”。在西方,对“情感”的分类也比较细致,如亚里士多德就把“情感”认为是“精神”的感受性,可以表现为多种,“灵魂(精神)的诸感受(感应)大概全都结合于身体的——愤怒、温和、恐惧、怜悯、奋励与快乐以及友爱与仇恨”[19]48。休谟则把“情感”看作是人性的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可以分为“直接情感”和“间接情感”两类,“我只能概括地说,我把骄傲、谦卑、野心、虚荣、爱、恨、嫉妒、怜悯、恶意、慷慨和它们的附属情感都包括在间接情感之下,而在直接情感之下,则包括了欲望、厌恶、悲伤、喜悦、希望、恐惧、绝望、安心”[24]。现代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哲学学科里把“需求、需要”看作是一种价值判断,由此,在哲学视域里,情感的实质被理解为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进行价值评价产生的反映。正如Chris Low认为思维具有透彻、客观的冷静品质,感觉提供了有形的物质世界是冷性的,知觉引导对事物的理解,但它们都没有提供价值。只有情感为人类提供了尊严和价值①。
上面种种分类虽有不同,但应该看到分类中都包括有对“快乐、愤怒、悲伤、恐惧”等情感用了不同形式来表达,这与心理学的认知也是吻合的。“然而把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四种具体情绪确定为基本情绪则是各种分类方法的共性”①。这样“精神”的“情感世界”可以认为包括“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四种基本内容。
“理性世界”是“精神”在现实世界的核心反映,“精神”在现实意义上多指向人的“理性”的表达。我们常常会说,某个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就是说此人遇事不慌,面临重大紧急事情也能冷静处理,反映的是“理性”精神具有。人是感性动物,更是具有理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就坚持认为:“理智在我们中是最高贵的,理智所关涉的事物具有最大的可知性……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25]。高扬“人的尊贵就在于人的理性”的康德也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26]马克思更认为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在理性指导下通过实践来创造性活动,也就是说人在现实中会以考量自身以及自身与他者、与世界的关系来反映自身的主体性,“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个体“精神”的本质属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情感”文化为主要特征,但也有对“理性”的探究,反映出很强的“理性”思维精神,只不过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专门明确给出“理性”的名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很好的例证。世俗文化有“这个人很通情理”,也很好地说明这点。所谓“情理”,是指人既有情感,又讲道理。道理之“理”,是需要理性思辨才能把握。宋明理学家对这些从哲学高度思考,提出世界万物“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则”的“天理”说,“理”当然也是人应遵循的规范(即“道”),也是人的本性(即“理性”),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宋儒在看到“理(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时,更看到了“理(理性)”的能动性,这在宋儒命题“理欲之辩”中可以清晰看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解释应是主张发挥理性的能动性,制约“过欲”,使人的情欲“理性”地体现。对于“理性”的形成,宋儒认为求知可获取“理性”精神。根据来源方式不同,人的“理性”可由“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获得。“见闻之知”是指要从闻见开始,类似于感性认知,下学上达,达到对“理(理性)”的认识。而“德性之知”不是指先天的,是指形成于具体实践过程,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正是说明作为理性之知的“德性之知”,需要通过问学进德修为,才能使主体精神品格提升。“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包含内容的分类,而这种分类与康德对“理性”的认知有很大程度的相通。康德认为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一是认识功能,一是意识功能,康德把前者称为“理论理性”,后者称为“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只处理认识能力,是人类运用逻辑思维能力,依据所获得的认识原理进行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它的任务是发现和抽取实体事物内部的真理,探讨客观必然性。“理论理性”往往依据于直观经验,感性、知性、思辨理性都从属于“理论理性”,而“实践理性”处理的是人的意志问题(欲求能力),意志本身就是自己实现对象的能力,所以“实践理性”是指人们运用理性来判断在特定情势下行动的正当性,它的任务是回答世界应当如何、人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指向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实践智慧、价值理性、推算理性和选择理性都从属于实践理性。康德对“理性”关注以及对其精细的分类,其用意很明显,主要是看到了理性是指导人的行为的能力和创造自身生存的依据,康德高呼“人为自然立法”,正是凸显“理性”在高扬人的尊严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理性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各种“能力之母”,“理性”精神的功能是可以认识自己,洞察世界,理智行为。“精神生活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从内心对客观现实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体验、反思和诠释”[27],依据前面的分析,有理由把“认知、思维、判断和实践”等纳入“理性”范畴,架构起“精神”的“理性世界”。
“意义世界”是人超越“现实”之境而形成的“精神”之维,它是指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需要找寻一个能够支撑起生命存续的具有方向性的目的系统,以此来肯定当下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28]。现实生命是短暂的,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恩格斯就说过:“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5]422因此,在人生“此在”的图景中,总是交织着对生的“焦虑”和对死的“恐惧”,“焦虑”和“恐惧”都是“有限的自我对自己有限性的意识”[29]。当“精神”意识到有限性而又不能满足有限性时,一种关切生与死的终极指向的意识系统就需要形成,这种意识系统必须可以解释人生的无限性存在的可能性,使有限走向无限,指导解决生与死之间的紧张。
中西文化都看到了人的存在过程与生死问题的关联,重点从现实生命价值的实现上来构建指导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意义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学说是生命之学,儒家也清楚认识到人的生命特质决定了任何由肉体上达到永生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人是无法改变由生过渡到死的必然性。儒家文化思想智慧就在于它看到了这点,然后对生命进行了巧妙的分类:现实生命(生理生命、肉体生命)和道德生命(精神生命)。现实生命就是生理肉体,儒家承认它是会被时光毁灭的,但精神生命是不会毁灭的,尤其是以道德充塞的精神生命更不会消亡,它会永存不朽。道德生命就是现实生命在“当下”时曾造福他人和社会,这种生命会因其造福了他人和社会而超越时空被人铭记,逝去时表现出积极价值,从而把有限的生命转化为不朽的存在。儒家“道德生命”的提出,超出个人的生活层面,把生命的现实与生命价值统一起来,追求道德生命的长存,超越现实生命的短暂性。所以人一旦确信道德生命的存在,把此作为坚定的精神信仰,就会对摆脱死亡的恐惧有所帮助。西方生死文化多是以宗教形态展现,宗教的具体形态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它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特征:预设一个无限美好、理想化和永恒性的彼岸世界,淡化现实生命存在的意义,让生命在彼岸世界的追求中超越有限性。如基督教文化预设“天堂”,以此为人的永恒归宿,人可以在“天堂”实现永生。佛教文化更是“了生脱死”之学,佛教文化不是过多着眼于“生”的关注,而是关注超越死亡以及死亡归宿问题。佛教文化认为世俗社会充满了苦,人们因为“无明”缘故而在苦海中备受折磨,而在另一个世界——彼岸世界才是充满幸福和快乐的世界。佛教文化让人们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只要能够去洞彻自己的本心,人人都能超越生死到达彼岸世界。
可见,“意义世界”是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成为“精神世界”的核心,正如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里克所说:“对自我的超越、对意义的求索和与他人联结的需要等精神最核心的元素常常会在人生回顾中出现。”[30]这个系统的搭建常常是由“价值、信念、信仰”的确立来完成,它们也相应构成了“精神”结构中的“意义世界”的内容。
注释:
①参见乔明琦:《中医情志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38-42页)。
[1] 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马斯洛,狄尔泰,施普兰格尔,等.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3.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2.
[4] 辞海语词分册(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52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9.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8.
[12]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4.
[14] 陶富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77.
[15]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
[16]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0.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19]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2.
[2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
[2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插图珍藏本[M].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3]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
[24] 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10.
[2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4-225.
[2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0.
[27] 王秀敏,张梅.现代人精神生活质量内涵的理性诠释[J].福州党校学报,2008(2):73.
[28] 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6.
[29] 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6.
[30] 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里克.老年社会工作: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估与干预[M].隋玉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