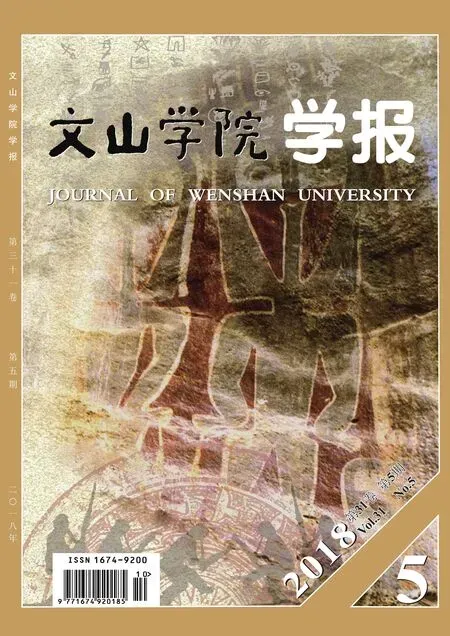西畴壮族“女子太阳节”多重信仰观念分析
黎海燕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丽江 674199)
西畴壮族属云南壮族侬支系,自称“濮侬”,操壮语南部方言,是云南土著民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西畴县汤果村都会举行一场特别的祭祀活动——“女子太阳山祭祀”。“女子太阳山祭祀”民俗活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子太阳山祭祀”又称“女子太阳节”。该日清晨,汤果村年满16岁以上的女性都到村子前的达坝河里沐浴净身,穿上节日盛装戴上头帕,正午时分来到村前的“太阳神树”下,由“布摩”(壮族祭司)带领“祭请太阳”,然后一路“护送太阳”来到村旁的“太阳山”顶,最后唱着《太阳古歌》把太阳“送”到天上。整个祭祀活动,除了“布摩”和两位男性祭祀“侍者”以外,任何男人不得进入祭祀场,男人们这一天的工作就是“伺候”女人过节。在汤果村,只有成年女人才能祭祀太阳、祭祀过太阳的女性才有成年的资格、男人“伺候”女人过太阳节,这一系列的习俗传承千年却从未改变。
“女子太阳节”的主旨是祭祀太阳,在中国有很多民族都崇拜太阳,比如彝族、哈尼族、苗族、瑶族、高山族、基诺族、蒙古族、土家族,还有与壮族同语族的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这些民族都有太阳神话,甚至有太阳图腾,有些民族至今仍延续着太阳祭祀活动。从祭祀活动来看,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和地域特征。汤果村的“女子太阳节”是发生在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根植于壮族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以祭祀太阳为核心,以祈求阳光照耀为主要目的,并包含多种壮族原生宗教信仰内涵的节日,犹如壮族历史的“活化石”,蕴藏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一、自然崇拜
(一)太阳崇拜
太阳崇拜是“女子太阳节”最突出也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表现。壮族女性为了讨得“太阳女神”的欢心不惜在寒冷的河水里沐浴净身,男人们心甘情愿的承担所有家务“伺候”女人过节,这些行为都说明了太阳在濮侬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除了汤果村,其他壮族生活地区都存在祭祀太阳的行为,太阳崇拜可以说是壮族人民宗教信仰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距汤果村不远的西畴县蚌谷狮子山岩画,据专家推断应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所绘,其中绘有两个太阳图案:一个太阳绘有21道芒纹,另一个绘有15道芒纹。据此可看出,西畴壮族太阳崇拜信仰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活跃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太阳崇拜的起源或许可追溯到旧石器以前更早时期。到了青铜时代,壮族先民将太阳图案铸在象征权威和财富的铜鼓之上表示对太阳的敬仰,说明壮族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把日神信仰融入在文化的主意识里,并希望它在世代传承中不朽和发扬光大。
到了现代社会,崇日信仰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壮族人的生活。四季轮回的稻作方式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太阳的重要性,是太阳给予人间光明和温暖,让万物得以拥有生机和活力,但太阳又把干旱和酷热带给大地,让人类遭受无穷灾难,所以对于太阳,人们是既敬仰又畏惧。当人们对外界事物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开启“诗性智慧”,采取愉悦神灵的方式祈求保佑,这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心理。在传统刺绣的壮锦上绣有太阳,在背婴儿的壮族背带上也有太阳,世代传唱《太阳古歌》,叙说太阳神话故事,每年祭“竜”的时候专门祭祀太阳神树,这些都是壮族人对太阳崇拜的表现,对祖先崇日信仰的传承与延续,也是壮民们智慧美化生活的体现。
(二)“竜”崇拜
在“女子太阳节”的“请太阳”仪式中,有这样一个行为:濮侬女性在太阳神树前祭祀跪拜,把封印在神树里的太阳请出来。神灵封印在古树之中,这种奇特的行为在壮民族的历史上贯古通今,所表达的含义正是整个壮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竜”崇拜。“竜”,云南壮语森林、树林的意思。“竜”崇拜泛指森林崇拜,也可理解为是树神崇拜。
云南壮族“竜”崇拜尤为突出,祭“竜”是云南壮族每年最重大的节日。“竜”崇拜,就是壮族先民对那些与自己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影响极大的山林等自然物的神化与崇拜[1]21。作为传统的稻作民族,壮族人选址建寨必须依山傍水、树林环绕,因为种稻离不开水,而水离不开森林,只有保护好森林,庄稼才得以丰收,人类才能够延续。所以每个壮族村寨都有一片“竜山”,“竜山”中最茂密茁壮的树称为“竜树”。云南壮族认为:“竜”的圣洁能免除疾病、瘟疫,预防自然灾害;有“竜”环抱的村寨,人能健康长寿,百姓衣食无忧;“竜”中长年流淌的清泉,是他们从事稻作生产的首要条件;他们把“竜”的萌、发、荣、枯视为春、夏、秋、冬的信息,并按照“竜”中的物候变化进行播种、薅锄、收割、贮藏等农事活动,他们还按“竜”中的植物生长周期、月亮圆缺和昼夜变化规律来制作自己的农历[1]4。在壮族民间,通常以一棵“竜树”的繁茂程度反映一个村落的繁荣昌盛,任何人不得破坏砍伐“竜树”,禁止在“竜树”周围扔污物或置葬,否则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每年须由“布摩”带领寨子里的男性进行祭祀。
汤果村村民把太阳神封印在“竜”树里的行为,是人们“竜”崇拜的人为手段,在云南壮族地区,人们还把始祖神——“布洛陀”、创世神——“乜六甲”、寨神都封存在“竜”树里,给这些“竜”树赋予了灵性,构建了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壮族人祭“竜”是为了庄稼丰收、人畜安康、祛病除灾、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祖先们借用“竜神”的力量促使人们爱护森林保护自然,这种“以神教人”的教育手段,看似扭曲,但却达到了全民教化的广泛功能。壮族人敬“竜”爱“竜”,这是祖先数千年经验的累积,也是壮族以人为本、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的表现。
二、动物崇拜
(一)鸟崇拜
“女子太阳节”是祭祀太阳,濮侬人也称祭祀太阳鸟母。在壮族人原始的宇宙观里,能飞上天的,都是鸟类,太阳是一只大鸟,雷公也是鸟形,所以崇拜鸟也有崇拜太阳之意。
汤果村的村民都是云南壮族濮侬支系,“濮侬”平日里称呼“侬人”,“侬”在壮语里有鸟之意,所以“侬人”也可汉译为“鸟人”。除了称呼,濮侬人崇拜鸟最强有力的实证莫过于濮侬女性身上穿的“鸟衣”。侬人女性的传统服装叫做“师侬”,汉译为“鸟衣”。如今侬人的传统服饰仍然保持着先民椎髻、羽饰、著尾等古代遗风。从汤果村祭祀太阳的濮侬女性身上可见一斑:上衣袖子大似翅膀,衣角两边上翘形如鸟翼,百褶长裙在臀部缠成类似鸟尾形状,颈上银项圈形似鸟头,从头到脚整个装扮如同鸟儿。可以说“鸟衣是壮族女性穿在身上的史书”[2]。
除了濮侬崇拜鸟之外,其他壮族支系也存在很多鸟崇拜的行为。作为南方百越人的后裔,壮族人崇拜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综观中国南方民族的太阳崇拜遗迹,凡是有太阳崇拜的地方多数伴随着鸟崇拜。河姆渡遗址中的“双鸟舁日”纹牙雕是两侧一对钩喙双鸟(鸡),面对太阳似在引吭啼鸣,又似托举太阳冉冉升起;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是四只神鸟等距的分布在太阳周围,周而复始的旋转。类似太阳与鸟的密切关系在现今的壮族壮锦、铜鼓中也有体现。壮锦“四鸟托日”是四只飞翔的鸟儿围绕在太阳四方,似托着太阳飞上天空;壮族铜鼓鼓面多以太阳纹为中心,四周绘以翔鹭(即鸟)环绕,这些图案都透露出一个古老的信息:壮族祖先对鸟的崇拜与太阳崇拜是同时出现的,太阳需要鸟的托举才能升上天空,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太阳更有能耐。
(二)水牛崇拜
祭祀太阳的濮侬女性除了穿在身上的鸟衣成为一大亮点外,还有戴在头上的水牛角形状的头帕、颈部水牛角造型的银纽扣也格外引人注目。侬人妇女逢年过节都要穿戴壮族传统服饰,头帕缠成水牛角形状,衣服上的纽扣也是水牛角造型,这些,都是壮族水牛崇拜的表现。在壮族民居建筑中也有水牛崇拜的印记,传统的壮族民居房顶四角向上翘起,形如水牛角,房顶横梁的中间用瓦片或是水泥做成对称的水牛角形状,造型独特、轮廓优美。这是壮族人民朴实表达水牛崇拜的方式,也是壮族人民对空间合理运用的智慧表现。
追溯壮族人水牛崇拜的历史,可从西畴县周边的岩画中找到踪迹。文山州麻栗坡大王岩画是壮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即四千多年前的美术杰作,其中绘有三头水牛图案;西畴蚌谷狮子山岩画中绘一副水牛头图案;砚山大山村岩画中也绘有水牛图案,这也说明,早在石器时代,壮族先民就与水牛共同劳作,相依生存。
在文山州境内发现的岩画中,太阳图案与水牛图案都同时存在。这两种对象的同时存在,也透露出太阳——人类——水牛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久远的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了农耕生产生活,天上的太阳主宰着地上万物的生长,地上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养水牛进行劳作,驯养水牛是因为壮民族历来居住在水田较多的地区,唯有水牛才是稻田里主要的劳动力,这就是壮族先民的生活场景。对太阳的敬畏,对水牛的感恩,把它们刻画在山岩上,并且有相应的仪式祭拜它们,后世人世代延续着这种崇拜信仰与祭祀仪式,这就是壮族这个传统稻作民族对恩泽人类事物的感恩表达。
直至如今,依靠稻作农耕生产生活的壮族人还是离不开水牛,所以,壮族人善待水牛。一些地方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牛王”活动,感恩水牛的辛勤劳动,在牛圈旁给牛王点香烧纸。有“牛王庙”的地方,村民们还带上祭品到庙里祭祀牛王。这种种现象都透视了壮族人与水牛互相依赖的生存关系。
三、其他崇拜
(一)太阳女神崇拜
壮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太阳对万物繁衍的重要作用,在把对太阳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精神层面时,“太阳神”就产生了。《山海经》中记载“羲和生十日”,羲和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太阳女神。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父系氏族取代了母系氏族的统领地位,太阳神的性别也由“女神”变成了“男神”——伏羲。而在远离中原的滇东南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缓慢,到了汉代或汉以后才陆续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且进入父系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许多母系社会的文化遗迹。直至如今,汤果村的“太阳节”祭祀的还是“太阳女神”——乜唐温。汤果村村民把祭祀太阳的行为称为祭“太阳鸟母”、祭“乜唐温”。“乜”指母亲,“唐温”指太阳,“乜唐温”就是“太阳母亲”“太阳女神”之意。无论是把“太阳神”称为“太阳鸟母”或是“乜唐温”,“太阳神”的性别都被定义为了女性。
汤果村的《太阳古歌》“找太阳”部分中唱道:太阳似姑娘/无衣裤裹身[3]。说明在远古时候,壮族先民把自然力人格化的过程中,“太阳女神”是最早出现的太阳神形象;在当地的太阳故事中,找到太阳的不论是“乜星”还是“侬人四姐妹”,她们都是女性;为了祈求“太阳女神”的庇护,只有年满16岁及以上的女人才能进行祭祀,男人不得进入祭祀场,就连在祭祀中引导众人跪拜的男性“布摩”,也只是充当太阳女神的侍者。从古老的太阳故事到如今严格的仪式禁忌可以看出侬人们对“太阳女神”的敬畏程度。
(二)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整个“女子太阳节”中比较含蓄的信仰观念,通过吟唱《太阳古歌》和叙说太阳故事来表达。在汤果村的太阳故事中,英勇善战的“朗星”射落了炙烤大地的十一个太阳、身怀六甲的“乜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太阳并化身神鸟送太阳上天,是“朗星”和“乜星”为人间带来了幸福。这些出于对祖先崇拜所创造出来的民族英雄,寄托了先民们征服自然的伟大理想,侬人们为了纪念祖先,世代传唱《太阳古歌》、祭祀太阳鸟母、叙说太阳故事,也是侬人们对民族历史的一种回顾,其现实意义是在告诫后人,不能忘记祖先开创美好生活的恩情,须勤劳勇敢才能幸福常驻。
“女子太阳节”是壮族先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探索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产物,创造这个文化的主体是壮族先民。如今人们世代传承着祭祀太阳习俗,其中也蕴含了祭祀壮族祖先、怀念祖先的心理。
外界对“女子太阳节”的解读更多的是围绕太阳崇拜,通过对“女子太阳节”中不同信仰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女子太阳节”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它不仅表达了侬人对太阳的崇拜,更广泛的是对大自然、动物和祖先的崇拜。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女子太阳节”中对太阳、竜的崇拜,是濮侬人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展现;对鸟、水牛的崇拜,是濮侬人万物和谐相处生活观的体现;对太阳女神、祖先的崇拜,是濮侬人感怀祖先亲情观的表达。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从自然崇拜到动物崇拜,再到人为的太阳神、祖先崇拜,由一开始对自然力和自然物的认识发展到探索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直至创造出神灵控制自然力达到利己的目的,这一过程反映了濮侬先民们在适应、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的思维变化。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原始宗教意识转化成一种审美意识、审美情趣沁入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节日、禁忌、服饰、艺术作品等方式展现出来。汤果村的“濮侬”女人们沐浴净身、穿上“鸟衣”,戴上牛角帕,跪拜太阳神树、祭祀太阳、祭祀太阳鸟母、祭祀祖先,其中的信仰观念并不止局限于“女子太阳节”这个“超时空”,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现如今人们的意识里,和“祭祀”有关系的活动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人们总是习惯以“有用性”为出发点来讨论祭祀活动,而忽视了祭祀对象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美”。濮侬女人们创造性的把传统文化汇集一身,把对大自然、动物界的崇拜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着装打扮上,所以,这些源于大自然的原生宗教信仰不仅美化了濮侬人的心灵与生活,更提炼了濮侬人的“诗性智慧”,让他们在这个“美”的循环体系中创造了更美丽的壮乡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