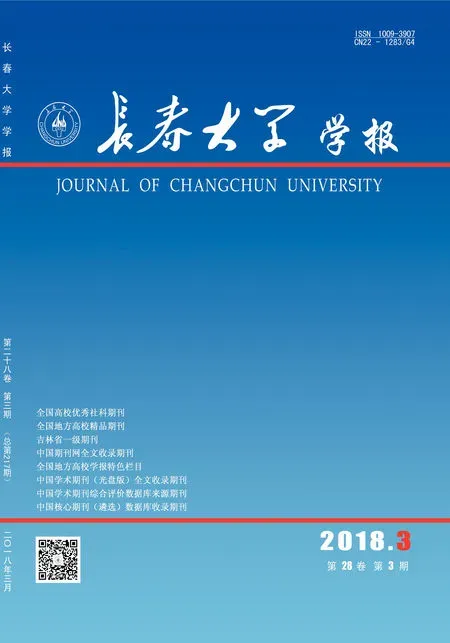新形式主义视域中的《野忍冬花》
曹良成
(阜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众所周知,传统批评和形式主义都割裂了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的统一。如何把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文学文本分析,这是当今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一书中指出,韵律等形式是“内容的形成因素,不仅仅是内容的反映”[1]68,是“意义的生发器,不仅仅是意义的容器”[1]68。陈太胜在分析伊格尔顿诗歌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式主义的批评”[2]21,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批评的真正目的,“在形式身上揭示历史和政治”[2]21。本文拟从新形式主义视域来解读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脍炙人口的一首自然诗《野忍冬花》,进而挖掘形式分析中的诗歌意义。
1 诗歌简介
1.1 创作背景:《哥伦比亚先驱报》
《野忍冬花》是古今中外学术界公认的一首描写自然的上乘诗作。这首诗开启了自然诗歌的先河,先于浪漫主义诗人关注大自然,也让弗瑞诺在时间上位列“美国诗人序列之首”[3]144,成为“美国诗歌之父”[4]。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国内不少研究论文或多或少进行了虚构。首先,他们一致认为这首诗创作于1786年。事实上,这首诗并非创作于1786年,而是发表于“1786年7月6日”[3]438,见刊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城市的“《哥伦比亚先驱报》”[3]438。至于具体的创作时间,弗瑞诺传记作家们大多没有提及,只有Austin写到了,即“我们不知道这首小诗具体是哪一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们得知,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开始写诗”[5]。其次,有些论文虚构了弗瑞诺创作这首诗的情景,说弗瑞诺在南卡州散步时看到了一簇生于幽谷的忍冬花,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其中不乏诗意想象,但缺少查证。最权威的弗瑞诺传记作家Leary,在传记中谈到弗瑞诺乘坐单桅帆船“蒙默斯号”到达查尔斯顿港口时“白色的野忍冬花已经在南卡州的海边或河边等潮湿的沼泽地盛开”[3]143,但只字未提弗瑞诺的触景生情,更不用说如此生动地描述弗瑞诺的触景生情。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朵花仅仅是一个象征,象征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的短暂”[6]。然而,不管怎样,提起弗瑞诺,人们总会想起他的《野忍冬花》。
1.2 诗歌语调:“沉思的忧郁”
“要区分诗歌中的语调和情调并不容易”[1]116。《野忍冬花》的语调或情调是“一种沉思的忧郁”[7]148:语调中透露出悲伤,情调中透露出伤感,语调中渗透着情调,情调中夹杂着语调。四个诗节中,我们都能找到伤感的词汇,比如,第一节中的tear,第二节中的white(象征死亡)和decline,第三节中的doomed和died,第四节中的frail等。最后1行诗“花的时光之脆弱”*文中诗歌引文均出自于比较权威的菲利普·弗瑞诺诗歌选本,即文献[4]。引文的中译文均为笔者所译,不再一一说明。,把悲伤的语调推向了最高潮。正如Leary的评价,这首诗“对于情调的唤醒几乎是毫无瑕疵的”[8]61。不过,诗人并未沉湎于忧郁中不能自拔,而是在忧郁中有所沉思,直面人生的短暂。
诗歌的强度和速度,与诗歌的语调一样,也涉及到诗歌的情感。这首诗的强度比较低沉,几近无声。诗行虽然比较简短,但诗歌速度是缓慢的。野忍冬花无法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如同戴着枷锁,在诗行中低回前行。
2 形式分析
2.1 诗节结构:春夏秋冬
《野忍冬花》整首诗分为四个诗节,每个诗节都是六行,押韵格式为ababcc。虽然,“六行诗节属于英语诗歌中较常用的诗节”[9]72,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比较多地使用六行诗节,但在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之前,以ababcc为押韵格式的六行诗节“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期间并不是最常见的,只是偶尔出现”[10]。这种偶然性出现在弗瑞诺的《野忍冬花》等不少自然诗歌里,尔后又在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自然诗中发扬光大,足见弗瑞诺诗歌的先见之明。
该首诗的四个诗节,点明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Arner在论文中指出了这首诗的四季内涵,却断定第三个诗节“包括秋天和冬天两个季节”[8]58。不过,笔者认为,这首诗的四个诗节与四个季节是一一对应的,每一个诗节依次描述了野忍冬花的春、夏、秋、冬的命运。一则,第三个诗节存在明显的字眼Autumn,并没有提及winter。当然,晚秋与初冬的气候难以区分,都存在“严霜”(Unpitying frosts),但不能据此就断定第三节是在描述秋冬里的野忍冬花,更何况诗人已经明确说出,“秋天的威力/会抹去这朵花的任何痕迹”。二则,尽管第四节述说的冬天不如第一节记叙的春天那么一目了然,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蛛丝马迹。在第四节中,诗人表面上是在感叹花的一生,似乎与季节无关,但该诗节的第4行诗“因为你们死去时都是一个样”暗示冬季的景象:万事万物皆埋葬在雪花中,万事万物皆埋葬在泥土中。
因此,《野忍冬花》的四个诗节的形式排列出了野忍冬花的四个季节。且每个诗节六行诗的形式又排列出了每个季节的不同时期,每个诗节中每两行诗依次述说着每个季节的初、中、晚三个阶段。第一节诗记录初春、仲春和晚春时期野忍冬花的情况:初春时,花儿悄悄地(silent)生长;仲春时,花儿盛开(blossom),枝条茂盛(greet);晚春时,花儿依然活跃,没有被踏青的人所踩踏(crush)。第二节诗记录野忍冬花的初夏、仲夏、晚夏:夏天之初,野忍冬花在大自然的照顾下一片洁白,随着天气转热;仲夏之时,在流水(soft water)和绿荫(guardian shade)的陪伴下,野忍冬花显得格外清爽;但好景不长,晚夏来临,野忍冬花的夏天岁月不知不觉离去(goes、declining)。第三节诗中包含诗人对秋的感叹:初秋时,诗人预感到了野忍冬花衰亡的命运(your future doom);到了仲秋,预感应验了,花枯萎了(died);到了晚秋,天气的严酷一点一点地蚕食着野忍冬花的花体。第四节是诗人对冬天的感悟:初冬时节,诗人感叹野忍冬花那来自朝阳和晚露(morning suns and evening dews)的小小的生命何其短暂;仲冬时,也许是一场雪掩盖了一切,让诗人顿悟出生命的哲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If nothing once, you nothing lose);到了晚冬时,诗人以直白又夸张的(an hour)方式再一次感叹野忍冬花脆弱且短暂的一生。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弗瑞诺在淡淡的忧伤中收获了四季人生的真谛。
2.2 语音形式:扬抑格“flower”
2.2.1 音高、音量、音色、纹理
《野忍冬花》的音高是低幅度的,音量不大,声音较低沉,从而形成一种既欣赏又伤感的音色。基于“沉思的忧郁”的语调,整首诗的纹理是紧凑的。诗行内的头韵fair flower、blossoms blow、sent soft、day declining、“She…shun…”、“…frail…flower”,诗行内的腹韵“…flower,…grow”、“…silent,…retreat”、“…once,…lose”,组合韵“…grieve…see…”、“…nor…more…”、“…morning…evening…”等,这些声音形式使诗行内部的纹理显得紧凑。跨行内韵“…arrayed/…bade…”、“…by/…thy…”、“…same/…space…”,还有诗行的首语重复“Untouched…/Unseen…”、“No…/No…”、“And planted…/And sent…”、“The space…/The frail…”等,都增加了诗行之间乃至整首诗的紧凑纹理感。这些紧凑的纹理,在表达诗人欣赏野忍冬花之余,也传达了诗人某种轻微的忧伤。
纵观全诗,清辅音s的声音比较多,比如so、silent、self、sent、soft、summer、smit、see、suns、same、space等。还有清辅音f的声音,如fair、flower、frosts、first、frail;清辅音sh的声音,如shall、crush、she、shun、shade等等。总之,清辅音远远多于浊辅音,给人的纹理非常柔和,轻轻地吹几口气,就营造出了野忍冬花生长的幽静环境。
2.2.2 节奏和格律
格律是规则的,是一种固定的背景,而节奏则是多变的。格律的变化形成了节奏,Eagleton直言,“许多英语诗歌的效果来自节奏与格律的博弈”[11]204。《野忍冬花》的主导韵步为抑扬格四韵步,在抑扬格四韵步的基础上,诗歌节奏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强化了诗歌的主题——flower。
该诗诗行一般8个音节,但第1行与最后1行为10个音节,第10、15-18行分别有9个音节。诗行的音节划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多元音音节如果“在读音上是表示两个元音,那么就要把它们划分为两个音节”[9]8。第1行的fair和最后1行的frail这2个单词,虽然在一般的语音规则中分别是1个音节,但在诗歌音节中应该算2个音节,每个单词中2个元音字母,在读音上表示2个元音,这样一来,第1行和最后1行分别算10个音节。在划分音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fair和frail这2个单词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除了音节的特殊性外,它们还押头韵,在意义上也形成对比,“美好”(fair)与“脆弱”(frail)的关联恰恰说明了这首诗歌的主题: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脆弱的,最终会在大自然中消亡。第10行多出的1个音节出现在murmuring这个单词上,第9个音节“-ing”与流水的潺潺声存在感官上的相似性,真切自然。其他9个音节的诗行都出现第三节中,第15、16、18行第9个音节出现在flowers这个单词里,音节形式上多了1个音节,实质上是对诗歌主角野忍冬花的一种强调,让读者和诗人一起不断聚焦美国特有的植物——野忍冬花。
综合考察这首诗的韵步类型,可以发现一个与一般诗歌不同的地方。一般诗歌在主导的音节数量诗行里也存在韵类变化,但这首诗的韵步变化全部发生在音节数量不规则的诗行里,而音节数量规则的诗行里,韵步皆是规则的抑扬格韵步。音节数量的不规则,再加上韵类的不规则,势必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些不规则的7个诗行中,flower这一主题词露头了5次,可见诗人的煞费苦心,也深化了诗歌的主题思想。在这些韵类不规则的诗行中,“重读位置的变化可以改变句子的意义,以及对某些部分的强调和突出”[9]21。第1行开门见山,fair和flower皆为扬抑格,突出花的美丽,与下文花的生命短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10行抑抑扬格“-muring by”,通过2个微弱的抑抑节奏“-muring”,凸显扬节奏by,以便引出随之而来的2行诗,河水流过,花的岁月即将流过。第15-18行还是抑抑扬格这种升调节奏,强调gay、did、frosts和this这几个词,说明大自然的威力可以消除一切,包括伊甸园中的花卉。最后1行诗中,除了抑抑扬格外,还出现了抑抑抑格这种几乎消声的韵步,以至于最后爆发出扬抑格flower。值得注意的是,扬抑格flower在第1行、第18行和最后1行先后出现,打破抑扬格等升调韵步的束缚,再次从韵步变化的角度激发诗歌主题flower的回响,余音袅袅。
2.2.3 押韵
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下有关该诗押韵格式的误解。国内不少论文文献在谈到这首诗的押韵格式ababcc时,混淆了交叉韵和连锁韵(interlocking rhyme)的区别,煞有介事地指出这首诗的押韵格式为连锁韵即交错用韵。什么是连锁韵?连锁韵即链韵(chain rhyme),“一个诗行或一个诗节中的某一个韵用于链接下一个诗行或诗节中的某一个韵”[12],比如,三行体诗歌(terza rima)的押韵格式ababcbcdc就是连锁韵,每个诗节的第2行的押韵用于链接下一个诗节的第1、3行。不难看出,该诗的六行诗节押韵格式与连锁韵毫不相干,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隔行交叉韵与双行韵的组合。
其次,押韵格式ababcc这种普通六行诗节的韵式在交替押韵后再来一个双行韵,整个诗节的气势完全落在双行韵式上,双行韵的重复实则是一种强调。《野忍冬花》这首诗伤感的感悟基本都落在每个诗节的最后两行诗上,韵式的强调与诗歌的主题不谋而合。第一节中的here和tear表达了晚春的感悟,诗人实则在强调其他花卉因为人类的介入而伤心落泪。第二节中的goes和repose强调了晚夏时期野忍冬花岁月的消亡。Arner发现,最后两节的双行韵“使用同一个韵”[8]56,并且,他认为,诗人的目的是“强化诗歌主题”[8]56。的确,第三节和第四节不仅韵式一样,且最后两行诗的韵种也一样,power/flower和hour/flower押同一个韵/au/,且重复flower一词,韵式的强调意味不言自明。一句话,最后两节诗的韵式强调比前两节诗的韵式强调更加强烈,从而突出诗歌主题。
最后,让我们看看《野忍冬花》的押韵。Eagleton认为,“押韵是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体”[11]198。押韵同一的是声音,但押韵并不单调,因为押韵存在意义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把押韵的精神沟通起来,押韵是相同与不同的矛盾统一体。从这首诗的押韵中,可以找到一种“反讽的并置”[8]56,一种张力。比如,重读音节全韵decay/gay中,野忍冬花魅力的消逝难道很幸运?从中可以看出大自然“向死而后生”的哲学思想。既是全韵又是单韵的押韵doom/bloom,消亡的厄运与盛开的兴旺形成强烈的对比,直指伊甸园里的花也不能逃避消亡的命运,同样,也隐含着“向死而后生”的哲学。第三节中的这两组交叉韵为第四节中“如果不曾拥有,又何曾失去”这行诗坦然处之的人生态度作好了铺垫。第三节的双行韵power/flower,野忍冬花的脆弱与秋天的威力形成明显的对比,野忍冬花最终被晚秋扫荡无遗。有时,这种对比是一种潜在的反讽,比如,arrayed/shade的搭配中,arrayed暗示着光鲜地打扮,而shade则暗示着死亡,生意味着死,生死循环的现象再一次出现,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规律。当然,该诗还有一些押韵并没有对比,而是共同加强诗歌的主题思想。比如,grow/blow强调野忍冬花的生长之美,goes/repose强调野忍冬花的逝去,hour/flower强调野忍冬花生命的短暂。纵观全部押韵,虽然它们都是在实义词内押韵,但很少像英国古典诗歌那样严格按照词汇分类进行押韵,12对押韵中,只有4对押韵是按照名词与名词或动词与动词分类进行押韵的,比如,动词押韵grow/blow和goes/repose,名词押韵power/flower和hour/flower。其他押韵都是实义词范围内的不同词性的押韵。比如:名词与动词的押韵retreat/greet,告诉我们,野忍冬花在这片隐居的地方独自挥舞招展;副词与名词的押韵here/tear,暗示着这里还有泪水,不是野忍冬花的泪水,而是诗人的伤感之泪;名词与副词的押韵eye/by,粗俗的眼光(eye)请从旁边(by)走过去,这与第二节诗歌的主旨是一样的,野忍冬花被大自然保护得严严实实;最后一节中,名词与动词的押韵dews/lose,露水(dews)失去(lose)了,流入了野忍冬花,养育了野忍冬花;动词与名词的押韵came/same,暗示着野忍冬花不仅死去时是一样的,来到这个世界时也是一样的。总之,这两组押韵与最后一节诗的主要内容是相吻合的。
2.3 语法形式:标点、词法、句法
纵览全诗,《野忍冬花》的动词是值得品味的。该诗中的动词存在三种时态: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一般过去时,还有动词的过去分词。与野忍冬花“产生直接关系的所有动词都是一般现在时”[8]57和第18行的包括grow、blow、greet,这些动词的一般现在时仿佛在诗人的眼皮底下一一呈现。还有一类动词的一般现在时是说明一般的客观规律的,包括goes、decay、lose、die、are、is、grieve,这些动词反映了诗人的顿悟,诗人从顿悟中发现了某种自然规律。诗中第5、6行的shall crush、(shall)provoke[8]57和第18行的shall leave都是动词的一般将来时,与此时此刻相对应,这些动词都是记叙将来的事情。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谁也说不清楚。另外,从shall leave这个短语得知,Autumn’s power应该指秋天的余威,也预示了下一节冬天的即将到来。一般过去时的动词包括bade、planted、sent、died、were、did、came,这些动词的过去时拓展了诗人的视野及其理解的范围,表明诗人“把野忍冬花视作从属于自然规律的来自于大自然的物体”[8]57,不受时间的限制。其中,过去时did是动词bloom的强调形式,加强语气,突出自然规律的不可违,即使这些花开在伊甸园,也无法逃避堕落的命运。该诗中动词的过去分词untouched、unseen等具有形容词特点,描述野忍冬花的现状,而过去分词smit则具有被动的含义,主要描述诗人的感受。无论是过去分词,还是一般过去时,抑或是一般将来时,都超出了一般现在时的当下范围,与野忍冬花有关,也与人类有关,“该诗的语言所营造的时间暂停反映了人类的缺席,而不是大自然自身的真实情况”[8]57。总之,野忍冬花既是真实的(生于南卡州一带),又是非真实的(时空的跨越),是从现实中浓缩出来的一种象征。
Arner认为hid是过去分词[8]57,但从句法的角度分析,hid是动词hide的一般过去式,用作主语fair flower的谓语动词。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了一个定语从句“that dost so comely grow”,前后用逗号隔开。在这2行诗中,谓语动词grow和hid的时态不同,时空不同,时空进行了跨越,野忍冬花的漂亮是即时的,但野忍冬花的藏身却是大自然开天辟地时的安排,再漂亮的花也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第4行的冒号既有提示下文的作用,又有总结上文的作用,冒号的这种双重作用强调前后两个诗行内容的一致性,以否定形式No开头的诗行,既是重复以否定形式“Un-”开头的诗行,又是对它的强调,第5、6行进一步强调第3、4行野忍冬花的幽居。第二个诗节中的分号隔离开前4行诗和后2行诗,前4行与后2行既是承接关系又是转折关系。承接的是一个季节的流转——初夏、盛夏、晚夏;转折的是前后的语气差异——转折前,诗人是为野忍冬花能够在大自然的呵护下蓬勃生长而感到欣喜,转折后,诗人在简单句和独立主格结构诗行中流露出些微感伤,因为野忍冬花日见枯萎。从时态的角度看,分号前后的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分号前是一般过去时,分号后则是一般现在时,大自然创造了一切,而当下的野忍冬花也逃避不了季节的轮换。第三节中出现了2个分号,前后是承接关系,描述自然客观规律,连上帝的伊甸园也无法抵挡秋风瑟瑟。第1个分号前的2行诗是一个复合句,过去分词短语作状语,其中还有一个定语从句“that must decay”,野忍冬花的魅力是一种衰退的魅力,还是逃脱不了大自然的宿命。第2个分号前的2行诗中,第1行是一个并列句,第2行是一个带有定语从句的同位语成分,解释上一行的flower。并列句诗行中的破折号把前后两个分句隔开,递进地说明这些花共同的命运。最后2行诗是跨行诗,行与行之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实际上是1个诗句。诗句的2个主语并列为1行诗,诗句的谓语部分另起一行,从而突显秋天的特质:寒霜的威力和野忍冬花的命运。最后一节诗中,冒号和分号齐聚。第2行末尾的冒号提示下文4行诗的内容是一种衍生的感悟,也可以看作后4行诗是对前2行诗的一种总结。第4行的分号并列两种哲学的感悟,后一种名词短语式感悟是对前一种复合句式感悟的画龙点睛,豁达之余还是存在一种感伤,感叹花命的脆弱(The frail duration of a flower)。
2.4 语义形式:修辞、意象、含混
现代派诗人认为,意象只存在于具体事物中,而伊格尔顿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将具体性与事物等同起来是一个错误”,“正是这种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网络才是‘具体的’,而被孤立思考的客体则是完全抽象的”[11]214。在《野忍冬花》这首诗中,野忍冬花是一个具体的意象,但这种具体的意象蕴藏于各种关系中,其中一种关系就是修辞。诗中拟人的手法非常明显,从thy、thee、tear、you等词可以看出,说话者把忍冬花当作人来对待,从而“暗示人类经验与植物经历之间的直接相关性”[13]89。诗人在第三节中引用伊甸园(Eden),其实就是在暗示野忍冬花也会像人类一样沉沦。
提喻这样一种修辞,关注的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以部分来指代整体。野忍冬花的生命时间就是依靠提喻来提示的,诗中用days来指代野忍冬花的一生,最后一节中又用an hour来夸张地指代days,自然而然引出野忍冬花生命的短暂与脆弱“the frail duration of a flower”。
排比处理的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共同营造一种强势的效果。第一节中,诗人通过4个排比句“Untouched thy…”、“Unseen thy…”、“No roving foot…”、“No busy hand…”,通过触觉、视觉等共同营造出清幽的野忍冬花这一意象。第二节中,“And planted …”和“And sent …”这2个排比句共同勾勒出掌控万事万物生死的大自然这一意象。
重复主要关注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从而给读者留下挥之不去的形象。第一节中的排比句实际上是在重复否定意义,Untouched、Unseen、No roving、No busy等词的否定意义又在最后一节诗里的单词nothing的重复中得以回响和强调。从重复中可以发现,野忍冬花的幽居最终导致野忍冬花的消亡,从而悟出人生的真谛,原本是空空(Un-、No、nothing),到头来还是一场空(nothing)。
隐喻关注隐藏的相似关系。如前所述,该诗最大的隐喻就是诗节的隐喻,隐含着野忍冬花的春、夏、秋、冬,也隐含着人的生、老、病、死。第一节中fair flower到最后一节frail duration of a flower,fair中预示着frail,frail也预示着fair,该诗隐含着“普通花卉的生命循环”[7]147,隐含着普通人的一生,也隐含着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以上种种修辞诠释了具体性的各种关系,通过这些修辞,野忍冬花美丽而脆弱的意象跃然纸上。
含混通常发生在“一个词语的两个或更多意义彼此合为一体,其意义本身就变得模糊不清”[11]188之时。如前所述,野忍冬花是真实存在的,但就诗人而言,野忍冬花是诗人亲眼目睹之物?还是一种象征?有人说是诗人亲睹之物;也有人认为,野忍冬花是一种象征,“诗中否定词的轮番出现暗示了野忍冬花之美的非真实性”[8]57。这些本身说明了诗歌的含混性,《野忍冬花》的美就在于其含混性。含混性还体现在诗歌的反讽中,该诗存在两处反讽,这些反讽增加了诗歌的张力。其一,该诗拥有抑扬格四韵步、六行诗节ababcc的押韵格式等比较固定的韵律,但这些韵律表现的野忍冬花之美却发生了变化,在诗人的笔下,这些花都变成了易逝之物。“诗歌韵律的相对稳定与野忍冬花的易逝”[8]54,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形式与内容互相讥讽,从而产生一种审美张力。其二,诗歌的说话者极力描述野忍冬花的幽居,使用了一系列的否定词,但说话者也没有发觉,这些带有人类观察角度的否定词已经干扰了野忍冬花的幽居,“野忍冬花的生存依赖于远离人类的幽居,但说话者擅闯野忍冬花的私地削弱了说话者创造的野忍冬花的幽居之美”[8]57。否定形式引起的反讽,阐释了诗歌的含混性,增加了诗歌审美的魅力。
最后1行诗“The frail duration of a flower”的含混性更值得玩味。这行诗经过2次修订,最初是“the empty image of a flower”,1788年修改为“the mere idea of a flower”,1795年才定稿为最终版本“The frail duration of a flower”。版本的差异体现了该行诗的含混性。前2个版本诗行是对前几行诗的概括,比较直接,丧失了不少诗味,而最终版本比较含混,更具诗意,“更能博得读者的同情心”[13]88。duration是多久?诗中给出了相当含混的答案,既是四季,又是一天的岁月,更是一个小时(an hour),也有可能是野忍冬花枯萎的一瞬间(For when you die you are the same),还有可能是一种虚无(nothing)。
综观全文,基于新形式主义理论来解读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最著名的诗歌《野忍冬花》,诗歌形式紧紧围绕诗歌内容来布局,诗歌内容在诗歌形式中不断得到升华,人类、自然、时间等主题在诗节结构、语音形式、语法形式和语义形式等诗歌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春夏秋冬中、在扬抑格的韵律突变中、在冒号和分号的陪衬下、在诗意含混中,《野忍冬花》和野忍冬花的主旋律“沉思的忧郁”一遍又一遍奏响。
参考文献:
[1] Eagleton Terry.How to Read a Poem[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
[2] 陈太胜.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J].文艺研究,2013(5).
[3] Leary Lewis.That Rascal Freneau:A Study in Literary Failure[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41.
[4] Freneau Philip,Pattee Fred.The Poems of Philip Freneau,Poe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LinkedIn:Ulan Press,2012:72.
[5] Austin Mary,Helen K Vreeland. Philip Freneau,The Poet of the Revolution:A History of His Life and Times[M].New York:A. Wessels Company,2010:71.
[6] Clark Harry Hayden.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Philip Freneau[J].Studies in Philology,1925,22(1):16.
[7] Bowden Mary Weatherspoon,Sylvia E Bowman. Philip Freneau[M].Boston:Twayne,1976.
[8] Arner Robert.Neo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A Reading of Freneau’s “The Wild Honey Suckle”[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1974(1).
[9] 聂珍钊.英语诗歌形式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 Gibbens V E. A Note on Three Lyrics of Philip Freneau[J].Modern Language Notes,1944,59(5):313.
[11] 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M].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2] Preminger Alex,Brogan V.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80.
[13] Vitzthum Richard. Land and Sea:The Lyric Poetry of Philip Freneau[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