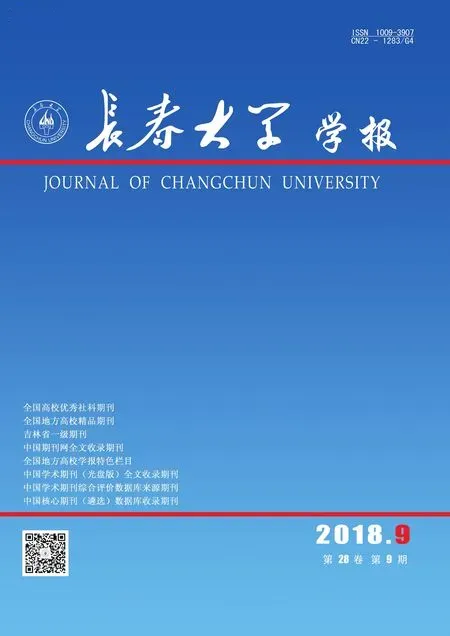现代市政思想的引入与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开启
王 谦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按照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考察,自资本主义出现后,统治城市的力量已由政治控制转移到重商主义,商人、财政金融家与地主代替了中世纪的城市管理者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力量,而当工业革命开始后,大量新发明的机器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将城市扩展的力量大大增加,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结构与面貌[1]。从19世纪开始,伦敦、巴黎、纽约等新兴工业城市异军突起,火车、电灯等现代化设施与高楼大厦成为这些城市的显著标志,代表了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最新成就,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锡耶纳等在中世纪风光一时的城市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开始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征程,用工业化获得的军事力量对古老的东方国家进行侵略。
1 现代市政思想在中国的引入
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现代化革新的时候,古老中国的统治者还在北京重重城墙的拱卫下沉醉于“万国来朝”的帝王梦之中,全然没有注意到外面世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英国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时,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们才慌了手脚,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了事。然而,清政府仍然拒绝接纳中国以外的世界,对美国公使赠送的大炮模型和一些现代科技书籍也予以谢绝,从而使中国错失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20年的宝贵时光,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2]。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仍未能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从封建王朝的幻梦中惊醒,仍然寄希望于腐朽的国家机器来苟延帝国的命运,反倒是清朝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于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廷重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洋务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以期在短期内增强国力,于是,清政府开始发展现代工业,在上海开办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现代化武器,在唐山成立开平矿务局开采煤矿。同时,在国内的上海、天津、福州、广州等城市与国外的横滨、神户、新加坡等处设立轮船招商局发展国际航运。此外,在文化方面,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开始教授学生英、俄、德、日等外语。至此,古老的中国终于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
清政府的官僚之所以能决心向西方学习,还与现代化思想向中国的输入有关。早在1847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在香港商人的资助下赴美学习,容闳学成归国后,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并被委托从美国购置机器在安庆建立军工厂,容闳则乘机向清政府建议选派青年出洋留学[3]。在容闳的推动下,李鸿章经过清廷的批准于1872年夏派30人赴美留学,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詹天佑等人。1875年,又从福建船厂选派学员赴法国留学;1876年,从天津选派7人赴德国学习[4]。之后,大量的青年学生由清政府派遣至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诸国进行深造。此外,清政府还奖励政府官员到国外长期游历,以考察、学习外国的科技与新政。随着这些出国人员的陆续归国,近代化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涌入。
有论者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开始早期现代化进程”[5]485。当现代化的工业技术、思想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城市也就随之发生了变革。但中国的城市并不像国外的城市大多从国家的首都城市率先现代化(伦敦、巴黎、柏林等城市莫不如此),而是由一些沿海、沿江的中小城市先行走上变革的道路。这是由于这些城市都是在列强的军事胁迫下被迫开放的通商城市,如上海、宁波、镇江、福州、厦门、广州、芜湖、安庆、汉口、杭州、重庆、天津、长春等,不仅如此,外国列强又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汉口、重庆等城市建立租界。这也显示出近代中国城市不同于国外城市的发展逻辑,即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变革所产生的推动力的双重影响下的特殊发展模式[5]465-466。因此,当上述城市先后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帝都北京仍在清政府所设置的层层军事防线中保持着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延续着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外逃以及随后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正式确立与铁路的进京,北京才正式在外力入侵与内部结构调整的合力下开启了缓慢的现代序幕。
导致中国城市产生变革的“外力”首先自然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先进的工业技术。同时,国外新兴工业城市建设所取得成就与早期出洋国人对这些城市的描绘,也激发了本土国人对于现代工业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想象与向往,特别是对于北京这个受层层军事屏障保护的传统城市而言,清末民初对于异域现代城市的想象与现代城市生活观念的引入,对于推动北京的城市变革起到了军事强力所起不到的作用。
2 国人早期的异域现代都市体验与想象
国人对于国外城市的想象是由早期出国游学人员、官员对欧美等大工业城市的描绘开始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晚清思想家王韬到欧洲游历,记录下了当时欧洲城市的繁盛景象。王韬初到伦敦时,“从车中望之,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寓在敖司佛街,楼宇七层,华敞异常。客之行李皆置小屋中,用机器旋转而上。偶尔出外散步,则衢路整洁,房屋崇宏,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6]。高耸的楼房、快速的交通与电器的使用是国人早期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印象。晚清官员郭嵩焘初到欧洲时也称叹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7]。大洋彼岸的纽约也是如此,近代邮政的倡导者李圭在美国游历,对纽约的印象是:“屋由三层高至七八层,壮丽无缘。行人车马,填塞街巷,彻夜不绝。河内帆樯林立,一望无际。铁路、电线如脉络,无不贯通。”[8]纽约是美国一个新兴的城市,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于1847年初到美国时,纽约还只是一个仅有25万至30万人口的小城市,而当容闳于1909年返回美国时,纽约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3]14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这些出国游历、留学的官员与青年学生,多是抱着救国的心态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其政治体制的,他们考察的主要对象是造船、铁路、电气等现代工业,城市本身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因而在这一时期,国人对外国城市仅仅是一种印象式的描绘,他们并没有考察现代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运行模式,也没有深入地体验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将现代城市与中国城市进行对比。这一时期国人与现代工业城市的初遇,没有价值上的评判。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洋务运动效果的逐渐显现与国内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城市设施与城市生活慢慢为人们所关注,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留意国外现代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的进步性,并将之与国内城市进行比较,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已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维新派的代表之一康有为在接触国外的现代城市文明后,很快被现代科技所吸引并对之大加赞叹:“电灯可以照夜为昼,电戏可以动跳如生,电板可以留声听歌,电车可以通远为近,影相可以缩人物山川于目前,印板可以留书籍报纸于顷刻,凡此开知识、致欢乐之事,人道所号为文明,国体所藉为盛美者,皆新物质之为之也。”[9]87在康有为看来,现代科技文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都市生活,是一种高于古代文明的新文明,应引入到中国来。当游历到法国后,他又被巴黎林荫大道的繁丽所折服,在康有为眼里,国都城市的道路不仅关系卫生,还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而相比之下,“则我国古者精美之路,如秦之驰道,陷以金椎,树以青松;唐京道广百步,夹以绿槐,中为沙堤,亦不足以与于兹。他日吾国变法,必当比德、美、法之首,尽收其胜,而增美释回,乃可以胜。窃意以此道为式,而林中加以汉堡之花,时堆太湖之石,或为喷水之池,一里必有短亭,二里必有长亭,如一公园然;人行夹道,用美国大炼化石,加以罗马之摩色异下园林路之砌小石为花样,妙选嘉木如桐如柳者荫之;则吾国道路,可以冠绝天下矣!”[9]143康有为所提倡的林荫大道理念,实际上是一种花园城市的设想,后来中国的许多城市在路政规划中都接受了这一理念。
然而,大多数国人还是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市政更感兴趣。在20世纪之前,人们还只能通过少量的外国游记了解国外的城市状况,到20世纪初年,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国外现代城市的交通、建筑、卫生、电器以及其他市政设施,以一种新文明、新观念的形式迅速在中国的舆论中散播开来,大量宣传现代城市观念的文章出现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报纸上,鼓吹现代城市的优越,北京的《群强报》还曾专辟“海外丛谈”的专栏,定期介绍外国城市的现代化市政,特别是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最为国人所称道:“先由美国纽育市走一走看看,看见有惊人的高架铁道,西洋的房子盖的很高,最高的约有三十层。他那高架铁道,总在十二三层的地方经过,围着街市绕弯,什么地方都可利用。”[10]在交通工具方面,人们也意识到了在城市开设电车的必要性,认识到电车的益处,“其能力可使背乡变闹市,远路变成比邻,补助商界,补助学界,补助军界、警界、政界,至于伶界、花界、报界,所受的利益尤大”[11]。此外,诸如城市供水、卫生、照明、通信等市政工程的重要,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对于市民精神生活的益处,都在这一时期传入国内。总而言之,现代化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国人对新生活的追求。
尽管现代化的城市对于封闭的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遵循资本主义与商业经济逻辑所规划的现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也有其自身消极的一面。梁启超到达美国后,就对纽约的近代化表示不以为然,在梁启超眼中,“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高等电车也”[12]1144。特别是街道上的各种快速交通工具,令他难以适应,“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辚辚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错,魂胆为摇”[12]1144。显然,纽约这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并没有给梁启超带来美好的体验,“居纽约将匝月,日为电车、汽车、马车之所鞺鞳,神气昏浊,脑筋瞀乱。一到哈佛,如入桃源,一种静穆之气使人悠然意远。全市贯以一浅川,两岸嘉木竞荫,芳草如箦。居此一日,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12]1148。 在梁启超看来,闲适的田园城市生活比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更符合人性,因此,在纽约游历期间,梁启超常常避开拥挤的闹市,选择到公园中消遣。
当然,梁启超对于现代城市的反感只是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他还不可能像恩格斯与芒福德那样对工业城市从生产方式与社会进化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批判,梁启超对于现代城市的体验与其他早期中国游历者一样,还处在初次接触现代城市的震惊体验过程中。
3 现代市政思想与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开启
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是第一种在全世界成为普遍形式的城市。工业化带来城市产业的集中,人口的聚集,城市主导地位的确立”[13]。在清末民初的世纪之交,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都先后开始近代化的进程。当地的城市居民也享受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优越,在外国势力的主导下,这些城市都修建了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建筑,城市供水、电力照明等设施也逐步完善,电车也先后在这些城市开行。而此时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仍然还保持着传统城市的格局,四重城墙构成的封闭空间严重束缚了城市的人口流动,而由于八国联军入侵造成的城市破坏又未能及时修补,此时的北京非但没有具备成规模的现代城市发展要素*清末北京已出现部分现代化要素,如电力照明、电话等,但仅限于当朝权臣与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未能大范围普及。,战争留下的创伤使其作为国都的传统城市形象也大打折扣。
民国建立,经过南北双方紧张的斡旋后,北京再次被确立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时代的更替与社会性质的变化,使人们对首善之区北京的城市功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不再是服务封建皇权的帝都,而是能体现共和精神、便利全民的新型城市,对于这种城市的标准,人们也利用国外的首都作为参照,“国都必具三要素:交通便利一也,道路宏洁二也,屋宇丽整三也。法之巴黎,美之纽约,德之柏林,英之伦敦是也”[14]。然而,这三个要素北京基本都不具备,有人指出,“京师商业最发达者,第一是饭馆、茶楼、淫子、花园四种,其次如马车、洋货、电灯、电话,亦渐有日增月盛之势,然若属于文明事业,交通则电车迄今未修也,教育则书肆日见其凄凉,卫生则自来水不如土井之畅销也”[15]。显然,在时人眼中,所谓的“文明事业”就是指现代化的城市市政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以现代城市的标准衡量,国都北京需要补的功课太多,历史积弊太深,特别是城内道路的恶化、交通状况的落后,最为市民所诟病。在清末时,“北京道路之坏者,著名于世。今虽渐修马路,然止于通衢,不及于僻巷,雨天则泥泞满地,晴日则尘埃蔽天。行人之不便,莫甚于此,亟宜修理道路,以便交通”[16]。为求交通的进步,电车逐步进入北京市民的视野,民国初年,北京的地方报纸经常刊文介绍国外电车的优势,“那电车要是到了加快的时候,旁边打雷似的,可以有火车那么快。按说人口多的地方,应该有拥挤混杂等事,而纽约的地方,有这样交通便利的东西,所以人口虽然那么多,一点也不混杂,而且很长的街,从这头到那头,使不了多大的时候,就可以走到,不像咱们北京城,从北城到南城,要用点儿的工夫,交通这么不便[17]。可见,在首善之区引入电车、发展快速交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除了发展交通、改良城市的外部形象外,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建设新北京的内在要求。在帝制时代因个人身份、社会阶层的差异与城市空间的区隔等形成的生活方式在共和时代成为腐朽文明的象征,打破城市生活资源的专权、垄断成为共和时代的新追求。民国成立后,“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18]。人们急切地希望过上文明城市的新生活。于是,创建城市公园、现代学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模范剧场等公共娱乐、文化场所的呼吁不断,人们认为这些都是“都市文化行政上必要之举”,是新时代“国家表示其文明之一种装饰品”[19]。这些民意表明,北京市民民主、自治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人们对于北京市政建设之进行已从早期单纯现代城市想象向国外现代城市模仿转变,最终将现代工业城市的标本移植到建设本土城市上来。
无论是提倡发展交通、引入电车,还是改良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公共空间,发展北京城市市政的初衷与落脚点都在于重塑民国国都的新形象,“中外观瞻所系”成为发展北京市政的主要动力。脏乱的街道、落后的城市生活、消极的城市形象,与国家首都的形象严重不符,“倘不急谋整理,渐次改良,匪特不足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且将为世界列强所笑”[20]。“首善之区”的建设,不仅是要树立全国模范,更是因为北京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在民国初立之时必须通过改造北京的城市形象以使北京获得外国的承认。当时,多数人都把建设“首善之区”理解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北京城,因而处处以国外的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作为北京的参照,“俾腐旧之都市得以早进文明,切勿固步自封,不谋建设,使外人诮我为古典的国家、历史的陈物,有市政之责者务当急起直追,不容视为缓图”[21]。可见,随着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现代工业城市逐渐成为北京市民眼中的理想城市图景,而作为帝都、古都的北京则被主要舆论所遗弃。
然而,在呼吁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喧嚣中,也出现了保护城市古迹的声音。与上海、天津等新兴城市不同,北京城是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拥有大量的历史古迹。清帝退位之后,大量的皇家宫苑收归国有,此外,还有城墙、牌楼、坛庙等古代遗迹,都保存较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庚子事件之后,西式的建筑如商场、饭店、银行等先后在北京出现,城市面貌呈现出新旧杂陈、东西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当外国的现代市政理念传入北京后,如何处理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迹与发展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古迹?有观点指出,“市之内政或非羁旅者所易知,市之外观实为游观者所共见。故苟欲筹办市政,宜先谋壮其观瞻,而欲壮其观瞻,不可不以保存古来建筑为急务也”[22]。这种观点把北京的古建筑视为国家的文化遗产,而保存这些遗产可能增加“国家之荣誉”。还有人认为,如果能保护好北京的古迹,“不独可资国民之观瞻,且使外人来游者亦可藉此以觇中国之文化”[16]。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北京的文化古迹与推进城市现代化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改善首善之区的城市形象以确立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
当然,保护古迹与现代化建设在市政建设的实践中充满了矛盾,保护古迹会给城市的近代化造成障碍,近代化建设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古迹构成威胁。现代市政思想遇到北京这样的传统城市时,必然会产生文化心理上的碰撞,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最终在北京的城市空间变迁上得到了呈现,北京的城市空间变迁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交叠的特征。我们在民国前中期的城市现代建设中看到传统的文化心理对近代化所构成的阻碍,特别是国都南迁北京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后,北京政府所施行大规模修复古物行为,这些具体的城市空间实践都能在早期找到思想、文化心理上的源头。
总体而言,在世纪之交乃至民国初年,现代城市思想随着早期出国游历的知识分子、官员等的引入,现代城市逐渐成为国人想象中的理想城市图景。伴随着舆论环境的成熟,现代市政理论日益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并向古都北京渗透,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北京城市突变变革的力量。同时,北京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思想的戒备也预示着北京的现代化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