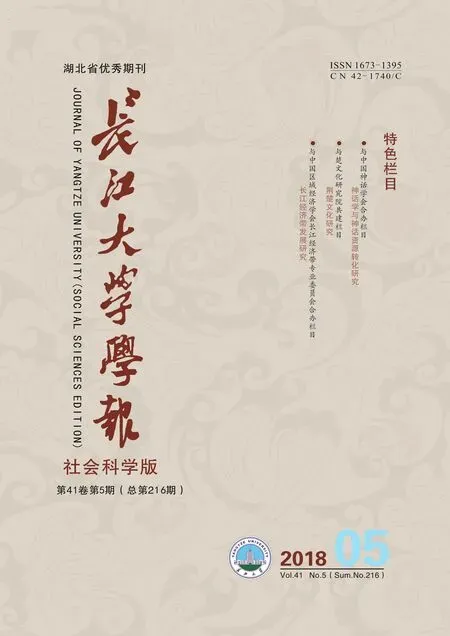从理学视阈看《论语》中乐的审美内涵
——兼论理学家对乐的价值认同
邓莹辉 陈翔宇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一
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孕育于原始巫文化之中,在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性格,存在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之中,成为鼓舞人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中,早已透露出一种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理性认识,如“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经·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永恒不衰的生命活力,革故鼎新的发展原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盈盈生意,不断变化发展,有着无限希望与前途的世界。中国人似乎从未真正彻底绝望过,总是怀着希望乐观地眺望未来,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总能够战胜困难,奋勇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乐感文化的传统,才从根本上维系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乐感文化的具体内涵是“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这种超越即道德又超道德,是认识又是信仰。它是知与情,亦即信仰、情感与认识的融合统一体。实际上,它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理性与感性二分、体(神)用(现象界)割离、灵肉对立的宗教境界。”[1]在人生快乐处求超越,在世俗生活中获道体,于有限中求无限,这正是中国实用理性在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上留下的烙印。
在中国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十分执著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他们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便主要是用来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有着非常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同样,孔子也非常重视对乐的追寻。《论语》中有24处提及的乐,是孔子与弟子之间长盛不衰的一个经典话题。“孔颜乐处”的范型流传千古,成为封建士大夫所推崇的审美人格理想和精神信仰,乐亦由此成为传统儒家的重要审美范畴。《论语》中,孔子关于乐有多处论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P229,231)此外,他还对颇得自己精神的学生颜回赞赏不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P208)孔子和颜回之所以能够安于贫困的生活,勤奋好学,乃是因为他们矢志不渝地追求心中之大道。在《论语》中,孔子曾对如何求道这一问题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贫,未足与议也”[2](P172),“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3](P58),“笃信好学,守死善道”[2](P249)。由此可见,对道的追寻,实在离不开安于贫困的坦荡之心,以及勤奋好学的钻研精神。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2](P171)正是这份坦荡之心,才能让人超脱于困顿不堪的现实生活,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通达,从而获得一种由得道而引发的乐的情感体验。
《吕氏春秋·慎人篇》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由此观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于乐的体验主要来源于道。孔子的一贯之道“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修养;二是以周礼为基础的政治典章制度”[4]。仁即爱人,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礼即周礼,强调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孔子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2](P167)这一论述较为明确地阐释了乐与仁之间的关系,要想长久获得乐的体验,就必须始终重视个人修养,做一个仁人,即一个有爱心,充满道德感的人。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使天下复归于文王之道,天下安定有序,百姓安居乐业,即臻于“大道之行”这一完美状态。正是怀揣这一抱负,他才在处于无用武之地的窘境时感叹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P79)孔子曾这样阐释仁与礼之间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2](P167)认为要想使道德修养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使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礼的规定。由此可见,复礼是行仁的必要条件,人的自我修养是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紧密相连的,个体的行为必须受到礼的制约。
乐这一情感性的审美体验源于对道的追寻,更离不开对道的体认和践行,即通过行仁和复礼的方式来调和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行仁强调主体自我道德修养的完善,获得仁民爱物之心,通过爱人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大同世界的构建。复礼则是以恢复周礼为社会政治目标,使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从而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达到和谐的理想状态。所以,传统儒家将乐集中体现为一种安贫乐道的人生范式,通过主体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的实践,即道德践履功夫,将恢复周礼以及实行仁道之治的外在价值理想内化为个体的人格追求,在主观与客观不断相符合的过程中,生发出一种道德之乐的情感体验。安贫乐道这一人生范式经过后世儒家的继承与发扬,成为传统士人所共同恪守的准则,也成为历代士大夫在遭遇挫折和失败时最好的精神慰藉,体现出了士大夫人格精神的崇高。
二
时至宋代,理学家们对乐的探寻,主要是通过对“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这两种圣人气象范型的讨论来展开的。乐作为理学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主要是指天人合一的情感体验。理学家们在“存天理”的理性思索与“灭人欲”的道德自律中,以心性为乐,通过涵养主体心性,达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直至天人合一之境界,即以生为本,以乐为最高境界的生命模式.这一生命模式突破了传统儒家拘泥于个人社会实践的层次,通向自然而然联结天人,追求形上之真的澄明之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人生关怀意味的审美之乐,又显示出无限的宇宙情怀。
宋代理学家对“孔颜乐处”作了集中而充分的讨论。在理学思想体系中,“孔颜乐处”的命题具有十分深刻的意味。周敦颐首先对其加以阐释:“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5](P38)在周敦颐看来,颜子之所以“不改其乐”,是因为他见到了“天地间”的“大”,即“至贵至爱”之物,这是比“富贵”更可爱的存在,而人们所向往的富贵是“小”。颜子在认识上见“大”而忘“小”,从而无论生活环境优劣与否,都能够“处之一”,在心则能“化而齐”。因此,颜子的“不改其乐”主要指的是一种“处之一,化而齐”的通达心境。程颢说:“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6](P135)孔颜所乐究竟为何事?二程认为,颜子所乐,是乐其心中之所乐,忘其生活之所苦。“颜子箪瓢,非乐也,忘也。”[6](P88)“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6](P399)虽然二程对此问题的回答十分含糊,但是通过对二者思想的整体把握,仍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程颐年轻时,在游太学时曾写过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专门讨论颜子所好为何物:“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字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6](P577)他认为正是因为颜子独好“圣人之道”,才深受孔子喜爱。一般认为,人之所以有某种爱好,乃是因为其能给人以快乐的情感体验,是出于人发自内心的热爱。程颐对颜子所好之学为何物的分析,似乎也间接给颜子所乐为何事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颜子所乐乃是对“圣人之道”的不懈追求,以期达到圣人之境界。对此,朱熹也作了相当细致的论述:“叔器问:‘颜子乐处,莫是乐天知命,而不以贫窭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乐天知命事,这四字也拈不上……加此四字又坏了这乐。颜子胸中自有乐地,虽在贫窭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将那不以贫窭累其心底作乐。’”[7](P795)“‘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7](P833)那么这“别有乐处”“自有乐地”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朱熹的另一段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问:‘颜子之乐,只是天地之间至富至贵的道理,乐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须是穷究万理要极彻。’已而曰:‘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千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害其乐。”[7](P795~796)所谓“孔颜乐处”,原来是指在“浑然与物同体”的状态中,于“动静语默日用之间”,穷究天理,从而进入到一种“物我化一”,“心与理一”的“至乐”境界。“孔颜之乐,乐处在心,是一种主体的自我感受。其所乐之事有二:一是仁者静观万物时的浑然与物同体,由自然界的活泼生机了悟心中的仁体,以仁为乐;二是吟咏性情时的感兴愉悦,在心体的观照活动中体验到诗意和美,产生自适、自得之乐。前者多带有静坐体道性质,后者是心灵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受用,要在‘静观’而‘自得’之。”[8](P246)总之,颜子之所以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P208),是因为颜子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从仁的境界中感受到了乐,即自我精神的满足。他之所乐,既不为贫富贵贱所转移,也不仅仅是停留于个体社会实践层面上的道德之乐,而是与天地万物同体,同宇宙本体合一的大乐。
宋代理学家除了对“孔颜乐处”有十分细致的论述外,对于“曾点气象”,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周敦颐可以说是“曾点气象”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寄情山水,吟风弄月,喜欢隐居山林之中。他以唐朝元结自比:“吾乐盖易足,名溪朝暮侵;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行。”[9](P59)而且还时常“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9](P87)。因此,他的学生程颢评价说:“《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6](P59)所谓“吟风弄月”,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融情于景的审美体验,借自然中的山光水色来表达心中的乐趣。程颢说:“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礼’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6](P136)他认为孔子“与点”,乃是因为曾点“与圣人之志同”,具有尧舜气象(圣人气象),尧舜气象的特征是“为国以礼”,重视礼治和秩序。程颐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晳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6](P369)在程颐看来,曾点气象实际上是一种仁的境界,具体表现为充满爱的生命关怀,使“万物莫不遂其性”,人与万物和谐共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正是一种自然而然,顺理而为的人生境界。朱熹则从他所理解的世界本体——理的角度出发,对“曾点气象”作了新的理论阐释。他在《论语集注·先进第十一》中评价“曾点之乐”时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俟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2](P306)他认为,曾点之所以得到夫子的认可,乃是因其超越了“人欲”的藩篱,认识到了天理的存在,它无处不在,“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是故无处不可乐,无事不可乐。只要能领略天理,“日用之常”即是可乐之事。朱熹在此将“曾点气象”构建为一种“理己合一”,本体至上(“存天理”),道德自律(“灭人欲”)的纯粹审美境界。
宋代理学家们更加向往“孔颜乐处”。他们一方面盛赞“孔颜之乐”,认为其乐是“至贵至爱之物”,是一种“处之一,化而齐”的通达心境,更是与天地万物同体,同宇宙本体合一的大乐;另一方面则对“曾点气象”颇有微词。程颐明确指出曾点是“狂者”,仅知晓孔子之志,而“未必能为圣人之事”。朱熹也认为“曾点气象”欠缺细密功夫:“曾点见处极高,只是功夫疏略。”[7](P1026)“曾点的意思,与庄周相似,只不至于如此跌荡”,“曾点言志,当时夫子只是见他说几句索性话,令人快意,所以与之。其实细密功夫却多欠阙。便似庄列。如季武子死,倚其门而歌,打曾参扑地,皆有些狂怪”。[7](P1027)在他们看来,曾点似乎是一个近于庄周的狂怪形象,较颜子缺乏细密功夫,故而“孔颜之乐”超越“曾点气象”,成为理学家所认同的人生最高境界。
三
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圣人气象的探寻,以及关于“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的理论阐发,将乐从一种存在于个体社会实践层面的道德体验,转化为对“浑然与万物同体”“天人合一”之本体世界的审美体验。达到至乐境界之途,理学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学至于乐”,二是“成于乐”。
理学家认为,要达到乐的境界,必须具备乐的功夫。乐的功夫的积累与养成是通过学习来实现的,程颐在回答颜子所好何学时说:“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6(P577)]他认为学习是“至圣人之道”(具备圣人气象)的重要途径。邵雍也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10](P445)更加明确了乐与学之间的关系:学是方法和手段,乐是目的与结果。因此,理学家历来重视对为学之方的探讨,并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周敦颐认为,成圣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务实胜”的认识论,即以“实胜”为善,以“名胜”为耻,实胜于名,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当以“务实胜”,即以务道德为本;二是“主静”和“一为要”的道德修养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欲故静”之说,“无欲”是“主静”的重要条件,又是成圣的基本途径,所以应当清除后天染上的种种欲望,复归到虚静无为的天性。所谓“一为要”,周敦颐解释说:“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乎矣。”[5](P38)“一”与“主静”之义相同,指的都是人心的纯粹虚静,内心没有任何成见,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进而达到“明通公溥”之状态,开明通达而又公正无私,体包万物而又无所偏狭,如若能够如此,便也十分接近于圣人了。在为学方法上,二程也受到周敦颐的影响,但又有所突破和发展。他们以敬代替静,使其避免堕入佛老,令人产生误会。二程提出了完整的为学方法,即“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6](P188),认为在道德修养上应该是恭恭敬敬,诚心诚意的,而在学问上应当是日积月累,不断进步的,又强调“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6](P157).这就将敬与有佛老意味的虚静作了严格区分。涵养道德用敬便可使人消除烦恼,获得心灵的宁静。“敬是闲邪之道。闲邪存其诚,虽是两事,然亦只是一事。闲邪则诚自存矣。”[6](P185)敬有闲邪存诚之义,主要指人的理性意识,即对理的自觉遵循。而敬与诚又是紧密相连的,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6](P127)敬乃人事之根本,是行天道,即达到诚的境界的先决条件。程颐也说:“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6](P1170)敬是进入诚的通道,是思诚的途径,亦即诚之达道。欲诚者须从持敬开始,使自己的道德行为达到与天道合一的至诚境界,与生而有之的本性之善保持和谐统一,如此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与孟子所谓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相契合。
朱熹则在二程持敬和“涵养须用敬”为学方法的基础上,作了新的理论阐发,提倡“居敬穷理”。“居敬”亦即持敬,“穷理”指的是格物致知,二者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说:“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11](P2450)将敬看作圣贤之学的全部内容,而外在的“致知”与“力行”都以主体内在的敬为前提。因此,他将道德修养论与认识论相结合:“涵养求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主敬、穷理虽是二端,其实一本。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7](P150)通过“主敬”来涵养道德,增强主体格物致知的本领,以穷尽万物之理,从而进入“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通透之境,由此个体便可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以及超凡入圣的独特的精神体验,体味到天理之大乐。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认同“学至于乐”。他上承朱子“居敬穷理”观念,兼顾修身养德和格物致知两个方面,对颜子之乐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他在《问颜乐》中言:“集注所引程子三说。其一曰,不以贫窭改其乐,二曰,盖其自有乐,三曰,所乐何事,皆不说出颜子之乐是如何,乐其末,却令学者于博文约礼上用功。……颜子功夫,乃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无不穷究而用功之广也。约礼者,言以礼检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内外精粗,二者并进。则此心此身,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中,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此乃颜子之乐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象颜子之乐,而不知实用其功,虽日谈颜子之乐,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无下手处,特说博文约礼四字,命学者从此用力。真积日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罢不能之地,则颜子之乐,可以庶几矣。”[12](P551~552)真德秀认为,颜子之所以能达到“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的乐境,与其“博文约礼”的功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颜子所学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内修其身,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养成内在的道德心性;外则格物致知,以自己的道德之心体天下万物,增强对天理的体悟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陶冶,随着道德心性的养成,以及对天理的体悟能力的提高,最终融会贯通,即“此心此身,皆与理为一”,如此,必至颜子之乐境。
音乐的教化,即“成于乐”,也能让人们步入令人神往的至乐境界。乐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最初是与乐教联系在一起的。乐作为儒家六艺之一,主要担负着移风易俗的作用。《荀子·乐论》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13](P207)孔子认为,乐是修身的最高阶段,人只有学习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3](P24)孔安国注曰:“文,成也。”这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是必须要经过学习礼乐来完成的。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P246~247)所谓“成于乐”,便是“更多直接讲内在心理的自由塑造”[14](P54),就是在强调要通过乐的陶冶来造就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乐具有“感动人之善心”的功能,可以直接地感染熏陶塑造人的性情与心灵。
理学家们意识到,要想到达至乐境界,除了以“灭人欲”的道德自律方式来消除私心外,还有赖于乐本身的感化作用,因为“乐者所以成德,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则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6](P128)。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德性修养,由此而引发乐的情感体验。朱熹则认为:“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2](P247)圣人作乐,也是为了感化人心,以修身养性为主要目的。通过乐来养人性情,净化人的身心,使人顺于道德而至于义精仁熟的境界,终成仁而使自身完满。正因为乐能够直接诉诸人的内心,正人之性情,使人渐入“中正和乐”之佳境,达到美与善相统一,滋养人的德性,因此,通过养心人们便能达到与宇宙自然融合为一的至善至美之境界,也即至乐境界。
乐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传统儒家认为,乐是一种存在于个体社会实践层面的道德情感体验,集中体现为安贫乐道的人生范式,是一种道德之乐。而在宋代理学家的眼里,乐则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了审美层面,成为“浑然与万物同体”“天人合一”之本体世界的审美体验,是一种审美之乐。“学至于乐”与“成于乐”两种方法的提出,特别是对为学之方、乐之感化作用的阐发与探寻,为普通人超凡入圣到达至乐境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