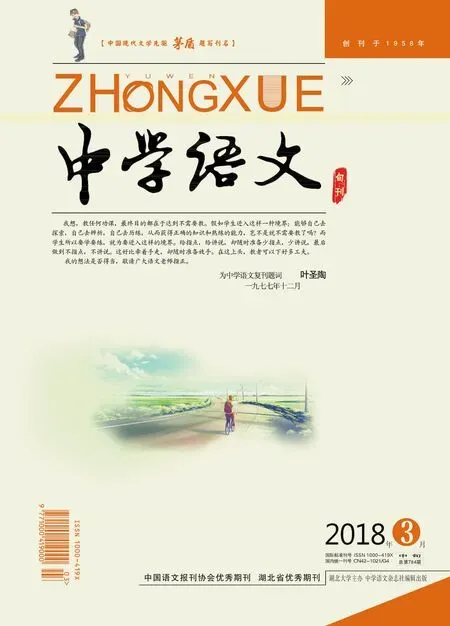黄蓉 你争口气
王梦影/文 周心印/评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迷思之一是黄蓉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的巨大转变。
开个脑洞,用武林类比学术世界看这个变化。在《射雕英雄传》里,年轻的黄蓉已然是光芒耀眼的科研之星:家学渊源、师从各领域泰斗、日阅论文三百篇。她脑子灵双手勤,年纪轻轻就能带研究生,甚至开始领导国内顶级实验室(丐帮)。这架势,是要开山立派掀风雨的。
也不过20年,俏蓉儿已是面带风霜的郭夫人,早早从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每天的生活重心绕不开襄阳的学区房,操心大女儿找工作小女儿青春期,灵巧劲儿主要用于发展老公的社会关系。如此精力分散,难怪被连博士学位都没拿到的后辈李莫愁攻击得很狼狈。
反观后来的巨擘郭靖,认识黄蓉时还是降分录取的边远地区学子,资质普通,靠着后者的裙带关系才进了洪七公的课题组,让努力有了契机。
那时候,也许会有少林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悠悠感叹:历史经验证明,女侠继续闯荡江湖的十不足一,大多数就是混一个名头就嫁人了。今年入山门前几名居然都是女的,真是占名额,挡了真心搞武学的考生的路。
临了补充一句:我不是歧视啊,郭夫人其实真可以争气点。
刚读黄蓉时年纪小,挺不满意剧情发展。小朋友有江湖梦:仗剑骑马,无所挂碍,誓不会像桃花岛家的小女儿,一身灵气都消耗在夫君儿女的小天地里。我可能也会想:虽然听起来让人不舒服,可黄蓉也不过如此。
工作后,我写过一个关于女科学家的稿子。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2400万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华山之巅,很少见到女性身影。更多的江湖女儿,藏在了波涛之下,或是搁浅在了生活的沙滩。采访中,不少教授告诉我,自己实验室里的女生表现不比男生差,最后走上学术深造道路的却远远少于男生。
似乎没人逼她们,这是她们的自主选择。这是我成人后慢慢明白的。当黄蓉站在襄阳城楼上,孩子们已经能独当一面,丈夫永远沉默踏实地立在身旁,我猜她是幸福的。她做出了选择,她不后悔。
黄蓉的女儿郭襄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她终生未婚,无儿无女,建立了一个顶尖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之星,书写了能载入武学史册的著作。光是她成果的证明、延伸和反证都能养活好几代人。如此学术大牛,后人对她的讨论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她的情史。
这就是江湖“历史经验”给出的女性单选题了:要么“不争气”却守着冷暖自知的幸福,如黄蓉;要么“争气”而总被“高处不胜寒”,如郭襄。
与此同时,江湖“历史经验”给男性的单选则是:学术,究竟是如郭靖 “为国为民”,还是如风清扬“独孤求败”。
太奇怪了,同样的起点,为什么要解答不同的考卷?当选项不平等,自主无意义。
“历史经验”是恶毒又狡诈的歧视,它把受不公平对待后的结果,当作继续这种不公平的理由。到最后,连不公正的受害者自己也迷糊了,看不到家庭和事业单选题以外的各种可能性:延长男性产假让夫妻双方共同照顾孩子、社会福利更深介入帮助家庭照顾老幼……
它伤害的也不只黄蓉一个,江湖艰难。
水少鱼虾众,资源分配不公平。同样研究《葵花宝典》,林家镖局申请项目基金就不如华山派更有机会。丐帮名声响,长老位置就那么几个,招生又那么多,打狗棒耍上天也只能慢慢等机会。
黄蓉郭靖们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大战里乌压压的背影。你求上山门,你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对武林未来说不上有多大责任心,你只知道行囊里是父母半辈子的积蓄。你以为武学千变万化,其实灵动与轻盈是奢侈,重复的挑水打桩才是常态。遇到糟糕的师傅,天天摁着跑镖不让正经练武。遇到好的师傅潜心向学,也免不了在师兄来访时心生彷徨——人家拳打得不如你、套路钻研不如你,去了小公司明教没想到创业板上市已经小康了,你还住山门宿舍,想结婚都买不起襄阳的房。
这时候,一些家伙在你耳边一遍一遍地说,“历史说明,江湖不是女侠/非侠二代/小门派/契丹混血……的地盘”,你或许就真的放弃了。你很遗憾,但也不后悔,这就是生活。
可这些家伙还要坐在江湖之巅俯视你的挣扎,假惺惺地对无数个更年轻的你发寄语:“我不是歧视你们,你们自己得争气。”
争什么气?气都要气死了。
(选自2017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
【解 读】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陈述学术界女性科技工作者从事高端研究的尴尬现状,揭示其深层次复杂原因。文章触及敏感的学术界话题,主旨宏大深刻,而以武林类比言之,语言诙谐风趣,感情沉郁悲怆,深见忧国悯世之情怀。
文章标题 “黄蓉你争口气”俨然是站在学术之巅的权威们对女性科技工作者发出的寄语,也代表不明真相与原因的社会大众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失望与期许。表象地看,女性在求学与科研的初始阶段,常常表现特别出色,诸如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就斐然,享有盛誉。正如不少教授告诉作者的,“自己实验室里的女生表现不比男生差”,甚至令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感叹:“今年入山门前几名居然都是女的,真是占名额,挡了真心搞武学的考生的路。”学术老前辈们真担心考研考博的女性太出色,名额占得太多,会挡了真心搞学术研究的男生的路。可后来,女性“大多数就是混一个名头就嫁人了”,等到她们成家立业之后,尤其是“孩子们已经能独当一面,丈夫永远沉默踏实地立在身旁”的时候,她们“一身灵气都消耗在夫君儿女的小天地里”。中国科协提供的统计数据很是确凿,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庞大到超过2400万人,可拔尖女性人才寥寥,2013年两院院士中女性只有5%,长江学者中女性仅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这种现状怎不令人对女性科技工作者失望呢?
平心而论,女性在求学与科研的初始阶段的出色表现,一方面确实是与她们本人的勤奋刻苦,积极进取有关,但同时也表明这个阶段的男性实际上是“沦陷”了。有大学教师感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热门专业,大学新生的队伍中男生越是少见。”甚至有重点大学的教师悲叹:“现在的男生消失不见了。”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确实令人悲戚,中学阶段的女生用心读书,非常吃苦,而男生大多贪玩,多数喜欢玩游戏,因此男生扎堆进了普通本科与职业技术学院。尽管这是中学教育阶段存在的严重现实问题,但能不能因为女生上重点大学、进热门专业的比例大,女生大学毕业后考研考博的比例高,而日后拔尖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寥寥,就断言是女性科技工作者“混一个名头”后就不努力了,不争气了呢?不能。作者的回答是:“争什么气?气都要气死了。”作者的愤激之语,确实是无情现实的无奈悲叹。因为女性科技工作者“不争气”的背后,有目前科研体制的弊端存在,其一是“水少鱼虾众,资源分配不公平”,同等层次类别的科研课题,年轻的科技人员申请项目基金就不如元老派更有机会,更何况年轻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呢?二是“丐帮名声响,长老位置就那么几个”,因为学科带头人名额有限,年轻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打狗棒耍上天也只能慢慢等机会”,让你慢慢等上十年,再熬上二十年,你还会有韧性乎?或许你混明白了在现有体制下即使熬白了头也断无出头之日,你还会坚守下去吗?其次还有社会舆论环境的浑浊,倘若你一个女性科技工作者“终生未婚,无儿无女,建立了一个顶尖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之星,书写了能载入武学史册的著作”,始终得不到人们的敬重,人们看不到你作为“学术大牛”的科研价值,倒是津津乐道你的所谓“情史”,八卦你的绯闻,试问,还会有哪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敢如此“争气”?郭襄的“高处不胜寒”,折射出世俗的冷漠,世态的淡凉,世人的无聊。这种对于性别的“恶毒又狡诈的歧视”不除,女性科技工作者自然失去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再次还有社会配套的福利政策的问题存在,男性科技工作者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中,而不必因休产假照顾孩子分心,可以将照顾家庭老幼的负担推给妻子,自己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中,女性科技工作者可以享受如此政策福利吗?目前社会有无可能“延长男性产假让夫妻双方共同照顾孩子、社会福利更深介入帮助家庭照顾老幼”呢?当然还有现实的生存困境的困扰,诸如你“潜心向学”,取得了不俗的科研成就,但面对“拳打得不如你、套路钻研不如你”的师兄谋职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已经小康了,而你依然独守研究院的单人宿舍,“想结婚都买不起襄阳的房”,难免心里拔凉拔凉的。虽然这第四个因素可能是男性科技工作者与女性科技工作者共同遭遇的困境,但前三个因素可能是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专利”了。如果不能从外部帮助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平等机遇,创造有利科研条件,创设宽容仁爱的人文环境,单单从女性工作者自身找原因,指责女性科技工作者“不争气”,那么作者的“争什么气?气都要气死了”的愤激话,今后还有得说。
——致敬殡葬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