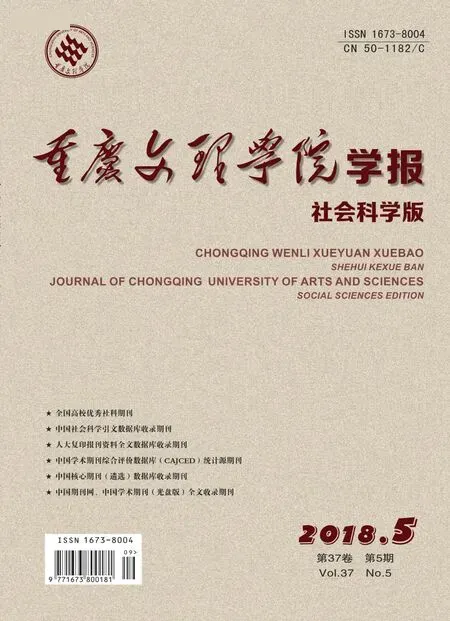多重空间的构建
——论空间视域下《地下铁道》的叙事艺术
赵聪聪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引言
(一)作家和作品介绍
科尔森·怀特黑德出生于美国纽约,早在童年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他毕业于最重原典的哈佛大学英文系,迄今为止共创作了六部小说。1999年怀特黑德发表处女作《直觉主义者》,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他佳作频出,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怀特黑德创作题材广泛且风格迥异,《哈佛杂志》授予他 “文学变色龙”的称号。2016年8月,《地下铁道》这一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问世,随之而来的一股“地下铁道旋风”迅速席卷美国。这篇小说构思巧妙,好评如潮,并且横扫各大奖项,相继获得了2016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度普利策奖。
《地下铁道》以美国19世纪上半叶历史为背景。当时南方种植园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北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日趋繁荣,西进运动初见曙光,整个国家发展日趋分裂。美国政府出台《逃奴追击法案》,黑奴逃亡和保护逃奴的行为都成了罪行,小说主人公科拉就生存在南北撕裂的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她生而为奴,不断受到奴隶主的虐待和周围奴隶的欺凌。最终,科拉忍受不了奴隶主的鞭打,决定逃出兰德尔种植园这一人间地狱,前往传说中的“地下铁道”。她一路向北,追寻属于自己的自由。从南卡罗来纳到北卡罗来纳,穿过田纳西,再到印第安纳直至更北的地方,科拉一路上目睹了种种的杀戮与不公。这是一段充满悬念和科幻色彩的旅程,折射了美国的时代背景,展现了黑人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一直存在着的恐惧与被歧视。跟随科拉的脚步,读者也领略到当时美国各州不同的政治形势与立场。哥伦比亚小说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评价这是 “一本勇敢和必要的书”,斯蒂芬·金也认为这是“有关逃亡、奉献、拯救的绝佳故事”。
(二)研究现状
由于《地下铁道》是怀特黑德的最新力作,因此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章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主要谈论其主题、出版价值和文化历史内涵。这部小说首先由《当代外国文学》引进,乔春梅在《出版广角》发表文章《自由之路的重新书写——〈地下铁道〉的价值探析》,着重分析其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探讨其出版的丰富文化内涵和价值;丁丽芳在《现代交际》上发表文章《黑暗之光:解读〈地下铁道〉》,探索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历史内涵。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这部作品的语言、叙事结构以及作家在叙述暴力方面的突破等,并且指出《地下铁道》是一部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历史小说。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关于《地下铁道》空间叙事的研究。对于《地下铁道》这样一部结构独特、寓意丰富的作品,探究其多重空间叙事对作品意义的呈现很有必要。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
随着后现代小说的发展,传统的时间观念被打破,叙事的空间性也越来越突出。就国外研究情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叙事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不仅是完善叙事理论的要求,也适应了创作实践的需要,空间越来越成为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以及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对象,可以认清并且拓宽人类自身生存的状况和环境,是当代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也可能是未来哲学的新取向。“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当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1]16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人类的空间已不再是一种纯自然的“真空”空间,而是一种人化的空间,“是一种被人类具体化和工具化了的自然语境,是充满各种场址、场所、场景、处所、所在地等各种地点的空间,是蕴含各种社会关系和具有异质性的空间”[2]381。个人思想和群体行动都必须在具体的空间中才得以进行,空间可以说是我们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
在一部小说中,作家会有目的地使用特定的叙事技巧,以丰富小说结构,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3],而《地下铁道》这本小说正是作者高超叙事技巧的体现。文本试从被边缘化的物理空间、矛盾的社会空间以及作品结构呈现出的空间形式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之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不仅是从作家创作角度考虑,更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所在。选择其他学者目前暂时没有涉足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作家空间叙事技巧的应用,呈现作品中作家所建构的暗淡混乱的现实物理空间、矛盾重重的社会空间以及作品最终整体结构的纵横交错的多维叙事空间。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主要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而空间形式对应的是作品结构,是作品抽象意义上的空间[4]23。
物理空间叙事关注作品中物理空间的叙事功能。后现代小说家利用物理空间的叙事来表现时间,并且利用物理空间的移动来推动整个叙事的进程。不同的物理空间会折射出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关系,激发出不同的叙事碎片。物理空间或者是自然空间虽然是人类社会进程的源头,但是主宰人类社会的显然已经不是自然空间而是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对社会关系的体现,强调社会关系的统治、服从与反抗[5]。空间形式则是按照空间的观念安排小说的结构,将散落在作品中的情节、结构等并置起来,小说的场景、人物塑造、章节安排和布局都与空间艺术密切相关。《地下铁道》一书中呈现了祖母的空地、伶仃屋、地下铁道、四十号、公园、阁楼、种植园木屋和马车等空间意象,这些都是黑奴的不正常生存空间,每一处都浸透着血与泪的回忆,每一处都诉说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作者巧妙地利用空间形式,使小说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一个混乱但又和谐的整体。因此,文本主要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作品结构的空间化三方面展开讨论,深入分析作家的空间叙事技巧。
二、物理空间:构建边缘化的暗黑世界
传统的文学作品对物理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的自然属性,只关注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或场景。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下,物理空间被重新赋予一种空间隐喻的概念。因此,物理空间不仅拥有其自然性质,并且可以传达出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地志空间的转换及意义呈现
从《地下铁道》文本的结构来看,全书十二个章节,其中六个章节是用具体的地名来命名,即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印第安纳→北方,这一物理空间的转换是主人公科拉寻找“奶与蜜之地”“迦南”的“出埃及”之路,不断推动故事的发展。凭着自己的勇气和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科拉走出了一条通往自由又充满血与泪的道路。德塞都说:“每一个故事都是旅行故事——一种空间实践,每天都经过若干地点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选择地点并把他们连接起来;他们从这些地点中建构出句子和路线。他们是空间的轨迹。”[6]115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转换就是空间轨迹的体现:佐治亚人间地狱般的种植园生活;南卡罗来纳的虚伪——只是把黑人当试验品;北卡罗来纳挂满尸首的“自由之路”;田纳西被火烧过的一片死亡景象;印第安纳的瓦伦丁种植园——一个黑人“黄金国”。即使最终到达北方,科拉却依然摆脱不了逃奴的身份,只能活在黑暗里,游走于“地下”,继续寻找着自由之路。科拉被残酷的现实驱逐着向前走、逃出来,短暂地站在阳光下,然后转身再度踏上逃亡之路,成为奴隶。自由是相对的,安全是暂时的,但桎梏是绝对的,科拉在逃亡的路上没有尽头。在白人的排斥和猎奴者的追捕下,科拉没有喘息的机会,停下来就意味着被捕或者死亡。
兰德尔种植园只是南方种植园当中的一个,它凄凉、狭小和危险,是一个充满绝望的被抛弃的荒原。奴隶们只允许在种植园内的特定区域活动,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在这一封闭的空间内,奴隶无法了解种植园外广阔的世界,无法品尝自由的滋味;兰德尔种植园内的伶仃屋是苦命人被放逐的地方,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公平与正义,只有恃强凌弱。落难伶仃屋,便预示着与无家可归的人为伍;南卡罗来纳四十号宿舍楼里的逃奴可以被随意用来做实验,他们只是美国白人眼中的一项财产;北卡罗来纳的阁楼是科拉的藏身之所,这间阁楼高不足一米,长仅有四五米。“她像老鼠那样绕着墙。无论是在棉田,在地下,还是在阁楼上的一间斗室,美国始终是她的监牢。”[7]194人是不是自由的与锁链无关,科拉把一座活生生的监狱变成唯一的避难所;公园本是城市公共空间,但在南卡罗来纳州却成为窥探和施刑的场所,充满着权力的制约与监视,成了一个权力场。公园里所有人都是白人,白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这里是白人的杀戮场,黑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践踏。俯瞰公园,科拉冷静地审视着白人市民,认为他们也是囚徒,戴着恐惧的桎梏。公园里的白人关注着阁楼的一举一动,同时科拉也在注视着公园里的芸芸众生,这就形成了两种空间互为凝视的状态。任何人都是不自由的,每个人都被置于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之中。正因为如此,福柯认为“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8]243;怀特海德对具体空间的选择,反映了当时美国南方奴隶被剥削的政治现实,深入剖析了人物内心世界,强化了小说主题。
作者有意识地利用“地点”“场所”或“环境”这样的空间元素,不仅塑造了女主人公科拉坚强与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并且在地理空间的转换中推动故事的进程,将故事情节层层展开,奴隶制的罪恶也因此昭然若揭。列斐伏尔说:“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9]每一处空间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它既是具体的物质形式,也能被分析和解释,从而构建其精神意义。
(二)“地下铁道”——一种地下乌托邦
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关系陷入僵局。自由州与蓄奴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去追寻自由。在他们所经之路上,有无数不知名的男女帮助他们藏匿行踪、逃脱追捕,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路”。到内战爆发为止,数万奴隶通过“地下铁道”的帮助获得自由。单个奴隶出逃或属匹夫之勇,然而当成千上万的逃奴声气互通、交织成网时,一整套帮助奴隶出逃的体系隐隐浮现,这张无形的网络成为激发南北冲突和美国内战的重要导火索。
在《地下铁道》中,怀特黑德利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历史,引人深思。作者用一条真实的地下铁路网络取代一个松散的、事实上存在于地上的拯救黑奴的联盟,地下铁道建在南方蓄奴州的地下,有月台,有火车,有站长,有乘客,有隧道,秘密运行在地下。火车不知何时会来,也不知开往何方,只有上车后才能够知道,因此地下铁道同样充斥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小说将本来抽象的营救黑奴的秘密运动空间化、具体化,“地下铁路”由此成为一个可感知的对象。奴隶们争取自由的勇气、智慧与白人废奴主义者的正义、勇敢结合在一起,交相辉映。
怀特黑德说,“地下铁道是连接州与州之间的通道,也是一次检验外界和自我的旅程”,在这里,铁道更像是一种穿越方式。文章中科拉一共三次踏上地下铁路,驶向未来,驶向自由。最终科拉到达地下铁道最后一段旅程的出发点——幽灵车站,逃出生天,踏上西进之路。“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老是跟人说,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7]78但是在黝黑的地下,科拉如何看到美国的全貌?只有一里又一里的黑暗罢了,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火车疯狂地向前行驶,她的“地下监狱”不断暗落,被黑暗重新吞没。地下铁路开启了科拉“格列佛”式的美国之旅,在未知的世界中奔跑,将黑暗狠狠地甩在身后,这体现了小人物穿越历史夜空的人性光芒和勇气担当。
作者构建“地下铁道”这一暗黑童话似的叙事空间,缩短了科拉的逃跑时间,减少了科拉逃跑过程中的障碍,使整部小说的叙事富有节奏感,形式与布局更加紧凑,因此达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令人回味无穷。“地下铁道”同时也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引起读者的思考:当“地下铁道”这一比喻意义的存在变成乌托邦似的地下铁道之后,美国的历史是否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黑人也是否会减少一些在历史中所受到的伤害?这一地下空间是科拉的希望,帮助她躲避赏金猎人、告密者和暴徒们的追捕,是一个科拉可以获得短暂自由的地方,是属于科拉的一片童话世界。“在这一头,是走入地下之前的你,到了另一头,就是一个爬出来迈进阳光里的新人了。”[7]340地下铁道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黑暗与希望,实现了科拉空间的转换。
无论是身处兰德尔种植庄园内的伶仃屋,还是奔跑于黑暗的地下铁道,科拉一直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化空间,远离城市与人群,更没有形成自己的全美印象。她不仅要提防来自黑奴内部的欺凌与侮辱,还要处处小心白人以及猎奴者的追捕,科拉正常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抑、限制与践踏,虽然在地下可以获得短暂的自由,可这样的自由只是属于地下的狂欢,这背后隐藏着的是白人奴役者的残酷以及黑人存在空间被打压的残酷,因此矛盾的社会关系与空间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支配着黑人奴隶的人生与自由。
三、社会空间:异化空间下的压迫与反抗
列斐伏尔断言空间始终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2]103。社会空间基于自然空间,是对社会关系的体现,强调社会关系的统治、服从与反抗。社会空间的形成势必造成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压迫,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一群体对社会空间的反抗,因此反抗与压迫并行。在蓄奴制的历史背景下,奴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折磨,对奴隶主必须保持绝对地服从。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支配、被边缘化。白人废奴主义者也只能生活在夹缝中,一旦被捕便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和废奴主义者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对空间的不驯服与对空间的驯服的历史一样古老,有空间的扩张就有反空间扩张[10]。列斐伏尔认为,如果空间的社会意义是其本身就有的属性,那么这种特征更多地反映了生产中的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空间既是统治的手段也是抵抗的工具。列斐伏尔尤其把反抗理想寄托于黑人、妇女等边缘群体的反叛之上,这些人能够颠覆种族或性别差异符码。在蓄奴者通过剥削空间来巩固自身时,反抗奴隶制的空间也不断扩大。
(一)社会空间的压迫与反抗
社会空间的压迫不仅体现在身体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如果精神虐待是一种无形的压迫,那么身体虐待就是一桩桩充满血腥的事实。奴隶、逃奴和白人废奴主义者都逃不过被惩罚的命运,他们在身体上承受着非人的虐待。科拉、切斯特、小可爱、逃奴路易莎以及西泽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奴隶主的报复与鞭打。南下佐治亚和佛罗里达的废奴主义者和同情者不是被驱逐便是遭到暴民的鞭打和凌辱,涂柏油,粘羽毛。白人马丁和他的妻子因藏匿逃奴而被绑到绞刑树上,最后被施以绞刑。逃奴不仅要避开赏金猎人,还要躲开黑暗骑士的追捕。科拉在逃跑过程中最大的敌手就是猎奴者里奇韦,他一路从佐治亚追捕科拉到印第安纳。在这场与猎奴者的博弈中,科拉有过恐惧与绝望,但她从未想要过放弃。科拉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在无数次的险境中与猎奴者斗智斗勇。
与身体虐待相比,精神虐待看起来是一种更加隐秘的存在,但它的确对奴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蓄奴制下,奴隶是不允许读书的,他们被剥夺了获得知识的权力与认识自我的能力。除了做苦工,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思想不能思考,因此就不会对奴隶主的统治空间造成威胁。在这本小说中,大部分奴隶都是文盲。他们生而为奴,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奴隶主禁止他们阅读任何书籍。奴隶们的语言被剥夺,身份被抹杀。白人文化凌驾于黑人文化之上,黑人文化可以随意被篡改。在兰德尔种植园,任何有心学习的奴隶都会让奴隶主感到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下,科拉反而更加珍惜每一个读书的机会,西泽也视书籍为精神的寄托。失去书籍与知识,他们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就会失去自由的精神空间。在西方文化中,《圣经》占据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是人们精神的信仰。但在奴隶制时期,黑奴却是被剥夺信仰的,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为奴隶主创造剩余价值。在北卡罗莱纳的阁楼里,科拉有幸接触到《圣经》。她贪恋于《圣经》就像久旱逢甘霖,即使在梦境中,科拉也会梦到方舟正逢其时,把他们带往灾难的彼岸,而后发现应许之地。在《圣经》的影响下,科拉思考着自己以及广大奴隶的命运,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审视自己的处境。《圣经》让科拉暂时忘记身体的折磨,寻找到精神的慰藉,获得自我救赎。可是对科拉以及对广大奴隶来说,谁又有绝对的自由与权力来阅读《圣经》?离开阁楼,科拉又一次进入了精神的荒原。科拉只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个,在残酷的压迫下,奴隶承受着残酷的精神虐待,他们不能享受全面接受知识教育的权力,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对世界也只能获得一些零散的印象,最后只得任人宰割。奴隶制剥夺了黑奴拓展精神世界的权力,并且把他们推向不见天日的奴隶制深渊。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社会空间的压迫与社会空间的反抗是两种相对的社会空间形式[11]。当奴隶主的压迫再也无法忍受时时,他们便会奋起反抗:黑奴反抗白人蓄奴者,白人废奴主义者反抗残酷的奴隶制,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与力量对抗不公的社会制度。列斐伏尔认为,反抗斗争聚焦于空间的解放和重构。为了反抗罪恶的奴隶制,科拉的母亲梅布尔、大安东尼、小可爱以及西泽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最后纷纷选择逃跑。但是只有科拉是逃跑的幸运儿,借助地下铁路,最终逃出生天。谋杀是反抗最为惨烈的表现形式。在生命最为危急的关头,求生的本能使科拉忘记了恐惧,忘记了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将一位白人杀死。在蓄奴制时期,白人废奴主义者也是反抗不公正社会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店主弗莱彻、站长伦布利、黑人铁路司机、萨姆、马丁以及妻子埃塞尔都尽自己所能帮助科拉及其他奴隶逃跑,他们有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并且义无反顾。通过这些反抗行为,黑奴和白人废奴主义者试图打破原有制度,重建新的秩序,为奴隶自身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在蓄奴制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抗争只是杯水车薪,改变不了自身被奴役的现实,只能任由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走,美国是一个他们身在其中但又不允许他们拥有的国家。
奴隶制下,黑奴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压迫。他们的身体被折磨,思想被摧残,自由被剥夺。蓄奴者对奴隶和废奴主义者的残害与敌视态度,构成了对奴隶生存空间的打压。但是,在任何社会或历史条件下,反抗与压迫都是并行的。面对暴力,他们绝不保持沉默,并且奋起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态度。
(二)异化空间
社会和空间相互建构,任何空间都是社会的产物,每个社会都必定有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生产。空间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社会生活既是空间的生产者,又是空间的产物,充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矛盾与斗争。”[5]384在南方,奴隶为奴隶主创造了大量财富,促成了种植园经济的空前发展。然而,奴隶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却不属于自己,反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他们相对抗。黑奴们在劳动中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是肉体被折磨,精神被摧残。奴隶们像动物一样生存,缺乏自我认知,丧失人类本质。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使人实现自由成长的条件,而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性本质的体现,反而成为桎梏人的枷锁。科拉的祖母阿贾里在奴隶买卖中沦为商品,不断地被贩卖、拍卖和转让,一次次地被估价、再估价,但是却仍然对奴隶制抱有希望。黑人小孩霍默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服务,并且每晚睡觉前将自己拷住才能安心睡下。在兰德尔种植庄园内,奴隶之间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窥觊彼此之间的利益,伶仃屋便是强者驱逐弱者的地方。受奴隶主的压迫,奴隶们的生存空间可以随意被侵犯,并且时刻被奴隶主所控制,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在种植园以外,为了追捕逃奴,品行恶劣的巡逻队可以随意出入和搜查任何人的家。这些巡逻队员在另一个国家早已成了罪犯,然而这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肆意地为非作歹。邻里之间毫无信任可言,只有监视与被监视。整个社会关系处于一种紧张与敌视的状态,是一种被异化了的社会,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黑奴们没有尊严,只能像动物一样被奴隶主驱逐,长久以来的奴性深深地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四、空间形式:多条故事线书写下的创新
不管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他们都根源于特定的历史事实。故事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讲述的内容以及剖析问题的深度,更在于作者如何将故事内容讲述出来。在《地下铁道》这本小说中,怀特黑德独具匠心,利用空间形式,在章节切换中构建了一个迷宫似的文本空间。空间形式是一种隐喻概念,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关于作品结构的空间化模式。龙迪勇指出:“具有‘空间形式’的小说当然不是单线小说而是复线小说,也就是说,此类小说一般都有好几条情节线索,而且这几条情节线索并不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而是按照某种空间关系组合成一个抽象的、虚幻的就像‘宫殿’‘剧场’‘圆圈’那样的‘形象性建筑物’。”[12]88《地下铁道》正是一本由多条故事线组成的小说。
这本小说结构缜密,并且非常富有节奏感。整部小说的章节都是由地名和人物角色的名字构成,其中还穿插有抓捕黑奴的悬赏公告。阅读这本小说,读者会感觉到仿佛是在时空交错中穿行,也好像是在拨动一个转盘,等待着未知的惊喜与不安。故事的主线是科拉的逃亡之路,中间交织着作为主线补充的故事线,次要人物得以轮番登场。小说的线性叙事节奏不断被打断,次要情节与故事主线的并置达到了一种共时性的效果,展现了叙事结构的空间性。初读这篇小说,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然而当读者跟随科拉的脚步穿越地下铁路到达北方时,一切迷雾逐渐消散,故事框架也变得逐渐明晰,一切篇章设置都恰到好处。可以说,这种文章结构隐喻了一个混乱、分裂与复杂的现实世界,但这个现实世界却不是杂乱无章的,最终还是会走向统一与整合,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当然,作者并不是随意穿插故事次要人物,而是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引出次要人物。这样不仅有利于整篇小说主题的理解,更能引起读者对小说人物的同情之心。这种谋篇布局呈现了更多的人物视角,使全书叙事也更加紧密和充实,拓宽了人物心理空间的疆域。当一次又一次穿越在黑暗隧道中时,科拉在不断的思考中不断获得成长,而阿贾里、里奇韦、史蒂文斯、埃塞尔、西泽和梅布尔这些次要人物的形象更加清晰和丰满:阿贾里在奴隶主之间不断被贩卖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映射了广大奴隶被当作交易品的悲惨命运;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里奇韦试图通过猎奴跻身社会上层;表面看似温柔的医生史蒂文斯却通过盗尸完成自己的医学研究;马丁的妻子埃塞尔对黑人欲进又退冷面热心的相处状态;西泽选择科拉作为自己逃跑的护身符并且固执地认为会找到回家的路,那样他将永远不再旅行;最悲惨的就是梅布尔带着对女儿深深的爱与愧疚,无声无息地被沼泽所吞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种叙事手法就如电影的特写镜头,放大某个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历程,洞察人物心理,使读者对人物形成一个全面而立体化的印象。在紧张的逃跑过程中,作者插入这些章节,放缓了整个故事的节奏,打破了章节之间固有的因果关系。这种碎片化的故事结构实现了主题并置、章节交替和多重故事等,创建特有的空间形式。
五、结语
《地下铁道》的空间叙事增强了小说的维度,使整篇文章更加立体化、可视化。怀特黑德以巧妙的笔法勾勒出了一个人间炼狱,写出了一个奴隶在蓄奴制时期的美国经历到的种种悲惨行为,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小说作者积极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小说形式,小说情节安排巧妙且富有节奏与张力。通过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空间形式三个方面剖析作品的意义,可以看出《地下铁道》主题思想的呈现和艺术技巧上的成就与空间叙事的多种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多重空间叙事方式的运用,故事进程随着物理空间的转换不断得以推进,社会空间的矛盾和异化也在压迫与反抗中得以揭露,而最终文本空间构建了一个既破碎又统一的整体。这三重空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协调。作者不仅实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创新与突破,更是实现了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形式,同时这也是作家寻找新的文学创作形式的大胆尝试。因此,空间叙事艺术是小说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地下铁道》当之无愧为一本横扫美国的现象级小说,值得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