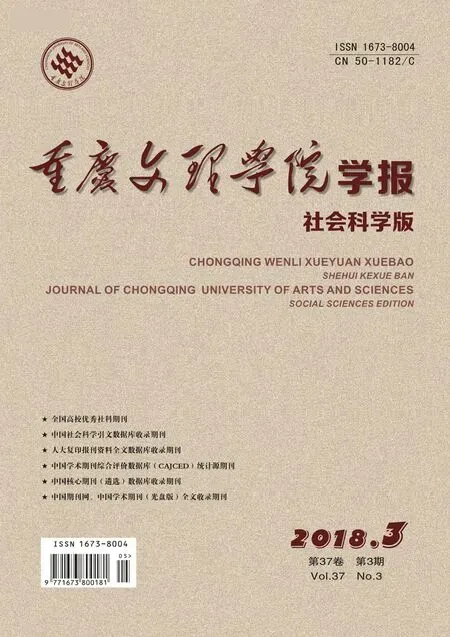文学是他者的在场
——由萨特《什么是文学》重审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冉一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闵行200241)
一、他者的本体论意义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如果上帝不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1]5。所以在现代世界,人性的本质是模糊不清难以确定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什么本来应该是什么的概念。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担忧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被容许的。既然没有上帝事先决定好的一切价值标准来给人类作为参照,那么人类就被迫地落入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这样一来,我们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1]11在这样令人抑郁的思想境遇下,萨特提出了他的理论与解药:“人是被迫自由的。”[1]1人失去了上帝的价值标准之后,被迫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做出解释并负责。但同时人的自主性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人可以选择自己成为什么。而且无法拒绝的是,只要人还活着,人就不可避免地不停地做选择。而人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非他人强迫。萨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例如向牧师请教——你已经选上那个牧师了;归根结底你多少已经知道他将会给你什么忠告了。”[1]6人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个人基于自由做出的选择,所以人就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1]7。因此,虽然上帝定义人的本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在不断选择与不断行动当中造就自己,成了自己。所以萨特说:“人除了记忆,别无其他。”[1]19
除此之外,萨特也对人类总体性做了解释,认为存在人性的普遍性。个体的人在行动中都会感受到人类普遍的阻碍,因此,或许无法对人性做出普遍性的解答,但是人类面对的环境却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人们又互相构成对方的处境。虽然每个人的意图可以各不相同,但至少没有一个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任何一种意图都是跟这些限制有密切关系的。萨特这样描述人的普遍性:“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但是它不是已知的东西,它在一直被制造出来,它是动态的,它可以选择自己是什么。”[1]22因此人是动态的,是不断生成的。但对于所有人来说的确具有一个被称之为普遍性的东西存在,即在人类不断超越性的行动中,人类不断对外界进行意识活动,并在意识外界的活动中意识到自己。个体的人类总是面对普遍的处境,并且人所固有的超越性总会使人在行动中超越这些限制,而在这超越的过程中,人意识到了自己,同时也意识到了别人。这正如萨特所说:“当意识成为一个超越对象的意识时,它就意识到自己。”[2]8萨特后来又解释说他的“我思”与康德和笛卡尔不同。“当我们说‘我思’时,我们是当着别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别人和对于我们同样肯定。”[1]21因此萨特的自由是在确定他者的存在之后的自由,而自由的成立必然要有他者的在场,个人的自由不仅召唤了自己,更召唤了他者。
二、作为他者的读者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第一章认为,语言行动是人类行动的一种,也是在超越事物的过程中去掌握事物的,而事物在被语言言说、被描述的过程中被意识,被超越,也被改变。既然如此,那么人的语言行为也时刻体现着人类对世界超越与改造。而这种改造世界的活动既是作家用语言创作而必然发生的事情,更是读者阅读时必然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作者和读者的超越性是如何在文学活动中得以实现的,两者处于何种关系?
首先,萨特区分了作者的阅读和读者的阅读,并清楚地梳理出作者与读者超越性实现的方式。他认为作者的写作是一种人固有的超越性行动,并在创作中永远预设着读者的存在。因为作者从来不会为自己而写作,作者永远不会同时是读者。作者的阅读一直是重演自己创作的过程,虽然他创造了大量的形象,但是作者并不能感受他们。因为作者在作品里永远只能找到他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得不到。而读者面对的却是有具体范围的书本,或者说面对的是一个个干瘪的符号。符号本身是干瘪而无生命的,直到这些符号被读者的意识所掌握。读者的情感和想象力像血液一般使这些符号获得生命,变成有形有色的形象与跌宕起伏的情节。因为读者的阅读行动同样属于萨特哲学范畴中所说的具有超越性的人类行动,所以作品在被读者意识到的时候,也不再是曾经具有客观性的干瘪的符号集合,或者说是“油墨渍”[3]111。比如卡夫卡神话的写实和真实程度,这一切从来都不是现成给予的,必须由读者自己在不断超越写出来的东西的过程中去发现这一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随着作者的语言符号又创造出新的作品世界,例如:“普鲁斯特从未发现沙吕斯在搞同性恋。”[3]123但是读者们却能在作品里发现作者并不知晓的事情。萨特认为读者的第二次发现同作者的第一次发现同样崭新、同样独特。因为意义不是字句的综合,而是后者的有机整体。
其次,萨特认为读者和作者在文学活动中互为他者,彼此召唤对方的自由。写作和阅读这两个部分需要不同的施动者,因此两者面对的对象若都是自己的投射的话,那么阅读和写作很难构成一个可以一直运动的关系。萨特认为:“只有为了他者,才有艺术,只有通过他者,才有艺术。”[4]124读者和作者在创造的时候,都必然预设着对方的存在,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只要他进行文学活动,那么必然需要对方来帮他实现他的自由,因此他者的在场是进行文学活动的必然前提。萨特这样形容这种关系:“阅读是作者豪情与读者豪情的一种结缔。”[5]135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并力图超越一切他想要揭露的客观事物,所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是自由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作品的世界可以令他自由畅游,自由创造,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也是自由的。读者与作者的自由在文学文本中喜悦地辨认出了对方,而互为他者的双方因彼此的在场而获得自由。萨特认为,文学召唤的自由即人类最高的自由,作者与读者的自由在文学中相遇,使得人类最高的自由同时在场,一起构成了这个伟大的世界。而这样一个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运转的文学活动是一直处于动态的意识活动,读者和作者也因为有了对方——他者,才使艺术得以存在,不断延绵。
三、误解与自由的阐释学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论述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彼此召唤关系之后,还提到了另一种关系模式——“误解”。
萨特所说的误解是从对文学实践的细心考察得出的。在《什么是文学》第三章“为谁写作”中,萨特举了两个法国文学史上的案例。第一个误解是作者主动选择的误解,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文学作为这般文学自行确定的时代,通过若干范式人物得以实现:波德莱尔、福楼拜、马拉美、兰波、普鲁斯特……”[4]4619世纪是文学依照其自主性发展的时期,这种文学脱离社会而以其自身为目的发展的状况造成了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作家如果在当代成名那必然是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诞生于以人民群众为对象的文学革命的失败。萨特发现19世纪后期的作家们在文学革命中将普罗大众作为写作对象进行召唤,但却出现了文学革命为反对革命的保守派带来益处的现象。而随着“误解”这个词的出现,为萨特带来了焦虑和疑惑。而“误解”这个词的使用与我们之前所知的文学作品作为自由的召唤之物,使读者和作者同时在场的认识似乎有一些偏差。因此这里关于“误解”有这样两个问题:萨特为什么认为是作者主动选择误解?误解的出现是否证明了萨特的坚持即文学是读者与作者彼此自由的召唤是失效的。
首先,关于作者主动选择的误解,萨特是这样解释的。在《什么是文学》第三章“为谁写作”中对文学史上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而梳理出一对经常错位的群体:潜在读者与实际读者,而这两者的错位就是萨特所谈论的误解。萨特认为17世纪的法国没有潜在读者,作者只能在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进行召唤。18世纪的法国虽然可以将资产阶级作为潜在读者,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之后,其身份便自动变成了实际读者,潜在读者就消失了。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又回到了知识分子的沙龙之中,加上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更使得文学发展成以其自身为目的创作活动。萨特认为19世纪的文学虽然发展了文学的自主性,但是这也使得文学日益远离社会和大众。而远离大众虽然是作者的主动选择,但也是作者的一种无奈选择。因为资产阶级企图通过限制文学的自由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希望作者的创作放弃文学的特性而按照一种“心理学”的范式进行。萨特在文中这样描述:
这一点很好理解:由于资产者不是直接控制食物,由于他主要是对人工作,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取悦于人或恐吓人;礼仪、纪律与礼貌支配着他的行为,他把他的同类看作木偶,他之所以想对他们的感情和性格有所了解,那是因为每种情欲对他来说都像操纵木偶的绳索。雄心勃勃但家境贫寒的资产者的必备书是一部“登龙木”,富有的资产者每日的必读书是一部“治人之术”。因此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加入作家会思考社会秩序,他就会使资产者感到厌烦,产生恐惧,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于作家的只是让他们分享作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这一来,文学就与在十七世纪一样,还原成心理学了。当年高乃依、帕斯卡尔、沃夫纳格的心理学还是对自由的一种起净化作用的呼唤,但是今天商人不信任他的顾客的自由,省长对区长的自由也怀有戒心。他们只希望人们为他们提供万无一失的迷惑人和统治人的良策。人必须是有把握略施小计就可以控制的,总之人心的法则必须是精确的、没有例外的。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不相信人的自由犹如科学家不相信奇迹。由于资产者的道德是功利主义的,他的心理的主要动力便是利益。对于作家来说,不再需要他把作品当作一种召唤诉诸一切绝对的自由,而只需要他向读者阐述心理规律,这些规律对他和他的读者同样起作用[3]179-180。
因此19世纪的作品,回到知识分子的沙龙之中看似是远离读者远离大众的做法,但却因此保护了作品的召唤功能,避免了文学沦为一种实用文本或者说明书。作者主动选择误解其实是试图保存文学自由的做法,误解的出现非但无法证明萨特所坚持的文学是读者与作者彼此自由的召唤是失效的,反而证明萨特的理论是有效的。在特殊时期,选择误解才能保证文学自由。这样一来就不难解释,为何萨特说这一时期作家认为“有名不如无名,艺术家生前的成功只用误解来解释”[3]181。此时的作者已经无法在他生活的当代来预设自己的潜在读者了,作者只能向未来求诸读者。所以作者假如在当代获得了成功,那意味着潜在读者与实际读者产生了错位,作者在当代的成功只能是一个误解。
萨特说的第二个误解虽然也是由于潜在读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错位造成的,但这种误解却比第一个误解更具政治意味。或者说第一个误解是作者逃避政治目的的结果,而第二个误解则是作者主动追求政治目的的结果。当作者主动选择不被理解,使得文学日益远离社会和大众,而这样的文学现状令许多作家为文学的前途感到担忧。为了挽救文学的毁灭,一些作者在世界的荒原中发现了一个可能成为潜在读者的群体——人民群众。但不幸的是,将人民群众作为潜在读者这一做法并不能让作者感到满意,但造成作者不满的原因并非完全归咎于人民群众。按照威廉斯的说法,“大众”这个词有正负两种含义。负面含义是带着轻蔑的“乌合之众”,正面含义则更多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例如威廉斯本人的笔下:“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5]281作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大众身上有着推动社会变革的正面力量,因此才将其作为潜在读者进行召唤,甚至企图发起一场以大众为对象的文学革命。作者们的这种意图与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都是吻合的,但这种吻合也注定了萨特为此事焦虑。因为在具体实践中萨特发现,作者预设的潜在读者——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实际读者。人民群众似乎对作者的召唤并不感兴趣,这一场文学革命却最终令反对革命的政治保守派获益。而这第二个误解的产生是否意味着萨特坚持的文学是读者与作者彼此自由的召唤是失效的呢?不能,因为潜在读者与实际读者的错位有这样一对身份的混淆 :作者-读者/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萨义德这样分析:“《什么是文学》中使用的字眼是作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但所说的显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6]65从文本来看的确更偏向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这对关系。萨特在文本里描述了作者呼唤的自由与人民群众需要的自由两者的偏差。
无产阶级想的不是要求政治自由,他们毕竟还享有政治自由,虽然说这是一个骗局;无产阶级目前也用不着思想自由;他们要求的与这些抽象的自由大不相同: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同时更为深切地、也更为朦胧地希望结束剥削人的现象。[3]183
毫无疑问的是,在这里两个自由的相遇并没有像萨特之前所说的因相互辨认而喜悦,反而为双方制造了烦恼,形成了一个误解。萨特认为,误解的形成是由于作者没有将自己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召唤。更因为作者在经历了不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历史后,自以为文学可以远离意识形态而独立,因此没有意识到“文学就是意识形态”[3]183。从这里可以看出,萨特对于这组关系的思考无疑是偏向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这对关系了。因此,第二个误解也无法证明萨特坚持的文学是读者与作者彼此自由的召唤是失效的。
四、朗西埃对“误解”的再探讨
萨特对于“误解”的探讨在当代仍旧激起了理论家的回声,朗西埃就是其中一个。在《文学的政治》里朗西埃先由萨特所说的“作者是自己选择不被理解的”进行探讨,再从词义的角度出发作了这样的阐释:“为什么‘误解’和‘敌意’能够被当作同义词,为什么艺术家和杂货店老板之间互不理解的习惯场景可以被叫作误解。”[4]46在这里他解释了人们使用“误解”这个词的意图,即体现一种排斥和一种区分。“误解”的使用,体现了两种阶层之间的交流结果。
首先,朗西埃认为,萨特讨论的误解并不应归咎于群众的知识水平,更不应归咎于作者缺乏“文学就是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反而应被当作一种统治阶级的阴谋。“它可能是文学精英和统治阶级的默许契约加封在公众头上的虚构。”[4]48因为文学的解释权被掌握在少数的文化精英手中,而普罗大众并不与文化精英共享同样的词汇库,因此朗西埃认为 “误解不是阐释学”[4]50,“误解在词汇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失算”[4]50。这种失算是不同群体对词语和物体的对应偏差,即“将关于一切的两个概念对立起来”[4]52。这里所说的两个概念是文学精英与普通大众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概念。
其次,朗西埃区分了两种“误解”,“文学非共识”与“政治非共识”(文学误解与政治误解)。前者是伴随人性天然存在的,后者往往充满现实的冲突。文学误解所指的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个性,这种个性来自世界上各种不同元素的无区别混合。朗西埃认为文学应该创造具有差异性的理解:“文学固有的非共识形式在于创造新的个性形式,进而破坏物体状态和意义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4]54正如同福楼拜和普鲁斯特总要在文本中书写一些多余的事物,力求满足这种丰富的差异性。而政治误解所指的是一个新创词汇将一种新的事物关系引入人们的视线,而这种新的关系无疑会破坏旧的事物关系。这种意图打破旧区域划分新区域的行动将会引起一场“政治的非共识”。
再次,与萨特对“误解”的态度正好相反,朗西埃认为“误解”并不是消极的,他反而认为人们在误解中所谈论的内容才是真正需要谈论的东西。在误解中带来的各种“非共识”的碰撞才是生活最真实的一面,更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时刻发生的事情。而文学的误解也是如此:“人们在误解的外衣下所谈论的东西,恰恰就是特殊情况下书本的结构本身和普通情况下的文学事件。”[4]48而文学的误解因其本身具有人类普遍的个性,所以朗西埃认为它将治愈政治的误解,或者说治愈生活当中的一切误解。朗西埃这种新的阐释发展了萨特的学说,并且在萨特的学说之上重新确立了新的内涵和文化意义。萨特虽然对误解充满了焦虑不安但却并没有对其作出否定,因为“误解”其实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朗西埃认为人们无论是政治的误解还是文学的误解,都是基于民主前提的对于词物关系的主观组合,所以朗西埃的误解更体现着一种平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理清一个思路:读者与作者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着互为他者的角色,而他者的在场是文学活动召唤自由、实现自由的必要前提。读者与作者之间虽然会出现误解的现象,但误解本身就是一种正当合法的关系。如果说萨特所说的误解都是自由的显现,那么朗西埃所说的误解则都是平等的显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对误解的探讨中,萨特的自由其实就是朗西埃的平等。
[1]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让·保罗·萨特.自我的超越性[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让·保罗·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D].施康强,等,译.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8]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M].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