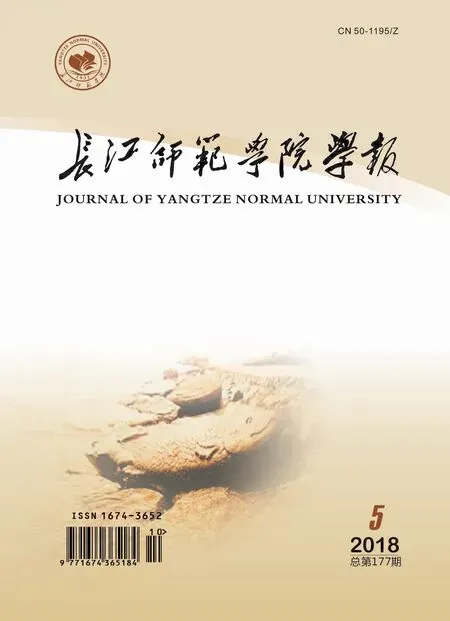从金石学家王昶看清中期经学与文学之关系
武云清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时代特征的学派之一,以侧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为鲜明特点。这一学术派别起源于明代中期的杨慎、梅,渐兴于清代初年“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鼎盛于乾嘉时期。学界对它的称呼不一,或称“考据学”、或称“朴学”、或称“汉学”;对它的形成原因也各持己见。梁启超主“理学反动”说,钱穆主“每转益进”说,余英时主“内在理路”说。不论是称谓还是形成原因,考据学的复杂性显而易见。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乾嘉盛世,一大批士人之所以从事考据学,是因为文字狱所致,“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入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1],从事考据学成为士人逃避文祸、远离政治的方式。文字狱确为考据学鼎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也不宜过度夸大。考据学在乾嘉盛世风靡当世,跃居学术界之主流,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更有赖于其自身特点,它既是时代的现实需要,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果。从学术发展进程而言,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必然结果,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严谨缜密的文献考证分析,运用由字而词、由词而义的治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经原则,整理、研究古代典籍,力求客观实证,而无意于议论褒贬,不至于被斥为“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所以有更多的学者愿意从事其中。乾嘉学者认为“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2],“《十三经》皆先圣遗言,其义本可相通者多”[3],这才是他们认为最接近著者原意的考证方法。
受盛世时期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学术氛围的影响,文学与学术合流,成为清中期的一股潮流。正统文人纷纷倡导“以经为本”。杭世骏主张:“读书必先自经始,读经必先自传注笺解义疏始。”[4]秦蕙田修纂《五礼通考》时,也是“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先儒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5]。纪昀称根本六经才能不悖于道:“惟根本六经,而旁参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经权,了然于心,脱然于手,纵横伸缩,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于道。”[6]钱大昕也说:“词章雕虫哂小技,枕葄六艺培本根。”[7]当时大多数学者少时研习辞章,壮年转而潜心经史考据,如钱大昕、王鸣盛、阮元等,强调“以经史为本”也是潜心考据的必然要求。而且,更为显著的是,绝大部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文人,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段玉裁为诗人兼经师。王昶曰:“往予在蜀中,丹阳陆炳示以《蜀徼诗选》,中有段君若膺诗,始知君为诗人。又数年南归,过苏州,见君硁硁侃侃,谭经悉本于古训,又以君为经师也。”[8]757身为考据家的翁方纲,提出了“肌理说”这一诗歌创作理论,使其成为乾嘉诗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王昶也是如此,他不仅以五十年心血编成《金石萃编》,也以“吴中七子”之一而称誉于乾嘉诗坛。对此,品评诗歌一向颇为苛刻的李慈铭称:“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凌廷堪)诗可以上接西庄、下揖芸苔。”[9]56认为王昶是乾隆时期仅次于沈大成的“经儒之称诗者”。
王昶为后世所知者,莫先于其金石学成就及其《金石萃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归入“金石学家”之列,其《金石萃编》堪称当时一部“集大成”的金石学巨著,集录历代各金石家之说,正如王昶自己所言,“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焉”,在金石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接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与赵明诚的《金石录》。参与编定此书的钱坫称“体大思精,海涵地负,集众说之异同,正史文之伪缺,实为向来金石家所未有”(《金石萃编跋》)。近代梁启超也称:“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10]其中凝结着王昶五十年的心血与精力,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文学领域,王昶早年肄业紫阳书院期间就因“吴中七子”之一而闻名域外。当时的两位院长王峻与沈德潜都很重视,激励弟子潜心学问,王峻教导门生“读书当自经史始”,沈德潜也主张“既当宗经,又当证之史学,以广知人论世之实”[11]1691。“通经读史”成为当时学院乃至整个社会盛行的风气。由于深湛于经史之学,王昶的文学思想也多与其学术思想有相通之处,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古文创作领域。
一、以经史为本
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位“通儒”,王昶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主张经史为一切学问之本源,以“信而好古”为上。晚年致仕归田后,王昶受阮元之邀主讲诂经精舍,在考核学生时,便以经史为本,“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12],这与他早年“古人不得志于时,必蕲有传于后,传后者非应科目词赋之谓”的言论也完全一致[8]618。可见,与科目词赋相比,惟有钻研经学才能传于后世。与当时其他考据学家一样,王昶也以“信而好古”为上,但不同的是,他并不排斥宋儒之说,而以此为“信而好古”的内容之一:“仆《易》宗王氏,《诗》宗毛郑氏,《周礼》宗郑贾氏,此后宋元儒先之说及己有所见者,采之附注于章末,以庶几于信而好古之谓。”[8]628作为一位金石学家,他始终坚持“抱残守阙,期于征信”的原则,坚信金石是最可靠的考证材料,“金石不朽,信有征矣”,“迨雕版既行,而辗转传伪,益不可胜计,其久而可据者,惟石本耳”[13],并声称“金石之学,上必本于经,下必考于史,故亦为学问中之最大者”[8]1127。王昶精于《易》学,“撰《郑易学通》,常悉推其说,罔不与天象合。《系辞传》谓‘仰以观于天文’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者。于是益信而有征矣”[8]659。曾协助编订《金石萃编》的门人朱文藻这样描述王昶治学之严谨:“每执卷商榷之余,辄鬯论读书稽古、诗文格律,从源泝流,皆切要实学。”(《金石萃编跋》)譬如“文王受命称王”这一后世学者争论不休的命题,欧阳修《泰誓论》曾提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14]的观点,王昶认为此类说法“皆以臆对而非有实据也”,“余考经传注疏及汉以前书,皆云西伯受命而称王,则称王而改元无疑也,盖其证有十四焉”[8]662,就此举出十四条例证,有根有据,切实做到了“信而有征”,由此可见王昶对于考据、实证的重视。其中,“从源泝流”既是王昶“信而好古”经学宗尚的体现,也是他强调诗乐源流的依据。
在王昶看来,“以经史为本”的学术思想推之于诗文领域亦是如此,也就是说,“经史”是一切诗文创作的源泉和根柢。
在《与彭晋函论文书》一文中,王昶明确提出了“湛于经史,以养其本”的文学观念:“然时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实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绝笔不为,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久之后达,则取于心而注于手,得其真也必矣。”[8]595强调经史在诗文中的根本作用,只有以经史为本,诗文中抒发的情感才能自然、真挚。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昶称赞赵文哲《媕雅堂集》:“大略据经史为根柢,循古人为矩矱,取丛书稗说为辅佐,又本诸萧闲真淡之志。”[8]699按他所说,赵氏诗歌之所以能成为“雅音之宗”,正在于“据经史为根柢”的特质。此外,王昶为门人陈朗论学诗之法时,也提出了诗歌创作应该“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主张:
窃以足下所业计之,当先学七言古诗,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腾汗漫中,烟云灭没,鱼龙吟啸,无所不有。经史,云烟也,龙鱼也,以气运之,以才使之,如是乃为七言古诗之至……当今之士捷取速化为能,规之以杜、韩已适适然惊矣,又何能上溯《风》、《骚》,本原经史?[8]622
经、史即“云烟”、“龙鱼”,是七言古诗的题材所在,是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只有具备雄厚的经史基础,才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使诗歌蕴涵风雅之旨,极尽变化之妙。正是抱持“从源泝流”的理念,王昶才提出了“词者,乐之条理,《诗》之苗裔”(《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词乃《诗》之苗裔,且以补《诗》之穷”(《国朝词综自序》)、“词之所以贵者,盖《诗三百篇》之遗也”(《姚茞汀词雅序》)的词学主张,通过上溯风雅推尊词体,使词体与诗并驾齐驱、同等尊贵,从而成为浙西词派全盛时期的“总结性人物”[15]。乾隆十九年(1754),王昶所作《殿试策》中称:“惟本之身以践其实,禀之经以正其源,博之史以广其用。反覆乎唐宋诸大家之文,以辨其体,而又卓然不惑于诸子二氏之说,如是而文不工者,未之有也。”此说与朱彝尊“稽之六经,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如是而文犹不工,有是理哉”如出一辙[16],二人都强调经史关乎诗文之好坏。朱氏明确指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16]263而王昶“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说法与此完全吻合,由此亦可见朱彝尊对王昶的影响。
终其一生,王昶都很重视经史对诗文的基础作用与本源意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昶在《沈柏参时文稿序》中借沈氏之言凸显“六经”之重要:“吾少时所谓思深而力锐者,大率以蠭气出之,轻心掉之,今浸淫于六经之旨,反覆于宋四子之书,始悔少时所作。”[8]743时文如能“浸淫六经”,便可达到理想境界。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在长沙为弟子唐业敬讲学时,也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古文的写作当中:“若既本经纬史,又于诸家中择一性之所嗜者,熟复而深思之,久之,深造自得,旁推交通,自尔升堂入室。”[8]1129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顺天乡试录后序》又说:“窃谓文以载道,而道备于经。古之学者,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盖三年通一艺,十五年而五经通,然后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后世士子,或殚心词赋鞶帨之术,于经义忽焉不详;或杂然习之,不求其端,不讯其末,其发于文章也,于斯道奚裨焉。”[8]676通过揭露当代士人不精经义、不考究竟之弊,从反面凸显文章中“经义”的不可或缺,体现了王昶“以经史为本”的思想。
无论是“湛于经史,以养其本”,还是“上溯《风》、《骚》,本原经史”,抑或是“禀之经以正其源”,都在阐述文学本源问题,也就是王昶对于文学本体的认识。沈德潜选编《吴中七子诗选》时,所关注的也是这一方面。《七子诗选序》曰:“七子者秉心和平,砥砺志节,抱拔俗之才,而又亭经藉史,以培乎根本。”[11]1360“亭经藉史,以培乎根本”既是“吴中七子”人格修养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根本依据。王昶作为“吴中七子”成员之一,也不乏这种共性。
“学”被王昶视为诗歌创作的首要因素,而且“学以经史为主”。乾隆四十八年(1783),好友吴泰来所作《述庵诗钞序》转述王昶论诗之言:
吾之言诗也,曰学,曰才,曰气,曰声。学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声以宣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涩者庶不敢妄厕于坛坫乎。
时值王昶任西安按察使之际,与吴泰来、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交往频繁,公务之余,他们以诗词唱和为乐,因此吴泰来所转述者,应是确切无误的。王昶认为,“学”“才”“气”“声”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强调“学”须“以经史为主”(《示朱生林一》)。还说:“盖学与才、气与法,四者缺一不可,然又须陶铸精粹,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8]1130晚年传授门生学诗之道时,更是将此四要素概括为“学问”“才气”“声调”。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在长沙奉命办理民事之案,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率唐业敬、唐业谦兄弟来受业,遂为其论学诗之道:“诗道之多,正如汉家宫阙,千门万户,然其择之也,与古文同。果能熟读深思,傅以学问,辅以才气,壮以声调,何患不成大家?”[8]1129即“学问”“才气”“声调”是诗歌创作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嘉庆元年(1796),王昶致仕归田后,主讲娄东书院时又说道:“诗道久榛莽,百鸟争啁啾。生平五十载,颇能辨源流。先贵学问博,次尚才气优。终焉协音律,谐畅和琳璆。所得敢自秘,劳子频咨诹。识途须老马,世幸毋訾尤。”[8]449王昶遂建构出自己“先贵学问博”的诗学理论体系,“学问”“才气”“音律”(或“声调”)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有先后之别的。他更注重诗歌中之“学”“才”而非声调格律,这也是他作为“格调派”后学而与其师沈德潜最大的不同。
反观王昶自己的诗歌作品,“以经史为本”、重视学问的痕迹非常明显。诗中考订印证的内容较多,经常有考证地理、名物、碑石的成分,即“以金石考据入诗”,大有“学人之诗”的特点,这种风格集中体现于从军边地以后的诗作。一方面,王昶常以诗考证地理、名物等。比如《春融堂集》中考证古物的长诗《雁足镫》,诗中极其详尽地描摹汉铜雁足镫的形状、来源等,不失为“以考据入诗”的典范,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引。试举《美笃寺》一诗以尝鼎一脔:
岧峣美诺寨,寨后峰如簇。厥寺更巍然,厥名曰美笃。严事者喇嘛,云本出天竺。非黄亦非红(喇嘛有黄红二教,以衣帽为别),白教世未瞩。祖堂达尔党(达尔党,地名,在西藏之后),世传在穷谷。有布鲁思古,梵行众所服。其胡毕尔汉(神魂之谓),转轮每来复。其经达丝拉,诵之可禳福。其佛色丹巴,尊与瞿昙属。其众尽犷悍,其术悉阴毒。番酉愚且顽,崇信等尸祝。层楼三重高,宝网四阿蹙。画壁所见稀,狰狞千手目。累累悬髑髅,森林横剑韣。忆昔四天王,护法愿已熟。臂或擎日月,身乃乘狮鹿。警兹行道人,清修倍齐遫。御彼波旬徒,幻化免挠触。何期变本初,遂作天魔族。呜呼西方理,清净断六欲。其衣尚坏色,其食仅斋粥。颇怪达赖徒,衣帛兼食肉。加以演揲教,秘戏佐淫渎。何况奔布尔,像设示诛戮。睚眦起诅咒,斗争助奔逐。铃铎仍铿锵,楣栏互起伏。旁行四句书,亦用银泥录。曩宋莎罗奔(土司适子出家日莎罗奔,庶子出家日曩宋),出家擅利禄。蹎习发交冲,并吞渐成俗。奇衷终无效,杀机久逾蓄。因致绝徼人,膏血途草木。真当聚而歼,焚庐讵为足(癸巳冬,是寺果为官兵所毁)。
此诗作于从军蜀地期间,整首诗皆在考证美笃寺的由来,绍述白教喇嘛的情况。另一方面,王昶还常以诗注的形式考证地理、水利等。如滇边时期所作《渡潞江》的诗注中便详细考证了潞江的名称与支流;归京后所作《奉命谳事新安》一诗的注释中则追溯了历代水利的发展情况。晚年归田后,这种考据之习依旧不减,《陈忠裕公祠宇落成诗以志之》末尾注云:“忠节授命在忠裕公前,故忠裕集有《葬夏考功诗》,然是时节愍牵连被逮,卜葬未成,其后门人昆山盛符升始葬之,宋荔裳琬曾纪以诗,然其葬处,我乡前辈未经记载,遍访无踪,因志于此。”《虎邱寓舍即事》其三诗云:“千秋楼阁仰峨嵋,新奉香山与拾遗。谁识青莲曾过此?烦君合作四贤祠。”诗末注释“四贤祠”的文字极其详尽:剑池上原本就有仰苏楼来奉祀苏轼。前太守任晓林以白居易曾经为苏州刺史,也建阁奉祀。赵翼因为杜甫诗中曾有“东到姑苏台”,所以三祠并建。王昶考证《文苑英华》而知,李白也有《建丑月十五日虎邱山夜宴序》,又依据《新唐书·肃宗本纪》考证建丑月为十二月,李白之宴虎邱在上元二年。嘱托于鳌图并祀李白,遂有“四贤祠”之称。
很明显,“以经史为本”的学术思想不仅体现在王昶的文学理论当中,而且还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这也正是李慈铭视其为乾嘉时期仅次于沈大成的“经儒之称诗者”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专于一家
“专”“精”是与“博”相对的一种治学方法,传统儒家追求“博观约取”,“博”是治学的门径,“约”则是最终归宿。章学诚强调博、约非二事,二者互相制约:“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17]而王昶视“博而精”为最理想的治学方法:“盖古之学者,读《易》如无《诗》,读《书》如无《春秋》,又于一经中颛守一说,历数世而不变,是以立志也定,而为说也博且精。”[8]863他认为,“精”“博”在治学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兼具才是完整的为学之道。嘉庆元年(1795)论研经之过程:“昔人三年通一艺,专守师传精古义。次乃涉猎采群言,阅年十五良非易。迩来饾饤夸搜罗,摭拾星宿遗羲娥。盈科渐进圣所训,记丑而博将如何。”[8]450惟有“博且精”,才能实现“立言不朽”。《跋稽古编》曰:“覃思深造,博而能精,殆未有不传,传久之,未有不益著且大者。”金石学中,王昶也强调征引之博,辨析之精。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葺友教书院时,王昶于所定规条中提出“盖博学者,圣学之所从入也”的论断,同时又主张“即质有不逮,或专习一经,以一说而通众说,或专习一史,以一史而通诸史,或通天文、算术,或为古文、骈体,或习诗词,或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各成专门名家之业”[8]1122,即资质尚浅者,退而求其次,可以一经一史为师法对象,进而通经通史。
整体而言,王昶在治学方法上更倾向于“专”“精”。《与汪容甫书》一文中着力申说“专精”之旨:“盖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则必不能致于用也……今之学者,当督以先熟一经,再读注疏而熟之,然后读他经,且读他经注疏。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经之义。务使首尾贯串,无一字一义之不明不贯。熟一经,再习他经,亦如之,庶几圣贤循循慥慥之至意。若于每经中举数条,每注疏中举数十条,抵掌掉舌,以侈渊浩,以资谈柄,是欺人之学,古人必不取矣。”强调“精”在经学中的重要性,而且是“致用”的决定因素。“精”表现为“熟一经”,即精通一部经书,这是经学最基本的治学方法。在王昶的治学图谱中,“精”与“专”“约”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困学编题词》云:“凡学要于博观约取,不约则不专,不专则不精,专乃能熟,熟乃能养。”“取诸也约,守之也专。”我们发现,王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就已经提出“为学必专于一家”的观点:
为学之途,犹建章宫阙,千门万户,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专于一家。颇怪今世文士辄曰我能经、我能史、我能诗与古文,叩其所业,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也,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而一经之中分茅设,若汉人之《易》,既异乎宋元矣,汉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师之说,深探力穷之,于彼于此掠取一二说焉,必至泛滥而无实,穷大而失居。推之他经皆然,推之史与诗与古文,亦无不不然。故愿足下专于一家,求所以入之也。[8]618
“通诸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而“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示戴生敦元》也称:“然必通诸经,乃于一经之旨,无不明晰。”钱大昕在写给王昶的书信中,也提出“通全经而后通一经”:“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7]430如此看来,在“通全经”与“通一经”的关系问题上,王昶与钱大昕的侧重点不同,前者重“通一经”,后者强调“通全经”。王昶认识到“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即《与汪容甫书》“兼通必不能精”的客观现实,转而主张“通一经”“专于一家”的治经方法。综观乾嘉时期,“专于一家”已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被士人奉为圭臬。戴震强调“贵精”:“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18]朱筠主张“治经当守一家之学”。阮元《晚学集序》肯定考据之“精”:“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王鸣盛《蛾术编》不满为学之“博”:“为学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丛生。”当时学者不仅在学术主张上宗尚“专精”,而且身体力行,治经时也如惠栋治易学、胡培翚专于礼学、刘宝楠精于《论语》等。王昶倡导“专于一家”,与学术界之主流完全合辙。
如前所述,王昶认为“专于一家”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经学,推之史学、诗学、古文等领域亦然,并屡次阐述这一观点。《示朱生林一》就说道:
学诗先博学,博而约取。举古人诗,反复循玩,融洽于心胸间,下笔自然吻合。又宜先学一家,不宜杂然并学。河西女子听康昆仑弹琵琶,谓本领何杂者,正坐此病,仿一家到极至处,自能通诸家。《楞严》云:“解结中心,六用不行。”皆是诗家妙谛,仆于此事三折肱矣,可得正法眼藏,故不惜为吾贤饶舌也。
通一家,自然可以通各家,这是学诗之取径。王昶劝导弟子戴敦元曰:“诗学,如《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三集》、《明诗综》诸书,亦宜浏览,其取法也,杜韩苏陆称最,亦以一家为宗。”(《示戴生敦元》)与古文以韩、柳、欧、苏四家为最相似,诗则以杜、韩、苏、陆为最。因此阮元称其诗“后宗杜、韩、苏、陆”[19]。其实,在王昶的思想中,不论诗还是文,都须“以一家为宗”:“古文之学,世所传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外,《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皆宜浏览,博观约取,以一家为宗。”(《示戴生敦元》)
王昶认为,“专于一家”,也就是“不宜杂然并学”,最终是为了达到“熟”的理想境界。滇边戴罪从军时期,他这样阐述“熟”的诗学境界:
昌黎《赠崔斯立》云:“往往蛟龙杂蚁蚓。”盖讥其杂也。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择杜陵诗,得其尤粹美者,强记而循诵之,务底于熟,使章句音节一一悬著心目,又寻绎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养焉。如是而驳杂之病乃除。诗词虽小道,不可以一蹴几也。矧杜陵又诗之最精深者,世人务小慧,辄欲弋获之,无怪仅得其麄觕钝涩,哆然自号为杜,而去之乃益以远。仆不喜人易言诗,尤不喜世人易言杜,正坐此病尔。《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为学诗者言,然学诗而蕲底于精与深者,无以易此。惟足下勉之。[8]606
“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是上述材料的核心观点。诗词创作并不会轻而易举就能达到“工”,最关键的是要做到“熟”。而“熟”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除驳杂之病而归于纯,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与循序渐进的过程。换句话说,王昶强调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去除驳杂,归于纯然,才能达到精、深的诗境,即《孟子》所谓“深造自得”。在他看来,古今诗人能达到这种诗境的惟有杜甫。“纯”与“专”相近,而与“杂”相对,是王昶“专于一家”的学术方法在诗学领域的极好体现。
古文理论中,王昶也主张“熟而后工”。他肯定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的论文之言,提出“作文,词不患不富,要归于峻洁”[8]606的观点。根据王昶自己所言,他曾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之文,而成《四家文类》,自序云:“孔子曰:‘多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择则约,约则熟,熟则沉冥融冶,忽与心通,忽与手会,汩汩乎左右逢其源焉,譬之水触地而出,不审其孰为淄,孰为渑也。如是合四家为一家,亦不自知肖于某家,斯为文之极工尔矣。”[8]734编选《四家文类》,是为了纠正后世拘守茅坤“唐宋八家”说之弊,主张以此四家之文为最,“合四家为一家”。专而熟,熟而“忽与心通,忽与手会”,左右逢源,这与《与彭晋函论文书》中“取于心而注于手”的观点完全一致,都需要深湛于经史之学。
总而言之,“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和“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被王昶很自然地运用到诗文创作与理论当中,这不仅是他的经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而且在清代中期文坛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当时很多文人都强调文学渊源于经学,如扬州学派中阮元、汪中、焦循、凌廷堪等人也都主张“为文须根柢经史”。阮元《跋朱文正公遗墨》云:“元尝谓若学相如、子文之为文,必先学许、郑、景纯之所以为学。非有根柢,不能文也。”[20]他们尤其强调骈文的写作必须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王昶虽然提倡“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但又没有受其局限,反而展现出一种较当时一般考据学家更为通融的姿态。与汉学家立异的宋学家姚鼐,亦在为王昶所撰序文中提出其“义理、考证、词章合一”的古文创作理论,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姚鼐《述庵文钞序》云:“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则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而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21]在姚鼐眼中,王昶不像其他考据学家那样过分强调“学贵专精”,过分尊崇考据而贬抑词章,而能兼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所作古文遂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因此,我们既要从王昶身上看到清中叶学术思想、文学理论与创作之关系的典型意义,又不能忽视他作为乾嘉“通儒”的通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