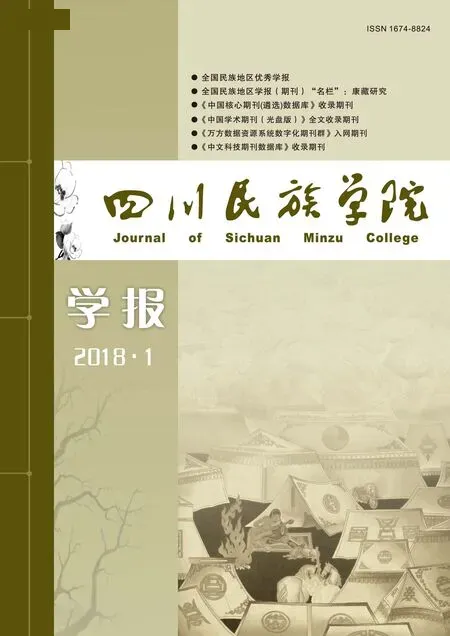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略述
才让项毛
一、《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及其藏译本
《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藏语为《`phags-pa-za-ma-tog-bkod-pa-zhes- bya-ba-theg-pa-chen-po`I-mdo》是一部宣说观世音菩萨心咒(六字真言)和观世音菩萨功德的大乘佛教经典。这部佛教经典大约于公元四世纪末即370年左右由李特赛(li-the-se)和洛赛措译师(lo-tsa-ba-blo-sems -`tsho)或托格(tho-gr)与李译师(li`I-lo-tsa-ba)*关于是谁携带由《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等佛教经典和法器构成的‘年波桑瓦’入藏,在藏族史料中众说纷纭,上述提法是搜集和比较十几部佛苯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而初步推测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同《百拜忏悔经》(有些学者译为《诸佛菩萨名称经》)、金制佛塔、弥扎手印(天然示现六字真言之宝石)以及金写六字真言等佛教经典与法器等,一同经由当时的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这是依据Alexander在其著作《The origins of Om Mani padme Hum:a study of the Karandacyuha Sutra》中认为《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是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于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创作’的观点。至新疆地区,再辗转至西藏阿里和山南地区,最后传到雍布拉康,史称“年波桑瓦”,成为佛教始传藏地的标志。
《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至今有两部藏译本,第一部是在公元七世纪由藏族翻译家妥弥·桑博扎依据当时大乘佛教逐渐流行的时代背景和历代赞布*依据《贤者喜宴》等藏族史料记载,从吐蕃第二十七代赞布拉脱脱日年赞起至松赞干布,多数赞布都会象征性地供养‘年波桑瓦’。重视该经的传统而在赞布的重视和嘱托下执手翻译,成为首批藏译佛教经典之一,但因种种原因现已遗失。*在各种藏文大藏经目录《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无法找到妥弥·桑博扎翻译该经的经目。大多为大译师襄·益西德所译。但在许多早期历史文献如《娘氏教法史》《布顿教法史》《贤者喜宴》中记载了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妥弥·桑博扎翻译了以该经为主的二十一部显密观音类佛经。因此,有些学术观点认为妥弥·桑博扎未译过该经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但目前我们也确实无法找到妥弥·桑博扎所译《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证明它存在。所以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得慢慢研究和摸索。第二部即现通行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是在公元八世纪中期到九世纪初期由藏族大译师襄·益西德重译。其经目被收录于《丹嘎目录》《旁塘目录》《布顿大藏经目录》《德格版大藏经目录》《北京版大藏经目录》《卓尼版大藏经目录》《理塘版大藏经目录》等藏文大藏经目录中。
二、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的内容和特点
从内容方面来讲,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由两大篇、四卷半构成。第一卷的主要内容为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向如来依次提出关于观世音解救众生于轮回的七个问题,世尊通过解答而将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德阐释的淋漓尽致。第二卷中观世音菩萨通过比喻的方式向大力阿苏啰王宣说食施世尊的殊胜,大力阿苏啰王也将观世音菩萨变身矮人降服自己的故事一一进行叙述。而后,虚空藏菩萨四问世尊关于观世音菩萨之殊胜,世尊不仅依次而答,还宣说了《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的殊胜及最后向菩萨众开示六度之法。第三卷中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再次向世尊发出十二问,对此世尊开示了自己化身白马拯救商主于罗刹岛、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之功德细微到毛孔、闻思《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的功德尤其是通过比喻来赞颂六字大明咒之殊胜性等内容。第四卷当中除盖障菩萨摩诃萨祈求世尊开示六字大明咒,世尊为其指路而获得其法。之后除盖障回到诣只陀林园听闻世尊为众弟子宣说若得戒得功德得智慧、若苾刍持戒应受持三衣、若作务时或入村落、若盗用常住物者、若苾刍受持别解脱之法。
通过对四卷半本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该经在包括内容、词句及结构等方面的一些特点。首先,在内容方面该经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该经用四十二个比喻将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以及该经本身的殊胜性阐述的淋漓尽致。这些比喻广泛取材于印度本土的山水地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正如藏族学者卡梅尔·桑木旦所说:“在佛教甘珠尔和丹珠尔当中没有藏人的思想和藏族本土的风俗习惯。同样,也没有藏地地理风貌等外器文明。因为,甘珠尔是将佛陀释迦牟尼之法从梵文翻译为藏文,丹珠尔是将印度班智达之论著从梵文译成藏文。”[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藏经本身所体现的地方性特点。二,该经为观世音菩萨化身宝马解救商王于罗刹岛之滥觞。解救落难者于罗刹岛之说在古代印度社会极其流行。在佛教早期的许多小乘经典中佛陀本人一般扮演着解救众生于罗刹岛之角色,如《增壹阿含经》中说到:“是时马王者,今我身是 。尔时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2]早期大乘经典如《撰集百缘经》中佛陀依然扮演着施救者的角色,其中记载到:“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彼仙人者。则我身是。彼时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3]然而到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首次替代佛陀成为救难者,只要念其名号落难罗刹岛之众生都能够得到解救。之后,观音信仰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而得到普及,解救众生于罗刹岛之说也从《妙法莲华经》中的说法发展为此后较为流行的即《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中观世音菩萨变身宝马解救商王于罗刹岛之说,该经在叙述完观世音解救商王于罗刹岛的故事之后,说到:“佛告除盖障菩萨时。圣马王者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是。于是危难死怖畏中救济于我。”[4]三,通过古代婆罗门中遍入天十法入思想对于该经的影响,我们可以得知佛教对于婆罗门思想的吸收。也可从该经重新诠释遍入天十法入思想来护卫佛教自身的现象时,亦可推导出佛教对于婆罗门一些神话类故事的改造。其次,在词句方面该经的特点为:一,法数(chos-kyi -rnm-grngs)词汇丰富。法数词汇是佛教系统化、概括化的一个缩影,在佛教经典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就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来说,全文共有18个不同的法数词汇,包括佛教中最常见的“六度”“十地”“八正道”“八万四千法门”“三皈依”等词汇。也有像‘七政宝’,其引法与现在有所不同。这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印度佛教中法数词汇运用存在差异的现象,如果与梵文原文做对勘研究,我们可从其中理顺法数词汇演变的过程。总之,法数词汇的运用让佛经内容的表达更加精确和规范,词句更加丰富和到位,而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亦不例外。二,出现古藏文及其写法极具特点。根据十六世纪由藏族学者仁钦扎西撰写的《丁香宝帐》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古藏文词典》[5],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全文共有二十一个古藏文。这些古藏文的写法与现代藏文的写法相比,在前加字、(sngon-`jug)后加字、(rjes-`jug)下加字(`doks-can)以及基字(ming- gzhi)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方面这能说明在厘定藏文之后的佛经中仍然有古藏文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世纪到九世纪间藏译佛经总的特点。另外,在结构方面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有以下两个特点。一,该经中除盖障菩萨和虚空藏菩萨,以及金刚手菩萨对世尊的发问和世尊的解答成为贯穿全文的主线,在三十七个问答式结构中该经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观世音慈悲思想和六字真言的功德。而这种问答式不仅出现于佛教经典中,在古希腊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中也出现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孔子的《论语》 等问答式或对话式结构的著作。二,经首介绍闻法众。不论是大乘佛教经典还是小乘佛教经典,介绍闻法众于经首似乎成为了一种惯例。如《佛说长阿含经卷一》卷首说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花林窟。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时。”[6]此外,像《中阿含七法品善法经第一》*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1册No.0001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卷第一》*中阿含七法品善法经第一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1册No.0026中阿含经等小乘经典也在一开始就介绍闻法众。但与大乘佛教经典相比,小乘佛教经典中之闻法者以比丘为主。而以《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和《妙法莲华经》等大乘佛教经典中闻法之众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要比小乘类佛教经典广而多。尤其是“菩萨众”出现在经首的闻法者之中是小乘类佛教经典所没有的。《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中不仅有比丘众,还有菩萨众、天子众、龙王众、甚至修外道者亦包括在内。从大小乘经首所列闻法众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其外在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内在不重阶层、种族、性别而重修持正法的精神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宗教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中同类经典之间的比较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从宗教学的角度讲,对文献的研究和比较,可以告诉我们古今中外人们的心路历程,可以知晓一种信仰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社会坏境影响下演变发展的,及其对社会的各种反作用。”[7]从中我们亦可得知同类经典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因此,本文也将《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与同类经典《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相同点来说,两部经典都涉及到了观世音菩萨依众生根器而示现种种身像救众生于各种困苦灾难的内容。根据李利安先生在其著作《观音信仰的渊源与及传播》中所提出的划分观音类经典的七种系统即净土往生系统、受记系统、华严系统、般若系统、救难系统、菩萨行系统和杂密系统对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与同类经典藏译本《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进行分析时,可以得出前者属于净土往生系统和救难系统相结合的经典,而后者则为典型的救难系统的观音经典的结论。这也是两部同类经典之间的不同点。
三、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其意义
(一)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
随着《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的翻译,印度观音信仰文化逐渐在藏地展露头角,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使观世音信仰得到初步的普及。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六字真言在整个藏族社会中成了从老到小,不分性别、地区、文化水平,人人皆念诵的佛经咒语。据《青史》记载:“特别是在朗日松赞以前,妥妥日年赞在位时,才开始有佛正法,历代都供奉严厉神秘物。除这种说法外,也就未闻其它的说法。到了松赞干布开许依修密宗的和威诸尊的修法后,显见才有许多修学密宗诸尊的人士,此后在麦阿忽以前,密宗的修士仍是隐秘,而有许多密行。如祈祷观世音菩萨及念诵六字真言,在小王(麦阿葱)以前,盛行于所有藏民中;而且松赞王所著《阎曼德迦修法》的书本至今还有。”[8]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吐蕃王朝时期藏族社会盛行念诵六字真言的民俗现象。二、对藏族历史的叙述与诠释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被翻译成藏文之后,藏族上层精英开始吸收印度观音信仰文化及思想。其方法之一便是用该经的内容和思想对如《嘛呢教言》《柱下遗教》《西藏王臣记》以及《贤者喜宴》等藏族历史著作中的一些历史片段和说法进行重新诠释。比如,在这些历史著作中作者不但从宗教意义证明了观世音菩萨降临藏地拯救众生的必然性,也将藏地本土的藏人起源于猕猴的传说用观音文化进行诠释,称猕猴为观世音菩萨所变。此后,这一说法不仅被藏族文化精英一再运用到著作当中,也被广大藏族老百姓世代传颂。三、对以藏王松赞干布和历代达赖喇嘛为主的藏族上层人物之身份认定和认同的影响。如上所说,为了使观世音文化融入藏族社会,藏族上层精英重新诠释了藏人起源等历史事件。除此之外,另一个吸收观音文化使其本土化的重要手段,便是用观音思想对以藏王松赞干布和历代达赖喇嘛为主的藏族上层人物之身份进行重新诠释认定。对于松赞干布为观世音化身之说,最早出现在藏族史书《嘛呢教言》《柱下遗教》当中。此后,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藏族史书普遍记载藏王赤松德赞为文殊菩萨之化身、赤则德赞为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等。五世达赖喇嘛甚至在他的名著《西藏王臣记》中认为藏族第一位赞普即聂墀赞布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说:“适有众敬王之裔与甲巴者,生有一子,圣者乃为之作加持焉。此子相貌,异乎常儿,眼皮下陷,眉如翠黛,齿如列贝,手臂如轮辐之支分,具足各种德相。……众言此人堪为藏地之王,遂以肩为座,迎之以归,因此遂称‘聂赤赞普’。”[9]同样,达赖喇嘛被诠释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首先出现在益西泽姆所撰第一世达赖喇嘛传中。此后,这种说法不仅普遍出现在历代达赖喇嘛的传记当中,也被藏族社会和民众所认同,甚至直接称达赖喇嘛为‘手持莲花’*在藏传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有许多名号,而‘手持莲花’也是其中之一,因观世音菩萨左手持莲花,故称此名。。
综上所述,《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被翻译成藏文之后,藏族精英分子为了吸收其思想,就通过该经的内容和所包含的思想对藏族历史本身和藏人上层人物进行重新诠释。在这个过程中《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不仅成了被诠释的思想依据,同时在这一诠释过程中促进了印度观音文化在藏地的传播发展。
(二)从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思想产生的影响谈其意义
在第一小节中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述了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依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观音文化在藏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评价观音文化通过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扎根藏地,以及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有哪方面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传承了印度本土业已衰微的观世音文化并形成藏传佛教初期思想的雏形。佛教在十二世纪因伊斯兰军队入侵印度而在本土基本消失。作为佛教的一支,观音文化也随着佛教的衰败而在印度本土一蹶不振。但自以《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为主的观音类经典被翻译成藏文,以及藏族文化精英对该经的诠释。观音信仰和文化不仅在藏地生根发芽,焕发第二春,同时也奠定了藏传佛教初期思想的基调与方向。其次,印度观世音文化与藏族本土文化相适应,继而促进了观音文化的本土化。从文化学的角度讲,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异地发展,就必须同本土文化相适应,否则很难被接受。随着《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等观音类经典传入藏地,藏族知识分子为了吸收和普及印度观音文化,依据《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的思想和内容对原有的藏人起源传说等进行全新的诠释,对藏族政治人物和宗教领袖的身份也用观音思想来认定。因此,观音思想迅速被藏族广大老百姓认可和接受,继而也促使了观音文化的本土化转化。再次,大乘佛教慈悲思想传入藏地之滥觞。慈悲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观世音菩萨在佛教中被认为是慈悲的化身。随着《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传入藏地并经过翻译和诠释,慈悲思想渐渐成为藏族文化的核心思想,并贯穿整个藏传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最后,促进藏族社会整合并加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随着观音信仰在藏族社会的广泛普及,观音文化成为藏族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因素。只要是藏人都会念诵六字真言,只要有藏人居住的地方就会出现与观音信仰文化相关的唐卡、隆达、玛尼石、玛尼经筒等宗教物品。因此,观音文化成了一种隐形的力量,使藏人有了更好的自我认同和彼此认同的依据,这不仅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团结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也成为了整合藏族社会的理论依据。
结 语
《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是在公元四世纪由李特赛和洛赛措译师或托格与李译师携入藏地,之后相继出现了由妥弥·桑博扎和襄·益西德翻译的两部译本,但前者现已遗失。印度观世音文化正是通过藏译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首次被藏人所了解,而且成了吸收观音文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因此,该经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同时,由于藏族学者通过该经对藏族历史和人物的全新诠释,使得印度本土业已衰微的观世音文化才在藏地焕发第二春,大乘佛教慈悲思想也成了藏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奠定了观音文化本土化的基础。
[1]顿珠扎西.喜马拉雅苯教网 访问藏族学者卡梅尔·桑木旦 ED/OL.www.himalayabon.com 发表于2015:11
[2]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2册No.0125
[3]中华大藏经.甘珠尔.第75卷:対勘本.撰集百缘经[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p525
[4]中华大藏经.甘珠尔.第51卷:対勘本.佛说大乘莊严寳王经[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p288
[5]安世兴编著.古藏文词典[M].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1版
[6]乾隆大藏经第0540-01部~杂阿含经五十卷(第一卷~第十卷)[7]严耀中 范萤.宗教文献学研究入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p10
[8]廓诺·迅鲁伯 著.郭和卿译.青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p70-71
[9]五世达赖喇嘛 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M].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