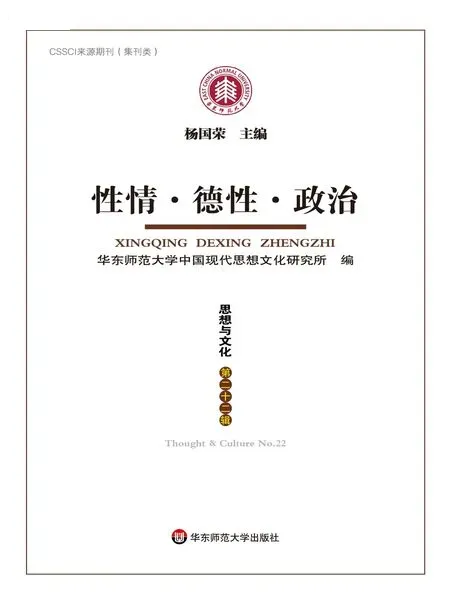情境中的德性原则
——儒家心性哲学的一种诠释方式*
●
近些年来,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中有一种倾向,即认为儒家心性哲学是一种情境主义的哲学话语体系,其核心概念“人性”——由于儒家人物在阐述过程中总是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之下予以展现,再加上初期儒家如孔子、孟子等的一些特殊言说方式——被认为不具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含义,而是某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的过程性概念,这种思想倾向以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和瑞士汉学家耿宁的儒学诠释为典型。我们同意将儒家心性哲学视为一种情境主义的哲学话语体系,但很难接受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的过程性的“人性”概念,尽管我们承认“人性”确实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中的“本质”意义,因此亦反对对之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我们希望通过解析《论语》和《孟子》中的相关文本,还原儒家心性哲学的情境化理论特质。我们认为,早期儒家将德性原则融入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德性原则在“事”中呈显,“事”或具体的道德情境是德性原则得以显现的载体。在此前提下,对孟子的“人性”概念作进一步的澄清,强调虽然“人性”在儒家尤其是孟子那里绝非固定不变的“本质”,但亦不是某种过程性的纯粹经验概念或某种心境状态,而是虽然寓于情境之中,却是超越经验、标志人之所以为人的逻辑根据,并成为从德性原则到道德行为的动力机制和内在保障。
我们还希望借助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对行为合理性的论证,从象征意义与情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反观儒家心性哲学的德性原则在情境中的显现方式。我们认为,儒家心性哲学的德性原则往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行为的效用或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信念、价值和情感等,这种象征意义在具体情境中会回溯到行为者身上并对其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产生切实的影响。
一、 “仁远乎哉?”与“能近取譬”
儒家心性哲学往往从情境入手对美德理论进行阐发,这种德性原则在情境中的当下呈现,在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文本中处处可见。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概念都能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直接呈显,而且先秦儒家如孔子、孟子等,都自觉地将这一点作为他们论证其心性论观点的首选方法,这与西方以寻求普遍性的原则规范为目的的道德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看“子见南子”一章,子路对其师孔子的行为十分不满,引得孔子连连发誓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按照平常的做法,当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别人的怀疑指责时,这个人应该立即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即引用某条一般性的原则(朱熹所谓“可见之理”)以说明他如此行为的理由或原因,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性的证成。但此处孔子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发誓的方式向子路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们说运用原则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性证成,这是一种论证方式,而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则是具体情境下的情感流露,在情感流露的过程中,其心性得以当下呈显。朱熹弟子疑惑孔子面对子路的“不悦”,为何“不告以可见之理而誓之”?朱熹引曾氏之言以明之 :“见南子过物之行,子路不悦,非常谈所能晓,故誓之如此。”[注]朱熹 :《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35页。“告以可见之理”即是以一般性原则进行推理,晓之以理;这种方式在脱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境后是可以做到的,如后世朱熹向其弟子们解释孔子之所以不得不去见南子的原因,那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孔子明知南子之行丑却又见了南子,这就是所谓“过物之行”,即超出常理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一时很难为常人所理解;面对子路的不满甚至指责,为瞬时摆脱当下的尴尬,他只能先以誓言表明心迹,因为那样一种情境下,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事,以不作过多托辞为好。心性的当下呈显奠基于此种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先验的理性。[注]李泽厚语,参见李泽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李泽厚 :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2010年11月4日,http ://www.infzm.com/content/52153。孔子以“天厌之”所表达的其实是“己厌之”,即从根本上而言,他是以一种内在情感(羞恶之情)的当下显现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自证清白。
“仁”是孔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对这样一个概念,孔子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且他也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有意识地去欲求或引导他人去欲求一个有关“仁”的确切定义;但是孔子却明确地欲求“仁”,并要求所有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都应该欲求“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无疑,给概念提供定义的方法是西方哲学所习惯的推理论证的基本方法,也是寻找确定原则的方法,儒家哲学却拒斥这样的方法。我们在《论语》中看到,孔子往往是面对弟子问仁的当下情境,采取随机点拨的方式,对“仁”予以解释,并且在解释的过程中,以一种最切合于提问者的心性的方式来解答。这就要求作为老师的孔子对弟子的品性、人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与对当下情境的明察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儒家哲学对经验整全的认识,此种对经验整全的认识又进一步为某一具体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了某种本体论的基础,从而使得“仁智”关系得以凸显。
孔子用“仁远乎哉”一语,表明了儒家意义上的“仁”不纯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规范,而更是一种与人之在直接相融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情感,后面“我欲仁”之“欲”恰恰显明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情感性质。孔子还说过“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句话中的“近”与“仁远乎哉”的“远”适成鲜明对比。“能近取譬”是对“仁”的一种解释,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同样地,与“我欲仁,斯仁至矣”相对应,这里也出现了“欲”字。不过,在“我欲仁,斯仁至矣”中使用的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我”,而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则运用了相对而言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主体色彩的“己”,但是“欲”和“能近取譬”却令标志道德主体的“己”的原则性规范含义重新融入情境化的情感显现之中。在这里,“远”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先验的原则、原理、理念的遥望,而“近”则是对发之于心的自身内在情感的当下体察,这种体察与具体的道德情境联结在一起,为儒家“仁”的实现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在宰我与孔子的一场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论语·阳货》),孔子以其独特的回答体现了“能近取譬”的“仁之方”。首先,孝是仁德之下的一个子目,如何尽孝,在儒家那里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宰我对“三年之丧”的儒家丧葬之礼产生了怀疑,认为三年时间太长了,并给出自己的理由,即“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就是以礼乐等原则规范的崩坏为借口缩短为父母守丧的时间。对此孔子只简单地问宰我这样一个问题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他没有强调原则规范的持守与维持,而是直接指向宰我的内心,从内心安不安这种情感的萌动出发,强调三年之丧的必要性,并指出宰我这种意图缩短守丧期的想法是“不仁也”,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若不守三年之丧,则无“三年之爱于其父母”。在这一番话中,孔子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道德情境,这一情境为“仁”提供了显现的场所,而在此情境下所做之事致使心之“安”与“不安”恰恰就是“不仁”与“仁”的当下呈现,这与宰我从礼乐等原则规范出发来考虑三年之丧的合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孔子看来,宰我之“不仁”,不是因为他违反了礼乐原则而不仁,而是由于他将礼乐原则超脱于孝的具体情境之外,妄图以原则来规制、约束人心。从孔子这方面来说,他并非以原则性的逻辑推论来说服人,而是推原情理以动人心。
当然,“仁”在先秦儒家那里也并非与原则性规范无关,因为“仁”本身亦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而且这种原则性的规范要求在道德的情境化当下决断中也发挥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作用。按照诺齐克的看法,原则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中的功能主要有智识功能、人际间功能、内省功能和个人功能。而智识功能主要表现于原则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中无关因素(如私欲等)的排除、为道德行为提供普遍性的根据以及将原则与具体情境加以联结等。[注]诺齐克 :《合理性的本质》,葛四友、陈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1—20页,原则与具体情境相联结的内容,尤其参阅第18—19页。我们感兴趣的是最后一点,即原则与具体情境的联结功能。这说明原则必须被运用于情境之中方能发挥其道德功能,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先秦儒家正是在具体的道德伦常中深切地体认到这一点,才努力地将“仁”及其他德性从原则的空泛性中解救出来,并赋予其以心的内在情感性质,由于情感具有能够当下体认和直接与情境相关联的特点,“仁”就成为活泼泼的心之发动,从而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无缝对接,毫无罅隙。诺齐克在考察原则与具体情境的联结功能时,不得不使用原则本身作为这种联结得以实现的动力机制,而考之具体生活实践,我们知道,原则实质上并没有这样的动力机制功能。例如,虽然每个成年人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是一条基本的道德原则,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具体情境下并不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做,尤其是那些对这条原则极为熟知的人更是如此,因为熟知往往带来情感上的麻木。儒家正是为了对治这种情感的麻木,将“仁”规定为人的内心情感,同时又没有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只不过将情感化入普遍性原则之中,使活泼泼的情感成为道德判断和行动的动力机制,并且,这种情感在具体情境里将原则与情境相联结的同时,突显“仁”的当下性(“能近取譬”),而克服原则性的距离感和“硬度”(“仁远乎哉?”)。
二、 原则融于“事”之中
郝大维和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提出,儒家心性哲学并不像西方道德哲学那样,试图为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理论”或“有关诸原则的普遍科学”提供基础,而是在审美性理解中去体察具体德性的适宜性,他们将之称为“情境化的艺术(arscontextualis)”。[注]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248.安乐哲甚至将这一判断推展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理解上,例如他认为道家哲学也是“情境化的艺术”,参见安乐哲、郝大维 :《〈道德经〉与关联性的宇宙论——一种诠释性的语脉》,彭国翔译,《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这个对儒家心性哲学总体特征的判断是准确的,这种“艺术”即是仁、义、礼、智等诸德性在具体情境中因缘显现、当下呈显的方式,以及行为者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下灵活运用原则的方法。其中,具体的道德情境是德性彰显和发挥功能的场所,原则是德性自身在经典中的本然形态,而这种本然形态要想与情境融合,还必须依赖于道德人格(士、君子、贤人乃至圣人)对情境的深察默识、德性修养程度,以及运用德性原则的灵活能力。
万俊人教授指出 :“孔子和中国传统儒家的美德伦理所关注的重心是个人美德实践和实现的关系语境。”其原因是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自古希腊时期就已流行于世的作为实体或作为权利(目的)主体的“个人”或“个体”概念,而是只有“处于关系中的或作为义务承担者的‘个人’概念”,抑或最多是“作为道德人格理想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概念”。[注]万俊人 :《儒家美德伦理及其与麦金太尔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差》,《中国学术》第六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1—181页。而这也是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在不同场合下一再强调的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儒家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角色伦理,这种伦理生活,强调“经验中的关系的首要性”,这意味着儒家道德哲学的“语境事实上是多变的、有机的、处在过程之中的、相互依赖的”,而且这种经验“在感觉上是整体的”,比如说,在一段友谊中,“友谊本身是最为具体的,而独立的朋友是对他们的友谊关系的一种抽象”[注]安乐哲 :《儒家的角色伦理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李慧子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编 :《儒家思想与社会正义——中美儒学论坛·2012》,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这种观点同时体现于安乐哲几乎所有有关儒家伦理学的著述中,如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儒家伦理学视域下的“人”论 :由此开始甚善》(谭延庚译,刘梁剑、安乐哲校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仍然持有儒家是一种“角色伦理学”并突出强调儒家“人”的概念是处于经验中的关系的观点。。正是这种友谊关系使得当事者成为朋友,如此一来个体之间的关系跃居第一位,而个体自身倒隐藏于这种关系的背后,但同时关系又是个体成就其自身的必要背景。此处的隐微张力在于,一方面,德性必须在这种具体的关系之中得以呈显,另一方面,德性又内在于道德人格的内心之中,并且关系只是德性实现的载体,而道德人格才是德性修养的真正目的。安乐哲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儒家道德哲学中的这种内在张力。
其实,儒家道德哲学重关系和角色,恰恰表明儒家德性伦理将每一种德性都落实到“事”上,使其在在都与某种“事”相关联,这里的“事”也即相对而言较为具体的道德情境。比如《论语·子张》中的第一节,子张阐述士应该拥有哪些德性,他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在子张看来,作为士,最基本的德性是勇敢、正义、恭敬严肃和孝顺,而这四种德性一一对应于四种“事”上,正是在这些“事”中,人伦关系得以显现,德性也似乎只能依附于这些人伦关系才能彰显出来。朱熹注道 :“四者立身之大节,一有不至,则余无足观。”[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189页。这就是说,士之为士,即在这四种事情上的德性表现,这样,德性与具体之事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甚至成为儒家德性论的一条确定原则,任何对德性的展现都必须通过“事”来进行。这一点在孔子著名的“君子九思”中得到更为真切的体现 :“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君子的九种思虑,明、聪、温、恭、忠、敬、问、难、义,均须一一落实于具体的事上,如视、听、色、貌、言、事、疑、忿、见得等,其关键是“思”字,它似乎类似于胡塞尔现象学所说的意向性,但儒家德性伦理学有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之处,即儒家并不着意于某种纯粹的意识结构,而是将一切意识结构完全融入于日用常行之“事”中。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实本身”是一种对意识的内在结构的本质还原,因此着力于某种先验建构的话,那么,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则是明确地将“思”切入“事”之中的“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这里的“位”带有强烈的关系或角色意味,即是一种日常经验的安顿,而无意于任何先验原则的追求。但是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教导”是 :“境域赋予概念以意义。”[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总体与无限 :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象学与儒家的情境主义存在着非常强的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我们在《孟子》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表达,如孟子说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这句话表明,儒家的德性原则的显现离不开“事”(事物和人伦关系),而且必须在对事物与人伦关系的深察默识中才能得以安立。安乐哲所说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对经验的整体认知,其本意或即在于此。
“思”即是在某类“事”之中思虑适宜于后者的德性或具体行为,此“思”的主体是某个道德人格,也即君子。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这种“思”,其目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成就君子人格,所以无论是何种“事”或关系,都是为“成人”提供载体的,“成人”或实现君子人格,乃至贤人或圣人人格,才是儒家德性伦理学的最终目的。当然,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事”或关系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那么一种真实的道德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也就随之建立起来。如果说德性在“事”上的显现是儒家德性伦理学的外在方面,那么“成人”或实现道德人格则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方面,后者在先秦儒家那里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德性修养工夫,这种工夫在孔子那里已经有诸多提示。比如说,孔子在论述“孝”这一处于仁德之核心和出发点的德性时,一再强调“孝”不能仅仅表达于外在的“事”(能养)上,真正的“孝”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恭敬、无违、忧心以及和颜悦色(《论语·为政》),一切均以内心之动机和态度为真正的标准,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儒家那里,真正的“本”是心性上的修养与磨练,而孝之所以能成为“为仁之本”,是因为孝是对父母之爱,“爱”又是仁之内在功能之一(“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所谓“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48页。,而爱是发之于人心之中的。但是,当孔子面对弟子的进一步申问时,又不得不从心性层面转向“事”的层面,如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以“无违”,后樊迟进一步问“何谓也”时,孔子再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颜渊》)。心性工夫必然要展现于日用常行的经验中,并在日常经验里加以磨练,并且内心的“无违”一旦表现于外,必定是合于礼的行为;在遵循礼仪规范的过程中,内在德性得以呈显。很明显,内在德性是本,而遵礼以行的“事”则是彰显此“本”的载体。所以子贡怀疑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天道暂且不论,就“性”这方面来说,孔子应该是时时处处在言说,只是结合着“事”来说,正因如此子贡才未能体会。
三、 从经验性的心境到超越经验的人性能力
除了这种鲜明的意向性(指向具体之事或具体之情境)状态之外,儒家的德性概念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征,即无所指向的心境状态,并且这种心境状态才是儒家心性哲学中的美德概念的特定意旨。[注]将儒家美德如仁、礼等,尤其是与礼关系紧密的“敬”,区分为指向某物的意向性状态和无所指向的心境状态,这一观点由凡蒙特(Vermont)大学哲学系汉学家陈心怡(Sin Yee Chan)提出,参见其所撰文章《儒家‘敬’的观念》(“The Confucian Notion of Jing (Respec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Apr. 2006, 56,2, pp.229-252),该文由臧要科中译,见方旭东主编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4—105页。孔子在说到仁时,曾说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即是强调仁作为理想人格的一种持久的心境,这样一种时刻不能堕失的仁的心境,显然并不指向某一特定之事或具体的情境,但却指向任何可能的事物和情境,并且它维持着某一人格的连续一贯性。如果说有所指向的意向性状态是某一美德的瞬时发用,那么,无所指向的心境状态则是美德发用的持续动力,并且到了孟子那里,后者又超越了某种道德理想人格的限制,成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为人禽之辨提供逻辑前提。不过,我们说一种心境状态是经验的或由经验累积而形成的,如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不违仁的心境,保持一颗仁心的状态,必定是在日常经验的积累过程中逐渐修养而成,即孟子所说的“集义而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我们如何能通过经验的积累而形成这样一种心境状态,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推溯。归根结蒂,我们只能追溯到一种普遍的人性能力,这种人性能力,在孔子那里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仁智能力,以及作为一贯之道的“忠恕”,而在孟子那里则是四端之说以及由此得出的对“性善”的明确判定,并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良能。我们认为,仅仅指出儒家心性哲学中的美德伦理是一种经验上的普遍心境状态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孟子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即由心善论性善乃至良知良能之类的概念。
应该说,如上那种将儒家美德概念理解成一种经验性的心境状态,是当代西方汉学对儒家心性论的一种理解趋势的必然结果。这种趋势就是将先秦儒家的人性(human nature)概念理解为一种过程概念(a process notion),从而避免西方哲学对本性(nature)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认识方式,即将本性理解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意义上的本质,这种本质为具有此本性的事物提供了存在的基础。[注]这一观念在儒家心性论最初引起西方汉学家关注时就出现了,此观念在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持有者是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另外,瑞士汉学家耿宁也有相同立场。参见Roger T. Ames, “Mencius and a Process Notion of Human Nature,” in Mencius : 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 edited by Alan K.L. Ch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72-90;耿宁 :《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编,倪梁康、张庆熊、王庆节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2、428、460页。耿宁认为孟子的四端尚不是德性,而是德性的天生自发萌动、萌芽或开端,尚需要培养和进一步发展。无疑,对儒家的人性概念作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理解显然是不符合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旨趣的,因为中国哲学自其发端起就没有西方哲学所追求的变化之中不变的实体意义上的本质概念架构,但这并不表明先秦儒家心性哲学完全缺乏对超越经验世界的普遍原则的理论诉求,只不过它将这种理论诉求寓于对具体情境在智识上的整体把握之中。而这种对具体情境在智识上的整体把握,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是一种纯粹经验的维度。但是,众所周知,康德已明确指出,经验的运用和经验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不违仁”作为一种心境,可以将其视为经验状态,但我们之所以持续具备“不违仁”的能力,却绝非纯粹经验能够予以解释。虽然孟子在运用四端说以论证人性善时使用了经验的情境类比方式,即“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是一种心理描述的方式,而心理描述无疑是经验的,但在举此例证之后,孟子紧接着又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及四端即人之“四体”,都表明孟子并没有将人的德性仅仅归于某种心理经验,而是认为在逻辑上那是人所必具的。安乐哲以孟子如下一段话而断定其人性概念是一种过程概念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其中的“扩而充之”一语使安乐哲确定,四端只是德性之萌芽,而不是完善的德性本身,要想达到或实现完善的德性,必须经过后天的经验上的对四端的持续扩充。[注]Roger T. Ames, “Mencius and a Process Notion of Human Nature,” pp.72-90.另外,上引陈心怡《儒家“敬”的观念》一文中也这样理解孟子的四端和儒家的美德概念,如该文认为同情是仁的萌芽,敬是礼的萌芽等,参见方旭东主编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第95页。这里首先要搞清楚孟子的四端的“端”所指为何,其次要进一步理解“扩而充之”是什么意思。朱熹将“端”字解释为“绪” :“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239页。这一解释为我们摆脱将“端”字理解为“萌芽”提供了一条思路。“绪”强调有物存在,至于此物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则暂且不论,只是仅有微小的端绪被我们所觉察;而“萌芽”则直接指出物的初始状态,犹如草籽之萌发。我们看到孟子认为四端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端”是在人心里存在的某物。只不过由于心的复杂性,其中并不止有这样的不忍人之心,还有“穿逾之心”(《孟子·尽心下》),后者却不能“充”,而需要克制乃至排除,所以四端在人心中只能以“绪”的方式被我们所察觉,但这种察觉却为我们体悟人性提供了可能性,而后来孟子以无比明确的方式强调,“四端”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四端”就是人性本身,而人性只能存在于人心之中,由此可知,恻隐之心等四端在人心里只是表现为人性的某种细微状态(道心惟微),但并非是不完善的状态。另外,“扩而充之”也不是说,由德性的不完善状态扩展到完善状态,而是说,将人心中德性的细微状态扩充到人的全身并外推至他人,如孟子的浩然之气一般。如同一寸精钢是钢,一丈精钢也是钢一样,人心中细微的德性之端绪是完善的德性,扩充而至全身乃至养成浩然之气发之于外的德性,那就是人心中的德性本身。孟子用“平旦之气”(《孟子·告子上》)来说明这一点 :清晨我们从睡梦中醒来,丹田一股清爽之气,孟子将之称为“平旦之气”,对此加以存养,即能最终形成浩然之气,也就是完善的德性(“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但“平旦之气”并非是异于浩然之气的另外一种气,它只不过是比浩然之气在规模上要小罢了,在性质上则是完全相同的。同样,四端只是在量的规模上比表现于人体之上并达之于他人的仁义礼智要小,而在性质上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并没有不完善和完善的差别。
因此,安乐哲受儒家情境主义的影响,对儒家心性哲学中的人性概念采取了经验的解释路径,将人性理解成一种不断养成的过程,且此过程永无休止;从另一处我们看到,安乐哲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他将“生成中的人”[注]安乐哲 :《儒家伦理学视域下的“人”论 :由此开始甚善》,谭延庚译,刘梁剑、安乐哲校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与人性本身搞混了,人必定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但人性不能与经验中的“人”的概念相混淆。耿宁则由于在对孟子“四端”说的理解上产生了偏差,致使其也将儒家的人性概念视为某种过程。耿宁在诠释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时涉及到对孟子“四端”的理解,他将“四端”之“端”解释为一种情感性的“萌芽”或“萌动”,并认为它们是“德性的开端”,但还不是德性本身,只有经过后天的修养扩充(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致”,或孟子的“推”、“扩充”、“存养”),“四端”才能进一步发展成完善的德性,即人性。这种解释与安乐哲殊途同归。但他们二人的如上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上述理解必然使得孟子论述“四端”的那段颇为情境化的文字变得难以理解,从而孟子的人性论也有被误解的危险,即将人性的那种存有论上的“人之根据”的意义,转化成经验上的某种物,即使这一物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过程式的。
四、 象征意义与情境
因此我们认为,儒家的情境主义并没有消解原则的有效性。先秦儒家将德性原则融入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使得情境成为德性原则的载体,同时,内在于心的情感又为情境中原则的发用提供了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类似于诺齐克所说的原则的个人反省功能。在诺齐克看来,拥有原则的人之所以会持续地按原则行事,是因为原则被这个人视为“将其不同时期的生活整合起来使之更融贯”,从而拥有整体的生活和身份的一种方法。[注]诺齐克 :《合理性的本质》,第27、28页。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诺齐克详细分析了原则的个人反省功能的内在机理,虽然他的分析带有强烈的效用主义或后果主义的色彩,但他所提出的“象征效用”[注]诺齐克 :《合理性的本质》,第46—59页。概念值得我们关注,应该将其与儒家德性伦理进行比较。在诺齐克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运用一个原则促使自己反思内在欲望并抵御外来诱惑,是因为原则与具体情境的结合会产生某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或者是对行为的预期效用或后果,或者是一种表达性(expressive)行为,后者的意思是 :“行为与情境之间的象征联系使得该行为能够表达某种态度、信念、价值、情感或任何东西。”[注]诺齐克 :《合理性的本质》,第49页。一个人之所以做出一个象征行为,其原因或者是对某种预期效用或后果的渴望,或者是这种象征行为所表达的态度、信念、价值、情感或其他东西对行为者的促动。而一个人之所以不会去做出一个象征行为,是因为效用会沿着象征联系回溯给该行为,从而使行为者因此行为的后果产生羞耻感或负罪感;对于表达性行为来说,行为者之所以拒绝行动,其原因就是任何人都希望表达一种无罪的态度,或者是其内在信念、所持守的价值、所拥有的内在情感综合而成了向往无罪的态度。
我们看到,诺齐克的象征行为的意义理论必须与情境相联系,而且“象征”(symbolize)本身就是将情境与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即某一情境下的特定行为代表或象征着原则容许或不容的所有行为。这种代表或象征,以意义回流的方式对主体的态度、信念、价值和情感产生持续影响,从而范导着人的行为方式或行动方向,并形成个体行为者的独特人格。
儒家德性原则的原初情感动力是道德主体自身拥有的人性能力,即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这是一种明确无疑的内在情感。这种不忍人之心被进一步表达为恻隐之心,作为四端之一,它就成为“仁”的端绪或“仁”本身。而在孔子那里,“仁”已经是一个象征性非常明显的字词,其自身承载着儒家人物心目中最具活力、最敏锐、最有包容性的德性原则,是一个集态度、认知、信念、价值和情感为一体的综合性德性原则。上文已经分析过,“仁”在《论语》中往往是以情境化的方式显现,孔子强调“仁”不远于己心,“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且需要我们“能近取譬”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象征效用的角度对道德主体提出的德性要求。另外,孔子认为他的一贯之道是“忠恕”,即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点。推己及人仍然是象征效用的运用,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明显是表达性的行为模式,即因自己内心的态度、信念、价值和情感综合而成的向往无罪、渴求无辜清白之态度,导致行为者不希望对他人造成无谓的伤害。这种伤害包括对其情感的伤害,而若把对方不欲求的东西强加于他,虽然客观上可能产生对其有益的效用或后果,但主观上显然会给当事人造成情感伤害,这是由表达性行为的意义回溯促使行为者在内省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判断。
这种内省反思在儒家的不同文献中被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如“诚”、“思”、“慎独”、“省”、“存心养性”、“反求诸己”等等。不过,儒家的内省反思不同于诺齐克的象征意义之回溯的地方在于,前者展示了一种形而上的层面,从而为内省反思提供了可能性的根据,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在这个层面上,儒家心性哲学拥有超越具体情境的维度。
孟子的四端说给我们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的思维架构。如羞恶之心(“义”或“义之端”)象征着特定情境之下的行为会产生让人羞恶之后果,或者表达了某种羞恶的情感,这种后果或情感回溯到行为之上,就使行为者产生了内在反省。辞让之心(“礼”或“礼之端”)的象征意义更为明显,因为礼及其仪式本身即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表达性极为突出,其所象征或表达的意义,在先秦时代极为丰富,这些意义在特定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上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最后,是非之心(“智”或“智之端”)则象征人的理智能力以及运用理智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对正确(正当、合理)与不正确(错误、恶劣)的确切态度、内在信念、价值判断和情感体认,象征效用与表达性的态度等共同为人的行为选择提供依据。这一思维架构一方面解释了人的德性原则的根源以及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为人禽之辨意义上的人之为人提供根据,同时还为人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方式予以担保。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已经初露端倪,如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也即是说作为礼乐之仪式或工具的玉帛、钟鼓都不是通过言说(云)的方式来显示礼乐的庄严、和乐、肃穆、敬重等气氛的,而是通过象征以及由操作这些仪式或工具的人的行为来表达如上意义的。这就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只有在情境之中,庄严、肃穆、美乐、和谐等意义才得以直观地显现。在前文所引“子见南子”一章中,孔子用“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所表达的恰恰是德性原则的象征意义(羞恶之情)对行为者自身进行回溯之后在行为者内心产生的反思功能,而这种功能的显示借助于特定的道德情境,即孔子见南子之后受到了其学生子路的指责,其中更大的背景是春秋时代周礼对于男女之防的原则规定和南子的行为处事对那些原则的违背,还包括孔子本人的身份及其所坚持的一贯之道。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明白子路为什么会因老师去见了一位女子就贸然指责,而孔子受到弟子指责后竟发下毒誓以自证无辜和清白。在这个案例中,原则的象征意义与情境的相互融合所引发的行为者甚至旁观者的内心反思功能,是极其明显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思功能,会促使行为者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回避某些行为,而坚持某种德性原则。
应该说,先秦时期乃至其后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人为架构起来的道德情境都是显现礼乐和其他德性意义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因此,整个中国传统的思维自始至终并没有摆脱以事物类推或类比意义的象征性特点,意义或价值往往就是在这种指事代物的象征性情境中得以相互勾连,与情境和原则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所赖以栖居的道德世界或“天下”。
综上所述,儒家的德性伦理采取的是在情境中显现德性的方式,它并非不重视道德原则的建构,只是儒家重视“事”以及寓于其中的人伦关系的先在性,并自觉地将原则建构与具体情境关联起来,以象征意义的效用或后果和表达性的态度、信念、价值、情感对行为者及其行为本身的回溯的方式,塑造道德人格,并彰显德性原则,后者在“事”或具体情境中的当下显现,构成了儒家心性哲学的鲜明特色。同时,情境主义固然是儒家心性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这使得我们不能将儒家人性概念作本质主义的理解;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得出,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人性论所坚持的是一种过程性的纯粹经验的人性概念,从而或者将人性看作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或者是将其视为某种经验累积而成的心境状态。若这样做,就必然会丧失人性在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禽之辨意义上的根据性意义,使得人性的超越经验的维度不能突显,我们也就难以理解儒家意义上的天道观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心、性、天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