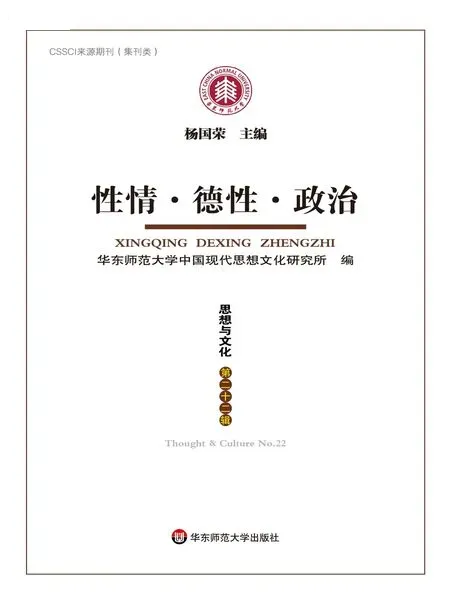孟子论“欲”与道德失败
●
道德失败的原因涉及许多方面,但一种常见的道德失败的原因就是道德的动机缺乏力量,而道德动机无力往往是因为道德的判断与情欲之间存在张力。这一问题反应在传统儒学中则涉及行动者自觉与自愿的辩证关系。自觉是道德判断符合“理义”的要求,自愿则涉及行动者的心理意愿和动机状态。当自愿背离自觉,道德的动机就可能遭遇挑战而被动摇。杨国荣教授在讨论知行问题时提到,行动或实践的过程包括我思、我欲、我悦,通过三者的统一,可以将自觉与自愿在行动中的张力得到一定的化解。[注]参见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26页。因此,由于“我欲”对动机的影响作用显著,“欲”也就成为讨论道德失败,特别是道德动机无力问题中的要点。
上述问题在孟子实践哲学中更为凸显出来,“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要求人们不能仅仅依照道德教条按部就班,还必须出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真诚意愿。如果行动者的道德动机力量不足,那么在行动时,道德的倾向就很可能被其他情欲状态所遮蔽,此时人们会出于其他的情欲冲动引发行动。又或者,即便行动者在其他情欲冲动不出现时,能够反思到自己的道德之心,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一旦诱惑出现,很容易就遭遇道德动机无力,成为习惯性的意志软弱者。
在这一过程中,“欲望”容易被认为是道德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孟子以为德性修养的关键在于“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所以许多有关《孟子》的传统注释都或多或少把“欲”作为道德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宋明儒者特别强调治“人欲”,将“物欲”、“私欲”视为害“仁义”的主要心理因素。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人欲并非都是“恶”的来源,消灭人欲将导致暴政。比如清代的戴震就反驳宋明儒者的礼欲之辩,提倡“体民之情,逐民之欲”。戴震认为圣人之欲善而常人之欲乱,“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注]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18页。。既然圣人之欲为善而不同于常人之乱,那么,导致道德失败的原因很可能并不是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的配比与结构发生了问题。
事实上,孟子对于不同的“欲”有着差异的理解方式,并且这些“欲”于道德修养的利弊好坏也并不相同。“欲”的对象不仅有各种感官享受,也包括“名誉”、“权力”等一般人们所追求的有价值的对象,甚至还包括了嫉恨、残暴等有害的欲望,比如“斗狠”、“好战”等。有些欲望并不必然导致道德失败,甚至可以通过“仁义”之心予以拯救而获得积极的意义;有些欲望却是“恶”的根源,对“心”造成莫大的贼害。必须谨防那些有害的“欲”,而对于那些并不必然有害的欲望,寻找到他们合理的实现方式,以及以恰当的配比与结构来生养它们,才是欲望治疗的最佳方案。
如果欲望本身并不必然致恶,而“欲”又作为常见的引发错误的原因而需要“寡”,那么,“欲望”与道德失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欲”所造成的道德失败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通过集中分析与“欲”有关的道德失败,可以看到孟子对“欲”与德性修养的关系的理解,也可以看到“寡欲”、“治欲”如何帮助人生养道德之心,以最终实现知、情、欲统一的完美境界。
一、 心好“理义”之欲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来描述四端之心。一些学者认为“四心”本身就带有诸如情感、态度、倾向等一定的动机要素。比如,黄百锐在一篇讨论孟子恻隐之情的文章中提到,孟子并没有西方哲学中关于情感与理性的截然二分的概念理解。他所论及的恻隐之情是包括了认知性的情感。[注]参见David B. Wong,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anuary 1991, Vol.41(1),pp.33—34.信广来认为“敬”同样涉及态度,“‘敬’”是一种可以指向他人或事件的注意、肃穆和心理上的关心的一种态度”[注]K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54.。事实上,“羞恶”、“辞让”都可能包含评估性态度和情感,因为行动者能够凭借它们识别对象的身份、地位、德性能力等因素,予以评价,并产生相应的情感态度。上述讨论多侧重于《孟子》中的道德态度、情感、偏好。然而,《孟子》中的道德倾向是否也包含一种“欲”性?[注]关于“四心”的心理因素的性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讨论。比如Angus C. Graham将孟子的四端理解为一种“道德冲动(impulse)”,于是这种冲动似乎就更类似于一种欲望而非情感态度。参见Angus C. Graham,“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Essay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engzi, edited by LIU Xiusheng and Philip J. Ivanhoe,Indianapolis : Hackett, 2002。Chad Hansen则区分了倾向、感受(feeling)和欲望,认为孟子的“四端”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主观内在的感受和欲望。参见Chad Hanse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64-165。Eric Hutton则通过分析荀子的文本指出,在先秦的古汉语使用中,“情”与“欲”的界限并非如英语中的“emotion”与“desire”一样较为分明,“情”有时也包含行动者的欲望。参见Eric L. Hutton, “Xunzi on Moral Psychology,” 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Dordrecht : Springer, 2016。上述的争议给我们一种启示,在先秦儒学文本中,“性”、“情”与“欲”往往密切联系在一起,而难以简单割裂,也很难直接等同于emotion,desire等词语,这也就造成用一种明显差异化的、定义性的心理概念来阅读先秦文献的困难。总体来说,我们虽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情感、欲望、态度、倾向等词汇,但需注意它们并不是绝对相区别的。使用这些现代术语有利于我们去把握行动者的动机心理因素,但不能割裂这些动机心理之间的彼此关联。从现实的心理动机来看,行动者的情感、态度可以进一步激发行动倾向或者对具体对象的欲求,反之亦然。因而,我以为,上述心理状态可以认为是推动行为的动机力量的构成部分,但关于它们之间的清晰界定,却不是本文所可以以及期望处理的问题。在某些时候,
对“仁义”的倾向偏好也展现出与其他欲求相似的性质。
首先,孟子有时将人们对仁义的偏好类比于对耳目食色等欲求对象的偏好。
故曰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
每个人都喜好可口的食物、悦耳的音乐、漂亮的美色,对这些可欲的对象的偏好类同于“心”对于“理义”的偏好。倘若耳目食色之喜好可视为“欲”,那么“心”的偏好不也具有“欲”的性质吗?并且,“欲”通常指想要某个事物,或者希望某件事的发生。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欲”通常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并渴求之,在获得对象之后会产生满足感。按此分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心”也有特定的对象,并指向相应行动与事件的发生,在实现目标时也会产生“悦”的心理情感。“心之于礼义”同样具有“欲”性。当然,尽管《孟子》中存在着这种类比关系,但是仁义之心毕竟是不同于食色之性的,在下述文本中,孟子阐述了两者的差异。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可以结合孟告之辩来讨论这段文本。告子以食色为性,孟子以“仁义”为“性”。两者发生冲突,这说明“食色”和“仁义”在孟子看来毕竟是不同的。关于两者的差异性,倪德卫、信广来认为,告子将“性”理解为生命所需的属性或倾向,强调的是一般生物学意义的“性”,孟子关注的是作为种群差异的“性”,也就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注]参见David Nivison, The Way of Confucianism :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Bryan W. Norden, Chicago :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153;Kw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pp.93—94。陈大齐认为孟子所谈之“性”只是人所固有的一部分,不是人所固有的全部。“性”指“仁”、“义”、“礼”、“智”,为人之特性,而“命”指口、目、耳、鼻,则是指一般生物性的生命属性,这一种对“性”与“命”的理解最为可取。[注]参见陈大齐 :《孟子待解录》,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5页。如果上述理解正确,那么,耳目食色与仁义礼智的差别并不明显体现在所对应的道德心理的差异,比如情感、欲望、理智的差异,而是一般生物性与人之特性的差异。如果从两者的这种类比关系来看,两者的差异并不否认道德倾向和自然倾向一样可以具有“欲”性。从食色之欲与仁义之性的差异来看,它们的差异也并不在对应心理能力的差异,而在一般生物性与人之特殊性的差异。所以,道德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具有某种“欲”的性质。
其次,孟子论及“欲”的对象多用“好”字,比如“好货”、“好色”、“好乐”、“好田猎”、“好战”、“好名”等等。“好”、“恶”多与“欲”与“不欲”相关。无论在《论语》还是《孟子》中,都出现了对道德对象的“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子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上》)“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孟子·告子下》)既然“好”除了可以指向财富、美色等“欲”的对象,也可用于伦理道德的目标,那么道德倾向对于“仁义”的偏好很可能也是一种“欲”。
另一段直接将对道德的偏好视为所“欲”的文本如下 :
孟子曰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义”作为所欲的对象,是人心皆有此偏好,“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仁义之“欲”与求生恶死之“欲”发生冲突,类比于人在饮食之欲中对“鱼”与“熊掌”间的难以取舍。这时“舍身取义”的行为就是由取义之“欲”推翻、战胜了求生之“欲”,而这种对“理义”的“欲”获得动机主导的原因就在于人能不“失其本心”,这样看来“本心”至少有一定的求“义”之“欲”性。如此看来,道德的倾向和人们对道德的偏好也可视作一种“欲”。[注]也可参照杨国荣对于《孟子·告子上》“理义之悦我心”相关段落的诠释 :“所谓‘心之所同然’,侧重的是‘我思’,其具体的内容是‘理’、‘义’等普遍的理性观念和原则,在孟子那里,这一意义上的‘我思’,与作为道德实践自我要求的‘我欲’具有一致性。”还有对《孟子·滕文公下》“欲正人之心”相关文本的解读 :“这里的‘欲’(‘欲正人心’)以‘善’为实质的内容,所谓‘可欲之谓善’。与‘我欲’相联系的‘悦我心’,已不同于单纯的理性思辨;以‘我悦’为形式,它同时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认同和接受。”所以,最后杨国荣认为,儒家道德哲学指向达成一种自觉与自愿的统一,也就是“我思”、“我欲”与“我悦”的内在统一。参见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第125—126页。
二、 食色之欲
从广泛意义上说,由于人们对“理义”的偏好也可以说是一种“欲”,那么孟子所说的“寡欲”中的“欲”的内涵就并非指一切人的经验性的心理欲求,而有特殊的内容。不同的“欲”在道德修养中有不同的价值,也就相应地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与修养方法,因而讨论欲望与道德失败的关系就有必要详细分析不同的欲望类型。食色之欲就是首要需要考察的对象。
追求食色等感官欲求一般被视作“小人”的特征。“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那么,“小人”呈现这种特征的原因为何?因为食色情欲本身有害吗?是否因为小人的食色情欲比之大人更加强烈而难以遏制?人们成为小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追求食色之欲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再次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里,“小人”追随感官情欲只是“以小害大”的事例之一,“饮食之人”并不能构成小人的主要特征。
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这里为了说明“以小害大”,孟子举出了三个例子,“贱场师”、“狼疾人”与“饮食之人”。按照文本的逻辑,这三个例子都是“养小以失大”的案例,因而都并非“养小以失大”的定义或完整说明。“养其小者”因而也就可能包括各种以小害大的情况。也许“贱场师”和“狼疾人”不算是道德相关的案例,而作为饮食之人更直接与道德相关。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道德相关的事例中,《孟子》里描述了各种“小”与“大”相比照的案例。比如《梁惠王下》中有关勇气的“大勇”与“小勇”;《滕文公上》有关社会工作的“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告子下》有关对待父母过错的不同态度的“亲之过小者”与“亲之过大者”;《告子下》君臣关系中的“大罪”与“小罪”;《尽心上》丧礼中的“大功”与“小功”;《尽心上》有关陈仲子亡亲戚君臣上下的“大义”与“小义”等等。因此,可以说,“饮食之人”并不等于“小人”,也就是说追求食色之欲并不是造成小人道德失败的主要原因,食色之欲与小人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只有当因为追求饮食而放弃仁义之心的修养之时,才构成“以小害大”的情况,成为道德失败的“小人”。
总体上来说,“小人”因为无定性,所以更容易受到各种欲望的诱惑。在孟子其他论及“小人”的文本中,“小人”体现出一种易受外界影响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才是“小人”区别于大人或君子的主要特征。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孟子·滕文公上》)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梁惠王上》)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孟子·离娄上》)
《诗》云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孟子·万章下》)
从上述与小人相关的描述看,小人犯错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影响,居上位者如果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所需,不能提倡孝悌仁义的教育,或者不能树立良好的道德楷模,那么小人就会受之影响而作乱犯法。“小人”一方面指封建时代常常受到生活所迫的普通民众,另一方面也指易受外界影响而没有稳定品性之人。这两种特征结合在一起,“小人”或者是因为缺乏良好的物质生活保障,或者道德教育水平偏低,因此没有稳定的心性,更易受到外界事物影响,从而“小人”的道德失败往往呈现出无自主性的特征。[注]这里根据先秦文本中两种“小人”的用法,并不是说孟子认为身份低微的普通民众就是“小人”。事实上,在《孟子》中,没有恒心而很容易被欲望诱惑动摇的往往是统治阶级。不过由于普通民众在乱世中,生活疾苦又缺乏教育,所以往往具有无恒心的“小人”特征,但是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放纵感官情欲而丢失仁义之心只是“小人”呈现出的道德失败的一种形态,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小人”未经德性修养易随波逐流。如此,“小人”养小体的原因便和孟子论述的原因相符合。“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小人”易被外物所蔽,被“小者”夺其心志,都是因为小人缺乏“心之官”的反思能力。“不思”也就无所“立”,无所“立”所以心志不坚。心志不坚者不仅会受到各种食色之欲的诱惑,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才是造成“小人”道德失败的根本原因。
食色之欲本身并不必然与人们对仁义的偏好相互矛盾。当齐宣王谈到“好货”、“好色”之“疾”之时,孟子以为,如果齐宣王能够“与民同乐”,将自己的私欲普遍化来关爱民众,那么此时食色之欲也可以拥有道德的意义价值。“与民同乐”包含了“仁”的要求。孟子通过齐宣王赦免牛的案例,提示齐宣王反思自己的恻隐之心,并敦促王将此心扩充推广,最后实现对百姓的同情关爱。对百姓之爱不是空泛的,而是包含了满足百姓所需的生存欲求,使百姓也能富足安乐的生活。对百姓之爱包含了食色之欲的内容,当食色之欲不止于齐宣王之私欲,而是能与民同,食色之欲就不再造成道德失败。
如此,“小人”养小体是因为“不思”而无所立志,也就是不能对仁义之心有所反思认识,不能坚定修养。缺乏了“仁义”之心的调节,食色之欲就是完全自私的,这时的“饮食之人”才是“小人”。如果能够运用心之官的“思”的能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饮食之人”因之也能照顾体恤他人的饮食之欲,此时“饮食”是必要的,而非不道德的。仅仅有“思”不足以成君子。在“心”的能力里,还需要有“志”,通过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将“思”指向道德倾向,人们便心有定向,会拥有“志”。如此人们会持守于道德倾向,并将对道德的偏好置于食色情欲之上,此时人们才会拥有“恒心”。有“恒心”者不再为不断浮现的各种私欲所困扰,而能够坚守仁义,拥有稳定的品性。
从“小人”的道德失败案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感官情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道德失败。作为两种所欲的对象,“食色”与“仁义”并不必然矛盾。在丧失“心之思”与“心之志”的情况下,人们才更易受外物环境的影响,无止境地追逐“食色”私欲,流于“小人”。
三、 权力之欲
与身处下位并一味追逐感官享受的“小人”又有所不同,统治阶级在食色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欲望,这种权力欲望与道德偏好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权力欲望是否必然会造成道德失败?在与齐宣王对话之时,孟子谈到了王之“大欲”。
王曰 :“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 :“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 :“否!吾不为是也。”
曰 :“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孟子·梁惠王上》)
由于齐宣王曾多次提及自己的“好货”、“好色”、“好乐”等食色欲望,因而孟子进一步反问王,追求大欲是为了肥美的食物、舒适的衣服、美好的姿色和悦耳的音乐吗?齐宣王明确回答“大欲”与这些感官享受并无关系,追求“大欲”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享受。因此,“大欲”是不同于食色之欲的另一种“欲”。
接着孟子描述到,所谓“大欲”就是想要扩张土地,接受各国的朝贡,成为天下之主,如此“大欲”就是一种追求权力的欲望。孟子认为,以齐宣王的所为来求得大欲相当于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王曰 :“若是其甚与?”
曰 :“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 :“可得闻与?”
曰 :“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 :“楚人胜。”
曰 :“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下》)
“缘木求鱼”虽然方法错误,但并不会造成有害的后果,而如果不以仁政来求“大欲”,则必然遭致灾难性的后果。随后,孟子督促齐宣王“反其本”来施行仁政,并认为如果施行仁政,那么齐宣王将仁者无敌,莫之能御。从整段论述来看,孟子并未直接反对齐王对权力的欲求,而是指出只有将“大欲”与“仁政”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多有学者将这段理解为孟子的说服策略。[注]参见Kw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p.177。这种说法有一定启发性,从孟子对齐宣王的多次劝说来看,齐宣王有时能够体察到自己的仁义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论说可能更侧重于进一步启发齐宣王以转化他,是一种德行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对仁义价值的证明论证。[注]有必要注意,在道德论说中可能存在两种方式,也就是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 :前者偏重于思辨理性方面的证明,也就是说理;后者是在不违理的情况下,偏重于道德情感、欲求等动机要素的唤起,也就是动情。我以为,这里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并非侧重于理论证明,而是侧重于调动情欲。但不可因此直接将孟子的道德理论认定为是基于欲望利益的规范性证明。从德性修养的层面来说,偏好道德的仁义之心“好”仁,而与其他欲求指向不同的行动方向时,两种所欲间会发生冲突与争夺,此时因养护仁义之心,其他的欲求可能被视作是对立危险的而需要被克制。但是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仁义之心都和其他欲求相冲突矛盾。从价值上来说,道德倾向的实现具有最高优先性,这不容置疑。但是从修养方法上来说,当其他欲求并不与道德倾向相冲突时,打消行动者的疑虑,敦促他去进一步实践仁政,才能加强行动者对道德倾向的进一步感知、认识和偏好,这样才能实现道德转化的目的。
孟子的这一说服策略并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因为确切来说,某些欲求并不必然与“好仁”相冲突。从权力欲望的内涵出发,“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这些目的中并没有直接损害“仁”的要求的内容。实现了这种“大欲”的“圣王”同时也是实现仁的典范。[注]当然圣王的行动出发点并不是“大欲”而是“仁义”,“大欲”的实现是施行仁政的附属结果。“大欲”与“好仁”没有本质冲突,这样才使得“大欲”具有被“仁”协调转化的空间,通过行动者践行“仁”,“大欲”同时也能够实现。孟子的论说中反映的是两种所欲间的可协调兼容性,而不是将“仁政”视作实现“大欲”的手段。
以手段来说,能够实现“大欲”的除了“仁政”之外还有“霸政”,但是“霸政”不具有完全的道德价值。“大欲”虽不必然与“仁政”相冲突,但是此欲必须受到“仁义”的制约。“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霸者虽能“以力假仁”成就大国而收获权力,但并不具有真正地成为天子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霸者虽有政治才能,但是由于他缺乏获得至高权力地位的合法性,他的统治是“僭越”的“不义”之罪。当实现“大欲”的手段以牺牲百姓为代价时,则不仅缘木求鱼,而且还会招致灾祸。当仅以权力欲为行为的最高目标,并假借“仁义”为手段时,虽然可能获得政治成就,但是并不能使民心悦诚服,并且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天子”的合法地位。只有以“仁义”本身作为行为的最高目标,才能成就圣王天子。“大欲”不必然与“仁义”之心相冲突,但其价值地位必须低于仁义本身,并且其实现方式也必须受到“仁义”的制约。
四、 好战与斗狠
如果我们将人们对道德的偏好也理解为一种“欲”,在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中,所欲与所欲间时有发生冲突而互相遏制的可能,并且争夺对行动者的主导力量。尽管许多欲求与道德的欲求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被仁义之心协调拯救而赋予道德意义,但有一些“欲”却会损害道德本性的生长发展。这些“欲”会贼害仁义之“心”,造成人们失去自己的善性,成为不仁者。“好战”就是这样一种欲望。孟子曾直接批评梁惠王不仁,而梁惠王就是“好战”的失败者典型。
孟子曰 :“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 :“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对曰 :“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尽心下》)
梁惠王“好战”,为争夺土地而驱赶百姓作战,造成百姓无辜惨死。而战败后,再驱使自己喜爱的子弟作战。仁者将对亲近之人的关心爱护推广到普通民众,而梁惠王不仅无视百姓生死,甚至为求战胜,将自己亲近喜爱之人也送入战场。梁惠王的“好战”之“欲”造成了大量无辜生命的伤亡,是最为恶劣的一种“不仁”的道德失败。从梁惠王的“好战”来看,战争的欲望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为战而战的“好战”之欲和“仁”的道德原则相矛盾冲突,“好战”者必然“不仁”,所以“好战”之欲对仁爱之心的伤害最为严重。
梁惠王的“好战”的实质在于他对于百姓生命的轻视,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讨论中提到梁惠王“杀人”之罪。
梁惠王曰 :“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 :“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 :“无以异也。”
曰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
以政杀人虽然是间接杀人,但孟子问梁惠王,“杀人”用棍棒还是用刀是否有性质上的区别,既然没有区别,那么梁惠王以政杀人的实质就是“率兽而食人”。孔子说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轻视他人的生命被儒家视作最大的罪恶。孟子所处的年代,战争不断,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无辜惨死,“好战”相当于“杀人”,孟子以为时代的症结就在于这种普遍的“嗜杀人”之罪。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战争时代,诸侯王倘若能有仁心而停止杀人之嗜欲,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不嗜杀人”、减少战争是实现“仁政”的最基本要求。由此可见为战而战的“好战”与“仁”水火不容,“好战”是一种最具危害性的“欲”。
另一种严重危害“仁义”的“欲”是“好勇斗狠”之欲。“勇”有积极的意义,但“好勇”的“小勇”是不值得提倡的。就君王而言,“好小勇”可能引发“不义”的战争,此时的“好勇”终至于“好战”而产生可怕的灾难后果。就普通人而言,如果不以“仁义”为前提条件,“小勇”可能会沦为盲目地嫉恨斗争。“夫抚剑疾视曰 :‘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匹夫之勇依靠一种相斗的冲动,只能抵挡一人,而没有伦理价值。孟子以为这种“好小勇”的“斗狠”行为不仅危害自身,更有违“仁”。“仁”以“事亲”和“孝”为基础和最重要的方面,“好勇斗狠”极有可能危害双亲家人。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 :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下》)
因为伦理事物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事亲”,而“亲亲,仁也”。五种不孝的行为里就有“好勇斗很(狠)”,这种行为会将双亲至于危险的境地。何以如此?在《尽心下》,孟子提到了因嫉恨互相争斗残杀的危害。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关系中,杀人者既然杀害了他人的父母兄弟,必然遭致他人的报复行为,如此也就将自己的父母兄弟家人连累其中。如若因相斗结怨,造成对家人的报复仇杀,那么等同于自己亲自杀害了亲人。如此,岂不是最为“不仁”的行为?因此,“好小勇”而“斗狠”也是一种危害道德之心的最严重的“欲”。
五、 道德失败与欲望治疗
对于熟悉《孟子》文本的学者来说,很容易发现上述讨论并不能穷尽《孟子》中有关道德失败案例的讨论,也不是对所有欲望的完整概述。但仅以上述分析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在《孟子》中,“欲”是多样的,“欲”与道德失败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孟子提倡寡“欲”以“养心”,一方面,所寡之“欲”有具体的内涵;另一方面,“寡欲”于“养心”之所以有效,在于道德之心的发挥也具有动机性效力,也可以视为一种“欲”,而与其他“欲”存在交互影响与“力”的较量。
从第一方面来说,人们的悦“理义”与“好”仁义之情欲不仅不当“寡”,而应该“养”,以使得仁义之心获得最大的动机力量。食色之欲与权力之欲并不必然导致道德失败,但需要“寡”,以使得它们低于道德动机,从而从属于道德动机,受到道德力量的支配。对于单纯的“好战”和“斗狠”这类置亲人和爱人于以及置百姓于水火的欲望,则不存在“寡”的问题,而应该予以更彻底地更正与防范,以免造成祸害“仁义”的灾难性后果。
从第二方面来说,由于我们将道德之心也理解为直接具有动机性力量,那么对于道德之心的生长与培养也就不能仅仅通过理性认知与知识传授,而需要像锻炼身体一般,去进行精心养护和有意识的训练。传统的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道德修养需要进入到精神修炼、身体践行与日常生活的演练中,因而提出诸如“养气”、“三省吾身”、“调息静坐”、“从人情事变”等生养道德动机的实践修炼方法。
当代学者也注重到中国哲学的身心修炼问题。比如一篇题为《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为参照》的文章指出 :“儒家修身传统的实践,即‘变化气质’、学习成为君子并最终达到圣贤境界,就恰恰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修炼与欲望治疗。”[注]彭国翔 :《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为参照》,杨儒宾、祝平次编 :《儒学的气论与功夫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文章同时引入了当代西方哲学中欲望治疗思潮的领军人物纽思浜(Martha Nussbaum,通常译为“玛莎·努斯鲍姆”或“玛莎·纳斯鲍姆”)的观点 :“认为哲学更多地应当深入反思人们的欲望、情感的维度而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理性。”[注]彭国翔 :《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为参照》,杨儒宾、祝平次编 :《儒学的气论与功夫论》,第7页。
事实上,与其说理性是“狭隘的”,不如说如果我们将问题更全面地予以考察则更有利于推动道德实践。杨国荣通过分析儒家传统提出,在实践中人们应该化口耳之知为身心之知以克服道德动机相关的实践问题。身心之知强调培养人们的意欲、情感以配合“理义”的道德要求。如此,则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的考虑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视域考察”。“如果综合考虑了相关的各种情况,包括客观上多重可能的趋向,主观上不同意欲之间各自的强度等等,则可能形成与单向的理性考虑不同的行动选择,后者往往更合乎一定的行动情境。这里的综合考虑,可以视为认知、意向、态度、欲望、情感等等的交融……通过扬弃意识活动的单向性,以避免引发意志软弱。”[注]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第130页。意志软弱是道德失败的一种常见现象。杨国荣提出身心之知的看法也启迪我们关注主体身心方面的情欲状态,而这样一种关注扩充了理性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看待道德实践并促进德性修养。
就当代儒学研究而言,理性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并且也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这一传统对于欲望,以及相应产生的各种实践问题的了解还不够充分。如果还停留在笼统的对“寡欲”的理解,将“欲”认作“在外者”而不予以重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道德实践的要求。从《孟子》的文本来看,“欲望”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而“欲望”和道德失败的关系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如此,“欲望”并不是道德失败的唯一原因,也不可能完全剔除。当人的心灵偏离了“仁义”的要求时,“欲”可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失调,这才是道德失败的真正原因。通过更全面地认识“欲”,努力培养更为协调优美的欲望配比与结构以克服道德失败,才能让我们真正拥有善良美好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