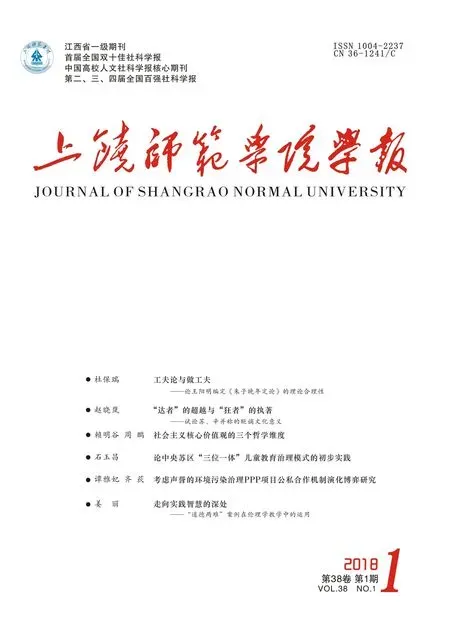程颐主敬论的内涵与特点
——兼论其对先秦儒家“敬”思想的创新发展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敬”作为一种修身的工夫早在先秦就已经受到儒家的广泛关注了,但直到二程特别是小程子程颐,才更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敬”之工夫的内涵。在二程之前,“敬”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道德修养工夫。程颐通过对经典的注释和阐发,完整地勾勒出一套系统完备的“主敬”理论,使“敬”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并且内涵得到了重大的深化,由此成为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修身工夫之一。
一、先秦经典文本中的“对象性”之“敬”
先秦的众多儒家经典都有涉及“敬”的思想,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指明程颐对其进行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只对其中重要典籍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整体上的考察。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宋明儒以六百年之长期,费如许之言词,其所宗者只不过是《论》、《孟》、《中庸》、《易传》与《大学》而已。”[1]31这五部书确实是宋明理学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先秦经典。我们先摘引其中关于“敬”的代表性用法并进行简单的考察,便可见二程,特别是程颐对“敬”的发展。
《大学》有“为人臣,止于敬”[2]5。《中庸》有“敬其所尊,爱其所亲”[2]27,“敬大臣也”[2]29,“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2]39。《论语》有“敬事而信”[2]49,“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56“临之以庄,则敬”[2]58,“其事上也敬”[2]79,“居敬而行简”[2]83,“敬鬼神而远之”[2]89,“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2]134,“执事敬”[2]146,“修己以敬”[2]159。《孟子》有“父子主恩,君臣主敬”[2]242,“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2]277,“敬人者,人恒敬之”[2]298,“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2]353。《周易》有“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3]341,“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3]342,“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3]348,“敬之无咎”[3]415。
从上面所引的五部经典关于“敬”的代表性用法来看,笼统而言,“敬”都是一种有对象的心理活动,并且对象主要是外在的经验对象,主要包括“人”与“事”两类。因此“敬”表明的乃是人在面对外在的人或事时,内心抱有一种恭敬之心,或者怀有一种认真谨慎的态度。“敬人”主要包括臣对君、子对父母、人民对统治者的恭敬、尊敬、敬爱之心;“敬事”除了要求认真谨慎地处理一般事务之外,在祭祀时、面对鬼神时更要有恭敬之心。这种“敬”具有功利的效果,如认真谨慎就有利于更妥善地处理各种事物,也能够避免外在的灾祸等等。但是其本身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活动,怀有敬的态度就有一种道德价值。由于儒家更强调“反求诸己”,使得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而非功利结果,功利结果具有偶然性和外在性,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而道德则完全取决于自我。
但总而言之,在这些先秦典籍中,“敬”主要还是一种对象性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伴随着主体与客体相接触、交感而生发,指向的是外在的事物。虽然孟子强调了“恭敬之心”是内在于人的,但是这种心理活动还是要在某种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中才会表现出来。
二、程颐“非对象性”之“敬”的提出
由于“敬”一定关联着外在对象,外在对象是敬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便对敬具有一种制约作用,因此其作为修身工夫便缺乏充分的独立性。而二程(特别是程颐)将“敬”建立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修身工夫,首先要做的便是把这种“对象性”活动的“敬”改造成“非对象性”活动的工夫。“非对象性”意味着“敬”不指向外在对象,因而能够独立于外在对象,成为一种即便在不与外物接触时人都能主动运用的修身工夫。
他们的这一努力在南宋就已经被注意到了,《朱子语类》中即记载:“程子说得如此亲切了,近世程沙随犹非之,以为圣贤无单独说‘敬’字时,只是敬亲,敬君,敬长,方着个‘敬’字。全不成说话!圣人说‘修己以敬’,曰‘敬而无失’,曰‘圣敬日跻’,何尝不单独说来!若说有君、有亲、有长时用敬,则无君亲、无长之时,将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说!”[4]朱子口中的程沙随虽然意在否定二程,但是他确实注意到了二程论“敬”与先秦儒家不同。他指出先秦儒家都不单独把“敬”作为独立的工夫,而是一定要说“敬亲”“敬长”之类。这其中的差异正如上文所说,是对象性的工夫与非对象性的工夫的差别,虽然程沙随没有用这样的概念进行区分,但是明显也看出了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别。而朱子站在维护二程道统地位的立场,自然要反驳程沙随这种论调,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程沙随的看法或许更为客观。
事实上,在《论语》和《易传》中已经出现了“非对象性”的倾向,这自然引起了程颐的注意。《论语》中的“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2]83以及“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2]159这两条中的“敬”在文本中都没有说明具体的对象,似乎可以视为非对象性的修身工夫。正如程颐对第一条进行的解释:“居敬则自然简。‘居简而行简’,则似乎简矣,然乃所以不简。盖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矣。居敬则心中无物,是乃简也。”[5]294他认为“居敬”是“心中无物”,因此自然“简”而不必多此一举再“居简”了。这种“心中无物”的解释正体现了程颐把“敬”理解为不涉及对象的一种非对象性的工夫。
但是《论语》本来就十分简约,文本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里的“居敬”“修己以敬”虽然在文本中没有具体对象,但是很有可能只是对象在语境中有所省略,并不见得“敬”已经成为非对象性的工夫了。这一点我们只要考察二程以前的相关注解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对第一条的“居敬”,《论语注疏》中,何晏注:“孔说:居身敬肃,临下宽略,则可。”邢昺正义曰:“言若居身敬肃,而行宽略以临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6]77在两人的解释中,“居敬”被解释为“居身敬肃”了,原本看似可能是非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就被实指为对象性活动的概念了。“敬”的对象成为“身”,意即以“敬”的态度去治身,“敬”指向的是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方式。第二条的“修己以敬”,《论语注疏》中,何晏注:“孔曰:敬其身。”邢昺正义曰:“言君子当敬其身也。”[6]231同样,在这一条中“敬”的对象也被指为“身”。
可见,无论是魏晋的何晏还是宋初的邢昺,他们都依然把《论语》中的“敬”当作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这种解释与上引程颐“居敬则心中无物”的解释具有天壤之别。因此,《论语》中看似具有非对象性意义的“敬”,也许确实只是因为其文本简约与模糊而已,程颐之前的那些解释,可能才更贴切《论语》之本义。
程颐似乎也是自觉到了《论语》这几条的模糊性与不可靠性,因此他对此仅仅是略加谈及,并未将之作为他新理论的基础。而在《易传》中,则有另一处明显具有非对象性倾向的说法。《坤》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3]333“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一句被二程敏锐地发现,这就是他们论敬最重要的经典基础。从大程开始,他们就反复地引用这一句并进行了解释。这一句优于《论语》中两句的地方,可以说在于其非对象性更明显、更明确,并且其文义更完备,义理更清晰。
但在二程以前,对这句话中“敬”的理解仍然为对象性的,孔颖达说:“言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3]333“用此恭敬以直内心”一句,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作“用此恭敬以直内理”(参见《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周易注疏》与此相同(参见《周易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然而《宋本周易注疏》与四库全书本《周易注疏》皆作“心”而不作“理”(参见《宋本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2页;《周易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3页)。统观上下文,作“心”于义较长。他依然把“敬”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认为以“敬”的方式去“直”“内心”,“内心”成为了“敬”的对象。这种解释遭到了二程的明确反对,特别是大程直接进行了批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则便不直矣。行仁义岂有直乎?”[5]120大程认为孔颖达的说法正是“以敬直内”,这就如同孟子所谓“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牟宗三先生指出:“敬是直通‘於穆不已’之仁体而自内发,亦如仁义之由中出,并非是外在的东西而可以假借袭取也。不是拿外在的敬去直吾人之内部,若如此,便直不起,至少其直亦是偶然,并无称体而发的必然性。”[1]243牟先生的分析精当地区分了两者的差别。大程否定了孔颖达的解释,便把“敬”的非对象性的特点凸显出来了,即“敬”在此并非一种指向特定对象的工夫。通过他的阐发,已经初步确立了“敬”之工夫的独立意义了。
然而,大程论敬虽然多,但言语过于圆融,对主敬工夫缺乏细致分析和具体讨论,事实上,他常常把“诚”与“敬”混在一起说,正如陈来指出:“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7]因此,真正把“敬”确立为独立修身工夫的人是程颐,程颐不但明确化了“敬”的非对象性意义,也具体讨论了敬之工夫的内涵*程颢还有另一著名的说法:“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0页)这也清楚地表明了程颢论“敬”的非对象性的特点,敬并不是敬于写字,不是专注此心于写字,而是非对象性的一种精神收敛,这种工夫就是进学的工夫。此外还有“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参见《二程集》第31页)也表明了这种非对象性。然而程颢虽然心中很明确这种“敬”的特点,但是并不如程颐对“敬”的工夫有具体的讨论。。
对于《易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解释,二程立场相同,都认为不能把敬作为一个直内的手段,但是程颐对这一句的具体理解却不与程颢相同,《周易程氏传》对此解释:“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徳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徳不孤也。”[8]程颐提出君子在修身方面需要着力的工夫是“主敬”和“守义”。而“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即能够做到“主敬”的工夫,内心自然能正直;道义能够付诸实践,外在自然就端方。“内直”和“外方”是用力于“敬”“义”所自然能达到的效果。因而虽然在“敬”能够导致“内直”效果的角度上,和孔颖达的说法相似,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敬”不以“内”为对象,“主敬”不是“直内”的手段。
简言之,按照孔颖达的疏,着力点在于“直”,“敬”只是所依据的一种方式;按照程颐,着力点在“敬”,“直”只是所达到的一种效用。他又说“敬义既立,其徳盛矣”,这里完全就只提“敬”而不再说“内”了,这里认为能够做到主敬,便是“德盛”。至此,“敬”之工夫的独立意义昭然若揭。整段注文清楚地表明“敬”不是以“内”为对象,“敬”是非对象性的活动,具有独立的意义。
事实上,从《二程遗书》来考察程颐对“敬”之概念的运用,会发现绝大多数时候他使用的“敬”都不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概念了,只有偶尔在对经典的解释和日常谈话时提到的“敬”才是对象性活动的概念。程颐的这种改造,使得“敬”由原本受外在事物制约的非独立性、相对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得到克服,变成了具有独立性、绝对性和必然性的道德修身活动。由此,这种工夫就能完全操之在己,人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张扬,自觉修身成圣的意义也获得了彰显。
程颐不但赋予了“敬”非对象性的新义,还以此来统合原本对象性的敬。《二程遗书》中记载:“且如恭敬,币之未将也恭敬,虽因币帛威仪而后发见于外,然须心有此恭敬,然后著见。若心无恭敬,何以能尔。所谓德者得也,须是得于己,然后谓之德也。(原注:币之未将之时,已有恭敬,非因币帛而后有恭敬也。)”[5]206又有“问:‘“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门、未使民时,如何?’曰:‘此“俨若思”之时也。当出门时,其敬如此,未出门时可知也。且见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门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盖素敬也。’”[5]184-185
第一条中的讨论涉及《孟子》,孟子的“恭敬”乃是待人时的恭敬之心,是一种对象性的“敬”。而程颐则指出这种“敬”是“因币帛威仪而后发见于外”的,也即只是具体情境中的一种表现。而这种恭敬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来,乃是因为此心有一种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的本有之“敬”作为其根源。因而在面对具体的对象和情境时,便能够表现为具体的恭敬。这里实际上就是把非对象性的“敬”视为更高一层、更内在一层的“敬”,这正是具体的对象性的“敬”能够产生的基础。第二条中亦然,《论语》所论也是处事待人时的对象性的“敬”,而程颐也认为其背后还有更高一层的非对象性的“敬”,因此说“且见乎外者,出乎中者也。”此心能够保有此本有之敬(“素敬”),遇事自然能够表现出合理的恭敬之心,这种恭敬不是遇事时才突然产生的,而是基于本有之敬而发见于外的。
在这两段中,程颐实际上以体用的关系来看待他提出的非对象性的“敬”与一般的恭敬之心,认为非对象性的“敬”乃是对象性的“敬”的根本,从而也揭示出“主敬”在修身工夫中的优先性。
在古代,中国哲学家受到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故较少直接创作,而其创新和发展往往借助于“以述代作”“寓作于述”的方式,因此只有仔细体会他们对经典的阐释,才能发现他们的创新和发展。上文正是基于程颐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来解释他如何改造和发展“敬”的概念的。
三、“非对象性”之“敬”的具体内涵
通过上文可见程颐确实改造和发展了“敬”的观念,以下讨论程颐“主敬”工夫的具体内涵,说明何为非对象性的敬。
儒家的修身工夫,一方面既要使人能够趋于道德境界,另一方面也要为人提供自足和乐的精神支撑。理学家认为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在他们的眼中,圣人不但是最高道德人格的体现,也具有最高的精神愉悦。这一特点在濂溪提出“孔颜乐处”时就已经深刻地揭示出来了。而学者之不乐的原因,很大程度来自思虑的纷扰,程颐便指出:“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5]147而如何面对这种思虑纷扰,便成为二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基于儒家的立场,不可能选择佛教逃避山林的方法避免与世相接,而强调一定要处事接物。他们认为佛教的修身工夫是“屏事不问”,是一种“静”的工夫,这种工夫不考虑义理对错,仅仅从自我清静安适出发来逃避外物引发的各种烦恼,因此他们认为这就是一种“自私”。基于对这种“静”的反对,二程认为有必要提出儒家立场的工夫以超越释老的工夫,而“敬”正是他们探索的结果。程颐说:“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5]189又说:“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5]168-169对于“静”和“敬”的差别,二程认为“静”是“忘”,是企图通过逃避和否定外物以求内心平静。然而人的生存不可能不与外物打交道, 因此,“敬”虽然也不执著于外物上, 但并不逃避与否定外物。由此,通过“敬”的工夫,人一方面能保持不被外物牵引,达致心灵的平和;另一方面又能正视外在事物,以入世的态度进行道德实践。由此就既能够克服思虑纷扰,也能够保证实践具有道德性。
与二程同时的张天祺和司马光都曾患于思虑纷扰,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张天祺坚持一上床睡觉就不思考任何问题[5]53,司马光则通过口念“中”字来避免纷扰[5]25。二程对两人都进行了批评,认为张天琪乃是以一种强制把捉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意识,这种方式虽然当下能够控制自己不思虑,但是这种强制把捉也是一种刻意的心理活动,这本身也已经是一种思虑了,因此不能真正让自己免于思虑纷扰。司马光的方法是念一个“中”字,这也是通过让心理活动寄寓在某个对象之上,以压制其他的思虑。两者的特点都是一种对象性的工夫,这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程颐在面对吕大临提出思虑纷扰的问题时指出:“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遂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5]8“昔吕与叔尝问为思虑纷扰,某答以但为心无主,若主于敬,则自然不纷扰。譬如以一壶水投于水中,壶中既实,虽江湖之水,不能入矣。”*[5]191对主敬的状态程颐有“有主则实”和“有主则虚”(参见《二程集》第169页)两种说法,两者并非矛盾,实际上只是程颐阐明的角度不同。“有主则实”是从水入壶的比喻来看的,壶中既实,则外来的水不能入,如同此心有所“主”因而是“实”的,外来的思虑纷扰就不会来进入其中。“有主则虚”是从此心中有无思虑来说的,此心中能“无适”,就没有各种思虑与其对象存于其中,因此是“虚”的,如果此心充满杂多的念虑,就是“实”的,就会产生思虑纷扰。程颐主张用“主敬”的方式来克治思虑纷扰,认为如果心中无主,就如同“破屋中御寇”,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贼时,此心根本无暇应对,只能疲于奔命。这表明如果用一般克制思虑的方式,也即当一种念虑要生出时,便用此心去克制它,那另一种念虑又将生出,如此则只是徒劳损耗精神。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象上,而对象是繁多而瞬息万变的,用有限的精力去面对无限的外物,必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非对象性的工夫修养自身,不追逐于外在的事物,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根本觉解思虑纷扰。而程颐便提出了“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的方法,也即“主一”的工夫。程颐说:“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5]149所谓“主一”,是一种内心专注、醒觉、自觉的状态。这种专注是非对象性的,既非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一外在对象,否则便会流于“东西”“彼此”了;也非把注意力集中在某种思维对象的“一”之上,否则也变成了对象性的活动了。这里的“一”,是形容此心通过保持专注醒觉而达到精粹无杂的“纯一”状态,“主一”不是“主于一”(以“一”为对象),而是“主而一”(“一”形容此心精纯)。
程颐又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5]169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一”不是对象,而是形容此心之精纯。而“无适”正是此心不执著于事物、不指向对象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是“一”的状态。
然而光说这种“主一”,毕竟也有些难以把握,于是程颐用更简单的方式表明了如何能“主一”。他说:“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5]149“俨然正其衣冠,尊其胆视,其中自有个敬处。”[5]185这些提法绝不是说“敬”或者“主一”就是外在容貌衣冠的整齐严肃。程颐说:“严威俨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须自此入。”[5]170表明这种方法只是进行“主敬”的一项基础工夫和下手处。一个人若要时刻保持整齐严肃,必然要求此心时时处于醒觉的状态中,才能够时时检点自己。由此训练自己时时保持此心警觉,就是做主敬工夫的方式。程颐甚至还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于一也……敬其心,乃至不接视听,此学者之事也。”[5]154这就是从训练自己保持专注避免外界干扰以至于“不听不闻”来指导学者了。事实上,这只是由于直接进行“主敬”“主一”对初学者来说难以把握,于是程颐便从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指点人,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主一”本身。
四、“主敬”与“未发”
上文讨论了“敬(主一)”的内涵,但是,为何通过“敬(主一)”而能够“自是无非僻之奸”“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能够不受思虑纷扰呢?为何能够达到“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呢?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将此工夫放在程颐整个思想体系中才能明白。
程颐认为,在对象性的工夫中,心是追随在外物上的,所以必然随着与外物的交接而不断产生纷扰的思虑。而要超脱出与外物相对的被动境地,就要采取非对象性的工夫,也即“主敬”“主一”。这种工夫要求此心不追逐于任何事物上,不执著于对象,而是保持一种专注警觉的精纯心境。这种心境的特点,其实正与“未发”相一致。“未发”乃是一种“思虑未萌,事物未至”[9]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通过主敬达到的“一”是相同的。《二程遗书》记载程颐与苏季明的讨论:“或曰:‘先生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5]201-202直接谈“未发”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领会的,程颐认为可以先理会“敬”,做“主敬”的工夫,通过涵养就能够自然明白此境界。也即,“主敬”是把握和领会“未发”的工夫。程颐甚至说过:“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5]317主敬可以说正是一种克服“意必固我”的方式,而由此所要达致的境界,则是一种“未发”的心境。由此,一方面,此心便能超脱出与对象交接而产生的纷扰之中,能够达到心宁的安定。另一方面,程颐认为“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5]204,“恶”乃是“已发”后才产生的,此时此心尚未受外物的干扰,也就没有物欲,因而“恶”也无从产生,于是此心保持有一种纯善的本然状态。这其实就是“自然天理明”,所谓“明”,乃“彰明”之义,此心纯然之善便能昭彰无遗,这也便是“未发”作为“天下之大本”之义。
然而,“主敬”并非程颐工夫论的完结,他说:“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5]206这就清楚表明了“敬”的工夫主要在于“持己”,仅仅靠“敬”对于完整的道德实践来说尚不够的,因为“善”还未真正在现实的实践中表现出来,因此说“都无事”。要真正成就道德,还应当“集义”,应当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道德实践。而“集义”关涉着“格物穷理”,这就涉及到其他的工夫,此处不能详谈了。
五、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程颐的“主敬”思想对先秦以来儒家的“敬”论有着重大的改造。他把原有的对象性的“敬”改造成非对象性的“敬”,这种改造凸显了“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深化了这一工夫的理论内涵。而“主敬”的具体涵义则是“主一”,即不执著于对象,而是保持内心的醒觉专注,便能够达致“天下之大本”的“未发”状态,由此为实践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程颐曾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5]188“主敬”只是他修身思想的一部分,必须配合“致知”才能充分展现其作用。但是他对“敬”的工夫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形成完整的系统,因此对其独立进行探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虽然未能从整体上探究程颐的修身思想,但希望通过对他“主敬”思想的探讨,能够对更深入地研究其工夫论有所助益。
[1]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等.周易注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黎靖德.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7-208.
[5]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陈来.宋明理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1:114.
[8] 程颐.周易程氏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
[9] 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