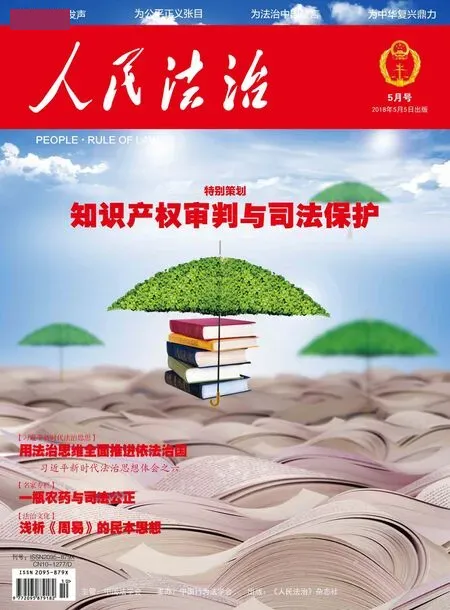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转换性使用理论研究
文/罗娇 严之

罗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博士

严之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转换性使用”理论对正确理解合理使用的范围具有重要价值,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实施应适当借鉴“转换性使用”理论,理性处理商业性使用、“挪用艺术”、文本与数据挖掘的著作权问题,正确界定新商业模式、新创作形式和新技术条件下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
合理使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著作权的权利边界,其适用范围的任何变化都可能重塑著作权法,正确界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平衡立法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是合理使用制度的重要命题。实践中往往辅以一定的标准来检验某一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否则,盲目扩张合理使用的范围将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抑制版权产业的开发和投资活力,进而“削弱著作权对开发创新性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转换性使用”作为近年来美国合理使用案件审判实践中主导理论,对合理使用范围的界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将为我国正确理解与适用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提供参考。
“转换性使用”范式的崛起
(一)合理使用及其“四因素”检验标准
合 理 使 用(fair use / fair dealing)是指既不需要著作权人许可,也不需要向其支付报酬的使用作品的行为。《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称TRIPs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国际条约均允许成员国规定包括合理使用在内的满足“三步检测法”(three-step test)的著作权限制与例外。
在合理使用的认定上,欧洲法系国家将所有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在其著作权立法中进行了具体、全面的列举,但缺乏检验某一特定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标准,法官难以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列举之外的行为进行认定;英国、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法与之类似,但会以判例法确定的原则作为法官审理个案时的合理使用检验标准。与它们不同,《美国版权法》对合理使用行为既有具体、全面的列举,也规定了概括性的检验标准。例如,其第107条规定了构成合理使用行为的概括性的检验标准;第108至112条,以及121至122条对某些构成合理使用的特定行为进行了列举,列举条款是概括性检验标准(第107条)的补充而非替代。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任何特定案件中判断对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应考虑的四个因素是:(1)使用的目的与特征,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营利的教学目的;(2)版权作品的性质;(3)所使用部分的质与量与作为整体的版权作品的关系;(4)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此检验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行为的概括性标准称为“四因素”。
(二)对“四因素”的肯定与批评
与列举性的封闭式的合理使用制度不同,以“四因素”为代表的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为作品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使用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因而逐渐被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采用。日本学者与我国学者也建议在本国著作权法中纳入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2011年我国发布的司法政策中,提倡将“四因素”作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检验标准。2014年6月我国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借鉴《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法”和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款“四因素”的基础上,打破了现行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行为的封闭式列举,将合理使用的检验标准列入著作权法中,构建了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使法官可根据新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与现行法相比具有明显进步。
以“四因素”为代表的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虽然为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作品使用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但其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长久以来广受诟病。有学者指出合理使用的判断因素似乎像童话般不现实,也有学者认为如此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善变多于合理”。立法实践中,有国家因担心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带来太多不确定性而拒绝将其引入本国的著作权立法中,如澳大利亚。司法实践中,也有法官指出以“四因素”为代表的合理使用的检验标准“灵活得相当于驳回了判决”,或认为以诸如“四因素”之类的抽象标准来检验个案的合理使用行为“是一种粗糙的公正”。
(三)“市场中心”范式的衰落与“转换性使用”范式的崛起
为了改善“四因素”适用的不确定性,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赋予“四因素”中的每个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来检验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并以此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进而增强“四因素”下合理使用制度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从近几十年的合理使用判决来看,美国法院主要采用了“市场中心”范式和“转换性使用”范式两种不同的“四因素”权重分配模式。
1.“市场中心”范式
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在“索尼案”中确立了以“四因素”中的第四因素,即“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检验合理使用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索尼案”中指出“对受版权保护材料的一切商业性使用都假定为不合理”,并在“Harper & Row Publishers诉Nation Enterprises”案中再次重申第四因素“毫无疑问是合理使用检验标准中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也在随后的“Acuff-Rose Music, Inc. 诉 Campbell” 案中认为,被告说唱组合对原告民谣的戏仿是为了盈利,不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在这些判决的影响下,使用的商业性似乎成了某一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的否定因素。自此,美国有关合理使用的司法实践中建立起了以市场损害为主导的合理使用检验标准,即“市场中心”范式。
2.“转换性使用”范式
“转换性使用”术语首创于1990年Leval法官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意在从转换性使用的角度对《美国版权法》第107条的合理使用“四因素”进行正确理解,从而避免过度的版权保护扼杀其他主体的创造力。Leval认为,合理使用制度最有活力之处在于它实现了版权法的最终目标——促进文化与创新,法官应当着重考虑版权法的功利目的,避免因版权保护的过度扩张而限制创新,而过分重视第四因素,即“市场中心”范式将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带来巨大危害,进而损害二次创新(secondary creativity),因为所有的合理使用案例中,都包含了某种市场损害,即作者将在某种程度上损失对原作品享有的版税。据此,Leval首次提出以“转换性使用”理论来检验合理使用行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4年的“Campbell”案中大量援引了Leval的观点,纠正了“索尼案”中“市场中心”范式的错误,在判决中采用“转换性使用”理论对戏仿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进行论证。“Campbe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综合考虑相关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转换性使用”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商业目的”因素:
“越具有转换性特征,其他因素(如商业主义)的意义就越小,这可能会影响合理使用的认定……当第二次使用是变革性的,市场替代至少较不确定,市场危害可能不那么容易推断”。
“Campbell”案的判决影响了美国法院后续一批有关合理使用的新判决,美国各个巡回法院纷纷将“转换性使用”作为合理使用认定的主要考虑因素,“转换性使用”范式也成为了美国司法实践中检验合理使用的主流理论。“Campbell”案自此被视为联邦最高法院最重要的有关合理使用的判例。
“转换性使用”范式的适用
Leval从版权法激励创作这一功利目的出发,将转换性使用定义为“必须是有生产力(productive)的、必须以与原作品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目的……是基于原始材料创造新的信息、新的审美、新的洞见和理解”。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分析“四因素”中的第一因素——“使用的目的与性质”开始,进行“转换性使用”分析。“Campbe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转换性使用”分析简化为“对作品的使用是否具有转换性”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转换性”。 “转换性使用”范式中,本文将前者称为定性分析,后者称为定量分析。
(一)“转换性使用”的定性分析
“转换性使用”范式中的定性分析,其目的在于阐明“转换性使用”与非“转换性使用”的区别,其司法适用的难点在于,是以“内容”的转换还是以“目的”的转换作为检验标准?以及“转换性使用”如何与演绎行为进行界分?
1.“内容”的转换抑或“目的”的转换
在早期的“Campbe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转换性使用”描述为“新作品是否基于更深远的目的或不同的性质而加入了新的东西,以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改变了原作品”。从这一表述看,“转换性使用”定性的关键在于二次使用与原作品相比,加入了新的“内容”,即实现了“内容”的转换。不过,有学者指出Cambell案对转换性使用的定义存在问题,因为它没有明确“转换内容”(transforming content)和“转换信息”(transforming message,即使用作品的目的)两个条件需具备其一,还是需同时具备,抑或需具有某种联系,才能构成转换性。
近年来的合理使用案例中,美国法院倾向支持一个更宽泛定义的“转换性使用”,即“转换性”(transformative)不仅包括对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对使用目的的转换。例如,在“Bill Graham Archives诉Dorling Kindersley Ltd.”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在摇滚乐队的人物传记中使用该乐队演唱会的海报,“具有优化传记信息的转换性目的,该目的区别于海报被创作时的审美与宣传之目的”,因此该使用行为具有转换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美国法院更加倾向以“目的”的转换而非“内容”的转换作为“转换性使用”定性的关键因素。当二次使用行为与原作品相比具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时,即使二次使用并没有加入任何新的“内容”,也可以构成“转换性使用”。例如,在“Perfect 10 诉 Amazon.com”案中,对于搜索引擎复制图像作为搜索时展示的缩略图,美国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原图是基于发挥娱乐、审美或信息功能而被创作,而搜索引擎将图像的功能转换成为用户指引信息来源”,因此也具有转换性。再如,“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对“谷歌图书”搜索引擎是否具有转换性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其认为搜索结果在目的、性质、表达、意义和信息方面是不同的,建立可全文搜索的数据库构成转换性使用。
美国法院以使用“目的”的转换作为“转换性使用”定性的关键,也与波斯纳的相关理论相契合。波斯纳认为,转换性(transformative)、生产性(productive)使用与复制性(reproductive)、替代性(superseding)使用不同,前者是指减少表达成本并因而倾向于增加原创性作品数量的使用,而后者只是增加了某一给定作品的复制件数量,减少了作者的总利润,并降低了有关创作作品的激励。对于转换性使用,即使复制者对原始作品本身并未增加任何东西,其对该作品的影响也可能是积极的。
2.是“转换性使用”还是演绎行为
区别转换与非转换的关键是使用“目的”的转换,而不仅仅是“内容”或“性质”的转换。明确这一点的意义还在于据此可以将转换性使用与对作品的演绎区别开来。否则,转换性使用过于宽泛的定义将严重损害著作权人享有的演绎权。
以“目的”的转换作为“转换性使用”定性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转换性使用”应当是具有新的、不同目的的使用,而不是有新的表达形式的使用;法院在认定转换性使用时,主要考虑使用是否具有新的目的,而不是是否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了字面上的修改。在二次使用行为与原作品“目的”相同的情况下,仅仅是“内容”“性质”或表达形式的转换,更倾向于被认定为演绎行为。例如,将小说拍成电影,或者对小说进行续写,可能与原作品的性质不同,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新故事,但它与原作品的目的是相同的——娱乐目的,因此它只是“内容”或“形式”上的转换,属于演绎行为,而非转换性使用。这一理念在“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指出,作品在内容或形式上的转换,是对作品的演绎;使用目的或功能上的转换,才是转换性使用所指的转换。Leval法官在该案判决中进一步阐明,演绎权控制的是将原作品的表达性内容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而谷歌的搜索和片段浏览功能所展示的信息非常有限,搜索人不能对原作品发生任何实质性阅读,因此不受演绎权控制。Leval法官同时认为,这与从音乐作品中截取一段作为手机铃声不同,后者是在乐曲中仔细筛选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一段,其目的是提供乐曲表达性内容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小片段,而不是提供信息。
(二)“转换性使用”的定量分析
将使用行为定性为具有“转换性”只是检验二次使用构成合理使用行为的起点,法院还需要评估转换的程度是否达到合理使用的要求,此即“转换性使用”范式的定量分析,其目的在于阐明二次使用行为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的“转换”,才能支持其构成合理使用。
1. 理论上的建议
在“Campbe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定量分析的原则性标准,即使用行为“越是转换性的就越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不过这一原则性标准对实践而言过于抽象、操作难度也较大,法院依然很难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系列通用的参数去评估哪些使用具有更多的转换性而哪些更少。对此,有学者提出,最好的办法是跳出概念分析的窠臼,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解决这一难题。具体言之,从转换性使用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估,评估使用行为带来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如果“使用越具有转换性,其对著作权人的市场损害则越小,而对社会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如降低交易成本或鼓励后续创新等方面的社会利益”。在方法上,可针对不同的情况,借助补偿法、替代法、减少交易成本理论、创新激励理论等经济方法进行分析,从而促进“转换性使用”范式在司法适用中保持一致性与可预测性。
2.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通常通过评估二次使用的“质”与“量”是否与“转换性使用”之目的相匹配,来对“转换性使用”进行定量分析。换言之,在“转换性使用”范式下,法院检验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行为时,首先考虑该行为是否具有转换性使用目的,其次考虑该行为对原作品使用的“质”与“量”是否超出了实现转换性使用目的所需的“质”与“量”。对于后者,在近期“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采用了“竞争性替代”方法进行评估。
“竞争性替代”方法可追溯到第七巡回法院判决的“Ty, Inc.诉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td.”一案。该案判决以鲜活的例子说明了何谓“竞争性替代”——“复制是补充原作品的,正如钉子是锤子的补充那样,构成合理使用;复制是替代原作品的,正如钉子(nails)是图钉(pegs)或螺丝(screws)的替代那样,则不构成合理使用”。以“竞争性替代”方法对“转换性使用”进行定量分析意味着,转换的程度应达到使用的结果不构成对原作品的竞争性替代,相应的转换性使用行为才能构成合理使用行为。具体到“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中,Leval法院是从“谷歌图书”搜索引擎中有关片段浏览功能的六大使用政策来分析使用行为是否对原作品构成“竞争性替代”:(1)原告的图书每页按行划分为8个片段;(2)每10页中有1页被列入黑名单永久地排除于片段浏览之外,约占一本书的22%;(3)同一关键词无论搜索多少次或在多少台不同的计算机上搜索显示的总是同样的片段,剩下78%的文本在事实上也不能获取;(4)片段是不连续的、分散的,即使通过多个关键词反复多次搜索,也无法获取超过16%的文本;(5)对于通过片段浏览即可满足搜索者购买需求的特殊作品,如词典、食谱、诗歌等,不提供片段浏览功能;(6)作品的权利人可在线申请取消片段浏览权。这些政策证明了搜索者即使经过长期努力也不能使片段浏览结果成为原告图书的竞争性替代品,因此谷歌的片段浏览功能并不构成对原告图书的竞争性替代,属于合理使用。
(三)“转化性使用”与“四因素”的适用关系
“转换性使用”范式并不否定或取代合理使用判断的“四因素”,美国有关合理使用案件的司法判决仍然以“四因素”分析作为检验合理使用的基础。“转换性使用”范式所影响的,只是法院分析“四因素”时的具体方法。
其一,转换性使用是合理使用成立的充分非必要条件。转换性使用通过传达新的、不同于原作品的信息,或通过扩展原作品的功能,而服务于版权法扩充社会知识总量的立法目标,因此对合理使用成立具有重要的说服力。“Campbell”案的判决中因此指出,“版权法以促进科技和艺术发展为目的,这一目的通常由转换性作品的创作加以推动……这样的作品在版权制度下,处于由合理使用原则所保障的呼吸空间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转换性使用”完全等同于合理使用,可以替代《美国版权法》第107条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的“四因素”。“转换性使用”理论的首创者Leval也在“作家协会诉谷歌”案的判决中也阐明,转换性使用不是合理使用成立的绝对必要条件,而是支持合理使用认定的因素之一;“转换性”这一术语不能被僵硬地作为理解合理使用要素的全部线索,而是对合理使用的评估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其二,转换性使用影响合理使用“四因素”的权重。认定合理使用时,如果把《美国版权法》107条规定的“四因素”视为各自独立、缺一不可的构成要件,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因素(1)与(2)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因素(4)未能区分“因批评导致的市场损害”和“因搭便车导致的市场损害”,只有因素(3)是符合经济学方向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误导性的。联邦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判决中也明确指出,第107条的“四因素”并非相互独立、缺一不可的要件,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应全面综合“四因素”逐案分析。事实上,“转换性使用”范式并不否定或取代“四因素”,而是影响“四因素”中各个因素的权重。如前所述,受“索尼案”、“Harper& Row案”影响的早期的合理使用判例中,美国法院赋予了“四因素”中的第四因素较大权重,即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者价值所产生的影响被认为是“四因素”中最重要的。据学者统计,1978年到2005年美国法院超过300份的合理使用判决中因素(4)的权重占比最大。但从2005年开始,“转换性使用”范式便占据了美国合理使用判例中的主导地位, “四因素”中的第一因素,即使用的目的与性质作为“转换性使用”分析的基础,在多个案例中其权重超过了第四因素。Laval法官也因此感慨,合理使用制度的灵魂在于第一因素,而第一因素的判断取决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转换性。在“转换性使用”范式的影响下,使用行为即使不满足第四因素,即使用行为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存在影响,但只要这种影响并不是“竞争性替代”的影响,仍可以被认定为构成合理使用。
“转换性使用”范式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启示
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看,以“转换性使用”范式为基础的著作权合理使用检验标准,至少可以为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界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带来以下启示。
(一)对商业性使用持宽容态度
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7条规定,对于“四因素”中的第一因素,即使用的目的与特征,法院需考察的事实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营利的教学目的”。由于第一因素特别强调了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美国法院在早期的判决中,商业性使用通常都假定为不构成合理使用。但以使用具有商业性来否定合理使用,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商业与非商业并没有明确定义,二者之间的划分也并不明晰,甚至很多使用行为界于二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其二,某些商业性使用因创造新产品或降低成本而对社会有益,其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版权人所遭受的版税损失。
在“转换性使用”范式下,使用具有商业性质并不能直接否定该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相反,应结合使用行为的特定背景进行判断——当商业使用行为通过其产品或实质性投资创造了教育或其他方面的社会效益时,法院应当倾向于支持其合理使用抗辩,而忽略其使用的商业性质。以“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为例,谷歌公司与“谷歌图书”项目虽然具有商业性质,但其大大便利了版权作品的使用:一方面,它大幅降低了终端用户合理使用版权作品的成本;另一方面,终端用户可以通过谷歌图书搜索引擎提供的链接,根据搜索结果购买其所需的图书,也扩展了图书本身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更何况,开发类似于“谷歌图书”等革新作品使用模式的项目,需要耗费大量的投资,并需要承担较大的市场失败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商业性使用持宽容态度,为能够带来明显社会利益的商业使用行为提供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空间,从而激励商业实体进行昂贵且有风险的投资,降低终端用户对版权作品使用的成本、提升版权作品使用效率。
(二)对“挪用艺术”持开放态度
“挪用艺术”(appropriation art),是指将现存作品的艺术形象或元素直接运用到新作品之中的一种艺术形式。简单来说,是通过将原作品中的艺术元素从原来的背景中“挖”走,放置到不同的背景、语境中来进行艺术创作。
美国第二巡回法院2006年的“Blanch”案,是将“挪用艺术”认定为合理使用的典型判决。“Blanch”案中,“挪用艺术”家Jeff Koons在其创作的一幅名为“尼亚加拉”(Niagara)的作品中采用了摄影人Andrea Blanch拍摄的照片。Blanch的照片描绘了一条女青年的小腿和穿着一双闪闪发光的Gucci凉鞋、脚趾涂着青铜指甲油的足部,她靠在一个男人的臂膀里休息。Koons“挪用”了Blanch照片中女青年的小腿和足部,去掉了照片中的男人臂膀等背景,然后将女青年脚掌的方向从45度角改为垂直倒置,在一只脚上添加了鞋跟,并修改了照片的着色。照片被包含在Koons的绘画中,与其他三双脚和小腿一起悬在有糖果图像、草地和尼亚加拉瀑布的背景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首先,Koons的使用与Blanch最初创作照片的目的不同,Blanch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创作了她的照片,而Koons则将其中的图像作为德国博物馆大型绘画的一部分,Koons的使用具有“转换性目的”。其次,Koons只从原始照片中取走了小腿、脚掌和凉鞋,排除了照片的背景和其他很多属于Blanch的创造性元素,其所使用的数量与“转换性目的”相符。综上,第二巡回法院运用“转换性使用”理论支持了Koons的“挪用艺术”属于合理使用行为。
美国法院从“转换性使用”的角度支持“挪用艺术”属于合理使用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这一后现代艺术创新形式获得了生存空间。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人小说”著作权纠纷,其著作权争议的实质与“挪用艺术”引发的著作权纠纷非常类似。当法律并未明确列举这一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借鉴“转换性使用”理论,根据个案情况来具体判断“同人小说”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在司法审判中运用“转换性使用”理论,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包括“同人小说”在内的“挪用艺术”这类创作形式,将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创作自由与文化权利,对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文本与数据挖掘持支持态度
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以下简称TDM),即利用自动分析技术分析文本与数据的模式、趋势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从文本或数据中导出或组织信息的过程。在信息暴增的大数据环境下,TDM技术可减少人类阅读时间的80%并且提升数据管理50%的效率,对提高科研效率、加速科学发现、促进科研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有望改变生活方式的TDM技术正受到市场失灵、法律不确定性以及信息孤岛的严重阻碍。由于TDM通常以对包括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在内的材料或数据进行大规模、系统性复制为前提,复杂著作权、数据库权及其许可协议所产生的法律不确定性,是其面临的最显著的法律障碍。
针对TDM面临的著作权问题,国际上采用了政策声明、联合宣言、著作权立法、司法判例等多种方式支持TDM的发展与适用。其中,美国是以司法个案的形式支持TDM技术的典型代表。自2003年以来,美国法院在多个判决中支持了TDM属于合理使用,以司法判例的形式解决TDM面临的著作权问题。这些案例中,美国法院运用“转换性使用”理论,强调了TDM的“转换性使用”目的,判定TDM所需的大规模、全文性复制行为,以及商业性质的TDM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虽暂未遇到有关TDM的著作权纠纷,但仍然值得借鉴“转换性使用”理论的相关理念,充分支持TDM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在著作权上为大数据环境下,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趋势的信息利用模式的变革创造空间。
结论
正如两百年前艾伦巴洛勋爵所言,“尽管我坚信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自己的著作权,但是人们不可以给科学戴上脚铐。”知识产权的设立,不只是为了补偿创作者的努力,更是为了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而著作权的本质,在于促进学习,而不是养富出版商。任何过度的保护都不会给著作权人带来额外的创新激励,法院应当直视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确保版权保护不会太过于扩张以致扼杀了创新。合理使用制度作为限制著作权保护盲目扩张的核心制度,对保护二次创新(secondary creativity)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属于“封闭式列举”,其僵硬性与滞后性对我国容纳新技术条件带来的新的信息利用方式带来了一定障碍。因此,我国在近年来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借鉴《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法”构建了灵活性的合理使用制度,司法政策中也提倡将“四因素”作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检验标准,为新技术条件下对作品的新型使用行为提供了空间,具有明显进步。然而不能忽视的是,1976年写入《美国版权法》的“四因素”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在适用时需要同时借鉴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转换性使用”理论,才能正确理解和界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增强灵活性合理使用制度的可预测性,既要避免因合理使用的范围过窄而遏制二次创新,也要避免因合理使用范围过宽而损害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激励。
--评《版权法之困境与出路:以文化多样性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