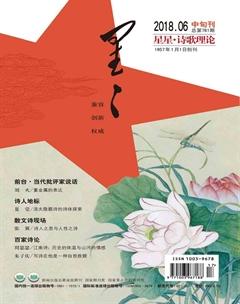洛夫隐题诗的诗体探索
夏莹
一、隐题诗的创作动机
当我们谈到诗魔洛夫——这位当代深具实验精神与创造性的诗人时,往往不能忽视《石室之死亡》(1965年)、《漂木》(2001年)等名篇巨制:“在现当代汉诗发展史上,《石室之死亡》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1];“《漂木》遂成就了其一次总结性的形而上建构及对生命全方位的诗性探求”[2]。诚然,洛夫其孤绝、雄浑的诗风,险峻的句法、爆破式的意象、富于歧义的诗行、虚实相生的惊奇感[3],都成为这位点石成金的“语言魔术师”之个性标签。而当被问及自认为创作中个人特色或独创之举体现在哪些方面时,洛夫却这样说道:
首先是历史题材的化用,我写得较早,像《长恨歌》《与李贺共饮》,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再一个就是隐题诗,算是我的创举吧。[4]
洛夫作隐题诗,始于1991年。据其在1992年的《隐题诗形构的探索》一文中回忆,多年前读到清史稿中一首叫《天地会反清复明诗》的藏头诗,是雍乾年间清红帮反抗满族入侵的宣传品。由此,洛夫想到:
当时帮会徒众和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故这类诗的造句与设譬都极粗俗,毫无艺术风格与价值可言,但这种藏头形式是否可注入饱满的诗素而创作出富于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来?不料这一反思竟诱发了我试写隐题诗的浓厚兴趣。[5]
这样,第一首隐题诗《我在腹内喂养一只毒蛊》便于1991年诞生了。此诗发表在《创世纪》第八十四期,当时洛夫因为“没有一位读者看出这首诗的诡异之处,我为竟无一人探知其中的隐秘而暗喜不已”[6]。其后,洛夫写隐题诗的冲动便一发而不可收,一年内完成了45首,并在1993年出版了诗集《隐题诗》(台北:尔雅出版公司)。1996年,洛夫又作隐题诗一首《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后收入诗集《雪落无声》(台北:尔雅出版公司,1999)。
二、同中之异:藏头诗与隐题诗
上已论及洛夫是受藏头诗的启发,创作了隐题诗。那么,藏头诗与隐题诗有何异同呢?
从诗体构成上看,藏头诗与隐题诗是相似的。它们都在诗句中隐藏了一些信息,而这些被隐藏的信息组合起来往往是作者意思所在。例如,《水浒传》中吴用在卢俊义家墙上题的藏头反诗:
芦花丛中一扁舟,
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难可无忧。[7]
诗的内容看似平淡,但其诗关键信息“芦俊义反”就隐藏于每句首字。同理,洛夫在其《隐题诗》集首,奉上的是《给琼芳》:
你兜着一裙子的鲜花从树林中悄悄走来
是准备去赴春天的约会?
我则面如败叶,发若秋草
惟年輪仍紧绕着你不停地旋转
一如往昔,安静地守着岁月的成熟
的确我已感知
爱的果实,无声而甜美[8]
这是一首写给妻子陈琼芳的隐题诗。初看,诗作呈现出安静中包含动态、甜美里带有沧桑之感,但经点出为隐题诗后,就能发现此诗隐藏的信息是诗人的深情表白:“你是我惟一的爱”[9] 。
尽管藏头诗与隐题诗有诗体上的相似之处,但是洛夫却给了他的诗一个全新的命名,“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10],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异大于同。
首先,中国古代藏头诗至少包含三种形式,隐题诗只是藏头诗的其中一种。另一种是“意在言不在”式的藏头。明代梁桥《冰川诗式》已经指出过:“藏头格,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离之景与情,而不言题意,至结联方说题之意,是谓藏头。”[11]第三种是每句头字皆藏于上句尾字的藏头 。[12]
其次,就创作动机和诗思方式来看,古代藏头诗多为笔墨游戏(其他如宝塔诗、回文诗等),也有某些利用这种不易被发现的方式传递秘密信息之用,因而不少藏头诗的艺术性不敢恭维。而洛夫写隐题诗,更多则是为了借古代藏头诗的形构,来进行尝试性质的改造:
我设想中的隐题诗,与前人所创仅有实用价值的藏头诗大异其趣;它是一种在美学思考的范畴内所创设而在形式上又自身具足的新诗型。它具有诗的充足条件,符合既定的美学原理,但又超乎绳墨之外,故有时不免对约定俗成的语法语式有所破坏,甚至破坏成了它的特色。[13]
如果说古人的藏头诗,是出于遵循某种“游戏规则”或保障“信息安全”的需要——这仍是对于既定写作秩序的维护;那么洛夫作隐题诗,就是在原有“地基”之上另造楼宇——他的创作目的是挑战秩序、推陈出新,其诗思方式是美学的、现代的。
再次,从诗体上看,藏头诗未能脱离格律体;而隐题诗则除了预设的句子采用藏头形式外,其余部分仍采用自由体,仍保留了较多可供诗人发挥、激荡的空间。可以说,隐题诗继承了藏头诗的某些诗体形式,却生发出超越原形式的创造性力量。这一点,将在下节详细展开。
三、隐题诗:诗体的继承与超越
隐题诗存在预设限制,这会不会增加诗人写作的自缚之感?但凡是重视诗体探索的诗人,又有谁会觉得“带着镣铐跳舞”毫无意义呢?
吴兴华对诗歌形式的论断相当精辟:“所谓‘自然和‘不受拘束是不能独自存在的;非得有了规律,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了规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们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表演”,“形式仿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公有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就都是作者的了”,“固定的形式在这里,我觉得,就显露出它的优点。当你练习纯熟以后,你的思想涌起时,常常会自己落在一个恰好的形式里,以致一点不自然的扭曲情形都看不出来”[14]。这篇发表于1956年台湾《文学杂志》的文章,既是对民国时期众多探索诗体形式诗人之观念的总括,也影响了其后台湾诗界对于古典诗学资源的勘探[15] 。
比如十四行诗,这种来自意大利的格律体诗,在民国众多诗人手中得到了异国的改造。孙大雨、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柳无忌、梁宗岱、罗念生、曹葆华、吴兴华等都在十四行诗体上进行过探索[16]。而对于中国本土诗体资源的继承与改造上,有朱湘对民间歌谣的吸收(如《采莲曲》),有吴兴华、林庚对绝句诗体的新写(如吴兴华《绝句四首》、林庚《四月》),也有鲁迅偶尔为之的宝塔诗《兵》;但是这些对中国古典诗歌体式的继承和改造,却没有产生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诗。卞之琳对吴兴华的“化古”有些许遗憾:“不论‘化古‘化洋,吴诗辞藻富丽而未能多赋予新活力,意境深邃而未能多吹进新气息……似乎在一般场合终有点‘入而未能‘出”[17]。戴望舒这样评价林庚的诗:“现代的诗歌之所以与旧诗词不同者,是在于它们的形式,更在于它们的内容。结构、字汇、表现方式、语法等是属于前者的;题材、情感、思想等是属于后者的;这两者和时代之完全的调和之下的诗才是新诗。而林庚的‘四行诗却并不如此,他只是拿白话写着古诗而已”[18]。这其间,除了“新瓶”与“旧酒”之间的争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诗人没有在中国古典诗体资源中,找到合适的现代诗之“容器”。以此观念再回顾洛夫的隐题诗,我们发现,隐题诗居然在中国古典诗体资源与现代诗中找到了可以成立的平衡点。表现有二:
其一,隐题诗的预设性,在节制为诗与开启诗语机能中找到了平衡。洛夫作隐题诗,虽然也历经了惊险迭起的“寻句”困境,诗人还是非常肯定“节制”为创作带来的“爆发”力量:
语言受一点限制也许更能产生诗的凝聚力。自脱去旧诗格律的重重束缚之后,新诗从未形成基于学理的章法,才气纵横者笔下天马行空,犹能自成格局,但有更多的诗人任笔为体,漫无节制,而一般效尤者便认为写诗乃可任性而行,从不顾及语言的尊严。隐题诗之设限,即是针对这一缺失,强迫诗人学习如何自律,如何尊重语言对人类文化所提供的价值。惟有重视语言的机能,才能跳出语言的有限性,掌握诗的无限性。
在受限的情况下,诗人只能想方设法打破自己熟悉的造句方式,去语言自身中寻求解决之道;在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甚至篇章之间寻找和谐的构成法。例如《我在腹内喂养一只毒蛊》:
我与众神对话通常都
在语言消灭之后
腹大如盆其中显然盘踞一个不怀好意的胚胎
内部的骚动预示另一次龙蛇惊变的险局
喂之以精血,以火,而隔壁有人开始惨叫
养在白纸上的意象蠕动亦如满池的鱼卵
一经孵化水面便升起初荷的灿然一笑
只只从鳞到骨却又充塞着生之恓惶
毒蛇过了秋天居然有了笑意,而
蛊,依旧是我的最爱[19]
“在语言消灭之后”才有了与神对话的机遇。这里的“语言”应不是指日常语言,而是经过构思与裁剪的精心设计过的语言,比如古代用来与天神沟通的祷辞,更暗指诗的语言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然而,在与“众神”的对话中,诗人腹中却“盘踞一个不怀好意的胚胎”——这也符合洛夫曲折其意的一贯诗风。从“胚胎”“龙蛇”“鱼卵”“鳞”“骨”“毒蛇”等一系列腾挪嬗变,最终到“蛊”;再通过“骚动”“惊变”“险局”“蠕动”“孵化”等充满紧张感与张力的动词,精彩地将“蛊”的诞生演绎出。蛊乃毒虫之首,历经生死争斗而出;蛊又有蛊惑与神秘之感:诗人的创作过程难道不是艰险的“孵化”过程?带有异质性、反叛性的现代主义诗歌难道不是摄人心魄的神秘魅惑之物?这首诗没有明说其意旨,却句句言在其中。词与词的遥相呼应,句与句在语言上跳跃又在意涵上勾连,完全没有因隐题诗的限制而捉襟见肘的窘困,可见诗魔卓越的语言操纵力。
然而,也不是任何时候诗人都可以妙手天成、任意为诗。洛夫曾说他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王维)》这首诗时,一时停滞不前:
行色匆匆却不知前往何处
到了路的尽头耳边响起破鞋与河的对话
水中他看到一幅倾斜的脸
穷困如跳蚤
处处咬人
坐在河岸思索一个陌生的句子
看着另一个句子在激流中逐渐成熟
云从发髻上飘过
起风
时,鱼群争食他的倒影[20]
诗人写到“穷处”二字时,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经其再三斟酌,终闪出“穷困如跳蚤”这句,也因而有了衔接完美的下句“处处咬人”。若没有隐题诗诗体上的限制,这偶得的警句也怕难以跳出。洛夫也得趣于这种被预设的定点所牵制带来的张力:“这种语言形同放风筝;风筝系于长绳的一端,飘然而升,在天空御风翱翔,自由而美妙,另一端却被牢牢地抓在手中,不致被风吹走。”[21]而偶发状态下迸发出的创造性,也令洛夫认为这些诗句“快捷有如神助”:
飞,有时是超越的必要手段,入土
之后你将见到
蝶群从千冢中翩跹而出
——《我什么也没有说 诗早就在那里 我只不过把语字排成欲飞之蝶》
花的伤痛从蕊开始,泪
溅湿不了
泪中的火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赠杜甫)》
饲一尾月亮在水中原是李白的主意
金光粼粼中
鱼和诗人相濡以沫
——《杯底不可饲金鱼 与尔同消万古愁》
其二,隐题诗自由体的包容性,在古典意象与现代诗艺中达成了平衡。由于没有格律限制,隐题诗实属半自由体,其可变性远远大于十四行体或者中国古代格律诗。可供发挥的空间甚多,因而诗可容纳的世界与观念就全靠诗人的诗艺呈现了。如这首《说她是水,她又耕成了田 说她是蛇,她又飞成了鹰》:
说话是一种女性毒瘤,我不是指
她的谈吐,而
是她那
水兽般滑溜的舌头
她在五行中其实属土
又不甘一生陷于泥淖而任男人深深浅浅地
耕种。据说世上种种切切都是她虚构的
成果
了却尘缘的唯一办法是在她的
田里种一畦罂粟
说着说着
她一转身又换了一幅脸,下一回
是什么谁也无法預知
蛇苏醒后脱下一件贴肉的内衣借给
她,于是
又有了一次血肉模糊的经验
飞翔距死亡最近,她
成为燃点成为风暴成为雪崩都有可能
了却尘缘的另一个办法是:心随
鹰扬[22]
此诗题脱胎于洛夫诗集《葬我于雪》(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中的《论女人》。《论女人》一诗颇有点亚历山大·蒲柏《人论》的意味:“既非雨又非花/既非雾又非画”“有时名词有时动词”“有时深渊有时浅沼”,却不及《人论》里对人之生存境遇的反讽式思考。而在这首隐题诗中,女人的属性细节得到了强化:女人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而她有“水兽般滑溜的舌头”;女人在《周易》中属坤卦,坤乃土、乃大地,因而可以被“耕种”;女人的祖先是夏娃,因而会被蛇诱惑,因而“蛇苏醒后脱下一件贴肉的内衣”。洛夫接连化用了三处中西典故,自然地点出了女人柔婉中自有变数的属性。甚至在诗的最后一节,“她一转身又换了一幅脸,下一回/是什么谁也无法预知”“于是/又有了一次血肉模糊的经验”这两句,表面上看,是写女人善变,但往深里想,这“换了一幅脸”不是指转世轮回吗?“血肉模糊的经验”不是指重新降生于世的撕扯,以及女性赋予新生命时的苦痛吗。这些带有传统意味的素材,经洛夫的点化,却具有了新的意味。而诗中“毒瘤”“罂粟”“蛇”等意象,迥异于古典诗歌中常出现的花意象、云意象,而带有了神秘、妖异的张力。尤其是最后她“成为燃点成为风暴成为雪崩都有可能/了却尘缘的另一个办法是:心随/鹰扬”一句,铺排的紧密节奏加上“燃点”“风暴”“雪崩”等意象,顿生重重危急感;而“心随/鹰扬”节奏又霎时舒缓,给人如同彻底放飞的释放感,一张一弛之间,极富感染力。
四、余论
尽管洛夫隐题诗中有不少精妙之制,但是也要看到隐题诗有时难度过大,而让洛夫这样的斫轮老手也自感力有不逮。比如含有虚词的题,如“了”“之”“的”等,为了照顾诗体结构,而不得不采用看起来很没有必要的跨行:“说书人脸色乍变手心捏/了一把冷汗”(《井的暧昧身世 绣花鞋说了一半 青苔说了另一半》),“尘土之外,无一物可资取暖”(《你是传说中那半截蜡烛 另一半已在灰尘之外》),“花萎于泥本是前世注定的一场劫数”(《我不懂荷花的升起 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再比如一些无法拆分的词语,如“蚯蚓”“咖啡”等,硬要用跨行法拆开,或是重新编一句都显得生硬:“蚯/蚓饱食泥土的忧郁”(《蚯蚓一节节丈量大地的悲情》),“咖啡匙以金属的执拗把一杯咖/啡搅得魂飞魄散”(《咖啡豆喊着:我好命苦 说完便跳进一口黑井》)。洛夫也认为这些生硬的“败笔”,不足为训。毕竟,对于诗体的建构,洛夫曾言:“诗的结构主要是一种‘情感结构,是情、思融合产生的有秩序的流动,也是一种韵律或节奏结构;写诗不能拘泥于语言间的机械关系,而要追求气势的统一、节奏的和谐以及内在生命的完整,即有机结构。与其要一首结构上起承转合却缺乏兴味的诗,我宁取一首结构上稍欠圆整而有饱满情趣与深致的诗。”
隐题诗是洛夫对于中国古代藏头诗诗体的继承,更是挑战秩序、推陈出新的美学超越。隐题诗则除了预设的句子采用藏头形式外,其余部分仍采用自由体,保留了较多可供诗人发挥、激荡的空间;其预设性,在节制为诗与开启诗语机能中找到了平衡;其自由体的包容性,在古典意象与现代诗艺中达成了共识。隐题诗体之创作有其自身的难度,因而也获得后来人的瞩目及诗艺上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郑慧如. 形式与意蕴的织染:重读洛夫《石室之死亡》[J]. 江汉学术,2016(1).
[2]沈奇,孙金燕. 生命仪式的向晚仰瞻——洛夫长诗《漂木》散论[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2).
[3]郑慧如. 洛夫诗的偶发因素[J]. 当代诗学,2006(2).
[4]朱立立. 关于中国现代诗的对话与潜对话──秋日访洛夫[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5]洛夫. 隐题诗形构的探索[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8-59.
[6]洛夫. 隐题诗形构的探索[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0.
[7]孙晓琴,魏薇,董玉芝. 追本溯源 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与鉴赏[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47.
[8]洛夫. 给琼芳[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7.
[9]2014年11月7日,江汉大学特聘洛夫先生为荣誉驻校诗人。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为洛夫先生和陳琼芳女士准备了洛夫诗歌朗诵会,先生更是诵读了三十多年前赠给太太的情诗《因为风的缘故》。而今,诗魔已逝,读此诗句却仍感其伉俪情深和诗意的永恒。
[10]郑慧如. 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以“超现实”在台湾诗歌中的流变为例[J]. 江汉学术,2014(3).
[11]杨柳. 语言中的游戏乐趣——藏头诗[M]// 于根元. 新编语言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420.
[12]对于这两种藏头方式的详细介绍,可见钟意菁. “藏头”露尾,一字千金——趣说“藏头诗”[J]. 中文自修,2014(28).
[13]洛夫. 隐题诗形构的探索[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9.
[14]梁文星(吴兴华). 现在的新诗[M]// 刘守宜. 中国文学评论:第2册[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147-148.
[15]张桃洲.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4).
[16]关于十四行诗的论述,可详见:许霆. 中国十四行诗史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7]卞之琳.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M]//卞之琳文集:中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92.
[18]戴望舒.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M]// 戴望舒诗文选:全本.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210.
[19]洛夫. 我在腹内喂养一只毒蛊[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7.
[20]洛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王维)[M]//洛夫诗全集:下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7.
[21]洛夫. 隐题诗形构的探索[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4.
[22]洛夫. 说她是水,她又耕成了田 说她是蛇,她又飞成了鹰[M]//洛夫诗全集:下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