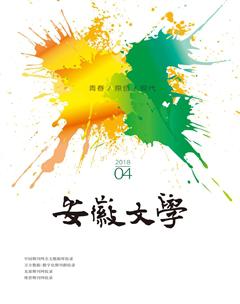金和诗歌中的穷苦描写和意象表达
钟翌晨
摘 要: 金和一生漂泊四方,避乱全椒、乞食泰州、南下广粤,过着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种漂泊感、孤独感、沧桑感始终围绕着他的人生。本文从金和生平及其诗集《秋蟪吟馆诗钞》出发,探讨金和笔下的穷苦诗歌类型,以及此类诗歌中的常用意象群,浅析金和的人生际遇和情感表达,及其作为末世文人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秋蟪吟馆诗钞 金和 穷苦 意象
一、金和的奔波流离
金和(1818-1885)字弓叔,江苏上元人,晚清著名诗人。嘉庆二十三年出生于安徽全椒县,其六世族金抱一曾为顺治六年的武状元,始定居上元。高祖金汉元,官至云南武定知府。曾祖金球是康熙年间的武进士。祖、父二代,皆未进仕,其父多年云游四方,金和自幼跟母亲住在外祖全椒县的吴氏族宅。[1]496全椒吴氏在明清之际为当地名门望族,书香世家,金和自幼跟随母亲吴氏习读诗书,且少小聪颖、苦学不辍。
金和成长于大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前期,他的人生以癸丑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童年至青少年阶段,金和父亲多年云游在外,母亲则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在生活上,对金和关怀备至;在学业上,更是严厉督促他求学上进。道光十八年,金和以优秀诸生被推选到惜阴书院就读,跟随当时的名儒薛时雨研习经史词赋,苦练八股文章,时人所称赞的 “白门四隽”,金和便位列其中。道光二十二年,金和目睹英军围攻金陵,清军不作为及清政府苟且求和,签订《南京条约》,血气方刚的金和愤恨写下千余首诗,爱国情怀和针砭时弊的诗歌内容充分体现了一个血性青年对社会弊端指责及民生疾苦的关切。
咸丰三年,太平军破金陵城,金和全家深陷危难。面对气焰汹汹的太平军,金和表现出非同常人的勇谋,“衣短后衣,与贼兵时轰饮,醉则杂卧酒甕侧向尔汝,因此颇探悉贼情,久之,遂与结纳”。[1]447了解太平军的内部情况后,金和只身出城向江南大营向荣进言献策,满怀期待的金和却未曾料想,自己赌上身家性命的冒险举动,非但未受到重视,反而遭到猜忌。此后,金和颠簸于大江南北,开启了后半世的流寓生活。其后期的流寓生活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江南地区四处乞食时期;其二,南下潮粤避难时期。
逃离金陵之后,金和携带家眷避难全椒。咸丰四年至十年,金和先后于泰州、清河、松江为馆,幕僚于常州,避难江北、东壩,辗转四处,饱受离苦。其诗歌记录了他匆忙的脚印,离开全椒赴馆泰州之时,写下《过扬州》《自姜堰抵泰州城》《晚渡邵伯湖》《晓发句容》《宿新丰》《过江浦》。离开松江之时,又写下《大风雨泊舟》《次日风雨更甚舟不能发》《舟次夜饮》等,从这些诗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路漂泊、一路歌吟的金和。
咸丰十年,金和受陆子岷之邀前往粤东,于是金和举家南移,先后于高明、潮州为幕府。此年间,他将人生阅历都赋予长篇歌行诗《兰陵女儿行》《丁烈女传》,赞陕西妇死节,不愿乞食而独活,自嘲难以与之相比。光绪三年,应唐景星之聘,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此后至光绪十一年,寓居上海,直至去世。
金和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他的足迹是不规则的流浪,他在这一动荡的生涯之中,将其所见、所感都化为凝练的文学,流传于后世。“文果载心,余心有寄”[2]287应是诗人笔耕不辍的希望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江湖之上,独有诗篇温暖他、陪伴他,不仅记录下他生活的轨迹,承载了诗人的凝愁孤苦,更传递了金和的精神。
二、穷苦描写的类型
金和生活在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外有列强侵占国土虎视眈眈,内有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国不泰而民不安,生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战乱带来的动荡不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也摧残着像金和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绪使他竭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献計献策得不到赏识,救国救民又不得其法。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下,金和用诗歌文字真实地描绘了一幅时代画卷,用极其辛辣的讽刺描述自己的所经所感。金和诗歌创作涉及广阔,既有爱国立场反对侵略之作,也有对清军内部腐败的揭露;既有天灾带来的民生疾苦,也有人祸造成的战火纷争;还有个人逃命于天地之间的疲于奔命之感,以及羁旅漂泊的思乡怀亲之痛。
(一)诗中之难
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金和之诗作 “得此而清之诗史不为廖寂也已”,[1]454堪称“诗史”。金和的人生经历就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爱国之热忱与忧民之悲恸化作笔端的波澜,乘兴而作,感时而发。简而言之,金和诗中之“难”主要源于天灾和人祸。
道光二十八年的大水灾持续了半年之久,此年正月时,金和有诗《正月二十九日作》:“谁知元日来,雨师忽叱驭。愁霖兼三旬,红日不掌曙。”灾难一直泛滥到六月,七月骄阳似火,诗人提笔挥毫《喜晴诗》:“比来廿余年,七次水灾吊……饿夫路相属,藁葬杂老少。”水灾肆虐,百姓遭殃,朝廷不仅不赈济灾民,还要收取租掉,全然不顾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倘再三日雨,屋角将擎漂。倘再五日雨,长街将垂钓。倘再十日雨,广野将飞艞。”诗人连用三个“倘再”,细致地描写了这场灾难之严重,农民之苦难,为百姓奔走呼喊,可唯独缺少这样任能选贤的君主解百姓于倒悬之中。同年八月,水患刚去,寒潮来袭,诗人像少陵野老般高歌《破屋行》,将救苦救难的希望寄托在佛祖身上,这表明诗人对统治阶级的昏庸和冷漠已感到失望。“饿死只合从空山,冻死都教在行路”在逃离苦难的路途中,依旧被苦难所吞噬,接二连三的灾难对人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金和诗中多次记录这场持续的灾难“人犹期稻熟,天又遣蝗知”,连绵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在金和笔下句句血泪。
如果说天灾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祸带给人民的负担与痛苦更剧于灾难,人祸主要源于战争和阶级压迫。在金和的诗歌中,有许多同情底层人民的诗歌,对高利贷剥削控诉的《印子钱》,对童养媳悲惨遭遇的怜悯的《苜蓿头》,可怜的女子被卖作童养媳后,被人弃之如猪狗,稍不称主人心便会遭到鞭打的皮肉之苦。再如《弃妇篇》,以弃妇的口吻道被无情郎抛弃后的心酸,追忆往昔之美好与现状之凄苦,使人闻之黯然泣下,颇有《诗经·氓》的痕迹。不同的是,被氓抛弃的女子在“躬自悼矣”痛定思痛后,依然敢于追求幸福生活,而金和笔下遇人不淑的女子却认为“郎身重如金,妾命薄于叶”男尊女卑下的奴性心理使女子对遭受的苦难只能默默承受,“阿妹似欲哭,莫亦疑郎无”这种苦难在封建男权压迫下是一种循环。
无休止的战争,是一切苦难的源泉。金和描述太平军统治下的金陵城 “出入必以夜,粥饭亦夜煮”人民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再者,太平军进城之后掠夺居民财产,稍有反抗之意之人,便有性命之虞。在《痛定篇十三首》中,诗人写尽了太平军对金陵城民的戕害,“求死无死所,求生则此辱”生死不由人的苦楚,生不如死的痛苦尽显眼前。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更是难以磨灭的印记,《邻妇悲》中的村民刘氏,自贼至之夜,家中亲人先后死去,独剩一人,哭喊道“只愿作鬼安,不愿作人哭”。诗人闻此事,听其哭,颇似我生平,推己及人,不自觉也眼鼻酸。
(二)诗中之饥
金和饱受流离之苦,与之相伴、形影不离的便是疾病、愁绪、孤独和贫穷,尤以穷甚。金和从不掩饰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诗中始终充斥着衣不蔽体、寒不果腹、流离失所的真实记录。金和穷苦一生的原因有三:
其一,家道中落,屡试不第导致家中无经济来源。金和经常在诗中自嘲,途经丹阳时,诗人恰逢“载麦舟”,进而呼唤“舟兮舟兮,今赠客矣”,话锋一转:“舟麦有时尽,客贫方未已”。[1]17这种随口而吟的幽默,可以看做是诗人的乐天知命。“中年更丧乱,天地避饥寒”[1]260此类直言不讳写自己饥寒交迫的诗,在金和笔下比比皆是,哪怕是与朋友饮酒作乐时,自嘲贫寒之句不经意流露“青磷笑我无归裝,未必死是驱穷方”。[1]29
其二,戰乱使得穷困更剧。逃难避乱的途中,家中珍宝遗失。诗人在《过扬州》一诗中附道:“书籍宝玉遗弃满道,中颇有稀世之珍,而为不知者所得,卖之既无善价,遂往往损失。”此时的金和在行途之中过着“偏值连天雨,空山断米蔬。几回贪贱价,不饭饱羹鱼”的穷苦生活。
其三,金和一介文人,身无一技之长,唯有四处为馆,煮字疗饥,诗人也曾自嘲说道“平生识字误”。居粤之时,金和曾以《近况》道:“多病忆家切,长贫入市稀。从来无客过,不用掩松扉。”病中多虑,总觉得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因贫穷而无钱入市,独居更加使人悲寂。
(三)诗中之泪
翻开《秋蟪吟馆诗钞》,字字血泪的诗篇中可以勾勒出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眼泪不曾擦干的老者形象,这就是金和。金和常于枕边写诗,“生趣既尽,诗怀亦孤”,“尤不敢居知诗之名……正如山中白云,止自始悦,未可赠人”,[1]283。“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写诗已经成为诗人的一种精神寄托。金和的泪浸透到忧国忧思的国家“家国平生泪,临江一黯然”[1]228;为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而流,为惺惺相惜的朋友而流“酒杯剩有平生泪,一读君诗一黯然”;[1]233为久别重逢的亲友而泣“一家来甚喜,乍见泪如潮”;[1]266为自己的贫穷苦困、抑郁不得志而流“极意周防秋冷后,更停老泪作飘蓬”。[1]204他每次流泪都是真诚而质朴的,每一篇诗章都寄寓了诗人深厚的情感。
四处为馆的生涯使金和郁郁寡欢,加之于松江冯氏处并不受礼重,金和便携家人离开松江,“不辞荆棘路,吾意又天涯”[1]204漫漫长夜在他乡风雨飘摇。此时诗人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漂泊无依让他于战乱之中四处奔走“居不成家况异乡”[1]208。奔波带来疾病和衰老令诗人顿生韶华逝去、潦倒无成之感,以及远离故土,亲人于战乱中离散、死亡以及国运衰落造成的民生疾苦都尽收眼底,自己想要改变却人微言轻的无力感,是对诗人精神上的深层折磨。
(四)诗中之鬼
金和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万千平民中的一员,金和对战争的杀戮的描写入木三分。
道光二十二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围攻金陵城,城闭消息不通,城内人惶恐不安,待到城门暂开,便出现了“老翁腰间被劫财,脚下蹴死几幼孩。村妇往往踣堕胎,柳馆摧拉遗尸骸”[1]21这样混乱的场面,人在极度惧死向生的时刻,往往与禽兽无异,而金和对这样惨烈的场面的刻画入木三分。
咸丰六年,金和乞食奔波途中,看到往日繁华之地,如今荒草蔓生,联想到自己“浮生已分长羁旅”[1]164,心中难免渐生哀痛之感,“一岁四来往,空林今暮寒。”避乱全椒之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金和提笔写下《全椒除夕有作》:“白杨衰草江南路,尽是无家鬼哭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加之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公开决裂,原本较为稳定的时局再次被打破。内忧外患的时局使得底层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湘军为争战功,大肆屠杀叛军,造成了白骨累累、哀鸿遍野的场景。
咸丰十一年,金和受陆子岷之邀南下广东,行船所见:“江湖满地剩干戈,处处青燐照绿萝。”慨然有叹:“不信夜台如许火,十年新鬼比人多。”暗示战乱不断,死亡已成为常态。诗人此时年近半百,远离故土只身前往南粤,看到这黑黢黢水面上若隐若现的燐火,想象战乱的残酷,死去的多是无辜的人。
三、穷苦诗歌的常用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周易·系辞》中就有“观象取物”之说,相同的意象传唱千年,亦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沉淀下来的共同情感意识。袁行霈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2]53即“意”是人的主观感知能力,“象”则是客观世界中客观存在的物体。诗人之意寄寓于“象”中,两者浑然一体,不仅能生动传神的表达诗人的主观感受,亦留给读者一种意犹未尽的想象、感同身受的共鸣。因此,诗歌的立意就显得格外重要。
大自然的所有生灵在诗人眼中都充满生意,这种物我一体的观念,体现在金和诗歌中鲜明灵活的意象。生活的苦难折磨着金和,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样饱经战乱、岁月风霜折磨的苦难成就了金和。细读《秋蟪吟馆诗钞》会发现,金和的穷苦诗歌创作,有大量意象反复出现,甚至形成了不同的意象群。正如金和经历苦难,苦难造就金和一样,诗人在选择这些意象时,这些意象反过来也强化了诗人选择这些意象时的情感表达。这些出现在诗人不同人生阶段的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灾难之歌
天灾是人类生存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人祸更是自人类社会始,就无休无止的纷争。在记录天灾人祸的此类诗歌之中,金和好用“穷途、赊酒、长剑、狂歌”等意象。狂狷之气来自文人天生的优越感,越是苦难之中,越是酒剑相伴,这是一种精神寄托。
当然,“剑”、“酒”、“歌”这些意象具有一定的自比性。酒是为了麻痹自己,消解现实之中不受重视的悲愁;剑是寓意不负祖上,解外患、平内乱的壮志雄心;歌是悲愤心情的慷慨悲歌;这些意象群共同传达了金和渴望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希冀。所以,金和才会在盟夷犯江时叹息“如此江山在,曾经蹂躏过”,又毫不保留地抒发自己的愤懑“登高抚长剑,来日定狂歌”。[1]33
(二)羁旅之舟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船舟是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最早的舟船意象可以追溯到《诗·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魏晋时期,江南民歌中多有采莲行舟的唱和。隋唐以降,舟船入诗已成常态。乘轻舟早发白帝的李白,老病孤舟漂泊西南的杜甫,沿月棹歌舟渡的孟浩然,舟船意象亦被赋予怀古伤逝、兼济家国、羁旅漂泊等诸多情感。
对于逃避战亂流离失所的金和,渡头、乘舟更是常态:
客心当此夜,世味胜孤舟。——《舟次夜饮》
此岸即今行不得,惊魂何处定风沙。——《渡江》
舻声澀处夜寒増,关吏搂头独有灯。——《夜泊口岸》
金和此类诗歌中常用的意象有“渡头”、“行舟”,诗人随着江上的孤舟行于天地,“行”意味着羁旅,而舟字则写尽了诗人的孤独,二者的重合可谓是双重的孤独。诗人行舟之时所见一望无际的茫茫水面,又使诗人联想到“江湖”、“江海”类意象,这个水上所感的世界又映衬着现实的社会,诗人感慨道“平生识字误,摇落此江湖”[1]255“春风满江海,何处止飘蓬”[1]257。因诗人总在行舟,所以眼之所见、心之所感,广阔的水面正如诗人一生漂泊,无依无靠,犹如人落魄行走江湖。“我亦江东至狂者,只今才尽可怜生”可谓是诗人对自己半生萍梗的评价。
(三)思乡之虫
金和诗集名为《秋蟪吟馆诗钞》,典出《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3]2之意。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秋虫”多指寒蝉、促织。《诗经》中便常有这一意象,主要是表达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感伤之情。“寒蝉凄切”多半是别离之情,“促织悲鸣”唤醒的是思乡之苦。避战、乞食流寓他乡的路上,金和多次与家人生离死别:
秋虫乱人意,不睡盼啼鸦。——《今夜》
风劲虫迟语,霜深水暗流。——《舟次夜饮》
梦在虫喧外,愁生叶落边。——《不寐望月》
孤虫果助余,沉吟当竹屏。——《秋夜》
一虫蘋蓼外,自诉大江秋。——《归舟》
常年羁旅伴随而来的便是浓郁的思乡之愁,“国仇方切齿,家难复吞声”[1]184,被攻陷的金陵是诗人牵挂的家国情怀,故园难归加重了诗人的苦闷和寂寞。“秋虫”这类意象被赋予的感情就是:痛惜别离、感同身世、远游思乡。诗人承受着身体上的疾病和衰老、心灵上的孤独和思念,弱小的“虫”传递的正是诗人的悲苦处境。除此之外,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寒蝉”、“孤雁”、“浮鸥”、“飘蓬”。秋后寒蝉、单飞之雁、浮沉之鸥、无根之蓬、深秋之虫,诗人自比弱孤无力、时日无多的此类意象,实则是对自己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来自归乡无望的挫败感。
金和笔下亦多次出现“桃源”这一意象,与其自身生活环境的一贫如洗,但其精神生活惟愿寄托于逃避战乱之外的“世外桃源”,或许是诗人的美好希冀。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染的诗人大都心怀“忧生之嗟”,金和好为吟咏的穷苦之歌不是单一的,究其一生,金和的诗歌写尽了漂泊泪、潦倒穷、别离痛、思乡苦、对死亡的淡泊、对人世的悲叹,并且通过笔端刻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兵荒马乱和广大人民的挣扎苦难。
战火燎原的时代,苦难成为整个时代下人民的常态。感情敏锐、心思缜密的金和对这苦难的感受更为突出。金和游荡在寂寞的生命长河之中,也辗转于战乱纷纷的祖国大地,穿梭在饱经苦难的人民之中,这使得金和在关注自身苦难的同时,更能推己及人,感受整个时代的悲怆和伤痛,诚如徐世昌评价“凡《清人》之翱翔,《黍离》之颠覆,身亲目睹,故言皆实录,可当诗史。”[1]461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为后人传唱千古,是因为诗人的痛苦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之中,这种感受穿越时间、空间,具有永恒的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1] 金和,胡露校.秋蟪吟馆诗钞[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