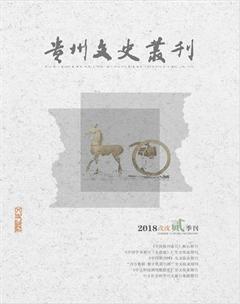“施于有政”——黎恂评传
王瑰

摘 要:清代贵州遵义人黎恂,进士出身,为官二十余年,不过州县主官,晚年升云南东川府巧家厅同知,方至五品,却未赴任而辞官归籍养老。黎恂也是贵州文化学界公认的贵州重要文化史阶段——“沙滩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其生平事迹,民国《贵州通志》、民国《续遵义府志》均有列传可查。但其在云南为州县官的十六年,叙述颇有不清者。今查云南诸府州县志,得黎恂云南仕宦履历、事迹颇为清晰,又其所著《运铜纪程》一书则揭示其心理甚多,于是黎恂一生之情怀与追求可以毕览。“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孔子教诲,是其家风,亦是其毕生所信、所行者。类似黎恂这样情怀与才干兼备的基层官员而不得升迁,是清廷政治之哀,亦是当今之深可鉴者。
关键词:黎恂 家风 儒士情怀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25-33
黎恂,字迪九,一字雪楼,晚号拙叟,清代贵州遵义(今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九年(1814)及进士第,三甲第三名。既及进士,分发浙江桐乡(治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知县,次年到任。在任六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冬,丁父忧,去官归籍。忧满不出。道光十四、五年间(1834、1835)复赴部选,拣发云南以知县用。历署平彝、新平、云州、沾益等州县,实任大姚知县。1道光三十年(1850)升东川府巧家厅同知,咸丰元年(1851),未赴任而引疾辞官,归籍,同治二年(1863)卒。
黎恂一生,享年近八十,可言说者甚多。就其大体来看,三十岁出仕,在官二十一二年,在家则二十五六年,但不管在家还是在官,他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曾改变,不同的只是转换了“施政”的平台。孔子之云“施于有政,是亦为政”,黎恂可以当之。
一、黎恂之家
明万历十年(1582),黎恂九世祖朝邦举家由四川广安州(治今四川省广安市)迁入贵州龙里卫(治今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旋因明廷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叛,遂又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迁入遵义县之沙滩(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沙滩村),为黎氏贵州开基之祖。
据黎恂侄庶昌编《贵州遵义沙滩黎氏族谱》,其家族在唐、宋、明,皆有为官者,不乏进士、举人。至清虽有朝邦第四子怀智,于明亡后弃官归家为僧,守节前明,但其后或文或武,仍代代有为官为吏者。耕读之风,可谓千年不绝。秉承家风,黎氏自开基贵州,即以重儒好礼为家法。黎恂直系八世祖怀仁,当明末扰攘之际,拒绝出仕,以教子孙重儒行礼之家法为务。1黎恂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不过,对黎恂性格、精神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安理。
黎安理,字履泰,早年是一个有着极高悲苦传奇的人物。安理祖母早卒,祖父续弦夏氏。夏氏为人凶悍,又好嫉妒,对黎恂祖父前妻所生诸子孙,甚不能相容。为此,安理之父不得不离家教书为生,但离家不甚远,夏氏仍不能容,不得已又远走至四川灌县(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教学谋生,并最终卒于灌县。安理幼时,夏氏乘其熟睡,以毒虫灌其口鼻,又诱骗至水边,推于水中,两次都因发现及时才得存活下来。十岁,以父不在家,亲自代父侍奉祖父母,终日操劳庶务,无所怨言,凡能养家事亲之技艺,皆潜心学习。侍奉祖父四十年,祖父欢心,祖父卒后,亲自营葬,头发为之变白。夏氏虽屡次毒害,不以为意,仍谨慎侍奉。夏氏将终,安理亦老,仍亲自侍疾数十昼夜而无惰色。2这个故事,几乎就是儒家上古圣人大舜的翻版。对于自己的父母,安理的孝心孝行更令人动容,如为治愈母亲早年感染的顽疾,还是童子时就潜心医方,精心调治,其母得以延年四十余岁,年近七十方卒。其父卒于灌县,弟子亦葬之灌县,安理多次前往抚墓痛哭,中举后,立即前去购置祭田。又至灌县寻找不堪祖母虐待,随其父前去的两个弟弟。找回二弟,三弟终不回,卒于外。三弟之子智力不足,学习三年,不识一字,安理亲自抚养,视同己出。对朋友又慷慨仗义,救人之难,不惜性命。安理就这样在世人难以承受的悲苦中,砥砺儒者之行,最终闻名全国,以孝义入于清代国史之中。3安理不仅砥砺儒者之德行,在终日操劳的生活中,仍争分夺秒地读书求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中举,后官至山东长山知县,当天理教起事乱境,保境安民,政声有著。
黎安理显然秉持了黎氏素有的家风,并在苦难提供的机遇下将其发扬到了极致。黎恂作为安理长子,是在他的道德示范、做人示范、情怀示范下成長起来的,受到他的教导和管束也是最多、最严格的。而黎恂显然也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嘉庆十五年(1810),年仅二十五岁的黎恂中举,四年后(1814),又中进士,清代贵州沙滩黎氏的第一个进士由此诞生。可以相信,进入仕途后的黎恂,祖上“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的家训,将是提醒他主政一方,造福一方的长鸣警钟。
二、桐乡名宦
黎恂及进士第后,分发浙江桐乡知县,次年到任。桐乡,属嘉兴府,处苏、杭之间杭嘉湖平原腹地,江南鱼米之乡,经济发达、人文厚重,相对于当时黎恂的家乡遵义而言,实是天堂。嘉庆时期,虽有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但并未波及江南,江南仍是一派长久承平的气象。黎恂初莅仕途,就补任此缺,也足令人羡慕。但是,这样太平的桐乡,相对于繁剧之地,是很难给主政者提供才华施展空间的。当然,如果其为官之志在于发财,那就是一个肥美之缺了。但是,黎恂的追求不是发财,而是施展才华,造福一方。就在这样太平无事的桐乡,黎恂主政六年,成了桐乡名宦,光绪时期修《桐乡县志》时,黎恂被纳入名宦传,与他并列的不过数人而已。
黎恂在桐乡任上,针对桐乡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安静为治”的施政方针,积极做的事情不过是正狱讼、弭盗贼、厘漕务等必须由政府提供的,确保桐乡基本公平、安定的公共服务。当然,黎恂也很清廉爱民,“洁己爱民”是光绪时期《桐乡县志》的编修者给予他的明确评价。在当时,为官一方,能做到黎恂这样,已经是此方百姓莫大的幸运了,但是黎恂并不满足于此。桐乡既太平无事,黎恂便多闲暇,这些闲暇他多用来与桐乡士子交游问学,提携后进,涵养学风,并在此方留下一句令士子们永久感怀的名言——“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与黎恂交游的士子,大多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间,黎恂为云南京铜运官,押铜北上时,不少旧日桐乡士子特意赶来相会,感情极为深厚真挚。
黎恂诸传中,光绪《桐乡县志》在叙述黎恂的政绩时,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件事,就是黎恂将父母亲接到衙署,有一弟亦亲来侍奉双亲、兄长,在衙署之中亲自垂范了儒家孝悌之美的家庭伦理,《县志》以“孝友怡怡,邦人为之感化”来记述黎恂的家庭景象。显然,黎恂确实是一名父母官,很有古守令的风范,非但要生养百姓,还要教化百姓。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黎恂独特的为政举措,但就黎恂而言,不过是他自小受染的家风。
黎恂担任桐乡知县的第六年,当时浙江巡抚因事过境,暗中察访所经府县官贤与不肖,收到了不少匿名投诉,其所经诸县,只有黎恂无劣迹,并且还得到了民间贤能的褒奖。为此,巡抚特将黎恂迁徙至大县归安任职,1给予进一步的历练和考察。但未及赴任,其父黎安理辞世消息传来,黎恂以丁忧去职,回到家乡遵义。2
三、读书办学
嘉庆二十五年,黎恂得到父亲辞世消息,即行丁忧,3但代任知县到任后,黎恂并没有立即回籍,而是在桐乡逗留了数月,以自己积累的养廉银近万两大量购买书籍,4全部带回家乡遵义,忧满服阙,以病告假不出,由此度过了十四年的家居生活。5
黎恂在家,民国《贵州通志》记其日日读书著述。6由黎恂早以“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自勉来看,日日读书并不足奇,这也是儒家所谓“修身”的必要途径。不过,黎恂读书也包含与友人的学问探索和交流,而且他很以这种生活为快,所以当他咸丰元年再次辞官归乡时,由于友人的先后辞世,也以缺乏文友的交流陪伴而伤感。7作为一个进士,且施政有为,而乐于魏晋“竹林七贤”的生活,且一投入就付出自己仕途爬升最为关键的三十余岁到五十岁的年龄,隐士的生活应当也是黎恂的真心向往。但是,黎恂的“归隐”,显然又不是道家那种真正心归自然的归隐,而是仍含着积极入世态度的儒士的归隐。
黎恂家乡遵义,历代为巴蜀边鄙之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土司杨应龙之叛平定后,改土归流,设遵义府,方开始全面植入中原政治文化制度,清雍正五年(1727)遵义府由四川划归贵州,管理又才更加有效。民国《贵州通志》言遵义地区处地僻陋,自明至黎恂之时文人学士值得称述者甚少。1黎恂恰恰有志于改变这种风貌。
黎恂从浙江归家,是可谓倾尽资财购买书籍的,而他购买的书籍虽然书名难考,必定绝大多数都是儒学之书。因为,黎恂回乡后,即以其书,填充了家族书院,让族中子弟及乡里好学者尽情研读,自己也亲自教导、提携。清代贵州名满全国的大学者郑珍、莫友芝都是得益于黎恂从浙江带回的书籍,方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的。黎恂子嗣及族中其他子嗣,亦得益于此,世代昌盛,除了黎恂侄庶昌这样的著名外交家、学者外,黎氏子孙直至清亡,代不乏名士,黎氏家族亦崛起为贵州望族。民国贵州文化界,就完全认可黎恂的文化之功,称他是筚路蓝缕,孕育一方文化的开创者。2这方文化,今天学术界和文化界一般称作“沙滩文化”,是贵州文化史的一个辉煌阶段,以黎氏家族及黎恂培养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及其后世皆居住在沙滩而得名。黎恂的希望完全转化为了现实。
因此,黎恂在家十四年,看似归隐,实是有为,他是把他的精力用在了修身齐家,以文化俗,改变桑梓面貌上。儒士的入世价值取向,他并没有放弃,只是以一种更婉转、厚重,而实际上更加积极的方式践行着。3
四、边陲干吏
大约在道光十四年底,黎恂进京参加部选,再次进入仕途,此时他已五十岁。出仕的理由,据黎恂自言,是因为贫穷。4这个理由应是真实的,但黎恂再出仕却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因为他的为官之道,清廉一如既往。
经过部选,黎恂以知县发往云南听用。根据黎恂在桐乡的政绩,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不公平,但黎恂毕竟十余年未出仕,朝廷要在边疆地区试验一下也无可厚非。初到云南,黎恂即展现出了能吏的本色,成功“救火”。
当时,曲靖府平彝县(治今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民间妇女蔡刁氏起事,自置总督等数十官,声势颇大。黎恂立即署理平彝知县,带兵捕剿,从昆明三昼夜到达平彝,比常规时间节省一半,5立即擒拿蔡氏母子及伪总督以下四十余人,赦其胁从,叛乱顿时平定。 黎恂成功平叛,首在于快,六七天的路程三天到达,最大限度地将反叛事件扼杀在影响最弱小时,平叛时贯彻擒贼擒王的原则,赦免胁从、孤立魁首,最大程度瓦解叛乱势力。这些都是中国历代平叛的经验,黎恂显然也是老于此道的,而且嘉庆时期天理教起事时,他也在山东长山县协助其父平叛,本身也积累过一线经验。6应该说,这次平叛是他在平彝的重要事功,但黎恂本人对这件事看得并不重。道光二十二年七月,黎恂铜差回滇,经过平彝,与故吏相聚,提到的是他在任时拿获恶棍陈阿信的事,听说他半月前病死,遂欢喜地方一害去除,1对于平叛这样的大事反而未置一言。
黎恂在平彝署理了三年左右知县,道光十八年短暂署理元江直隶州新平知县(治今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旋改任楚雄府大姚县(治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知县。2在新平短暂的任上,黎恂就成了新平县有清一代的十八位名宦之一,以“政治平允,宽厚爱人”为百姓所久思。3而在大姚任上,黎恂则建立了二十余年仕宦生涯的最大事功。
大姚县人刘荣黼,曾官翰林院编修、遵义知府,与黎恂为同榜进士。黎恂任大姚知县,适刘荣黼致仕回籍,两人志趣相投,皆以大姚设县久远而志书稀少残缺为憾。黎恂遂在刘荣黼的大力协助和共同工作下,修成了大姚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志书,即今存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的《大姚县志》。这是黎恂对大姚县作出的重要文化贡献。不过,在大姚任上,黎恂的“文治”要退居其次了,此时的云南给他提供了施展武略的新平台。
道光中后期,清廷的统治力度已经急剧下滑,鸦片战争的失败,集中暴露了清廷軍事、政治上的极大隐患,有识之士如林则徐、曾国藩等皆有深刻认识。由于嘉庆以后,以铜矿采冶为中心的云南矿业面临洞老山空的局面而急剧衰落,开矿鼎盛时期聚集的大量矿工和产业链上的相关人员大量失业,矿源枯竭引发的生存危机,大大压缩了迤西回汉民众的生存空间,回汉矛盾渐生。道光十九年,顺宁府缅宁县(治今云南省临沧市)回民与两湖客民发生械斗,拥众千余人,波及邻县。黎恂调署顺宁府云州知州,再次奉命平乱。黎恂强势传唤双方头目于县衙大堂,镇之以威,而后不分回汉,决之以公正之理,暴动得以平息。若是深入了解过道光以后云南回民的起义历史,就能知道这种回汉无别的态度,已经足以看出黎恂在政识上已超出当时云南大多数官员。
道光二十年(1840),黎恂领京铜运官之差,二十二年(1842)九月回任大姚。二十五年(1845),永昌府(治今云南省保山市)的回汉矛盾在官府的挑唆下,趋于激烈,大量无辜回民被杀,迤西各处回民遂大举反清,云南地方当局无法收拾。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廷调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查办永昌事件,平息回民起义。地当金沙江川滇要冲的大姚县,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混乱之中。黎恂作为大姚父母官,有保境安民之责,在事变未蔓延到大姚之时,他已洞察事态的发展趋势,提前在大姚创办团练,并不看好清廷正规官兵的实战能力。后来几乎席卷全滇的杜文秀起义,主要就是被团练扑灭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被团练扑灭的。团练不是黎恂的发明,但在云南却是他开创的。
义军进攻大姚,由于黎恂准备充足,团练有力,得以击溃义军,大姚得安。后又奉命率团练解白盐井(治今大姚县西)之围。与黎恂同岁的总督林则徐见状后,十分赏识,下令在全省推广团练。黎恂一生的仕途终于迎来了升迁的转机,可惜此时的他已经年逾六十。
道光二十八年(1848),黎恂署理曲靖府沾益州知州,次年为他人所代,4被代后黎恂可能是回任大姚。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林则徐告病辞官,辞官前,他已向朝廷举荐黎恂为“卓异”,并题升为东川府巧家厅同知,1官居正五品。但是,黎恂也告病辞官,咸丰元年(1851)得到批准,未及赴任就回籍了,2此时他已66岁。黎恂仕宦生涯,至此结束。
五、辞官心理
黎恂当升迁之际辞官,借口是生病,病或许不假,但绝非影響到非辞不可,实际原因则是自己本来无心仕途,迫于贫困才重新出仕,出仕后经济上仍然入不敷出,牵累多年,实在不值,索性辞官。3无心仕途,不难理解,因为他本来就有林下生活的向往,也确实在为官的黄金阶段,家居十四五年去享受这份乐趣。再仕之后,虽然在职责履行上,兢兢业业,文武精敏,百姓感怀,但心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份“林下”向往。
“林下”向往可以理解,出于改善贫困目的而重新做官,做官十数年却仍旧入不敷出,这就超出常人对当时为官的理解了,而且黎恂为官还是在清廷早就实现丰厚养廉银制度之后。云南知县养廉银每年在800-1200两之间,以1000两的中位水平来看,就算不贪,这也足够他养家糊口了。4黎恂首先是一名清官,否则他不会在桐乡、新平都被后世修县志时列为名宦,否则他也不会有贫困之叹。黎恂为官之所以常年入不敷出,根本上是道光时期,官场的公务执行成本越来越高了。这种执行成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腐败,且是一种体制性腐败。有为之士在这种环境里谋求有为,本身就是对自己心理的极大熬煎。黎恂就一直处在这种熬煎之中。道光二十年,黎恂领该年京铜正运一起运官,万里运铜至京,交户、工二部铸钱局收用,往返历时两年,行程一万六千五百余里,途中作日记,公务履行、见闻感受多所记载,后辑为《运铜纪程》一书。5透过该书的记载,黎恂的辞官理由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如黎恂历来的“林下”情结。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黎恂的运铜船队行至荆州郝穴(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区)下江面,值傍晚,见江洲中群雁飞集,自由翔止,便油然而生江湖情怀,恨名利缰锁,不得云飞水宿。当晚,宿于江岸,对明月空江而抚琴奏《平沙落雁》之曲。6这是真隐士的风采,但是儒士而隐,毕竟还有对当时政局不满的原因。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中旬,行至九江,九江关税使福泰不按章、按时收税,让船队在九江拖延十日,还纵容两湖调往广东海面的兵丁登上铜船,任意差遣、打骂、勒索船工,黎恂百般恳求福泰出兵弹压,他却畏兵如虎,不敢置一言,对船队却又始终不放行,直到黎恂交足他希望的税银后,方才放行。其间,黎恂望见陶渊明所隐居之柴桑山,便生向望,并耻于自己为五斗米折腰。7可见,他的“林下”情结,实有对现实的不满。
类似令人愤怒到不吐不快的事情,所在多有。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四,船队行至运河山东济宁州草桥闸(又名通济闸),以运河水量不足,泊于闸下。至十四日,水渐涨,铜铅重船无虑搁浅,十五日,船队请过闸,闸官以未接到漕运总督令,拒绝开闸。运河行船,苦在等闸,有水时不及时放行,再等就是十数日。黎恂见状,愤怒至极,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日记上发泄一番,“吾辈所办亦王事也,而节节受掯如此,可慨也夫!”不仅在运输沿途,就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师,黎恂为完成这趟流程、环节完全有文件规定的铜差,仍要忍辱负重,百计千方,这在他的《运铜纪程》中是有很多记述的。1
为理解黎恂的愤怒,这里不妨对京铜补充几句说明。自乾隆初年以后,清廷户工二部铸钱局铸币用铜全采滇铜,每年云南须运铜六百余万斤至北京交局,这部分铜便称京铜,是国家金融运转的根基所在。清廷极为重视京铜的安全足数到京,运官由府佐或州县主官中能干者充任,沿途督抚全部动员,对铜船在境内依规行驶、按时、安全行使负有最高责任。京铜按时、足额运送到京后,主官要得到皇帝的引见,并且原任官职任期满后,可以免调进京引见,在提拔时也有一定优待。可以说,京铜运京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基础性金融工程,重视程度仅次于江南湖广粮食漕运。但是,就是这样的国家工程,沿途官吏仍要上下其手,肆意阻挠行程,从中渔利,作为有为之士的黎恂,怎能不为之愤怒感伤!
黎恂这趟铜差,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严重亏损的。根据《云南铜志》卷3《京运·请领银两》的记载,滇铜京运正运每起(共铜一百一十万四千四百五十斤),国家给予的费用,包括水脚银、杂费银、险滩剥费银、舵水工食银,以及运官预支一年养廉银,共计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二两余。这些银两是完全不够开支的,到底欠缺多少,难以考明,但从黎恂沿途借贷来看,其欠缺应有数千两白银之多。据《运铜纪程》不完全记录的开支,黎恂在重庆即开始借款度日,重庆贷银二千四百两,2宜昌贷银三百两,3在江苏六合,六合县令贷款赠银三百两;4到达北京,虽然有近三万斤余铜已为户部购买,仍派遣自己的儿子到河南彰德府知府(原黎恂在浙江时拔擢的士子)处贷银七百两;5前后贷银三千四百两方完成铜差。仅此一斑,已可想见当时公务执行成本之高,整个官场腐败之严重。所以,黎恂在户部领到所卖余铜银后,虽然已被户部克扣三分之一(应领银三千三百八十两,扣除户部克扣的领费,实领二千一百两),仍还要将所剩不多的银两立即命人带到工部和户部,将尚未交足的户、工二部书吏的好处费交足。此情此景,黎恂不禁发出“万苦千辛,皆为人作嫁衣裳也”的无奈而悲痛的感叹。6当然,京运铜差对运官而言,也蕴含着巨大利润空间,只要谎称沉失,私自卖铜就行,而且很多运官也是这样干的,但是黎恂拒绝了这样的欺君之行。
所以,在如此高昂的公务执行成本之下,清廉自持的黎恂想像在浙江桐乡任上一样积累点财富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他铜差结束回任大姚,用三年多的时间修完《大姚县志》后,迤西回民起义便日益高涨,迟早及于大姚。黎恂深知清廷正规官军战斗力之不可靠,首开云南团练,很多费用也是要从他的养廉银里支出的。团练练好,战端即来,生产破坏,保境安民之责大之如天,又何遑节省开支,累积财富?战乱既平,官事告一段落,六十五岁的年龄,即便升官,又能有什么作为,又有什么可以贪恋的?索性辞官,善始善终,实在再好不过。
六、家门遗风
咸丰元年,黎恂辞官回籍,早年“林下”之友,基本湮没无遗,“林下”之乐已不可得。数年后又发生了几乎覆盖贵州全省的咸同农民大起义,黎恂故宅、藏书焚毁殆尽,不得不以老迈之躯四出辗转避祸。但是,虽然遭此大难,黎恂的内心还是十分坚定,不管避祸到哪里,他都“焚香展卷,意兴翛然”,7其道心是无比坚定的,也在以这种方式传递他的坚定信念。黎恂的儿子们,传承了他的精神,在乱世之中发扬着黎氏的家风。
黎恂有五子,兆勋、兆熙、兆祺、兆铨、兆普,兆熙早卒,其余四子民国《遵义府志》皆有列传。长子兆勋为清代贵州诗文名家,与莫友芝、郑珍为挚友,捐资出仕为县学教谕,苗民起义,以办团练防御立功,擢升为湖北鹤峰州通判,其才能为湖北巡抚胡林翼所赏识,留在省城使用。后以丁父忧去职回籍,旋卒于家。兆勋类似其父,文武兼通。少子兆普,则以孝友、行医、求稼穑之理闻名。三子兆祺,四子兆铨事功最多,在官场上,其风节有过其父者。
兆祺随其兄兆勋等学诗文,后以在乡中办团练,并率领团练抵御起义的农民军和太平军石达开西征军立功,得奖知县。同治五年(1866),云南巡抚湘军著名将领刘岳昭率军取绥阳(遵义府属,治今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兆祺以其禹门寨屯粮转输供军,为刘岳昭所赏识。1后又随蹇訚军克湄潭(平越府属,治今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以功赏知府衔。东下南京,依曾国藩。刘岳昭升云贵总督,招兆祺入滇。既入滇,“忽不乐曰,我不惯趋侍贵人。遂翛然归居贵阳,以赋诗终老”2。兆祺凭借自己的才能,屡为当时显贵所看重,千里邀用,仕途的前程是很可观的,但是他以不合心意而毅然辞官,不为当官而当官,乃父遗风尽显。
兆铨以协助其兄兆祺在家办团练起家,刘岳昭取绥阳后,亦论功以知县用。刘岳昭入滇就巡抚本职,即调之入滇,同治八年(1869)署理寻甸州知州。当时云南以平滇西杜文秀起义,于各府州县征兵,凡征兵一人随征兵饷银四两。兆铨以迤东新定,重在招集流亡,安抚民生,抗命不遵,并上书上官,极言其弊。提督馬如龙以兆铨抗命,诉至总督刘岳昭处,3岳昭以兆祺为“强项令”,并且“实心为民”,让马如龙给予优容,最终亦罢征兵之命。4未久,清廷议改道广西输送京铜,于迤东各州县征用马匹驮载,每征马一匹,随征银二两,寻甸州征马三千匹。兆铨以寻甸本不出马,抗命不遵,委员到州衙索马,兆铨以辞官抗争,铜运改道议阻。云南巡抚岑毓英,在迤东平定后,以互换之名,将曲靖回民迁往寻甸,又将寻甸汉民迁往曲靖,阴谋待滇西杜文秀起义扑灭后,就便坑杀迁到寻甸的回民。兆铨得知后,以十余万回民性命系于己身,遂以全家数十口性命向岑毓英担保回民不会反叛,连续三年向岑毓英陈述请求,才终于得到不杀回民的承诺。回民迁回故地,计口授资,兆铨亲自坐在路旁监视,回民扶老携幼,感激涕零。5后又任职安宁、昆明、镇雄各一年,6凡在云南为州县官八年,平反冤狱数十起。在官为民,在兆铨这里比他的父亲还多了几分烈气。
黎氏一门,自黎恂从浙江桐乡带回万两白银之书籍后,尽皆读书修学,加以二百余年家风熏陶,后世人才辈出,或学或官,甚至哺育出了黎庶昌(黎恂弟黎恺之子)这样的著名外交家和一流学者,直至清亡,遵义沙滩黎氏都是贵州名门。黎氏所居之遵义沙滩,成为贵州的文化中心。如今贵州文化史上便有“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的美誉。如此文化贡献,又岂是几个单纯的高官所可比拟的。
七、结语
黎恂作为一名进士,为官二十余年,实际只在州县一级,对清帝国的影响难以言大。但是考察他的一生,又不难发现是极具价值的一生。不管是为官还是在家,黎恂的言行都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儒士,其办实事的能力也无愧于能干。但令人深思的,便是这样的士大夫却难以在官僚序列里爬升。从这个方面来说,黎恂的遭遇反映了清廷的日暮途穷。因为黎恂这样的人并不孤单,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黎兆祺为何不愿趋就贵人,黎兆铨为何总在州县任上,原因也许还在于他们的人生价值在黎民而不在仕途,靠屠杀起事的小民在官僚序列里爬升,在他们而言是一种煎熬——是在为国效力,却也是在为国“屠民”。所以,基层有为亲民之官的价值体现如果出现了矛盾或分裂,或许就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
同时,黎恂一生不管在官还是在家,其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孔子所谓“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儒士精神,这也是他和他的家族的家国情怀。黎恂两次辞官,动因不一。首次辞官,严格说只是不出仕,正当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之盛年而如此选择,根本上在于他的文化使命感和家庭责任感。三十岁到五十岁,也正是培养塑造子女的时候。在他心中,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教育好家中儿女,传承家风,是好过单纯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五十岁后,儿女已经塑造成型,自身精力体力还可有用于民,于是再出仕。出仕之后,虽然黎恂的勤勉精敏一如既往,但王朝暮年的气象日渐深沉,有为之人不得有为,有为之为须以杀戮止杀戮,则是暮年遇知己终于升迁而又辞官的无奈。虽然无奈,再次居家待终,虽逢国家丧乱而颠沛流离,仍意兴自如地读书,其道心不灭的信念又何其之深!这种信念之于今日之仕者,恰恰是最为缺乏的。
附:黎恂云南仕途履历简表
Performance has Politics——LiXuns Comments and Autobiographer
Wang Gui
Abstract:Scholar LiXun,born in Zunyi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of Qing Dynasty, who had been a county magistrate more than 20 years, but he chose to resign from his new official post of Qiaojia office,Dongchuan prefecture—— a late promotion for his old age. LiXun was also a recognized founder of Shatan Culture——an important stage in Guizhou cultural history. His life story has been compiler in R.C.Guizhou Annals and R.C.Zunyi County Annals while his 16 years long curriculum vitae in Yunnan province was not clear enough. Checking in prefecture and county Annals of Yunnan, as well as Yun Tong Ji Cheng——a journey diary of LiXun,we could see his deeds and psychology and ambition in his whole life.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s Practicing filial piety and friendship is also politics, which was also the Family Style of his own and his faith and life's practice. The grass-roots officials like Li Xun who both have deep feelings and talents who couldnt be promoted was the sad action of Qing government,as well as the precious source of today's learning sources .
Key Words: LIXun;Family Style;Confucian scholar feel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