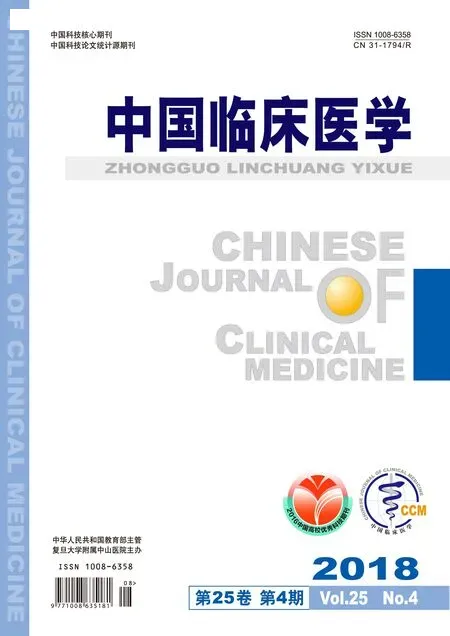上海城郊社区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洪 维,郑松柏,李慧林,杜艳萍,唐雯菁,陈敏敏,朱汉民,程 群*
1.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质疏松科,上海 200040 2.上海市老年医学研究所骨代谢研究室,上海 200040 3.复旦大学老年医学中心,上海 200040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退化性疾病如骨质疏松症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和负担[1-2]。老年女性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高危人群。前期的调查研究[3]发现:1990年上海城区60岁及以上老年妇女总骨折发生率为19.6%,郊区为8.8%;而1998年上海城区老年女性总骨折率上升至23.4%,郊区为9.8%。随着城市化进程,城郊人口结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均较20年前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病特点及危险因素也较20年前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城郊社区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社区老年女性骨折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的城郊差异,为不同地区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防治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人口分布的统计学分析确定样本量后,以上海中心城区和近郊共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宁虹桥和天山社区,嘉定江桥和闵行颛桥社区)中65岁以上免费健康体检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各区人口分布特征,按照年龄构成比进行分层抽样。共纳入4 428人,其中城区2 033人(年龄65~93岁),郊区2 395人(年龄65~97岁)。纳入标准:可自行活动,愿意参加本项研究的社区65岁以上老年女性。排除标准:(1)患有明确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包括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库欣综合征、终末期肝肾疾病、晚期肿瘤;(2)近1年有明确使用影响钙磷代谢药物史者:包括双膦酸盐、雌激素、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降钙素、肾上腺皮质激素;(3)长期卧床者(卧床时间≥3个月)。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2014K028),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后采集资料信息。
1.2 样本量的计算 参照文献[4]报道的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总患病率30%~40%,依据预期现患病率公式,计算出所需最小样本量3 993人。考虑到社区居民拒绝率为15%,且此次研究涉及社区较多,预计每家社区筛查1 500人。再按照每家社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对符合条件的居民进行分层抽样,去除不符合入组标准及数据不合格的问卷,最终入选社区老年女性4 428人。其中城区2 033人(年龄65~93岁),郊区为2 395人(年龄65~97岁)。
1.3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1.3.1 问卷调查 所有患者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月经史、文化程度、骨质疏松性骨折史(是指患者能回忆绝经后发生并明确诊断的脆性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定义[5]:为低能量或非暴力性骨折,指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明显外力或“通常不会引起骨折外力”而发生的骨折,亦称为“脆性骨折”,包括骨折次数、类型(髋部、椎体、四肢、除以上3个部位外发生的骨折)等。其他资料包括:父母髋部骨折家族史,近1年跌倒史(跌倒是指突发、不自主的、非故意的体位改变,从而倒在地上或更低的平面上),户外锻炼(每周),奶制品摄入(每天),钙剂摄入(每天)等。户外锻炼(每周):跑步、快走、跳舞等方式的活动(不包括家务劳动),分为无、活动量少(每天<30 min)和活动量多(每天大于或等于30 min)。奶制品摄入(每天):指食用牛奶、奶粉、酸奶等奶制品,分为无、<250 mL、≥250 mL。钙剂摄入(每天)分为有和无。基础疾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及其他关节炎),糖尿病(1型和2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胃肠道疾病(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或肠切除术后),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肌梗死)。
1.3.2 人体学指标 空腹测量身高、体质量,计算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体质量(kg)/身高2(m2)。握力测试:采用云鹏牌WL-1000握力器计算左右手握力各3次,计算平均握力=(左侧握力+右侧握力)/2(kg),取最大值。跟骨定量超声(quantitative ultrasound, QUS)骨密度测定:应用美国Hologic公司Sahara型跟骨超声骨密度仪测定研究对象左侧跟骨的骨密度,并记录T值。
1.3.3 跌倒平衡测试 计时起立行走测试(timed up and go test, TUG):受试者尽可能快地从普通高度有靠背及扶手的椅子站起,直线行走3 m后,转身走回椅子并坐下,记录时间;5次坐立测试(five timed chair rising test, CRT):受试者从普通高度的椅子上站立并坐下5次,记录从开始站起到第5次坐下接触到椅子所用的时间;串联行走试验(tandem standing test, TGT):受试者在指定尺子上行走8步(尺子约10 cm宽,3 m长),1只脚放在另1只脚前面,两脚距离不超过1 cm,从直线串联式姿势开始。如果脚偏离直线超过脚的宽度,认为该步失败。如受试者可以在直线上行走8步,其中6步为正确行走,记录为6/8。

2 结 果
2.1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及一般资料的城郊差异 结果(表1)表明:城区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为26.27%,高于郊区的21.67%(P<0.01)。城区老年女性平均年龄、受高等教育比例、父母髋部骨折史、奶制品摄入≥250 mL/d比例、钙剂补充、跟骨超声骨密度值和T值及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胃肠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均高于郊区女性(P<0.01);初潮年龄、户外锻炼活动量多比例、无奶制品摄入比例小于郊区(P<0.01)。城区女性近1年跌倒发生率、TUG和CRT完成时间均大于郊区(P<0.01或0.05),TGT及平均握力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1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及一般资料的城郊差异

续表1
at值,bPearsonχ2值,c趋势χ2值,dMann-WhitneyU检验Z值
2.2 老年女性不同年龄段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的城郊差异 结果(图1)表明:城区老年女性在65~69岁、70~74岁、75~79岁、80~85岁、85岁以上年龄组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患病率分别为21.48%、27.84%、27.93%、30.98%和31.58%,而郊区老年女性分别为19.91%、23.24%、23.10%、27.35%和16.26%。城区老年女性骨折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高,而在郊区妇女中,骨折患病率随着年龄上升,到85岁以上反而显著下降。

图1 不同年龄段城郊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
2.3 老年女性骨折次数和骨折类型构成比的城郊差异 结果(表2)表明:城郊老年女性骨折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骨折部位上,城区老年女性椎体骨折的构成比高于郊区,而郊区老年女性四肢骨折的构成比高于城区(P=0.005)。

表2 城乡老年妇女骨折人群中骨折次数和骨折类型构成比 n(%)
2.4 城郊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临床危险因素的logistic逐步回归多因素分析 结果(表3)表明:城区老年女性中,年龄越大(OR=1.016,P<0.001),近1年有跌倒史(OR=2.335,P<0.001),父母髋部骨折史(OR=1.517,P<0.001),TUG完成时间越长(OR=1.042,P=0.007)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跟骨骨密度T值是其保护因素(OR=0.814,P<0.001)。郊区老年女性中,年龄越大(OR=1.019,P<0.001),近1年有跌倒史(OR=3.761,P<0.001),TUG完成时间越长(OR=1.326,P=0.015)是独立危险因素,户外锻炼运动量多是保护因素(OR=0.958,P=0.022)。

表3 城郊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临床危险因素的logistic逐步多因素回归分析
近1年跌倒史(是为1,否为0),户外锻炼(无为1,活动量少为2,运动量多为3),年龄、跟骨超声骨密度T值、TUG完成时间均为连续变量
3 讨 论
Johnell等[6]研究显示,女性一生中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概率为40%~50%,远高于男性的13%~22%。绝经后妇女发生骨折概率比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卒中、乳腺癌发生率总和更高[4]。本组郊区老年女性的骨折发生率虽然低于城区,但高于1990年和1998年骨折发生率[3]。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固有因素如年龄差异,本研究城区女性的平均年龄略高于郊区,而年龄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随着年龄增长骨折风险增高[7]。此外,荟萃分析显示父母髋部骨折史是不依赖于骨密度的骨折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8]。本研究城区老年女性的父母髋部骨折史比例显著高于郊区,且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髋部骨折史是城区女性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
在非固有因素中,运动不仅增加峰值骨量和骨强度。一项对65~75岁老年女性研究还发现,规律运动还可减少跌倒、背痛[9]。本研究中郊区女性户外锻炼活动量多的比例高于城区,是骨折的保护因素。问卷调查过程也发现郊区妇女的户外锻炼形式多为参加广场舞等强度较高的锻炼形式,而城区则以散步为主。有研究显示不同运动方式对骨折和骨密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0],本研究中未对运动强度进行量化,其相关性需进一步细化分类研究。除了运动,日常膳食中奶制品的摄取对老年妇女骨密度有保护作用,但对预防骨折结果不一。Sahni等[11]的研究显示,平均年龄55岁的人群牛奶摄入与提高髋部骨密度有关,但与髋部骨折无关。瑞士一项队列研究[12]显示,每天1杯牛奶(200 g/d)不能减少任何骨折发生率,且每天饮用1杯以上牛奶(>200 g/d)骨折率反而增加,可能与牛奶中D半乳糖过多导致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有关。本研究城区的大量饮牛奶(>250 mL/d)比例显著高于郊区,这可能部分解释城区骨折发生率高于郊区。此外,本组城区居民钙剂摄入也高于郊区,但logistic回归分析均未提示补钙与总骨折发生率相关。对于补充钙剂与骨折的关系目前仍有争议,一项纳入26个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补充钙剂可减少总骨折和椎体骨折,但不能减少髋部骨折和前臂骨折[13]。因此,钙剂补充与骨折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双能X线吸收检测仪测定骨密度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也是最重要的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的方法之一[14]。但由于设备昂贵,检查成本较高,该方法不适合在社区对人群进行大规模筛查。而跟骨定量超声法利用超声波的发射和穿透衰减评估骨的力学特征,可以反映跟骨骨量和骨微结构,携带方便,操作简便,也具有独立预测骨折风险的价值[15]。虽然本研究城区老年女性的跟骨骨密度和T值高于郊区,logistic回归分析T值高是城区骨折的保护因素,但城区骨折发生率却仍高于郊区。进一步分析骨折危险因素发现城区老年女性近1年跌倒发生史及跌倒风险测试均高于农村。且跌倒和TUG时间长在两组人群中均是独立危险因素,在城区老年女性,有跌倒史者是没有跌倒患者的骨折发生率的2.335倍,郊区为3.761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比于骨质疏松,跌倒才是骨质疏松性骨折最重要的原因[16-17],87%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18],约50%的低创伤性骨折发生于未达到骨质疏松诊断标准的患者(T值大于-2.5)[19]。
肌肉平衡功能下降是老年人跌倒的直接原因,可作为预测跌倒风险的有效指标之一。澳洲一项对1 126例女性10年纵向研究显示,TUG是评估非椎体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20]。本研究也提示,TUG完成时间长是两组人群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城区TUG完成时间大于郊区。CRT是评估老年人大腿肌力和耐力的测试[21]。本组城区的CRT完成时间大于郊区,进一步提示城区老年女性下肢肌力差于郊区。TGT是评估老年人平衡能力的测试,有研究显示跌倒者的TGT时间显著短于无跌倒史者[22]。但本研究的两组人群TG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与骨折无明显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此项测试过程中,患者理解度有差异,配合度较差,且中国人群中尚无此检查的评价标准值,缺乏评价效度的研究。此外,有学者认为双手握力与全身肌肉力量有很好的相关性,是反映老年人功能活动状态的重要指标[23],但也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24]。本研究两组人群平均握力无明显差异,也不是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仍需对中国人群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观察研究。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采用问卷调查回顾性研究方式,未提供X线摄片依据,一些骨折如椎体骨折常因无明显自觉症状而被漏诊,据统计2/3的患者无明显严重症状,而3/4患者未寻求就医[25]。有些老年人因为记忆力减退,回忆有误,因此有可能低估了实际骨折患病率。此外,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是参加社区统一体检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不是整群抽样,因此一些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未能纳入本研究中,如本研究中郊区85岁以上老年骨折率反而下降,可能与数据结果的偏倚相关。
综上所述,上海城区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高于郊区,骨质疏松性骨折与多种因素相关,其中跌倒和年龄是城郊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在城区中,父母髋部骨折史、跟骨超声骨密度低者更易骨折;在郊区中,户外锻炼活动量多是保护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我们应针对城郊居民骨质疏松性骨折各自特点及危险因素,预防其发生,提高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