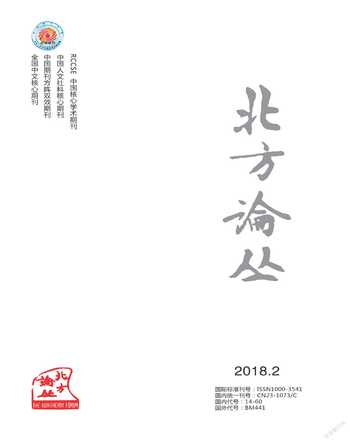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
杨柳
[摘要]北魏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从《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
[关键词]北魏;洛阳;《洛阳伽蓝记》;文学生活
北朝三书之一的《洛阳伽蓝记》,以地理为经,以史事为纬,记载了北魏京师洛阳近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同时也反映了北魏中后期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史意义。论者以为,这部佛教寺塔记,实乃“拓跋之别史”。该书也反映出,从平城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本文对此试做探讨。
北魏迁洛之后,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下,迎来政治经济繁荣昌盛的局面。洛阳城仅佛寺之盛,已令人震惊,《洛阳伽蓝记·序》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在文化方面,北魏统治者也开始变得自信起来,以正朔自居,而贬四方为蛮夷。文化学术开始兴盛,与永嘉之后北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状况不同,此期甚至于“斯文郁然,比隆周、汉”。《洛阳伽蓝记》卷二借陈庆之与杨元慎二人之口,道出其时北魏的雍容大气:元慎谓:“我魏膺篆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终使南来士人陈庆之叹服:“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土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填,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总之,因孝文帝大力提倡,并躬身力行,礼乐文化在中原复兴,洛阳重新成为文化重镇。
而随着北魏洛阳文化的复兴,文学也逐渐走向兴盛。迁都洛阳之前,因为北方长期陷于政争与战乱,文学之事可谓黜矣,间有作文,也是仓促之间,马上成文。《北史·文苑传》云: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迫于仓卒,牵于战阵”,形象地道出了北朝早期士人鞍马间为文的写作状况,所作也多为“章奏符檄”这种实用性极强,极具时效性的官方化文体,少有体物缘情的个人化书写。
北魏皇族本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尽管也知道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因而常常文武并提,但实际上,北魏早期并未能真正实现文武并治。在鲜卑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城时代,包括皇帝在内的上层社会在很长时期并未对诗歌文学有太大兴趣。皇室的宫廷宴会并不赋诗,而是举行射箭等比赛,全然保持游牧民族的风气,很多将领也对读书不屑一顾。但到洛阳时期,因为孝文帝“锐情文学”,文的分量甚至已超过武的比重,以至于孝文帝因“文武之道,自古并行”,而“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特作《讲武诏》。孝文帝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在选拔人才时,“文才”即是重要的考量标准。他曾多次诏告各地官员,对文思遒逸者,要以时发遣,唯恐遗漏。赢州刺史王质献白兔,托高聪作献表,竟令其惊呼:“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对于南来士人王肃等,孝文帝也颇为欣赏、倚重。《洛阳伽蓝记》载:“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洛阳伽蓝记》记载他对于文学的好尚,例如,对于前人的文学作品,孝文帝相当熟稔,《序》载:
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他更是满怀热情投人文学创作,引领了文坛风习,给北魏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魏书》记载,刘昶出镇彭城,帝赐以御集,曰:“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笑耳。”又赐崔挺文集,谓之“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时可观之。”冯熙葬日,“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帝以冯诞为司徒,“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代为谢章”。诞卒,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上迁至洛阳后,北魏文人转入相对比较稳定的城市空间,创作场所由锋镝之下、鞍马之间,转为安稳的朝堂之上、庭园之中,文学活动明显变得丰富起来,文学也不再只是军国文翰这样基本的实用性书写,而是回复了更多的可能,诚如《北史·文苑传》所云: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
由平城到洛阳,士人的文学空间和文学生活发生较大变化。浓郁的文化氛围,开放的城市空间,使得其时士人的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朝堂之上、君臣游宴之中已加人文学活动,而且统治者亲自组织、参与:
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日:“向宴之始,君臣肃然,及将末也,觞情始畅,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孝文帝身体力行,在君臣之间展开了联句、作诗等文学切磋与探讨。元勰的应诏诗显现出过人才华,令其大为赞赏,甚至评论道,勰之被举,乃为至公。勰“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诸弟之中,勰特受信重,孝文帝曾以丕、植兄弟相比拟,表示愿弃二曹“才名相忌”而当以“道德相亲”。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恐怕是重要原因。自先秦而来的赋诗言志传统亦被承继:孝文帝于太和十三年(489年)“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太和十七年(493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迁洛之后,此类活动愈多。孝文帝“至北邙,遂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
诗可以兴,在这类活动中得以体现。例如,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与群臣联句: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太和十八年(494年),高祖孝文帝发兵进攻南齐,这年年底,他亲自到达悬瓠,次年正月,于悬瓠方丈竹堂宴请随从群臣,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这些诗句均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以三皇五帝文德远被来自我期许,抒发谋求一统、辉光四表的政治怀抱,孝文帝诗句更显露出如日中天的气势:“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足见其乃以白日光天自喻,表达征服江南、混一区宇的豪情壮志。联句颇具兴发感动的效果,适足以令君臣之间互相激荡,士气得以鼓舞。
王公贵族的庭院、佛教寺庙,也俨然成为士人的文学活动场所。《洛阳伽蓝记》卷四载,临淮王或率宾客游于后园,常常“诗赋并陈,清言乍起”。卷二载,张伦的居室颇为豪侈,“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盗相属,深蹊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姜质《廷山赋》即是游张伦园林山池,爱之“如不能已”而作。洛阳伽蓝不仅建筑华美,内外环境也是景色秀丽,风光宜人,甚至奇花异草,莫不具备。例如,卷一景林寺,“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卷三景明寺“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寺内“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雷,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这些佛寺常有文人涉足。佛寺,不仅是佛事活动、官民游观之所,也是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场域,文人士子常在寺院游玩观光,吟诗歌咏。卷五载,凝玄寺,“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卷四宝光寺环境优美,“葭菱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常常选择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风雅一时。
诗可以“群”的功能在这样的文学空间里得以凸显。士人以诗文交游,表达情谊,相互交流、切磋。有些研究者提出,南朝士人和北朝士人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他们的创作、交流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南方的士人大抵居住在城市里。凡做官的人,多聚居于建康(今南京),如王、谢诸族,多在建康乌衣巷置有邸宅;不做官的人又在会稽(今浙东一带)置有别墅。他们的交往很多,经常集会作诗谈玄。北方的士族则绝大多数留居在家乡的“坞壁”之中,处于独学无友的境地。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北方文人对待创作的态度也与南方迥异。南方文人以文会友的机会很多,诗文往往公诸同好,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修改和补充。北方士人长期居住在“坞壁”之中,缺乏交流造成故步自封的心理状态。但据《洛阳伽蓝记》,起码在北魏洛阳时期,上述差异几乎不存在,文人之间不乏交流、品鉴活动。例如,该书载,元或的庭院雅集中,常常组织诗赋创作品鉴活动,依据品鉴结果进行赏罚:对优异者“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绯绸、绯绫者”。河东裴子明即因为为诗不工,被罚酒一石,“子明饮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可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云,江南文人作诗文,喜欢听取别人的批评,而北方文人却不然,反而会生气,从而告诫其子千万小心云云,仅为一时之印象。如《魏书·儒林·陈奇传》所载,游雅因为与陈奇不合,竞取陈奇所作《论语》《孝经》的注“焚于坑内”,并且禁止后生们听取陈的学说之类,恐怕还是北人快意恩仇的性格所致。
北朝士人的这些诗文酒会、风流雅集,足可媲美金谷、兰亭盛事,甚至生死也未能阻碍文人们的这种风流雅韵。《魏书·文苑》载,裴伯茂“少有风望,学涉群书,文藻富赡……好饮酒,颇涉疏傲”,可谓竹林七贤中刘伶一般人物。裴伯茂卒后,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余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醉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且各赋诗一篇。这次悼念活动,可谓他们对往昔饮酒赋诗雅集活动的纪念。《魏书》卷四十七还记载了一则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或钦爱之。及或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寺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今有梦,又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得梦之夜。
梦中以诗永别,“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简单而又悲戚。
据《洛阳伽蓝记》,当时还形成一些文人的群体,如清河王元怿周围当有一个文人群体,影响甚大,堪比梁孝王、陈思王:
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民。至于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垂,嘉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燕。
卷三记载,在邢子才周围俨然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才士群体:“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是以衣冠之士,辐凑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籍甚当时,声驰遐迩。”诗赋创作与交流成为这些文人群体交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据《魏书·阳平王熙传》载,元熙爱好文学,其身边也集结了一批文士:“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其因政治争斗失败而陷于穷途末路之时,以书信与诸友,忆及当日风流:“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
诗可以群,也表现在外交场合中。《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场发生在杨元慎与陈庆之之间的辩论,双方陈辞都颇具文采,直可视作一场文学活动。在这里,外交场合也是双方展现文学才华的平台。又,《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日:“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玩,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日:
“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这里记录了王肃与高祖及群臣的一次宴会,在鱼肉与羊肉、饮茶还是食酪这样的饮食习惯冲突的背后,是南北文化孰高孰低的文化较量。王肃在高祖面前以大邦小国比喻“羊”和“鱼”,以茗为酪奴,不免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种种微妙心理,而高祖以“习”字喻之,恐怕不乏调和矛盾之意。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不乏政治色彩的文化冲突,却是通过颇具戏谑性的文学活动进行的。君臣围绕“习惯”一事字说出七言押韵的譬喻,使得现场气氛和缓轻松、诙谐有趣。在民族文化的冲突中,这样的文学活动实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生活也开始呈现出个人化、情感化的倾向,“诗可以怨”,而不再是什么“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
一些文人以诗赋来对现时政治进行讽喻,也用诗赋表述政治上的失意与希冀。阳固《演赜赋》《刺谗》《疾嬖幸》,写出了昏暗的政治、官场的腐败,讥刺那些谗言、嬖幸之徒。拓跋顺《蝇赋并序》表达了对“名备群品,声损众伦”,“点缁成素,变白为黑”的苍蝇之属的鄙弃,批判谗贼之流把持朝政,以至于交乱四国,忠良遭害。袁翻于被贬官平阳太守之时作有《思归赋》,既是远离故国的凄凉:“望他乡之阡陌,非旧国之池林”,也是浮云蔽日的怅怨:“怅浮云之弗限,何此恨之难禁”,最后还是表达了“愿生还于洛滨,荷天地之厚德”的希冀。常景亦曾以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位古人自况,抒写政治上未能如意的愁闷与牢骚,以及“穷达委天命”的自我宽慰。《咏扬子云》诗云:“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北史》也记载,宋道琪为京兆2E'喻法曹行参军,坐愉反得罪,道琪作诗及挽歌辞寄之亲朋,以见冤痛。《元熙墓志》也写到元熙欲为元怿报仇,起兵诛元义、刘腾,反被元义所诛一事:“王临刑陶然,神色不变,援翰赋诗,与友朋告别,词义慷慨,酸动旁人。”其《将死与知故书》也是情深义重,悲戚酸楚,颇为感人:“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为己,吾何言哉!”其《致僚属》则表达政治争斗失败之后的秉持忠义不改的决绝心态:“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洛阳伽蓝记》还记载了元子攸、元恭作为北魏末年乱世中的悲惨帝王的遭际。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乃是彭城王勰的第三子。尔朱荣僭立为帝三年后,元子攸在文武百官的拥立下登上帝位,后诛杀尔朱荣。随后,尔朱兆举兵京师,于晋阳活捉元子攸,并将其缢死于城内的三级佛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这一段曲折而又悲怆的历史,并叙及孝庄帝临终作诗:
时兆营军尚书省,建天子金鼓,庭设漏刻,嫔御妃主,皆拥之于幕……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日:“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
节闵帝元恭,则在北魏末年政治的动荡之中,十年不语以避祸,却终未能逃脱悲惨的结局。他于元子攸之后被推上皇帝宝座,实际军政大权却掌握在尔朱兆手中,在此种情况下,只能强打精神,劝慰大臣们“君臣体鱼水,书轨一华戎”(《联句诗》)。而當他终于一年后即被高欢赶下台,被关押到洛阳崇训寺,他写下“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特别真实表现了北魏末年凶险动荡的政局,以及诗人心中万般的无奈:“时运正如此,惟有修真观。”
吟诗作赋,已成为此期北朝士人表达情意的一种自觉习惯。夫妇、兄弟、友人等私人性情谊,有时便用诗文来表达。《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归顺北魏,其南朝之妻谢氏来奔肃,而此时王肃已尚北朝公主。南北二妻,以五言诗的形式角力,用比兴表述心意,谢诗委婉缠绵,公主所作则大胆泼辣、当仁不让: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谢氏的五言诗里包含很深的哀怨和讽刺,“丝”“路”“胜”皆有谐音双关之意,幽凄婉转,正见出南朝文学擅用比兴的长处。难能可贵的是北魏公主的答诗承谢氏之比兴而来,浑然天成,说明其对比兴手法运用娴熟,但其语气则强硬不容商量。
《北史·彭城王勰传》记载到孝文帝与其弟元勰通过诗歌传达幽微的心意:
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韃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示勰日:“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孝文帝与元勰,既是君臣,亦是异母兄弟。孝文帝要求勰效仿曹植七步作诗,元勰文思敏捷,所作“问松林”一诗挟风云之气,即景而慨叹历史之沧桑、宇宙之混茫,颇具风骨,意境苍茫。而最后一问“风云与古同”,语带双关,既唤起对古今变化的拷问,又将曹丕曹植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典故暗蕴其中,颇具谲谏意味。孝文帝正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故大笑曰“此诗亦调责吾耳”,后即下诏:“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书监,侍中如故。
此期北朝人诗文中的友情,也令人感动。元熙于政治斗争失败之际,以诗赠袁翻等友人,表达人生失意的悲痛,显现出知交之谊情深义重:“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北人本不屑儿女情长,歧路言离,欢笑分手,不像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记载的江南习俗:“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但南安王桢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于华林都亭为之设宴饯行,孝文帝为之饯行,并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颇具怅怅离别情怀,并命众人赋诗作别。咸阳王禧将还冀州,高祖亦“亲饯之,赋诗叙意”,元澄“从行征至悬瓠,以笃疾还京”,孝文帝“饯之汝汶,赋诗而别”(《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成王元澄传》)。《魏书·阳平王熙传》载,中山王熙“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诗也常常为此期文人用作戏谑、游玩,诗可以乐。前所引《洛阳伽蓝记》载孝文帝君臣与王肃之间关于“羊”和“鱼”,茗与酪之高下的争论中,也足见出其时人对艺术语言的自觉,不只是当其为工具、津梁,得意而妄言,而是探究如何以妙言传意,更注重享受语言带来的美感与乐趣。这可与《晋书》记载的一则故事相参看:
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座,共作了语。恺之先日:“火烧平原无遗燎。”玄曰:“白布缠根树旒旒。”仲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仲堪眇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
可见魏晋南北朝人对语言之美、之趣的发现与享受,诗亦可为乐。
在这些文学活动中,颇有些文人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例如,《洛阳伽蓝记》载,荆州秀才张斐预于临淮王或组织的雅集活动,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清新别致,不让于南朝诗歌。孝庄帝的临终诗歌与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在思想、意象、意境等方面亦有著共通之处。诗歌表现出对于死亡的哀叹。其中,“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与陶渊明的“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与陶诗“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可谓异曲同工。前文所提及的姜质游张伦园林而作《庭山赋》,因文辞鄙俗而为人所嗤笑。姜质其人史书无传,《北史·成淹传》提到:“子霄,字景鸾,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庭山赋》的确文辞粗陋,但于此亦可见时人对文学的热情,而对于诗赋,时人能识别其鄙俗,可见北方士人实已具备较高的文学欣赏水平。
总之,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空间发生较大变化,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较为浓郁的“尚文”风习。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