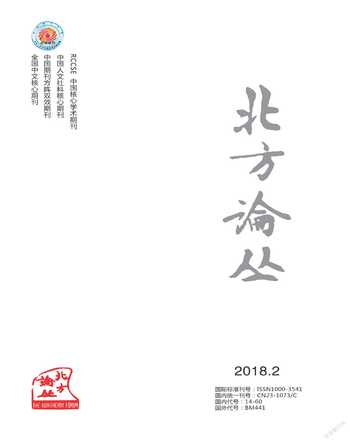《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刘秀玲 刘书惠
[摘要]《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非儒;《易经》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内含丰富的儒道佛哲学思想的名著。不过,小说对于道佛和儒家哲学思想的艺术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对于道佛思想,小说以小说人物普遍接受认同,日常慎重礼待,甚至把道佛修行作为情感寄托和人生归属选择来呈现;对于儒家思想则是以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反对立的情节描写来表现,体现出鲜明的非儒思想倾向。而恰恰是后者“体现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包含着近现代的思想因素”,使小说思想更具时代性和社会进步意义。因此,《红楼梦》儒家思想研究应该有非儒思想的辩证分析。而早期儒家思想的确立与汉以后儒学的发展演变都离不开对《易经》的认知和解读,《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始终引导与影响着儒学的发展进程。所以,《红楼梦》儒家思想研究也应该有小说非儒思想易理接受关系探讨。
一、“言情”主旨与“重礼抑情”思想倾向
《红楼梦》大旨“谈情”,小说把人之情性描写放在第一位,把建立一个纯真“有情”世界作为主人公的生命理想追求,这与儒家传统的“家国至上”文化情怀、“克己复礼”道德规范相违,而且向“重礼抑情”的文化理念和精神信仰提出挑战。
中国有“德治”和“礼治思想文化传统。原始儒家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主张通过“礼”的规范,制约人的“情性”,以达到拥有“仁”的社会理想状态,这一思想是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础。而在中国的“德治”和“礼治”思想文化传统中,原始儒家“克己复礼”“当仁不让”“杀身成仁”等思想主张的传承,也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家国利益至上”责任意识和“重禮抑情”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重礼抑情”思想文化传统形成,儒家角度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原始儒家创始人孔子一心构建以“仁”为核心的大同社会,一生致力于和谐规范的政治体制构建的实践。孔子高度重视“礼”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士一年》)社会规范作用,并高度赞美“周礼”的周全和完备。“孔子创立儒家,其对周礼的注重直接导致儒家思想中以礼为中心的社会格局设想以及儒家治世安民措施的提出”。并且在情礼关系方面,孔子也有明确的思想主张,如《论语·八佾》载孔子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表明真实的感情是礼之本的观点;而《礼记·檀弓上》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则说明孔子主张以礼制为重,不能因情坏礼,具有“以礼抑情”的态度倾向。即原始儒家主张“礼虽然源于人的感情,但礼并不以人情为目的;相反,礼源于人情,但同时又要制约人情。也就是说,情要以礼为范围、标准”。基于情礼关系认知,儒家在和谐社会构建理念中,强调作为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的礼的重要,明确应该有“家国至上”责任意识,有“当仁不让”“杀身成仁”精神品质。而这恰恰表明“儒家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地位,而是用礼来制约人,使人在无意识中自然地服从礼的规范”。
二是受《易经》“整体观念”和“适度节制情感”态度影响。《易经》中八卦是承载阴阳变化的自然大环境,六十四卦是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自然小环境,阴阳和谐不断变化使得自然社会大小环境周而复始相交互动。所以,《易经》展现自然整体观念,有遵阴阳变化规律使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的思想内涵。同时《易经》也具体阐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和谐之道,如《易经》比卦之“比”其含义是“亲密比辅”,从《易经》立比卦的宗旨来看表达和睦相处、互相帮扶的思想,传达对内和睦亲善得平安吉祥,对外和睦交往得国泰民安的“和谐”意愿;《易经》中孚卦阐述“心中诚信”的道理,传达心之诚信贯通天人物我之意,可作为儒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主张的思想源泉;《易经》观卦强调观察主客双方情况的重要,含有为上者以美德感化于下,观民风正君道的思想,所以观卦又可看作儒家“以人为本”,决定社会施政方针的思想萌芽,等等。原始儒家又进一步在《易传》中提出“太和”观念,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传》)由于儒家和谐社会建设理念形成有《易经》哲学认识基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家国至上”责任意识、“克己复礼”道德规范、“重礼抑情”政治态度,寻根溯源具有《易经》思想认识来源。
《易经》有“利在于守正”的情感态度。《易经》咸卦卦辞,从广义看阐明事物普遍的“感应”之理,从狭义的角度看则是侧重揭示男女交感之道。咸卦以人事喻谓男女“交感”之理,从其爻辞看咸卦是强调“感”止于“正”必吉,悦以能静为宜,意在告诉世人感通以“正方”为婚媾之善,而不能达到“心灵”的感通皆是应该谨慎的道理。还有《易经》困卦,象征困穷之态,其卦象有男女失正,面临险难而内心愉悦的表征。从其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上六爻辞“困于葛菇,于脆兀危;日动悔有悔,征吉”。可以看出处于此种情状中是很难自拔的,结果必然是会陷入麻烦与烦恼之中,从中表达“不当位”的情感行为在现实社会中会受到诟病,产生问题应该禁行的道理。基于对《易经》“适度节制情感”的认识,原始儒家提出“利在于守正”的情感主张,强调要把情感控制在适度的范畴之内,所谓“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序》)。因为“人的精神不是自足自觉的,而需要以天道治之,包括节制理性之要求。事实上,儒家正循此脉络展开”。
原始儒家的“重礼抑情”文化思想是人之社会性的体现,符合社会和谐相处的现实需要。但原其“家国至上”责任和“适度节制情欲主张,在后世儒家传承中出现了机械僵化情况,导致其规范意义强化人性关怀成分削减。宋明时期统治者利用宋儒所提“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之天性大开杀戒,以致出现“守节”和“愚孝”畸形社会问题。而思想僵化和极端道德束缚必然引发社会思考和批判。明末清初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明确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在此社会背景环境下,曹雪芹则大胆扛起言情的旗帜,通过小说创作来揭露僵化儒学“以理杀人”的伪善。由于“《红楼梦》‘大旨谈情在思想倾向上与晚明李贽、汤显祖等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们的尚情观念有着较为明显的传承关系。李贽、汤显祖们张扬‘谈情‘至情‘情教‘唯情等思想观念,借此与‘存天理、灭人欲理学道统观念对峙”,因此,在《红楼梦》中可见贾宝玉是“情”的守护者,是一个爱的化身。同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力量,也召唤社会的变革和人性关怀的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却是一篇为情而战的宣言。这份宣言不是针对原始儒家的“适度节制情感”主张,而是针对后世儒家机械僵化的思想和封建统治者借刀杀人的暴行而发出的。
二、“崇女贬男”态度与“男尊女卑”等级观念
“男尊女卑”等级思想是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产物,其体现了社会分工和劳动力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在中国“男尊女卑”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民族心理根深蒂固。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男尊女卑”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当权者利用其结构社会政治制度,构建封建道德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从‘天道出发,为‘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等级格局寻找合理性证明,使之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真理”,使得中国“男尊女卑”为核心的等级制度有理可据,达成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想共识。而《红楼梦》开篇作家即言自己的创作动机是放不下心中“行止见识,皆在我之上”的女子,即便“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也要把她们一一记录下来“使闺阁昭传”。贾宝玉的“男女生成论”,在“内帷厮混”的种种作为,以及小说所描写的贾府男女人物在品行才情上的差异,都说明作家有鲜明的“崇女贬男”思想倾向,并且向封建等級思想观念发出挑战。
中国儒家封建等级思想,深受《易经》“阴阳之道”影响。首先,《易经》哲学中有循序而动思想,《易经》八卦序列及六十四卦卦序,体现宇宙构成成分存现关系,体现人事变化的顺序;《易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分处高低不同的位次,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位置,体现地位、条件、身份等高低不同的秩序,提示不同卦位和爻位的对象,要自我定位,审时度势,依序顺理行事获吉福的道理。原始儒家认识到《易经》依序而动思想的客观性普遍性,对其进行社会秩序层面的分析,提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彖传》)这种社会伦理主张,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结构体系。其次,《易经》阴阳属性的分类为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体系建立提供了依据。《易经》乾坤两卦是六十四卦的母卦,乾卦纯阳坤卦纯阴,两卦相错生成六十四卦如同男女交合人类产生一样。乾卦天性为健,坤卦地性为顺,揭示人类社会中男人要走乾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女人要走坤道驯顺温柔包容博大。据此,在深入解读六十四卦的基础上,《易传》对于自然和社会秩序有了基本认识,即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系辞上》)。这里的“天尊”是指君子要像天一样追求高远自强不息,“地卑”是指女子要像大地一样谦虚、包容厚德载物。“贵贱”是指人所处的社会层级和位置,而非男女天性有好坏、尊卑、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在原始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观念中,其内涵是男女各顺其性、各司其职,本质上男女人格是一种平等关系。
中国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确立,也有《易经》认知基础。《易经》受时代的限制言少义晦,阴阳顺性解释不够具体明确,这为后世误读甚至改变“男尊女卑”本质提供了可能。《易经》揭示乾卦“具有开创万物,并使之亨通、富利、正固这四方面的‘功德,意在表明阳气是宇宙万物的‘资始之本”(《周易译注·乾卦统论》)。同时乾坤是一对互为矛盾的卦,坤卦继乾卦之后,寓有“地以承天”“天尊地卑”之义,在一卦的阴阳互为矛盾的关系中,阴处于附从的、次要的地位,依顺于阳而存在、发展。所以在易理上体现阴柔阳刚、阴弱阳强特点,揭示阴顺阳、阳凌阴为当位的道理。据此,延伸到社会层面,很容易被理解为男强女弱、女性依附服从男性为正道。加之原始儒家在解读男女关系方面,观点主张阐述不够明确,也造成“重男轻女”思想的强化,如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篇》)。孔颖达在《论语正义》中解释为:“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逊)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朱熹则在《论语集注》解释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淮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此两解意义相去不远,皆有明显的贬损女性之义。
原始儒家的等级思想体现了对现实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为大同社会实现提供了认识基础和思想保障。纵观中国封建制度,在战国末期大体形成,到东汉初年正式提出三纲说,汉代之后等级制度越来越森严,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思想的确立,将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而失去了仁、中庸思想内涵的等级制度和思想也必然导致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畸形发展。明清两代当权者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倡导极端的贞节观念,对女性提出“当终受于从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极端道德要求。而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加之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人中国,使得人们的眼界开阔思想活跃。于是清朝时期出现“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如李贽以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大加痛斥批判,对于社会上“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指出:“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中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
曹雪芹通过小说创作对“男尊女卑”封建等级思想发出挑战。在小说中,贾宝玉尊重女性、保护女性、赞美女性,坚决反对蹂躏、践踏女性。在“芙蓉女儿诔”中,贾宝玉评价晴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把女儿推崇到至高至极的地位。不仅如此,小说中的贾宝玉对待下人全然没有一点主子的架子,他与秦钟交友告诉他不分叔侄,就论兄弟朋友;他对贾府的那些小厮,欢喜时没上没下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谁也不理谁。基于此,贾宝玉在大观园中“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而“不带色欲、肉欲色彩的怜香惜玉,这在中国古代生存场中,从来都是一种男性主体十分稀缺的品质。男性出于人际间的自然感情而不是性欲需要与女性建立情感关系。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男尊女卑天理的背叛”。而小说中所体现的男女平等思想,应该与《易经》“各尽其职、各守其份”阴阳之道是一脉相通。
三、“自然随性”与“积极有为”
《易经》揭示乾卦天性为“健”,坤卦地质为“顺”。《易传·象传》解读乾卦义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义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易传·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意在表明宇宙是阴阳消长充满无限生机,不断变化流转、生生不息的整体,启发人们应在人世间积极有为、刚健自强、穷通思变。原始儒家秉持《易经》阴阳运行之道,奋发努力尽自己的人伦义务和社会责任,展现出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红楼梦》开头就暗示主人公是一块“无才补天,幻化人世”的顽石。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贾宝玉一个既无“补天之才”,又“顽石”性十足的人。一方面他“潦倒不通事务,愚顽怕读文章”,对于光宗耀祖走仕途经济的规劝十分排斥,对于“文死谏”“武死战”的儒家忠君思想大放厥词;另一方面,他又“行为偏僻性乖张”,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率性而为全然不顾身边人的指责非议。所以从儒家角度看,贾宝玉是儒家积极人世思想的“槛外人”。“他既不克勤克俭,遵循那平庸可怜的仕宦传统;也不酒色昏迷,混入那荒淫得可耻的纨绔之群;他表现出一种逸出常规超脱现实的畸形姿态”。
但小说中的贾宝玉却是一个“无事”忙的人。贾宝玉要建立一个充满爱的“有情”世界,“情”洋溢在他的心中,也散发到他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大观园内外,贾宝玉不仅对自家姐妹细心体贴,对待地位低的丫鬟仆人也关怀爱护,还把对人的爱意扩展到自然中。他会在极不堪的繁华中想到去望慰小书房中寂寞的画中美人;斗草后女儿们丢弃在地的并蒂菱蕙,他会独自用心掩埋平服。小说第三十五回写贾宝玉“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浓浓的”。甚至为了情,贾宝玉不惜委曲求全,小说第二十五回,贾环为暗算宝玉“把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给宝玉造成了伤痛。怕贾母对赵姨娘母子动怒,贾宝玉把事情承担下来,说:“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贾宝玉的心目中只有“情”没有“恨”。“贾宝玉不知疲倦地爱人、寻求爱,把与周围的人建立一种亲情关系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为的就是建立一个充满“情爱”的快乐世界。由此,虽然从儒家角度看贾宝玉,他是一个任性乖张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之人,但从贾宝玉对于“有情”世界的构建实践来看,他却是一个执着努力坚持不懈的人。这种执着和坚守集中体现了贾宝玉刚健进取风范,也从中可见《易经》哲学“自强不息”精神品质。
曹雪芹经历过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衰落后的贫困潦倒,深刻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他对于所谓的儒家正统思想有理性的评判,體现出“人世有为”的生活态度。小说开篇即说“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来记录自己“曾历过的一番梦幻”。即便面对僵化儒学的禁锢,曹雪芹依然执着地探寻本真,竭力构建有情有理的理想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生命本真与自由的追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凤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于是在《红楼梦》中有大观园有情世界的描写,有贾宝玉对于仕途经济的深恶痛绝,有愤然弃世出家的决绝。而“《红楼梦》之所以感人,也正是它看破色相之后仍有大缅怀,大忧伤,大眼泪,即放弃一切身外的追求,但仍有对‘情义的大执着,不仅有爱情的执着,还有亲情的执着”。而曹雪芹的这份理想追求和信念执着,可以说正是几千年前《易经》刚健自强精神的情感转化和文化传承。
“《红楼梦》将拒天理进一步延伸到对封建社会核心观念补天济世、仕途经济的拒绝,具有时代特点和人文关怀的品质。但文化观念的传承往往是复杂的,其过程往往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有保留,有批判,有摒弃,也会有新的开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小说的精神主旨之一,这是没有疑问的。也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作为个性化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艺术的表达,还有独特的哲思。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包括对儒家学说理念的继承和批判,《易经》是《红楼梦》的重要思想渊源,分析小说哲学思想与《易经》哲学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可以深人理解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对情理关系的深沉思索,并进一步感知《易经》普世价值的持久生命力,挖掘出《红楼梦》儒家批判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