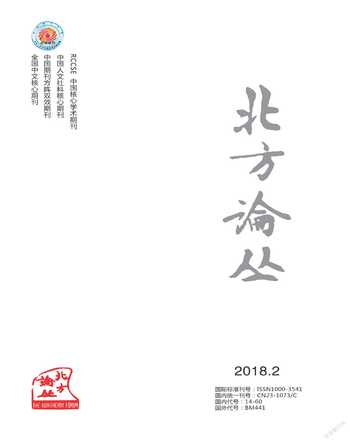时空与食事:宋元明时期的饮食谱录及其所蕴含的社会饮食风尚
王汐牟 王强
[摘要]饮食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更加细节的呈现。宋元明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到顶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数量众多的饮食谱录编撰成书,是宋元明时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的产物。不同时期饮食谱录的编撰体例和内容,既是社会与时代特色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宋元明三代各具特色的社会饮食风尚。
[关键词]宋元明时期;饮食谱录;社会饮食风尚
饮食谱录作为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饮食中最直接、细致、真实的载体。宋元明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持续向前发展,而彼时亦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数十部饮食谱录问世。通过分析宋元明饮食谱录大规模编撰成书这一文化现象,探讨其中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社会饮食风尚及其时代特征,同时也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细节之处丰满宋元明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
一、宋元明时期饮食谱录编撰概述
宋元明时期,饮食谱录的编撰成为一股社会风潮,出现了三十余部与饮食相关的谱录典籍。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专门记述饮食制作的食谱以及综合谱中的饮食制作内容上。如下表所示。
宋代的饮食谱录相当丰富,根据《宋史·艺文志》《通志·二十略》,以及其他文献记载,这一时期诞生了15部46卷与饮食谱录类典籍。不过,目前存世的只有郑望之所著《膳夫录》、司膳内人《玉食批》、林洪《山家清供》、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四者中,《膳夫錄》主要记录了隋唐时期的饮食,“很可能是宋人随手抄录有关烹饪的一些记录,作为备忘录之”。而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和林洪《山家清供》则内容、体例相对完整,所以,在此主要以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和林洪《山家清供》为代表对宋代的饮食谱录做一探讨。
《本心斋蔬食谱》,又名《疏食谱》《说郛》《山居杂志》《千顷堂书目》,以及《丛书集成初编》等书中都将之归于陈达叟名下,但《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言道:“明汪士贤《山居杂志》载此书,题日清漳陈达叟撰,不著时代。《千顷堂书目》亦作达叟,题日宋人。考左圭《百川学海》载有此书,则宋人无疑。然《百川学海》所刻,其序自称本心翁,而书前标题乃作门人清漳友善书堂陈达叟编,则达叟乃编其师之书,非所自撰也。所载食品二十种,各系以赞,皆粗粝草具,故日疏食。《千顷堂书目》加草作蔬,失其旨矣。”如四库馆臣所言,《本心斋蔬食谱》虽在陈达叟名下,但他只能算作一个编书者,真正的作者乃是其师本心翁。邱心诚在《本心斋蔬食谱作者考略》中进一步考证本心翁为两浙西路建德府淳安(今杭州淳安)人夏讷斋。
《山家清供》作者林洪为南宋后期泉州晋江人。《说郛》卷22中收录的《山家清供》文前有“宋林洪字龙落号可山人和靖先生裔孙”字样。《山家清供》记录了南宋泉州地区的104种有名的食谱,主要是山野人家的清淡饮食,以蔬菜、粮食、水果、花卉为食材,制成食物。
承继宋朝政治统治的是元朝。元祚虽短,但也诞生了《饮膳正要》
《饮食须知》和《馔史》,以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等饮食谱录。
《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四库全书》中称其为和斯辉)是元廷蒙古族饮膳太医,其成书并进呈朝廷是在元代天历三年(1330年)。该书共三卷,主要是从养生、食疗、饮食禁忌等方面记述元宫廷饮食,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
与《饮膳正要》比较,《饮食须知》所重尤在养生。作者是浙江海宁人贾铭。此书可谓是贾铭一生饮食经验的总结:“书中所载,自水火以及蔬果诸物,各疏其反忌,皆从诸家本草中摘叙成书。自序谓物性有相反相忌,《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相半,令人莫可适从,兹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全书八卷,主要从“慎饮食”的观点出发,记述水火、谷类、菜类、果类、味类、鱼类、禽类、兽类等食物的性味、反忌、毒性等,非常实用。
无名氏《馔史》见于《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食之属的存目。书虽名日《馔史》,但内容乃“杂记饮食故事。所采如《酉阳杂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类,大抵习见”。且内容颇“支蔓”,多“与馔无涉”。四库馆臣们还认为,此书“旧本题日元人,亦臆度之也”。所以,从中难以窥见元代饮食风貌。
至于倪瓒《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乃元末著名画家倪瓒所录自家食谱,其中所收50余种菜肴制作方法,大致能反映元代江南地区的饮食风貌和文人情趣。明代饮食文献更为丰富,“反映饮食水平的综合性著作有《易牙遗意》《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遵生八笺·饮撰服食笺》《闲情偶寄·饮撰部》,以及《寂园杂记》《升庵外集》《明宫史》的饮食部分”等。《四库全书》子部谱录食谱之属还收录了韩奕的《易牙遗意》以及无名氏编撰的《天厨聚珍妙馔集》等。其中最典型者为《易牙遗意》《天厨聚珍妙馔集》和《宋氏养生部》。
《易牙遗意》的作者韩奕,生于元文宗之时,明朝时隐居不仕,因推崇名厨易牙,故以为书名。《易牙遗意》共2卷,介绍了酿造、脯鲜、蔬菜、笼造、糕饼、炉造、汤饼、斋食、诸汤、果实、诸药等11个门类,收录了150多种调料、饮料、面点、糕饼、菜肴、蜜饯和食药的制作方法,内容非常丰富。但关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周履靖校刊,称为当时豪家所珍。考奕与王宾、王履齐名,明初称吴中三高士,未必营心刀俎若此,或好事者伪撰,托名于奕耶。”即认为此书或是韩奕仿照《古食经》所为,或是别人编撰而托名韩奕,不足为据。
宋诩《宋氏养生部》,从体例和内容上也可以看作明代饮食谱录著作。宋诩是明代松江华亭人,但书中记录的饮食做法不仅仅局限于松江口味,还包括了许多北京菜。他的母亲朱氏在宫廷显贵府中做官厨,后来就将生平食谱教给了宋诩。全书分为6卷,第一卷是茶制、酒制、酱制和醋制;第二卷是面食制、粉食制、蓼花制、白糖制、蜜煎制、糖剂制和汤水制;第三卷是兽属制、禽属制;第四卷是鳞属制、虫属制;第五卷是菜果制、羹制;第六卷是杂造制、食药制、收藏制、宜禁制。
而《天厨聚珍妙馔集》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该书作者早已不知是谁,四库全书中也只是存目而已,内容今人已不得而知。
二、宋元明饮食谱录编撰的时代特征
宋元明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商业繁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一时期所编撰的饮食谱录在我国古代饮食谱录编撰的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代饮食谱录的传统;另一方面,对于清代饮食谱录的进一步发展和总结具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是谱录数量增加,种类也更加丰富。宋元明时期的饮食谱录在数量上有着显著增加,种类也越来日趋丰富。除去茶谱、酒谱外,宋代编撰成书的饮食谱录有《本心斋蔬食谱》《山家清供》,元代则出现了忽思慧《饮膳正要》、贾铭《饮食须知》、倪瓒《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以及一部无名氏编撰的《馔史》,明代则有韩奕的《易牙遗意》《天厨聚珍妙馔集》《宋氏养生部》等。
此外,宋元明时期出现的动植物谱录以及其他谱录中有相当部分是记述以其作为食物原料进行加工和制作的,如宋代赞宁的《笋谱》、蔡襄《荔枝谱》、傅肱《蟹谱》、韩彦直《橘录》、王灼《糖霜谱》、高似孙《蟹略》、陈仁玉《菌谱》,明代朱橚《救荒本草》、王磐《野菜谱》、潘之恒《广菌谱》等,也从侧面反映出宋元明时期饮食谱录典籍的丰富。
其次是体例结构上的日益成熟。在体例结构方面,由宋至明的饮食谱录编撰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分类、编写结构的日益清晰和著录内容的日益丰富上。
宋代陳达叟《本心斋蔬食谱》相对简单,书中总共记述了20种蔬食食谱,每条食谱以非常简略地语言介绍了原料和制作方法,并附有16个字的赋。如同书中第一条“啜菽”的记述:“菽,豆也,今豆腐条切淡煮,蘸以五味。礼不云乎,啜菽饮霠。素以绚兮,浏其清矣。”书中所著每种蔬食也是寥寥几句。
林洪的《山家清供》从内容上来说比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略显丰富,书中记载了一百多种食谱,包括菜、羹、汤、饭、饼、面、粥、糕团、点心等。每种食谱下都详细记述了食物的名称、用料、制作方法,其中还夹杂着掌故、诗文。如书中第一条“青精饭”的记载中,从青精饭的原料食材青精、粳米到做法,再到《本草》中的食疗效果,以及杜甫关于青精饭的诗都详细记录下来。
元代饮食谱录在体例结构有进一步发展,内容较为丰富。《饮膳正要》全书共3.1万余字,第一卷记录有三皇圣纪、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和聚珍异撰94种,每种下面均细细说明其食疗效用、材料、调味品、烹调技术。第二卷则记录有诸般汤煎55方、诸水3种、神仙服饵24方、食疗诸病61方,以及四时所宜、五味偏走、食物中毒、禽兽变异等内容,主要是养生保健的饮食和制作方法。第三卷主要是关于食物的原材料的,其中谷品43种、兽品31种、禽品17种、鱼品21种、果品39种、菜品46种、料物28种,一共200余种。每种下面都以文字介绍其性味和作用,甚至绘图加以说明。贾铭的《饮食须知》以“慎饮食”为中心,从水火、谷、菜、果、味、鱼、禽、兽等八个方面介绍了360多种食物的性味、相反禁忌、多食造成的病症、还有食物有毒的形态特征和解毒的方法,体例清楚,结构清晰,内容详尽。
至于明代的饮食谱录在体例结构上已经成熟,所记内容也十分详备。韩奕的《易牙遗意》和宋诩的《宋氏养生部》,不仅将食物的原料、调料、烹制方法以及用量都一一记述下来,而且菜肴、面点、汤、蜜饯等各类食物都包括在内。
三、宋元明饮食谱录蕴含的时代饮食风尚
由宋至明700年的时间,经历了北宋、南宋的沿袭、元代蒙古族的统治以及明代长期的统一。品评诸谱录中的内容,每个阶段的饮食谱录都带有各个时代独有的烙印。
以《本心斋蔬食谱》《山家清供》为代表的宋代饮食谱录,从表面上看体现了宋代社会追求清淡简朴的饮食风尚,但细品之下发现其中带有士大夫文人不予世俗人同的心性意趣。如《本心斋蔬食谱》中所记山药的做法:“玉延,山药也,炊熟,片切,渍以生蜜。”不过是将山药煮熟、切片然后用蜂蜜腌渍,与民间食用方法几乎无异。但随后附上的16字:“山有灵药,录于仙方,削数片玉,渍百花香。”却让这本简单的蔬食谱带有一种饮食中的情趣。这也正是此书序中本心翁所要表达出的“无人间烟火气”。
林洪《山家清供》看似主要以蔬菜、水果、花卉做食物原料,制作方法也是一般百姓家中常见做法。但其行文中对于清淡饮食的介绍,却都带有一种借饮食抒发情怀的意味。如书中记载的以芹菜为原料制作的碧涧羹:“既清而馨,犹碧涧然。故杜甫有“青芹碧涧羹”之句。或者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诵咏之?不暇不思,野人持此犹欲以献于君者乎?”古人有美芹之献的典故,诗圣杜甫又有“青芹碧涧羹”的诗句,南宋词人辛弃疾撰抗金救宋十计取名《美芹十论》,而《山家清供》中,不仅记芹菜的做法,还缀以前人诗句,使这道农家野味变身为文人品评的雅意山珍。而且作者笔下的水果、花卉如山桃、梅花、菊花等都可以成为食材,以梅花汤饼为例,梅花汤饼有梅花之香、梅花之形;梅花在文人雅士心中本性高洁,梅花汤饼自然是《山家清供》中的一道不可缺少的美食。
宋代是文人士大夫群体迅速扩大、文人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其时,文人士大夫主张简朴清淡的饮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的品性修养方面,《山家清供》中作者直抒胸臆:“吴中贵家,而喜与山林朋友嗜此清味,贤矣”?“以松黄饼供酒。陈角巾美髯,有超俗之标。”二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考虑。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对于饮食和养生都有独到的见解,苏轼曾经写过《养生说》《节饮食说》,黄庭坚也作《食时五观》一篇,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蓝田玉”一则就表明了他的养生观点:“长生之法,能清心戒欲,虽不服玉,亦可矣。今法用瓠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烂蒸以食之。不烦烧炼之功,但除一切烦恼妄想,久而自然神气清爽,较之前法差胜矣。故名法制蓝田玉”;即不用烧制丹药,戒除私欲,就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
至于成书于元代的《饮膳正要》既体现了元代宫廷和贵族的民族饮食的特色,也展现元代社会饮食的多样化。元代统治者是蒙古族,统治疆域也十分广大。虽然元朝仅1个世纪的时间,但其独特的饮食文化却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所编撰《饮膳正要》具有鲜明的民族交流、中外交流融合的特点。张元济曾为此书再度出版所写的跋语中说:“其书详于育婴妊娠饮膳卫生食性宜忌诸端,虽未合于医学真理,然可考见元人之俗”。
《饮膳正要》具有明显的蒙古族饮食的特色。第一卷中的聚珍异譔类中的食谱几乎大半都要选用羊肉或者羊的内脏。有学者对此作了统计:“以聚珍异撰为例,共载95方,其中55方突出了羊肉的用量,另有21方还用了羊的心、肝、肺、肚、肠、髓、脑、头、尾、肋、月圣、蹄、皮、肉、血、乳、酪等,共計76方与羊品有关,占该类方的80%。”_90羊肉是蒙古族的传统主食,进入中原后,一方面接受了中原地区的饮食;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以羊肉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此外,《饮膳正要》中还记录了许多欧亚其他地区的饮食情况。比如,卷一“聚珍异馔卷”中的“八儿不汤,系西天茶饭名”,“西天”在此是指“西域,包括中亚细亚及南亚次大陆在内,为古代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经历之处”,八儿不汤即是自古代印度传人的饮食。
在宋元明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明代社会生活中的饮食开始走向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高峰,这在饮食谱录典籍中的表现就是饮食品种的全面化和丰富化,以及饮食文化的奢侈化和精致化。
韩奕《易牙遗意》中记载了150多种食物的制作方法,从调料、饮料、糕饼到面点、菜肴、蜜饯、食药几乎无所不包。其中百姓生活中的炉灶类面点就有“椒盐饼、酥饼、风消饼、肉油饼、素油饼、烧饼面枣、雪花饼、芋饼、韭饼、白酥烧饼、薄苛饼、卷煎饼、糖榧、肉饼、油饺儿、麻腻饼子”等。而《宋氏养生部》的编撰源于作者宋诩要知天下之味,他“世居松江,偏于海隅,习知松江之味,而未知天下之味竟为何味也”。书中汇聚了南北饮食,内容极为丰富,记录有四十多种面制品、三十多种蜜饯、百余种的禽肉水产的菜肴以及各种各样的饮食制作方法。
在饮食品种的全面化和丰富化的基础上,明代社会的饮食文化开始向着奢靡精致的方向发展,而且越演越烈。正如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写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纵绮,通晓歌舞之场,半丹床笫之上……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究其原因,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繁荣,商品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结构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富商大贾,生活极度奢侈淫靡,“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鲤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辨也”。一般士绅甚至寻常百姓也深受这种奢靡饮食风气的影响,“绪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奢侈的饮食风气之中,只有极少数士大夫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在精致的同时沿循着文人的雅致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