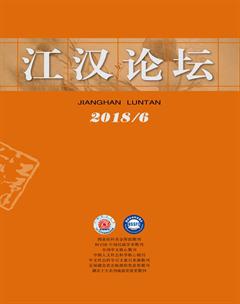讲故事的伦理:从史诗到小说
周莉莉 赖大仁
摘要:在西方讲故事的文学体裁中,史诗和小说最具代表性,它们的故事常常以对善恶伦理的精彩呈现而著称。它们呈现善恶伦理的魅力,不仅来自于故事中人物引人入胜的善恶交织,而且还来自于潜藏于其中的讲故事的伦理。“客观性”是赞赏它们讲故事的伦理时最常用到的词语,但是,同样的“客观性”在史诗和小说中却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从史诗到小说,讲故事的人从吟诵诗人到隐含作者,讲故事的方式从有声的讲述到静默的书写,“客观性”已从尊崇神意的客观,转变为个人意识对话的客观。
关键词:史诗;小说;讲故事的伦理;客观性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当代美国历史小说的记忆伦理研究”(项目编号:WGW162006);江西省高校“青马工程”专项课题“韦恩·布斯的小说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6QM27)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79-06
在西方文学中,史诗和小说都是备受人们喜爱的叙事体裁,它们中许多精彩纷呈的故事成为了不断传承的文学记忆。在这些故事中,善恶的冲突备受关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其津津乐道、印象深刻。在叙事作品当中,与善恶相关的伦理话题,其实涉及两个层面,因为“所有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①。也就是说,读者所谈论的善恶,关涉到故事中人物的伦理和讲故事人的伦理。故事中人物的伦理表现人物的伦理观念及行为,而讲故事的伦理则是讲故事的人将故事讲好的伦理立场。
无论史诗还是小说,故事中引人入胜的伦理意蕴,都是人物的伦理和讲故事的伦理共同产生的效果。其中,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像人物那样,具有易于辨识的善恶特征,即使他们以人物叙述者的身份出现,也有区别于人物价值观念的隐藏的伦理立场。讲故事人的伦理立场以“客观性”最受推崇,即讲故事的人客观地呈现人物的善恶,在故事中保持中立的伦理立场。但事实上,从史诗到小说,讲故事人的伦理都并非完全没有善恶倾向,它们的“客观性”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导向。从史诗的吟诵诗人,到小说的隐含作者,讲故事的伦理从尊崇神意的“客观”,到书写的“客观”,价值立场已然转变。
一、从史诗到小说
虽然讲故事的传统不是以史诗,更不是以小说为开端,但是在西方文学中,史诗和小说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史诗的英文Epic来自于希腊文Epos, 原义即有故事的意思。它以韵文的形式,描述神话传说中神和英雄们的故事,其中集大成之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既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经典,也是古典叙事的典范,奠定了史诗在众多故事中的地位。小说的英文Novel源于拉丁文Novus,含义为新的,意指新的故事。无论是被卢卡奇称为现代小說开端的《堂吉诃德》,被米兰·昆德拉称为欧洲第一部伟大小说的《巨人传》,还是被伊恩·瓦特列为代表小说兴起的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的作品,都是对传统故事的突破,它们用散文代替韵文,用现实生活代替神话传说,这些新的故事使小说成为了现代叙事中出类拔萃的文学形式。
黑格尔、卢卡奇和巴赫金等文学理论家,都曾经论述过史诗和小说的差异。黑格尔将这两种叙事体裁的不同,归因于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他将小说称为市民阶级的史诗,“在这种体裁里,一方面像史诗叙事一样,充分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旨趣、情况、人物性格、生活状况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却缺乏产生史诗的那种原始的诗的世界情况”。黑格尔所说的产生史诗的那种原始的诗的世界情况,是指个人的意志和情感尚未分裂,个人信仰和集体信仰尚未分离的时代。产生于这样时代的史诗,讲述的是个体行动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相结合的故事。在他看来,小说产生时的世界情况已经缺少了这样的整一性,出现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因此小说最常用也适合表现的是“心的诗和对立的外在情况和偶然事故的散文之间的冲突”②。
同黑格尔一样,卢卡奇也分别从产生史诗和小说的社会现实中,探寻它们之间差异的缘由。他把古希腊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称为一个同质的世界。在那里,自我与世界虽然有差异,但却不会永远感到相互陌生,因为对于置身其中的希腊人而言,世界是熟悉的,可掌握的,各种先验存在的知识、永恒本质、美德以及意义,在他们提出问题之前就给予了答案。而到了后希腊时代,先验观念与世界的完美对应关系,被散文世界的生活现实所动摇,这个孕育小说的世界不再是史诗所在的那个能够为生活提供所有意义的世界,它更多的是没有答案的生活现实。“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③。
这两位理论家根据时代和观念的变迁,解释从史诗到小说的转变,将个体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分离和矛盾,视为小说诞生的原因。虽然他们都更加赞赏史诗,但也在这样的对比中发现了小说的优势。黑格尔所说的,小说最适合表现心的诗和散文世界的冲突,其实反映了小说在个人与世界关系上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它可以在事迹的生动性方面,以及在表现人物及其命运方面,拥有比史诗更多的权利。又如卢卡奇所说,因为小说不像史诗那样有先验的世界为其赋形,所以它的形式可以祛除先验观念的强力,具有自身的表现力,能够通过自身形式的塑造,揭示并构建生活总体。
此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也选择了用史诗与小说进行对比,更深入地探讨了小说形式的表现力。他认为包括史诗在内的小说之前的文学体裁,都已有自己的程式,它们出现的时间往往都远在文字和书籍之前,一直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古老的口头宣讲的本色。“在所有重要体裁中,唯有长篇小说比文字和书籍年轻,也唯有它能很自然地适应新的无声的接受形式,即阅读的形式”④。他把小说的语言称为活着的语言、年轻的语言,将小说视为新世界产生的唯一体裁,也是唯一不受固定程式约束的形成中的体裁。他分别总结了长篇小说和长篇史诗的三个基本特征。小说的特征,其一是修辞上的三维性质,与小说中的多语意识相关联;其二是小说中文学形象的所在时间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三是小说中文学形象的塑造最大限度地与并未完结的现代生活进行交互。⑤ 而史诗的特征,其一是它以一个民族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其二是它渊源于民间传说而不是个人的经历;其三是史诗的世界远离当代。⑥ 相比于讲述过去、源于民间传说、远离当代的史诗,小说是多语的、当下的、未完成的。巴赫金论述了适应于无声阅读时代的小说,比口头宣讲的史诗更具有活力,更能够与现实世界发生互动。
相较于前面两位理论家,巴赫金赞赏小说胜于史诗。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从史诗到小说,不仅是从口头叙事到书面叙事,从韵文到散文,从神话英雄故事到现实生活故事,而且还是从承载生活总体形态的叙述形式,到揭示和构建生活的形式叙述,从相对稳定的意义表达,到多语的、当下的、未完成的意义生成。小说相对于史诗的这些变化,不仅是叙述形式的改变,也不仅是拉近了故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而且还包含着对确定性意义的挑战,具有伦理启蒙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似乎并不在于故事中的人物,因为在史诗和小说中,都不乏各种有着善恶品行的人物。在这两种叙事体裁中,发生较大变化的是讲故事的人。他们从史诗中借助神力为故事赋形的人,成为了潜藏在小说形式中由故事赋形的人,从有血有肉的吟诵诗人,成为了由书写文字建构的隐含作者。从吟诵诗人到隐含作者,从口头表达到书面表达,既是意义从确定性向不确定性滑动,也是讲故事的伦理开始发生转变之时。
二、史诗中讲故事的伦理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谈到,“伦理(ethike)”是把“习性(ethos)”一词在拼写上略加改动而来,意指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德性。⑦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并不是指现代意义的美德,“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⑧ 他举例说,眼睛的德性不仅要使眼睛明亮,还要使视力敏锐;马的德性在于擅长奔跑,以及能够驮着骑手冲向敌人。而就讲故事的伦理而言,它应该是讲故事人沿袭自风俗习惯的德性,讲故事的人以此为德性,意味着它具有优秀的功能,能够使故事被很好地讲述。
对于史诗讲故事人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赞赏荷马,认为与其他史诗作者相比,他意识到了诗人应尽量少地以自己的身份讲话,因为这不是摹仿的作为。⑨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仿,即是讲故事伦理的“客观”价值立场。但是事实上,史诗大多来源于口口相传的远古记忆和神话故事,很少有能够验证诗人“客观性”的事实证据。即使像荷马这样,尽量摹仿人物说话,尽可能地在故事中隐退自身的价值立场,他是否“客观性”地摹仿了人物,也因为参照物的缺失而无法判断。因此,“客观性”作为史诗讲故事人的德性,它的优秀功能并不在于摹仿真实的人物,而是能够达到逼真性的效果。为了实现这种缺少现实依据的逼真效果,史诗讲故事人常常借助于神灵的力量,这也形成了他们“客观性”的价值立场。
在史诗盛行的时代,讲故事的人从风俗习惯中沿袭而来的德性,是对诗神的尊崇。古希腊时期,创作灵感被归于神的赐予,讲故事的人被认为与神有着精神上的联系。他们从缪斯女神那里获得神力,一个连着一个地传递她赋予的灵感,缪斯女神将他们连成了一个有着共同过去记忆的整体。史诗的吟诵诗人常常不是第一个讲述该故事的人,他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如同磁铁传递磁力一样,传递来自于诗神的灵感。在故事的讲述中,他们的德性,不是他们自身关于善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他们讲故事的个人技艺,具有优秀功能的是他们被赋予的灵感,这在当时的风俗习惯中,被认为是把故事讲好的关键所在。他们讲故事的伦理,即是在传承故事的过程中,延续传统,保持这样的神圣性。
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和伊安的对话,讨论诗的灵感时,就把伊安擅长解说荷马史诗的本领归于受到神力驱使的灵感。在对话中,苏格拉底用占卜家、算学家、医生、画家、雕刻家等等有专业技艺上的人,与伊安这样的吟诵诗人进行比较,向伊安论证他擅长解说荷马的本领不是一门专业技艺,因为如果这是像其它职业那样的专业技艺,就应该能够运用到所有故事的解说上,而不是像伊安这样,能将荷马解说好,却不能同样好地解说其他诗人。以此为依据,苏格拉底称,“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⑩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荷马也多次说到诗人与神的联系。他分别以“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招灾的愤怒”{11} 和“请为我叙说,缪斯啊”{12} 开始这两个故事的讲述,而且,在故事当中,他也用“神圣的歌手”、“通神的歌手”来称呼吟诵诗人。荷马以缪斯女神的歌唱和叙说开始他的故事讲述,建立了他介于缪斯和凡人之间的讲故事人的身份,而故事中那些获得神的感召的吟诵者也与之呼应,使吟诵诗人从诗神那里获得灵感,凭借神力讲述故事的身份深入人心。因为,如卢卡奇所言,那个时代是问题还未提出就已有答案的同质世界。无论吟诵诗人是否模仿人物讲话,或是采用哪种人称进行故事的讲述,他们讲故事的伦理始终是从这种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德性,即对诗神、对传统的忠诚追随。
“史诗的故事讲述者说的是一个传统故事。促使他讲故事的主要动因不是历史性的,也非创造性的,而是再创造性的(re-creative)。他在重述一个传统的故事,因此,他最需遵守的并非事实,也非真理或娱乐,而是‘神话(mythos)自身——保留于传统之中,由史诗的讲述者加以重新创作的故事。”{13} 史詩吟诵诗人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延续着一个传统的故事,在古希腊时期,他们将这样的延传看作是像磁石向一个接一个的铁环传递磁力一样,传递缪斯女神赋予的灵感。而在现代意义上,这是他们的个人信仰融入了整体信仰,将他们彼此紧密相连。虽然这其中也不乏吟诵诗人的个人创作,但他们始终不是创作一个全新的故事,告诉人们关于过去的事实,或是向人们传递真理,或是提供娱乐。他们是在对传统故事进行再创造,整体信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讲故事的伦理,保持着对传统共同记忆的敬意。因此黑格尔才会说,荷马描述他的史诗世界亲切如道家常,诗人自己和他的全副心思都显现在诗里。{14}
三、小说讲故事的伦理
在小说中,讲故事的人不再是延续口头传承的习俗,他们讲故事的德性也不再是对来自于诗神的灵感的尊崇。在小说兴起的17、18世纪,讲故事的主要方式已经从口头叙事转向书面叙事,讲故事的人也在物理空间上与他的故事相分离。他们无法在听众面前召唤神灵,赋予他们讲故事的灵感和权威,以获得听众的关注和信服,他们隐匿于书写的文字当中,等待着被理解、被阐释。他们需要凭借这些书写的文字,才能激发人们对故事的兴趣,因此,他们讲故事的德性,更多地体现在这些文字当中,而非对诗神的敬意。
对于小说讲故事的伦理,以福楼拜为代表的小说理论家,主张小说讲故事的人尊重事物的客观性,客观地显示故事,而不是讲述故事。福楼拜在写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对在纸上写下我心中的什么东西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反感。——我甚至认为小说家‘没有权利(在任何书刊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上帝难道说过自己的意见?这说明为什么我心里有许多东西让我感到窒息,我想吐出来,却咽下了。其实,有什么必要说出来!偶然遇到的任何人都比居斯塔夫·福楼拜先生更有趣,因为此人更一般,因而也更典型。”{15} 在福楼拜看来,遵循客观性是讲故事人的优秀品质,讲故事的人应该保持故事的客观性,尽量不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把这种品质视为小说讲故事人的德性。
对于福楼拜所说的“客观性”,美国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斯指出,小说家虽然隐去自己的痕迹,却并没有从故事中完全消失,“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根据作品的需要,创造一个超然或介入的隐含作者,而不是全然地冷漠性创作”。{16} 作家以隐含作者的身份隐匿于叙述者身后,无论隐含作者是通过非人格化叙述者超然地显示故事,还是通过人格化叙述者讲述故事,都是在呈现各种具有不同生命观的价值观念。小说的隐含作者戴上叙述者的面具,通过各种技艺,变化他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进行故事的讲述,让故事具有了亦真亦假的双重性。面具的虚假性暗示了故事的虚构性,叙述者的讲述又往往引人入胜,讲故事人的善恶倾向,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中,而这才是小说讲故事伦理的“客观性”。
不同于史诗中被赋予神圣身份的吟诵诗人,小说讲故事的人没有明确的身份,他们对文字表述方式的选择,透露出不同的身份信息。他们可能是人物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也可能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或是第三人称叙述者。他们变换着各种身份,进行故事的讲述,如同戴上了不同的面具。用韦恩·布斯的话来讲,在小说中,讲故事的人是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进行故事的讲述。他们隐藏于不同的叙述者身后,如同抄写员一般,将故事书写而成。但是,“无论他如何试图做到非人格化,他的读者都必然会构建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的这位抄写员的形象——当然,这位抄写员绝不会对所有的价值保持中立。我们对他各种信念的反应,秘密的或公开的,将会有助于决定我们对作品的反应”{17}。
布斯所说的“隐含作者”,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从作者创作层面来看,虽然一些小说家称自己只是故事的“抄写员”,不会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带入到故事当中。但事实上,这位“抄写员”并不是对所有的价值都持中立态度,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隐藏在故事中,是小说的隐含作者。虽然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作者的观念,但也并非是中立的,他们的价值倾向往往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再者,从读者解读层面来看,无论作者如何让这位“抄写员”不表露出自己的价值立场,读者都不可避免地要从他那里获得故事的图景,也会去构建这位“抄写员”的形象,并且洞察他的价值观念。作者的书写以及读者的解读,在对话中形成着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这即是小说讲故事的伦理。
小说讲故事人的德性,体现为隐含作者价值立场的对话性,这不是讲故事人拥有某种先验的信仰,或是遵循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即使小说讲故事的人讲述的是宣扬美德的故事,也不能说明讲故事人的德性具有优秀功能。一个故事不会仅仅因为它包含着讲故事人对勇敢、正义、善良等美德的教诲,就进入好故事的行列。还有一些小说故事,虽然涉及暴力、罪恶、色情等与美德相背离的内容, 但却并不影响讲故事的人凭借他们德性的优秀功能,使故事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可。小说讲故事的人讲好故事的德性,不由他们故事涉及的是宣扬或是违背美德的内容而决定,他们在故事中讲到的善恶,是属于人物的伦理这个范畴,虽与讲故事的伦理相关,却还不是讲故事的伦理。诚如巴赫金所言,小说是多语的、当下的、未完成的,它没有先验的或是恒定的价值立场,它讲故事的伦理,即是向这种关于价值立场的对话开放。
这样的对话性意味着小说中任何一种身份的叙述者的品质,都无法成为所有小说讲故事人的德性。隐含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进行故事的讲述,这些身份各异的叙述者,呈现出隐含作者各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它们可能是保持善恶中立的“客观立场”,可能是惩恶扬善,也可能是关于善或恶的伦理反思。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伦理立场,都不是隐含作者恒定不变的价值观念,它们总是处于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当中,这才是小说讲故事的伦理。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是对理想主义的批判或是颂扬,他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智慧才是小说的智慧{18}。
隐含作者这样间接地显示或讲述,无法像史诗吟诵诗人那样与故事及整体信仰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形成了不同價值观念的对话。人物叙述者不一定比非人物叙述者更能拉近读者与故事的距离,非人物叙述者也不一定就比人物叙述者更加客观,不同人称的叙述者也是同样,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孰优孰劣。叙述者带着爱恨情感的讲述,不一定就说明隐含作者怜悯或厌恶某些人物,叙述者看似超然地显示仍可能包含着隐含作者的情感,在这真实与虚构之间,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是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
四、当说者被说时的伦理启示
从史诗到小说,虽然同样是讲故事,但讲故事的人却从用自己声音讲述的吟诵诗人,转变成了需要通过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来解说的隐含作者,从说者转变成了被说的说者。当说者被说时,讲故事的人不再是具象的讲述者,而是隐身于故事之中的隐含作者,由故事塑形。在故事中保持静默,用书写的方式进行讲述的隐含作者,也将自身的价值观念一并隐于故事中。虽然吟诵诗人也会模仿人物讲话,让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史诗故事中隐退,但是作为被说者的隐含作者,与作为说者的吟诵诗人,他们隐退所呈现出的讲故事伦理却不尽相同。吟诵诗人的隐退是让自己的讲述更逼真、更具神圣性,而隐含作者的隐退却是在真实与虚构的交织中,让各种可能性在关于书写的对话中产生。
吟诵诗人也可以让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故事中隐退,但是,他们在讲述中对人物的摹仿,与小说中隐含作者以书写的方式,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呈现人物,所体现的讲故事的伦理是大相径庭的。吟诵诗人的摹仿,并没有创造出具有独立个体意识的人物,这些人物与吟诵诗人一样尊崇神意。例如,在《伊利亚特》中,是神明挑起了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斗,而当阿基琉斯因阿伽门农的羞辱而狂怒时,也是女神雅典娜的出现,让他止息怒狂,把铜剑推回鞘盒。{19} 这样的例子在史诗中还有很多,这些被摹仿的人物常常在神的驱使下,产生某种想法,或者采取某种行动,并没有个人意识进行思考、表达和行动。这样的摹仿,可以让故事更逼真、更可信,却并没有真正让不同的个体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仍然是作为说者的吟诵诗人以权威的声音,保持了故事的神圣性,他们讲故事的伦理依然以神意为尊。
而小说中的隐含作者,不仅失去了缪斯女神赋予的神圣光环,也远离了与之相连的权威身份。他们变换叙述者面具,进行故事的讲述,形成了真实与虚构的交织,袪除了他们身份的神圣性。无论隐含作者以哪种叙述者的身份讲述故事,他们都无法现身表明自己的意图。他们的意图都在书写的文字当中,他们所说的,需要被阐释才能够传达。当说者被说时,抑制了一个权威的声音,也释放了多种可能性。无论小说中叙述者具有通晓故事中一切的“神力”,还是仅讲述自身的所见所闻,都因为面具的虚构性,使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变得扑朔迷离。
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小说时所说,“关于构思和创作细节,作者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愈大,他也就愈难免沉没到对现实生活散文的描绘中去,而自己却不投身到散文性的日常生活中去。”{20} 相比于吟诵诗人,小说作者拥有了更大的创作主动性,可以更多地描绘生活中丰富多样的事件和人物,即使是讲述传统的故事,他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各种讲述故事的可能性。小说作者对构思和创作细节的探索,使他们不仅仅书写关于自身的真实故事,而是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寻找素材。因此,他们很可能并不投身于自己描绘的生活当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常常与故事中的价值观念有着各种差异。
戴上叙述者面具的隐含作者,不能像吟诵诗人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同时也与现实世界的作者存在着差异,“这个隐含作者致力于表达的主要价值,不论他的创造者在真实生活中属于何种派系,都是由全部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21}。在小说中,隐含作者不再遵从神意为故事赋形,他们通过叙述者进行讲述,将故事连同他们的技艺都编织在小说的形式上。由于小说作者可能并不投身于他所描述的生活当中,所以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可能并不来自作者本身,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个体。而且,隐含作者的技艺,在他们与叙述者之间,形成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出不同个体意识的交织。无论是人物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还是不同人称的叙述者,都不是完全地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念,或是客观地呈现某一独立的个体意识,而是在小说的全部形式中蕴藏对话,也蕴含了隐含作者讲故事的伦理。
例如,在《堂吉诃德》中,隐含作者赋予了叙述者凌驾于主人公意识之上的意识,让他不仅能够讲述堂吉诃德的日常生活、兴趣爱好,甚至心中的所思所想,而且能够与读者在这位主人公的背后窃窃私语、秘密共谋,取笑他的异想天开和荒诞行为。如果从福楼拜的小说“客观性”标准来看,这样的叙述方式,与“客观显示”相去甚远,但这丝毫没有减损这部小说讲故事的魅力。即使叙述者对堂吉诃德的讽刺淋漓尽致,即使有很多的读者跟随着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对主人公评头论足,嘲讽他的可悲可笑,都并不代表隐含作者讲故事的伦理。隐藏在叙述者之后的隐含作者,用面具拉开了与叙述者、读者的距离,他可能加入到他们当中,也可能跟他们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甚至用叙述者、读者凌驾于堂吉诃德意识之上的方式,从同样的反讽距离,注视着他们,对这些种种可能性的包容才是这部小说讲故事的伦理,它让这个故事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巨人传》这部小说也是如此,虽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出现,称他在一块草坪里发现了卡冈都亚的家谱,开始了他的故事讲述。但是,这份家谱中各种夸张的事迹,揭示了家谱本身以及叙述者发现家谱事件的虚构性,暗含了隐含作者对叙述者佯装真实的反讽。隐含作者对叙述者虚构故事行为的揭发,并不是为了讲述另一个更为真实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并非是隐含作者讲故事伦理意图之所在。选择以第一人称进行故事讲述的隐含作者,原本可以更巧妙地隐藏于叙述者身后,让故事如叙述者真实的生活经历一般“客观地”呈现出来,可是,隐含作者却有意地透露出叙述者的虚构,消解了故事的客观性,与故事中打破禁忌的狂欢相互呼应,在这里,小说讲故事的伦理已然超越真与假、善与恶的两极对立,使各种伦理对话成为可能。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不一而足,彰显了小说讲故事的独特性。
从史诗到小说, 是讲故事的人从吟诵诗人到隐含作者的转变, 他们讲故事的方式从有声的讲述,转向静默的书写,他们把故事讲好的德性也从尊崇诗神,转变为对各种不同的个人意识及其对话的呈现。在史诗中,吟诵诗人无论是用自己的声音叙述,还是摹仿人物说话,他以及他摹仿的人物都听从于权威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神灵,来自于口口相传的记忆。而在小说中,无论是叙述还是摹仿,隐含作者都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由全部的小说形式来表达。通过书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形式,缺少了权威声音的指引,却使各种个人意识的对话成为了可能。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隐含作者与读者都可能在小说的形式中形成不同的个人意识的对话。这不仅是讲故事的人的价值观念从先验到生成的变化,而且也是讲故事的人袪神圣化的过程。当多语的、当下的、未完成的小说形式承载起永无止境的个人意识对话,讲故事的伦理的“客观性”就被重新书写。
注释:
①{13}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0页。
②{14}{20}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7、112、168页。
③ 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3页。
④⑤⑥ 米哈依尔·巴赫金:《小說理论》,《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513、515页。
⑦⑧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页。
⑨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9页。
⑩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1}{19} 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
{12}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 福楼拜:《致乔治·桑》,刘方译,《福楼拜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13页。
{16}{17}{21}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92, pp.70-71, pp.73-74.
{18}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作者简介:周莉莉,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22;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