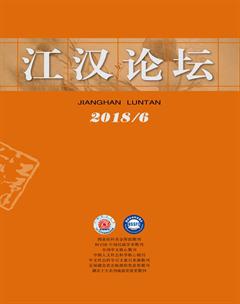巫楚文化与陈应松的乡村小说
摘要: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主要有“荆州系列”和“神农架系列”等类型。陈应松因“底层写作”被世人认可,同时也因“底层写作”代表作家的标签而遮蔽了对他乡村小说丰富性的深入研究。近年来由于“底层写作”的回落或泛化陈应松似乎被评论界有所冷落。其实,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上不断超越自我,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忧愤深广的呐喊;人性强悍的表现;崇巫尚鬼的神秘氛围和惊采绝艳的文风特点。
关键词:陈应松;乡村小说;巫楚文化;神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92-07
我国文学具有悠久的乡土文化传统,历代作家对土地格外偏爱,对乡村异常迷恋。乡村对于文学、对于当代社会和人类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同时,乡村具有宽阔的胸怀,与大地相连,沉默不语,守候着人类的生与死、常与变。陈应松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以诗歌登上文坛,后来转向小说创作,迄今已有30余年创作历史。陈应松和喧嚣的文坛始终保持距离,与热闹的大众文化保持内在的紧张,潜心于乡村小说创作。按照评论界的分类,他的小说主要有“荆州系列”和“神农架系列”等类型。其中“荆州系列”按照创作时间和题材又分为“船工”、“郎浦”和“野猫湖”三个阶段。“神农架系列”的写作主要发生在“郞浦”和“野猫湖”两个阶段之间。前几年陈应松因为被评论界称为“底层写作”的代表而被世人认可,近几年也因“底层文学”的泛化或回落似乎有所冷落。其实,“荆州系列”的“野猫湖”书写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方面已全面超越了陈应松之前的创作。像长篇小说《还魂记》这类作品,不仅仅是陈应松个人创作历史的艺术高峰,也是新世纪乡村小说的重要收获。“底层写作”标签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陈应松乡村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将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创作置于中国现当代乡村小说的框架,从整体上分析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独特价值。陈应松乡村小说具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忧愤深广的呐喊;人性强悍的表现;崇巫尚鬼的神秘氛围和惊采绝艳的文风特点。
一、忧愤深广
张正明先生在论述楚文化史时,将“念祖、爱国、忠君”作为楚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在我国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只是楚人尤为突出而已。楚国处于强邻之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因此养成了楚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① 唐人裴度在《与李翱书》中论述楚辞的特点时说:“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楚辞》这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个人色彩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在于屈原炽热的政治情怀和充满正义的政治立场,在于屈原对真理的追求和爱国的情怀,更在于屈原内心强烈的愤懑、哀愁、痛苦以及惶然无助的绝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这种忧愤深广的呐喊契合了一代代作家艺术探索时苍凉的心境和不老的情怀。
陈应松生长于楚地,深受《楚辞》影响。早期写过《楚国浪漫曲》、《楚人招魂曲》等组诗,表现出强烈的巫楚文化色彩。他认为屈原的《九章》“都是内心直接悲愤的倾诉,干脆就是直抒胸臆”,是“个人化的倾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豪不掩饰自己的企图。”② “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真理、美德和正义的辩护者存在的”。③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世俗化潮流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世俗化潮流同样影响着文学创作。部分先锋作家在虚拟的空间沉迷于形式的实验,某些新写实小说对芸芸众生采取旁观的态度,个别“私人化写作”在个人世界里低呓私语,诸多新生代作家在欲望化的个人叙事中表现出对物质世界的迷恋。这种创作潮流必然造成“这一代作家整体性缺席,整体性失语”。④ 这种判断是否公允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这样的呼吁确实值得人们警惕。当然,虽然社会日益轻佻浮华,麻痹虚伪,可是,总有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⑤。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责任和良知就是屈原表现出来的“九死未悔”、“上下求索”的深广忧愤精神。陈应松要求自己以“‘打破头往前冲的强势介入生活和艺术”⑥。
无论是“神农架系列”还是“荆州系列”,陈应松都关注乡村和土地,“时刻与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⑦。 《乌鸦》写出了1990年代初乡村贫富悬殊,农民心理失衡的现实。富裕起来的七叔总是将自己和解放前的地主肖老六相比,并为此心神不宁,担心“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会出事”。《承受》中城乡和谐、贫富共处的乌托邦想象成为泡影,现实阶层的差别与鸿沟粉碎了现代性的美好想象。雨中送伞的细节让船工王七父子消除芥蒂,彼此理解,共度生活风雨。显然,陈应松对于超越阶层的情感是清醒的,怀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陈应松持续关注的题材:《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炸山修路导致神农架森林千疮百孔;《猎人峰》中野兽充当了自然的守护神,对人类的破坏行为进行疯狂报复。乡村政治是陈应松乡村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层面:《独摇草》中开篇就是酒醉村长射杀五位村民;《吼秋》中村镇干部为了形象工程举办蛐蛐大会,完全不顾泥石流的险情,最后导致悲剧;《野猫湖》关注留守妇女的情感问题;《无鼠之家》中农村信教的问题等等都是陈应松忧心忡忡思考的范畴。不难发现,“荆州系列”的“船工”、“郎浦”书写主要表现楚人的强悍,这种创作回荡着寻根文学的余响;到了“神农架系列”就更加突出现实矛盾的尖锐,而这正好与19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突出同步。“野猫湖”书写则聚焦底层深处蕴藏着的历史、时代和人自身的疼痛。虽然,“关注底层”的主题在当代文坛一直绵绵不绝,但陈应松的小说显然燃烧着格外浓烈的情感。这使得陈应松与其他乡村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区别开来。莫言、贾平凹都有对于乡村苦难的深广忧患,莫言写出了被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作品富有传奇色彩;贾平凹冷峻剖析乡村走向破败的症结,风格朴实而感伤。陈应松则借助楚风的鼓动,将苦难中的不幸、抗爭、呐喊写出了浓烈的诗情、锥心的痛感。
“荆州系列”的“野猫湖”书写中,《滚钩》是以“挟尸要价”这一社会新闻改写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性。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进行文学构思的一种方式,如余华的《第七天》、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和贾平凹的《极花》等。卸任村长成骑麻的儿子成涛与村小学校长的肥老婆私奔了,并且校长老婆整整大成涛二十多岁。而校长却不愿离婚,希望老婆回心转意,因此就不允许成骑麻的嫡系孙子小虎上学,以此要挟老婆现身。可是,校长这种荒唐行为没有让成涛屈服,只是让成骑麻一筹莫展。当然更让他纠结不安的是捞尸这一营生。长江已无鱼可捕,成骑麻不得不成为刑满释放吸毒人员史壳子手下捞尸队的员工。“政府不管这事”,“没有公益捞尸队,连在江湾竖个警示牌子也小气死了”。显然政府不作为,管理缺失。与当下政府形成对比的是,“从他父辈算起,都是渔民,也是水牛市民间慈善组织‘义善堂的成员,专门捞尸葬尸的,不收分文酬金。1949年后‘义善堂解散,政府接管,还是捞尸不收钱。‘文革时投江的多,那时政府瘫痪了,但成骑麻的老爹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他和村里渔民义务捞尸。一年捞过两百多个泡佬,后来,他九十岁的爹死了,这事儿好像就没人管了”。这样,也才给史壳子们提供了“用武之地”。通过对比,陈应松对时代和社会进行了批判。同样对于教育,陈应松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水乡的孩子一天到晚读书,却没有掌握游泳的本领,这里的教育是缺席的。三个大学生溺水而亡,学校因“处理得当”却受到表扬。学校动用各种宣传机器,把本来应该承担责任的事情,变成了值得宣传、赞扬的事情。同样,乡村伦理混乱不堪,人们缺乏必要的廉耻之心。“这些年村里就一带二、二带三,姑姐带弟媳,嫂子带小姨”公开卖淫,而嫖客也是本村或邻村的农民。世风日下、民风堕落,岑寂的乡村日益破败。
无论是对乡村生存困境的焦虑,还是对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担忧,抑或是对精神困境与人性背弃的焦虑,陈应松都是“凭借我的血管和我的嘴。通过我的语言和我的血说话”(聂鲁达语)。这句写在他长篇小说《猎人峰》扉页的话或许能看出陈应松的心迹。他说:“我的目光从来是真实的,不会因文坛的风向而变化。盯住人的基本生存现状。我认为我的写作的一点成绩,就是对文学真实性敬畏的结果,对文学赤裸裸表达现实生活严酷的一点心得。”⑧
因为“神农架系列”对底层的关注,陈应松成为底层写作的代表。而陈应松也认为底层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对“政治暗流的一种逆反心理的写作活动”,同时,底层写作也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是对“当下恶劣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抵抗、补充和矫正”⑨。确实,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与其说是新世纪兴起的文学思潮,倒不如说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的社会责任、“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深广忧愤、“长太息以掩涕兮”的苍老心境和“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在陈应松乡村小说创作中的鲜明体现。
应该指出的是,陈应松并不是因为“底层写作”这一社会或文学思潮才开始关注底层。他对底层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从登上文坛之日起底层就是他写作的题中之义。同样的道理,他也不会因为“底层写作”回落或者泛化而转移创作方向。“荆州系列”的“野猫湖”书写持续对底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描写。陈应松也因“直面人生的种种惨淡相,以疯狂的心理折射出社会发展中的某种让人感到震撼的痛苦”(陈思和语)⑩,而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陈应松说过:“文学是生命的一部分,它通过肉体来歌唱灵魂。文学是灵魂不屈的显现。文学是一种申诉。”“我们写着,不是要对某时、某人、某地、某事做简单的同情或评价,我们要写下我们自身对命运的发现,写下人类生存的理由。”{11} 陈应松不仅仅有着社会学家的深刻剖析,诗人的热情书写,更有哲人式的忧患意识和知识分子的冷峻思考。陈应松对底层生活充满深广的忧愤,以悲悯的情怀追寻人生和命运的规律,以诗性的语言表达对生活、生命的关注、审视和思考。
二、人性强悍
烦躁不安、争强好胜,“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计。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这种强邻之间战战兢兢求生存、谋发展的处境,促成了楚人强悍的人性。“楚人好战喜斗”,“尚武的传统,正表现了楚人奋发的民族精神”{12}。中原礼仪文化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平和之道并不适合楚人的性格。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多受神秘文化影响,随性而为,面对个人及社会重大问题的反应往往受情绪的激荡而表现出急躁、偏执甚至颠倒迷乱的“狂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考察楚地风俗时说,“(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民风、民情内化为楚人的文化性格一直继承下来,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楚人。楚人躁急执着,好使性气,行为上往往也带有狂态,甚至成为痴狂、愚狂或骄狂。
陈应松是怀着虔诚的文学梦想走上文坛的,像很多作家一样,开始时是以诗歌引起文坛的注意,出版有诗集《梦游的歌手》。陈应松的诗“大都凝重,而又带一点涩味:感情上的苦涩和表达方式上的艰涩”。这种“凝重”、“苦涩”源于陈应松“怀着严肃的心面对生活,思考生活,力图透视到生活漩流的深处”{13}。但他“不是沉溺于个人的狭小情怀,表达淡淡的哀愁的那种诗人。他的歌声决不轻飘,绝不追求表面的俏丽。只有在歌唱生育他的乡村时,我们才感到他心情柔和的一面”{14}。这种“苦澀”、“艰涩”或许源于陈应松早年生活的奔波劳碌。艰辛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难以言说的生存之痛内化为愁苦、焦灼的性格。陈应松高中毕业后成为回乡知识青年,当过民工、拉过板车,招工当过水手,在长江上颠簸,上过大学,留在武汉,却和城市难以和解,深感孤独,精神总在漂泊。他写过诗歌、散文、戏剧,也写过一些戏剧性很强的影视剧本。无论是他从事何种职业,无论是他从事何种题材的创作,陈应松总是能在空灵的艺术形式中探析深邃的人性,用诗意的语言、倔强的形象表达强悍的人生。
陈应松心中理想的小说是“粗粝、凶狠、直率、诡异、强烈、干硬、充满力量、具有对现实的追问力量和艺术的隐喻力量”。这种贴近地表的表述不仅仅表达了陈应松对小说审美艺术的追求,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在芜杂、纷乱的生活表象下探求生活的规律和存在的价值尺度,试图洞察人物故事背后深层次的联系。对人生、人性以及命运的探讨成为陈应松创作的主要动力。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中,暴力、杀戮、死亡充斥其间,被侮辱者、被损害者踟蹰乡野,作者试图在向死而生的生命之旅中发现人性之光,寻找重生之路。
《黑艄楼》中个性狂傲的“我”不得不受制于“矮子”的指使(矮子的父亲是驾长),“我”如同困兽,通过自虐(如酗酒)、自审和堕落来反抗现实;《黑藻》中狗鱼驾长和他的拐子儿子终生彼此折磨却又不能分开;《豹子最后的舞蹈》中身手矫健、硬朗、亢奋、八十五岁的猎手老关让凶猛的豹子闻风丧胆;《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背尸赶路,一路上和灵魂对话不止;《八里荒轶事》中的端加荣到八里荒独自开荒,幺女被狼吃了,她竟愤怒地将狼咬死;《马嘶岭血案》中敏感、偏执的九财叔,一口气砍死七个神农架山区踏勘队的成员,其中包括自己同村的农民;《到天边收割》中善良、软弱的金贵最后对老柳树的态度,一改之前的忍辱负重,突然有了“有仇不报非君子”的气概;《一个人的遭遇》里的刁有福用个体的弱小力量与权力进行毁灭式的抗争;《猎人峰》中猎人白秀演绎着“最为惨烈的、最为传奇的、最为暴戾的、最为混蛋也最英雄的故事”;《无鼠之家》中木讷老实的阎孝文千里归乡,杀死和自己妻子偷情的父亲阎国立;《野猫湖》中香儿为与同村妇女庄姐的同性之爱,而放任自己的丈夫三友吃毒狗肉身亡;《夜深沉》中隗三户的名字源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性格上也有楚人的情绪型的特点,几天时间,他从进村时赶走偷牛贼,迅速转变成为为偷牛贼提供便利的人,并且有种犯禁的快感;《送火神》中留守儿童五扣通过不断烧毁他人的房屋来赢得他人的注意,最后也因此被众人心照不宣地赶入了火场,葬身火海。这些人物性格强悍,情绪多变,偏执顽强,狂放不羁,具有巫楚文化特有的“狂”态。
“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由此形成了特殊的风尚”,“尚赤,即以赤为贵”{15} 。陈应松认为楚人的特点是“不服周,不肯轻易屈服,就是撞倒南墙也不回头,犟,但也有韧性”。陈应松笔下的人物总是流淌着不安和野性的血液。这些人内心向往自由,性情率真,但是由于现实的贫困、文化的贫乏、出身的低微和性格的冲动,很容易在性格的两端过山车式快速转换,自卑与自傲、自闭与自省、自爱与自虐、自责与自戕无缝对接。狂躁之性与灼热之血孕育了狂野与绝望,野性粗犷与躁急好胜成就了人生和命运。巫楚文化的精神在这些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凸显了陈应松小说沉重、窒息、粗粝、紧张的特点。
当然,这些人物由于出于封闭、凋敝的生存环境,他们身上的血性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动物的本能,是为了适应生活而进行的无意识抗争,不同于萧红《生死场》中农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陈应松忧愤深广地介入社会,聚焦底层生存状态,在批评中蕴涵同情,在理解中饱含批判。
三、崇巫尚鬼
张正明先生指出:“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他们对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渐渐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至于社会习尚,则有久盛不衰的巫风;艺术风格,则追求挺拔、清秀与诡奇、缛丽的综合。”{16} 楚国的巫和医往往一身二任,“巫彭作医,巫咸做筮”。巫彭和巫咸是楚人敬奉的两位神医,一般连称“彭咸”。巫与医也一般合称巫医。对于楚国人来说,巫上可以通鬼神,下可以寄生死。而巫师与鬼神交流的手段,一是祭祀,二是卜筮。楚国鬼神之道昌炽,巫觋之风盛行。《太平御览》卷135引桓谭《新论》曰:“昔楚灵王矫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王逸《楚辞章句·〈九歌〉》也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可见,崇巫尚鬼是巫楚文化的重要内容。巫楚文化也因此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根据李泽厚的考察:“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17} 李泽厚将这种传统称为“巫史传统”。而日本学者藤野岩友则将《楚辞》定性为“巫系文学”,《离骚》是“以巫为中介的人对神和神对人之辞”。巫演唱的舞歌即《九歌》,由巫进行的招魂即《招魂》。{18}
陈应松乡村小说塑造了许多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巫楚文化色彩。《猎人峰》描写了一个时间似乎静止,远离现代化发展,处于原始状态的神农架山区。鲁瞎子是猎人峰一带公认的大歌师,会唱全本的《黑暗传》、《红暗传》、《神农老祖传》、《鸿蒙传》等。同时鲁瞎子也是一位巫师,能掐指算命、精通道场法事,经济活泛,在人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大家敬仰。显然,这是一位具有远古楚巫文化魅力的人物,是神农架山区神秘文化的代表。而来去缥缈、仙风道骨的老郎中能“抽山混子筋、治百病”,还能说出“天地闭,贤人隐,恶兽出”的古训,给人治病也是神神道道。如给白大年治病,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伸向空中抓去,口中念念有词:“九死还阳兮,九死还阳,九死还阳虫来兮,九死还阳虫到!”老郎中将褡裢在空中甩了两圈,伸进手去,抓出一条脆骨蛇,即九死还阳虫。老郎中将蛇掷于地下,蛇断为九节,待蛇正要合拢时,“老郎中将九节蛇拾于掌中,一运气,两掌嗞嗞冒出青烟,一合掌,一碾搓,双手就一堆黑糊糊的粉末了。然后取出酒葫芦,用酒调和,敷于白大年的断腿处,绑扎起来”。三天后白大年的腿就消肿了,一个月后则活动自如。这种夸张、神秘、玄之又玄的人物描写,增添了神农架的神秘色彩。同时,这种具有本土特色的神秘色彩,使陈应松乡村小说创作与一般的魔幻现实主义区别开来。
同樣,一些具有崇巫尚鬼的巫楚文化情节使得陈应松乡村小说显得神秘莫测。如《像白云一样生活》中白莲垭的天坑,每逢天阴下雨,天坑里就有鬼魂的乱叫。《马嘶岭血案》中,老麻相信千年老树成精,夜晚树心里面锣鼓喧天。九财叔则对鬼和鬼市坚信不疑。受了惊吓,九财叔“从头上扯了一把头发,让我用一张树叶包好,烧了,放进他装水的碗里,喝了,用一块石头刮着空碗,把碗交给我”,嘱咐“我”为他喊魂。而“我”则看见黑白无常率领一群野鬼簇拥着九财叔向“我”走来。《火烧云》中陈应松对求雨的祭祀仪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当地长者先扎火龙,龙须草为龙须,胡萝卜为龙眼,领着村民抬着火龙去黑空洞。由长者主持求雨祭祀仪式。先有长者和声大喊:“……烧死你旱魃!烧死你旱魃!我求你瘟火两部,两界神王!……”众村民用哭腔嘶声应道:“天干地渴,老龙下河!天干地渴,老龙下河!”紧接着三只铳齐响,几只狗对天狂吠,草龙前放上一盆水,泥地上插上写满奇怪文字的木牌。高潮为草龙点火,十几个村民在熊熊大火中齐声大喊:“烧死旱魃!烧死旱魃!请龙王,请龙王!”只是虔诚的求雨仪式没有应验,而是引发了一场山火。一切都显得神奇迷离、神秘莫测。
由死去的魂灵充当叙事者,是文学叙事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如《浮士德》、《神曲》、《百年孤独》以及我国的魏晋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陈应松的长篇小说《还魂记》担当叙述功能的柴燃灯是一位返回故乡的游魂、孤魂。小说通过鬼魂手记参透生死,为失语的村庄诉说、奔走。小说中关于“吊冤”、“破血盆”、“坐棺”、“守灵”、“过阴兵”、“守魂”等巫鬼情节比比皆是。如穿着印有太极图青色道袍的道士,手持桃木剑和令牌或者引魂幡,为寒婆的女儿超度,口念“饯送邪祟,扫荡宅舍……”“人死如灯灭,如同汤泼雪。要得亡魂转,水中捞明月”。念迎亡诀、净心诀、净身诀、金光咒,撒米,杀公鸡等。为死者穿上“五领三腰”:上身五件,下身三件;内为白衣,外为青衣。谓之清清白白去托生。破血盆:“亡者早产,血水污染了地府,阎罗王要治罪于她”,亲友为她破血盆赎罪。柴燃灯在生死之间的九天时间,见证了乡村之痛:残酷而又诡异的乡村现实、瘫痪而又变异的乡村政治、痛苦而又无序的乡村生态。陈应松将亡灵叙事与巫楚神秘文化有机结合,写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个人魅力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陈应松乡村小说的叙事视角丰富而独特。像《太平狗》、《豹子最后的舞蹈》采用的是动物视角。陈应松吸取了巫性文化的精神,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在底层的书写中隐喻中国民主政治的混乱和底层人民生存的困境。当然,陈应松说:“我涉足的地方有那么多神秘的东西,吸引着我去了解、去表现。我总觉得神秘的东西有象征意味,与现代主义有关联,而我又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所以就把它们突出化,用小说来表现神秘主义。”小说的神秘性是为作品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服务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小说的诗意和哲学意蕴。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天书”、“十八拐”;《望粮山》中的“天边的麦子”都是为了让叙事更具有独特的风格,能深刻、形象地呈现土地的神秘氛围。
陈应松乡村小说崇巫尚鬼神秘氛围的渲染延续了寻根文学的文脉,突出了巫楚文化的绚烂。同时,热烈、绮丽的巫鬼情节和氛围在新写实小说灰色人生的哀叹和悲凉中显得格外的惊奇、靓丽。这何尝不是陈应松乡村小说超越一般新写实小说的意义所在?
四、惊采绝艳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楚辞》大为推崇,赞叹《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鲁迅认为《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这里的“时”主要是指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而“地”则是说楚辞流行于沅、湘,“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惊采绝艳被认为是巫楚文化独特的文采。只有这种烂漫靓丽的文采才能表现楚人剽悍的人性和浪漫的想象。莫言对陈应松极为推崇,认为他“用极富个性的语言,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梦魇和幻觉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神农架但又超越了神农架,这是属于他的王国,也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个亮点”。
陈应松说:“作家所追求的真实,是由他对词语的那种矢志不渝追寻的真诚度所决定的,真诚度越高,那样的真实也越令人信服。”{19} 陈应松对小说的语言非常重视,将方言土语、粗话俚语和诗化语言、欧化长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语言诡谲奇异,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有效地继承了楚辞惊采绝艳的风格。
陈应松的小说语言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地名:皇天垭、韭菜垭、杀人岗、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乱石垭、八人刨、狼牙尖、巴东垭。这些地名凸显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制造了紧张、焦灼、诡异和荒凉的小说环境。陈应松还特意指出这些地名本来就存在,并不是他的胡编臆造。同时陈应松乡村小说的方言俚语俯拾皆是。如《狂犬事件》中村长赵子阶的语言常常含有愤懑,但是也饱含乡土气息:“我老在乡里挨训,乡长把老子当龟儿子杵”,“歪嘴巴吹火,邪完了”,还有“太阳牛卵子热”,“十个指头被炸得筋筋吊吊了”。《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王皋“看着自己晒在阳光下的手,那不是手,是个树根子”等等。《巨兽》中罗赶早看见棺材兽吓得“三魂吓掉了两魂半”,“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进,憋得脸就跟溺死的人似的”。方言土语的灵活运用使得陈应松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生活质感。斑斓奇崛的语言浸润着巫楚文化的神秘,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
陈应松以诗人的气质与巫楚文化邂逅,追求“有音乐感的、节奏像石头一样响亮的语言”{20}。《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大火烧得整个天空都是通红的,好像涂满了鲜血,烧得星星呯呯下坠,河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沸腾的气泡”。《野猫湖》中“野荠菜的花白白的,在晴风中蔓延。池塘的小荷盯着阳光在嫩黄地翻飞,有小鱼东奔西走”。当代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因为各自创作目的和个性不同,有的侧重于主题的追求,有的着意于人物的塑造,而陈应松则在句子的锤炼上用心最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陈应松用诗化的语言描写疼痛的乡村,将一曲曲人间悲剧幻化为瑰丽的彩虹,升华为靓丽的美文。“华丽飘逸,灵动飞扬,神奇浪漫”,就是巫楚文化的强烈特征。
同时,陈应松深得巫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精髓,能在各种文体中穿越自如。《一个,一个,和一个》是戏剧和小说的文体融合,小说情节的展开依靠人物简洁的对话,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同归于尽,一切成空。刘得华和姚方合谋把史阳除掉,史阳不仅骗了他们的钱财而且玩弄了他们的老婆。但是,计划尚未实施,两人就起内讧相互厮杀,一人被杀,另一人锒铛入狱。史阳则坐山观虎斗,渔人得利。人性的愚蠢和贪婪通过话剧和小说融合的形式展示得淋漓盡致。“发楚声”、“书楚语”,陈应松在小说创作中时常穿插一些楚地的传说、民歌。如《猎人峰》中《黑暗传》、《红暗传》、《神农老祖传》、《鸿蒙传》等民间传说、民歌直接大段出现,与小说情节水乳交融,有利于凸显小说的神秘性和地域性。
中国现代小说就是由《狂人日记》的十四则日记掀开了新的一页,小说的文体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小说的散文化就是五四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茅盾、郁达夫、丁玲等都著有日记、书信体小说,小说也因此更多地表现自我,更具有抒情性。而对小说文体更具有挑战性的则是诗歌、散文等文体的渗透与融合。如冯至的《蝉与晚祷》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歌、散文。而文体融合的创作倾向与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思潮有密切关联,同时也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有很大关系。陈应松吸收五四文学的精神营养,最先以诗歌登上文坛,同时也写过大量的剧本,后来才专门从事小说创作。而他的散文、书法也有非常高的造诣。陈应松秉持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无比热爱,一直追求不同文体的融合与突破。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融汇各种不同文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还魂记》也许得益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小说的扉页交待了故事的由来:“本人喜好在乡野乱窜。某日,雷电交加,被狂风暴雨阻隔,在野猫湖一荒村破舍避雨,发现一墙洞内,有一卷学生用作业本,已发黄破损,渍痕斑斑,字迹杂乱,难以辨认。细看是一本手记,为一野鬼所作,文字荒诞不经,颠三倒四。带回武汉后稍加润饰,每段文字附上小标题,公之于众,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仅此而已。”这部小说是所谓“野鬼手记”,既然是手记,就没有什么规则,想到什么就记录什么。陈应松让死魂灵返回家乡,关注岑寂的乡村生态和颓败的文化精神。小说叙述自由出入诗歌、散文、公文、戏剧等各种不同文体之中,追求“没有规则的小说”,这样灵魂才得以解脱和自由。陈应松认为“所有的文字都应该叫文章,是没有文体之分的。好的文章就是好的文学,不管叫什么,小说,诗歌或者散文”{21}。而詩歌、散文则自然融合在小说的节奏之中,“使得小说并没有突兀之感”{22}。《还魂记》的写作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文学传统、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文学,即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记忆书写我们的精神故事,小说是精神生活的纪实。
陈应松惊采绝艳的诗情语言的文风追求,为乡村小说涂上了浓郁的楚风色彩,将苦难写出了地域文化的美感。这种文风的追求将苦难凝练为一种魅力,激活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和“良知责任”{23}。这是陈应松乡村小说独特的境界与力量。
值得庆幸的是,陈应松是一位有内在定力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他不因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盲目迎合,不因物质世界世俗眼光的转移而怀疑恍惚。他在漫长、孤独的热爱与坚守中,表达自己的创作立场、艺术倾向和生命哲学。陈应松沐浴巫楚文化,通过崇巫尚鬼的神秘情节和意象,在方言俚语、诗性话语的铺排叙述中突破文体局限。在强悍、躁急的人性塑造和紧张、粗粝的生存环境描写中,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忧愤深广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12}{15}{16}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8、105、63页。
② 陈应松:《写作是寻找自己的归途——在“屈原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春夏的恍惚》,地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
③ 陈应松:《对湖北作家后继有人的期待》,《文艺报》2014年4月28日。
④ 艾伟:《承担与勇气》,《文学报》2003年10月30日。
⑤ 陈应松:《与“底层叙事”有关——在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的讲话》,《所谓故乡》,地震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⑥ 陈应松:《〈太平狗〉及现实主义》,《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
⑦ 陈应松:《文学应当参与社会的进程——在韩国的演讲》,《天下最美神农架》,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⑧ 韩晗、陈应松:《现实、乡土或底层》,《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8期。
⑨ 陈应松:《底层叙事》,《穿行在文字的缝隙》,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⑩ 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封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1} 陈应松:《世纪末偷想》,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3}{14} 曾卓:《梦游的歌手·序》,《梦游的歌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17}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18} 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9} 陈应松:《语言是小说的尊严》,《所谓故乡》,地震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20} 陈应松:《神农架和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武汉图书馆的演讲》,《天下最美神农架》,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21} 陈应松:《还魂记·后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页。
{22} 刘芳、黄念然:《论反讽的中介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3} 何垚、黄希庭:《〈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国和,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湖北咸宁,4371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