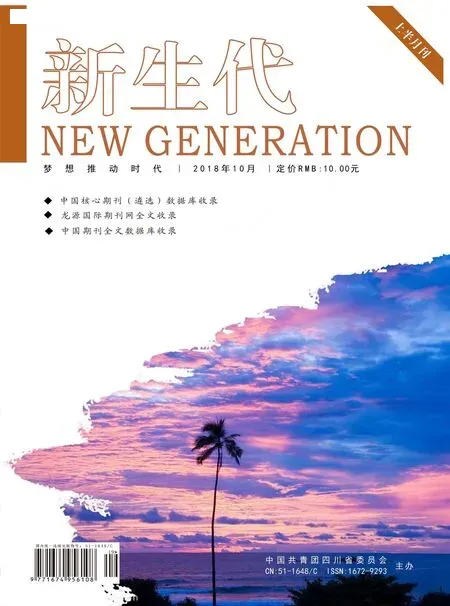学前教育阶段虐童行为的法律监管体系构建
马超 张心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017年,是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后,全面“二孩”政策实行的第三年。新生人口的增加,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却迎来了早教问题的突然“井喷”。“携程亲子园”、“红黄蓝事件”的出现引发了包括各类媒体、社会组织以及广大网民的口诛笔伐,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确立以后,公众零容忍的虐童事件却未能没有停息。法律应该如何起到在国家治理规则起到它应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一、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确立
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确立之前,学术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往往面临如何对虐童者进行刑事追责的问题。虽然刑法中有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对虐待、伤害行为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制,但现实案件中却难以处理,施虐者的行为事实难以入罪,因为故意伤害罪要求受害人生命健康权的损害达到一定的标准,一般的虐待儿童行为只是造成一些肉体疼痛,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根据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家庭的成员的规定,对于一些幼师虐童案也不能用虐待罪进行处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在浙江温岭幼教虐童案发生以后,温岭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了施虐者颜某,后来却又因为难以定罪,该案被依法撤销,前后实施虐童行为两年的颜某,仅被拘留了十五日以后就被无罪释放。
随着幼师虐童,或是看护人员虐待老人这种案件在全国范围内的发生愈发频繁,在舆论与学界的呼吁下,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罪名的确立,可以说在刑法上弥补了关于虐待罪立法的不足,将非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虐待行为划入到了刑法保护的范围。
(二)法律效用
在此之前,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行为,被限定在了家庭成员之间。即除第二百六十条针对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规定了虐待罪,第二百四十八条对被监管人规定了虐待被监管人罪以外,如需对虐待家庭成员以外的被监护、看护对象专门治罪,一直存在着刑事立法方面的缺失,在现实中即使发生了类似行为,同时需要运用刑事法律调整时,也多以“寻衅滋事”进行处罚。这导致了其他施虐对象产生虐待行为时,要试图去套用其他罪名。但这往往会出现不适用或者嵌套不能完全吻合的情况,从而会降低施虐者的罪行。浙江温岭的幼师虐童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后果是,不仅不能对于虐童行为实施有效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学前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
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正是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实现对于除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施虐群体的有效打击,同时也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严格规制监护人、看护人等群体的行为以实现对于这类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
二、虐童行为的原因分析——仍未消减的法律思考
(一)刑法规制的局限性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是立法工作的进步,弥补了刑法有关方面的缺陷,也是国家对儿童保护,人权保护十分重视的重要表现。同时,刑法是制裁方式是最为严厉的,通过对犯罪人员的生杀予夺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刑法来规制有关的虐待行为,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从2015年11月1日“刑九”生效以来,关于虐童案件的报道仍然频繁出现了公众视野之中,2015年11月,30多名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的儿童被针扎,2016年11月,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一民办幼儿园教师疑似拿针管扎学生。2016年12月,河北深州一所幼儿园的几位保育员涉嫌虐待孩子。2017的“携程亲子园事件”以及“红黄蓝事件”的发生更是震惊全国。但是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幼儿园虐童行为适用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判例仍然较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中,目前仅有五例关于幼儿园虐童最终适用于虐待被看护人罪的判例①。在已有的判决中,我们发现存在着罪名适用混乱的现象,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一项选择性罪名,在对幼儿园虐童行为应是“虐待”,但是最后判定的罪名却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和“虐待被监护人罪”。同时,还存在处罚力度较轻,附加刑中的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不规范的现象,应该说这是和此罪确定的时间较晚,条文内容不明晰,在司法实践中应用不够充分有着比较重要的关系。
(二)相关立法建设不完善
从不同法律的性质来看,刑法具有谦抑性,是保护社会利益不受侵害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在民法、行政等法律对法益的保护不够充分时,才会把“刑法”作为有效保护的最后手段,所规制的行为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②。在接连不断的虐童事件发生以及司法实践中,使得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规定中,处罚标准没有阶梯变化,刑罚方式的单一,缺乏整个法律体系的支持的缺陷暴露了出来。
而且目前整个针对学前教育的监管体系建设并不完善,相关的立法包括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教育部批准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2016),《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2017)等,在各地还有专门的《学前教育条例》,同时还有一些学前教育的规范散见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乃至于《宪法》中,总体来说,立法数量不少,但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尤其是在对比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都进行全面的规制。学前教育作为《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四个教育阶段之一,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层次较高的法律进行学前教育的规范。同时,国家在0—3岁的托儿所的监管方面缺少立法规范。国务院的《幼儿园管理条例》只对3岁以上的幼儿园,这个立法空白也给给了一些利益集团上下其手的空间。
总的来说,虽然相关规范很多,但大多是指导性的,只是从宣传和号召上发挥作用,缺乏对实际操作的规制,有些区域还存在着立法空白。关于学前教育的法律监管体系没有形成,没有从多个层面形成系统化多元化的学前教育领域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三)行为主体缺乏从业资格
从目前我国已经发生的虐童事件来看,大部分事件的发生都与幼师队伍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在这一环节当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幼师队伍的素质,幼师的不负责任,打骂行为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直接威胁。虐童事件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相关的从业人员缺乏儿童权益保护意识,没有专业教育,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缺乏较严格的准入门槛。许多早教机构为了快速敛财,多采用“先上岗,再考证”的办法,让没有教师资格的工作者进入到从业领域,从而直接导致了这些未经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对儿童做出了暴力行为。
在另一方面,一些托儿所、幼儿园经营十分“隐蔽”地进行经营,这些“黑幼儿园”无牌无证,缺乏必要的安全、消防设施,办学条件堪忧,有些地区经济不发达,早教资源缺乏,也难易符合相关的从业标准。
(四)缺乏有力的监管体系
幼师准入门槛的缺失,市场经营的混乱,反映出早教机构的监管力度仍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携程亲子园事件”中,这种早教机构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在2015年,携程曾经开办幼儿园却因为没有相应资质而被叫停,但在年底,因为上海妇联的牵头介入,上海《现代家庭》杂志旗下“为了孩子”学苑与携程合作成立“携程亲子园”。这其中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我们难以知悉。现已查明占有《现代家庭》杂志社100%股权的股东正是上海市妇联,同时亲子园负责人张葆葆有着横跨政商多界的复杂背景,这些信息也更加让人疑惑。那么这恰恰说明了我国目前在监管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相比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学前教育的师资以及监督管理都存在缺失。随着我国逐渐放开二胎,供需之间矛盾逐步产生,一系列学前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入门槛,教委和工商部门却都有准入的权利,这使得准入和管理都出现了齐头并进现象,从而使一些资格并不健全的教育机构钻了制度的空子。
三、学前教育阶段虐童行为规制中法律体系的构建
规制虐童行为可看做是对于儿童的一种保护,目前狭义的儿童保护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救济、社会救助和替代性养护等措施,对已受到或可能受到摧残、忽视、虐待、剥削及其他形式伤害的儿童提供的一系列救助和安全保护,以使儿童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就要求不论是在法律、监管还是学前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要各司其职,才能切实做好儿童的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使儿童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实现自身的成长。
(一)完善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在对虐童行为本身的规制上并不存在法律缺位的现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执法未必严、量刑未必够以及惩治未必准的现象,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使得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立法最初目的。因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定罪以及处罚的针对性以及震慑力问题。
具体到《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就是要从罪名的认定标准的确认、儿童证言的效力、儿童证人的保护以及提高虐待被看护人罪的法定刑,并且规范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
这些问题解决的主要路径一方面在于立法层面加进行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在,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形成更具权威性的法律解释或是指导性案例,通过总结案例来讨论措施并广泛推广,解决目前关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如何适用的问题。从而最终加强定罪针对性以及提高惩处效力。
(二)推动《学前教育法律》的立法工作
在2018年2月教育部所公布的工作重点中,已经提到要推动《学前教育法》的起草,去弥补目前缺少一个专门、系统、高位的《学前教育法》的空白。新的《学前教育法》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完善学前教育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并且要积极地引导国家关于学前教育方面经费投入、保障幼儿教师的正常待遇和规范不同地区办园条件的标准等方面,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
有了基础立法并不能够足以解决的实际的问题,为了解决学前教育领域的资源稀缺、从业主体不规范、幼师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动态的法律监管体系
法律是在封建宗法制度退化以后,由传统的伦理秩序向现代的法治秩序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2]。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主要的管控工具。然而,由于立法技术的限制,以及法律本身需要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性才可能保持法律的权威的特点。从早教市场扩张的速度来看,或者说各个市场领域所出现的新型的商业模式,采用立法手段进行全面规制,其立法成本将会非常高昂,或者说基本上不现实,对于其法律规制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因此针对办学、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强行打压,同时也需要专业的监督部门来加强引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监督的合理有效运行。法律规制必须克服其所具有的静态化、稳定性的特征而与整个社会脱节的缺陷,去不断加强法律规制的适应能力,要能及时解决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所产生的矛盾。
虐童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现象所形成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映照在法律方面,就是就整个学前教育监管体系的设置不够完善,而且虐童案件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虐童案件的受害儿童精神损害难以回转,所以对于虐童行为,必须从根源上寻求解决办法,如果不从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视角出发,只是依靠刑法的规制,或者基础法律的统筹那么,法律本身所应有的教育功能和救济功能就难以得到实现。
1.提高幼师队伍的准入门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教师应把保护幼儿生命和促进幼儿健康放在头等重要位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章第21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从教师层面对其行为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
在对幼儿园的日常教学过程,幼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地影响到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是虐童案件发生后的直接行为人。那么若要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首先就要提高这一队伍的准入门槛,从幼师的培养入手来将强对于幼师的专业素质及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培育。此外,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严惩虐童行为幼师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幼师的心理落差以及降低幼师的职业认同度,那么如何培养幼师队伍以及提高幼师的待遇,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于幼师的待遇,另一方面要提高幼师的准入门槛,加强幼师上岗资格审查,定期考核以及定期培训,同时要将幼师队伍加入到整个教师队伍的统一管理,保障其应有的福利待遇,定期进行培训,从幼师的培养以及认同度等方面入手,加强幼师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助于为学前儿童创造良好的身心环境,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从学前教育作为启蒙教育,以及幼儿园所需要承担保护、教学的多重任务,在幼教与幼儿之间,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同时也是儿童权益与儿童心灵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2.规范学前教育机构的市场经营行为
截止到2016,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77.4%②。学前教育的缺口仍然很大。学前教育的市场仍然是一个供给方市场,所以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营行为,必须要加以规制,对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幼儿园进行分类管理。
进行学前教育机构从事教育活动必须要有严格的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只有严格完成这些程序的教育机构才有资格从事相关的行业,对于一些区域,政府应该扶持幼儿园的发展,投入相应的资金,使不规范的幼儿园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办学条件特别差、无证无照的“黑幼儿园”、“黑托儿所”要坚决地予以取缔。
3.建立起系统的安全防控机制
从学前教育的相关行为主体出发,在幼儿、家长及幼儿园建立完善的联动机制,通过包括微信、短信、录像、实时监控等多种手段,让家长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孩子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有利于园方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是从不同阶段出发,在事前要加强预防,建立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定期儿童报告机制,把握儿童安全、幼教行为等关键控制点。在事中要加强控制,确定负责幼儿监管的机构,在事后的救助上,要及时将虐童行为人引入司法程序,形成司法震慑,并且在虐童案件的处理上,要考虑儿童心灵的脆弱性,推动侦查、审判机关对被害儿童实行 “一站式”询问,在专门区域,由专门的侦讯人员进行询问,避免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
四、总结
2017年发生的两起影响巨大的虐童事件,一个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全国知名的连锁幼儿园,另一个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最高,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并且在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的亲子园内。也让人不禁想象,在没有发达媒体报道的地区,学前教育的环境目前会有多糟糕。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学前教育事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越来越多的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开始将自己的子女送入各类托儿场所之中,但随着而来的问题就是,早教教师的培养却难以跟得上早教市场扩张的脚步,学前教育的机构建设水平难以跟上因为教师的素质教育可不像资本一样可以迅速膨胀,早教教师对幼儿的耐心与同理心的培育也不是一日而成。根据上海总工会的一项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只有35所,而上海0到3岁的婴幼儿人数却达到了80万。在供求失调的早教市场中,有许多托儿所,幼儿园“无证半血”托儿所遵从市场规律,选择降低教师的准入门槛,实行“先上岗,再考证”,使得许多非专业教师、不合格教师进入幼儿队伍,导致幼师队伍整体素质降低,资本涌动比法律规制要更加地汹涌。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应再仅仅扮演一种维持“底线”的角色,也要起到批准者与保护者的作用,要能担负更多的责任。应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立法方式,要多在源头上深挖,通过多种法律规范齐头并进的方式。首先要提高各个群体关于儿童权益保护意识,让儿童本身、家长还是幼师队伍,都应该清楚何谓虐待以及如何防止虐童行为的发生,当发现此类问题时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及相应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行政惩罚等。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加强各方面制度的完善,办学更为规范并纳入正轨。同时要加强监控力度,实现整个学前教育透明化、制度化。对于现有隐患要及时排查,对于未出现问题的要防患于未然,以顶层设计带动整个社会的行动,构建起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立法体系建立了,关系理顺了,才是对于打击虐待儿童犯罪的最好解决办法。
注释:
①任靖、刘志娟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内0105刑初516号》;宋瑞琪、王玉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6)吉0302刑初138号》;宋某虐待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冀0102刑初127号》;王某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刑事判决书《X2017)辽1322刑初101号》;邢某虐待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冀1026刑初312号》。
②参见文献: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16页。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发布的2016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