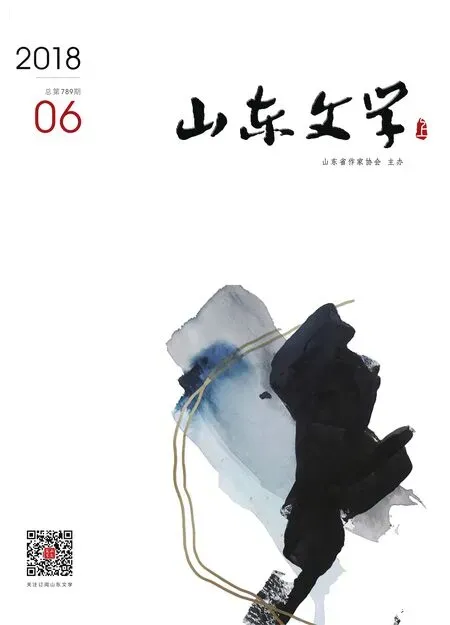灯烬
晓 寒
父亲是跟着母亲走的。
年轻时母亲就嫌父亲走得慢。这种事她不好对外人说,只好跟我们几姊妹唠叨,你爸啊——她无奈地摇着头,把一个“啊”字拖得老长,像是从老远的梦里飘来的,听了让人昏昏欲睡——走条路都让我看了发火。接下来这句,就真实多了,有一种尖锐瞬间俘虏了我的听觉。我看一眼母亲,她原本松弛的脸绷紧了,右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舞动。我怀疑要是父亲站在跟前,她的手指有可能会戳到他的脑门上。不过生气归生气,他们还是免不了一起出门,去走亲戚,下地干活,上邻居家串个门,借个米和油什么的。有时才走两三丈远,母亲就失去了耐心,她喊着父亲的名字,张继统,你的脚能不能提快点?怕踩死蚂蚁啊?母亲的声音急促、干燥,冒着火星子。这么大的声,父亲肯定听见了,但他不回话,照旧迈着从容的步子。腰上那条白手巾一摇一晃,一双洗得发白的黄跑鞋像两条迷失了方向的船,懒洋洋地划动。母亲白了他一眼,脸沉下去,灰蒙蒙的,一副要下雨的样子,双脚突然注入了力量,把父亲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就这样一快一慢,隔老远走着,像一个即将收官的残局,剩下最后两颗棋子,冷落而无奈地对抗。这回,父亲走得更慢,用了五年的时间,才赶上母亲。
母亲是在冬天走的,那个冬天冷得硌人,一阵又一阵的风里,像是藏了数不清的刀子,顺着田垄杀过来。路上积了水,东一洼,西一洼。水边结了冰,村里人口中的麦芽冰,一茬茬的,像狗的牙齿,棱角分明,闪着锋利的光。没有父亲远远地尾随,母亲孤独地上路,冰茬因为突然受重纷纷断裂,喳喳地响在她的脚下。这次她比任何一次都走得快,走得决绝,连背影都没留下。父亲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躺在他和母亲睡过的床上,蜷缩着身子,把头埋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像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后,被一张疲惫的大网笼罩着。
床上的被褥换成了新的。雪白的枕头、床单、被套,没有一个污点,如同刚刚转世的镜子,照出过往的点点滴滴,在同一张背景下,镜头不停地切换。母亲弯着腰扫地,端着茶走动,慢条斯理地叠被子。这个存在了四十多年的房间,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掉,也换不掉母亲的气息。这一点,父亲比我们更明白。
我蹲在床前问父亲要吃点什么,他动了一下,我隔着被子感受到了父亲果断的拒绝。大姐掀开被子的一角,凑到父亲耳边,爸,你要啤酒吗?在大姐看来,这个当口,只有啤酒还能唤醒父亲的饥饿。父亲喜欢喝酒,到老了我们不再让他喝白酒,担心喝醉了出意外,只买啤酒给他。他拿起一瓶撬开盖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就底朝了天。这种喝法,连我都做不到。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相信,这是个八十岁的老人。大姐满怀期待父亲爽快地答应着坐起来,结果父亲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仍旧捍卫着原来那个姿势。很明显,大姐失望了。她坐到床沿上,扭过头默默地望着父亲,表情像纷乱的树枝,梦魇般交缠。
傍晚,父亲从床上起来,拖把椅子坐在大门口,目光扫过屋坪里的水缸、篱笆、一张废弃的桌子,然后挪向远处,像在搜寻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想找什么,连着屋坪的是一条泥沙路。几十年了,这条路一直固守着最初的样子,顺着河的方向,蹑手蹑脚穿过空空的田垄,再翻过一座拱桥,最后一闪身,钻进山里不见了。天冷得慌,路上一片荒凉,一条黑狗缩着脖子夹着尾巴,可怜兮兮地向桥那头挪去。很显然,父亲什么也没找到。他把目光收回来,在上衣口袋里捣腾了一阵,摸出一包皱巴巴的软白沙,看得出他想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来,结果连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过去帮忙,父亲一把拨开我的手,这只苍老的手充满了拒绝的力量。纠缠了一番后,父亲终于拔出一根来,点着火吸了几口,伴着一连串的咳嗽声,烟雾从他干瘪的嘴里冒出,在傍晚的光晕里绕来绕去,最后盘了他一脸。我们坐在旁边,被一种巨大的茫然包围,谁都不知道此刻该对这个失去妻子的男人说些什么。这个冬天的傍晚,天空冰蓝,冷风低低地叫着。一种幽深的梦境般的静默聚拢在我们周围,柔软、厚重,像是淤泥一般。
父亲吸完烟,烟雾没有像以往那样,把他领进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身子变得松垮而柔软。他照旧拧着眉,把烟屁股往地上一丢,伸出右脚旋转着把它揉成粉末,突然转过头来,像是问我们,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妈呢?做什么去了?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一连串的诘问,语气里充满了责备。父亲冷不丁冒出的话让我们面面相觑。我愣了下神后,接过话头,爸,我妈还在做事呢,等下就回来了。父亲听了眉头舒展开来,他说那好,等她回来就吃饭。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记忆突然短路,他恐怕连想都没想,就把自己毫不犹豫地丢在了昨天。
大姐一脸焦虑,把我拉到一边,爸成这个样子了,往后怎么得了?她低着头,不停地搓着双手,仿佛这个世界又塌了一半,这无疑是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事实上,我并不如大姐那样担心。父亲一辈子在泥巴里打滚,他只是沿用了一个农民的狡黠,为暮年的孤独和悲伤找到了一块缓冲的平地。往后,还跟以前一个样子,母亲随时会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帮他找东找西,给他念紧箍咒。这样也好,父亲什么也没失去,心里那些牵挂和依赖,原封不动,完好如初。
实质上,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和身边众多的同龄人一样,顶多算一对柴米夫妻。走的是祖宗的老套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对父亲有种种的不满。她嫌父亲抽烟。父亲烟瘾大,他自己做了把烟筒,一根两尺多长的水竹子,在麻石上磨得溜光,再在两头套上黄铜烟嘴和烟斗。这把烟筒像爱人一样伴随着父亲,消弭着他的白天黑夜。烟火在上面越积越多,越来越浓,泛着隐隐约约的光,看上去像古画中的物件一样遥远。每天吃过饭后,父亲拿起烟筒,从铁皮烟盒里撮一撮烟丝,塞进烟斗。嚓的一声,洋火着了,父亲粗大的手指上升起一簇蓝色的火苗。伴着他嘴里吧嗒吧嗒的响声,烟斗里的烟丝一明一暗,像我家那盏老式煤油灯,失去灯罩的庇护后,胆怯的火苗,在夜风的威慑下躲躲闪闪。父亲抽烟和别人不同,一连抽上六七袋,烟斗烧得叽哩咕噜地响。黏稠的烟油冒出来,滴到地上,哧的一声,变成零零星星的黑点。那些黑点儿像是父亲身上遗落的某样东西,一个个鼓着眼睛,哑然地审视着周围。烟雾渐渐密集,把父亲和外界隔开,为他构筑起一个虚妄的世界。他躲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知道,是找到了自己?还是丢失了自己?呛人的草烟味在厅屋里肆虐,母亲路过时总是捂着鼻子,眉毛打着结,弯弯曲曲,像一座陡峭的难以攀越的山。
她也嫌父亲喝酒,她当着我们的面大声责备父亲,你总有一天会被酒醉死了去。父亲习惯了母亲的刀子嘴,他一声不吭,用沉默熟门熟路地敷衍着母亲。父亲好酒不假,但远没到酗酒的地步。母亲也只是反对,并不担心他酗酒。母亲再清楚不过,就算他有意做个酒鬼,也拿不出这笔本钱。父亲就是经不住人家的劝和哄,和他一起喝酒的都是知根知底的邻里亲朋,酒倒好了,开场白大同小异。统生,你又不是不能喝,喝这点还会醉?边上的人赶紧帮腔,人家一劝一哄,父亲就顺着杆子往上爬。他乜斜着眼睛端起杯子,也不看里面的酒是多是少,便呵呵笑着,喝这点那肯定没事。只要一端杯子,局面就失控了。父亲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像喝水一样。喝到最后,他就跟人家讨酒喝,再倒一杯,喝完这杯不喝了。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醉了。每次喝得踉踉跄跄回来,照例会遭到母亲的训斥,又喝那么多?你没见过酒是吧?酒给了父亲底气,他的嗓门大起来,盖过了母亲,只是口齿不清,好端端的一句话说得磕磕巴巴。你莫,莫管得宽,喝,喝两杯,怎么了?然后倒在床上打起了呼噜。
父亲确实大醉过一回,把郎中都叫来了。那是三哥把被褥从学校挑回来的那个晚上。父亲是希望三哥好好读书的,他在饭桌上对我们说,你们十一姊妹,总要读一个出去,就老三吧,卖禾种都要让他读。三哥在兄弟里排行第三,成绩好,是读书的料。结果上高中后,他说那些老师太凶了,便自作主张,一股脑把东西挑了回来,坚决不肯去了。那回,我们都认为父亲不行了。医生在给父亲打针,母亲把一杯浓茶放在床边的小方桌上,转过身偷偷地抹眼泪。她的阴沉在脸上聚集起来,成为一种针对父亲的汹涌的酸楚和无奈。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也站在母亲那边,反对父亲喝酒。我就是弄不明白,明明知道会醉,喝那么多做什么?
母亲最嫌父亲的,是他只知道老老实实地做事。往往是这样,父亲正在灶屋里洗碗筷,母亲一把抢过来,这些事不用你操心,我会做。言下之意明白得很,父亲是个男人,要出去干正事、大事,而不是在这些鸡毛蒜皮家务事上浪费时间。偏偏母亲嘴里的正事、大事,父亲就是干不来。有一次,新来了个姓吴的办队干部,母亲叫父亲去请他到家里吃顿饭,联络一下感情,以后好多多少少受些照顾。父亲死活不去,他一反常态,像个话唠一样搬出一大堆理由。我跟他不熟,又不是亲戚,也没事要求他,请他吃饭做什么?母亲急得直跺脚,骂父亲,你真是个死脑壳。
我对父亲的印象,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母亲,他曾长时间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抽烟,喝酒,下地干活,这是父亲生活的全部。他不紧不慢地重复着这几件事情,对付着一个个无休止的寡淡的日子。时间似乎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今天看到他,是这个样子,明天看到他,也是这个样子,隔上三五个月,还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在心里认定,父亲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就像山上那些年老的树,比一个村庄更老的树,它们一次次经过我,和我对望,用我刚认识它们时的表情。
我结婚比较晚,婚后去了县城谋生,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接父母来住。父亲来时,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带着他那把烟筒。我说,爸,在我这烟筒就不用了,抽这个。我把一条盖白沙递给父亲,他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火,时间顺着烟的方向,一截截化为灰烬。最后一个烟圈从父亲嘴里出来,越来越大,荡开屋子里的寂静,逃出我的目光。刚洗的烟灰缸里,有一小截完整的烟灰,还在怀想着它的雏形。父亲看了一眼,貌似在怀疑记忆的可靠性,自己到底抽没抽过烟?他说这什么烟啊,抽了跟没抽一样。还是草烟好,你去把我的烟筒拿来。我把烟筒拿给父亲,看着他熟练地完成那一套程序,装烟丝,用手压紧,划火柴。可这一次,并不如平日那么顺利,他使劲地吸着,但没有听到我听惯了的那种顺畅的咝咝声。他的脸憋得通红,腮帮子鼓得老高,额上的青筋像一条条吸饱了血的水蛭,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父亲不肯轻易放下烟筒,又拿它没有办法,就像置身于一场博弈,手里攒着筹码却不知如何下手。一袋烟抽得马马虎虎,草草收场。父亲沉默了片刻,随即很轻松地对我说,先放回去吧,昨天夜里车子吵死人,没睡好,等过两天再用。
我接过烟筒打量着父亲,他顶着一头灰白,黧黑的脸上像有八爪章鱼爬过,留下拖泥带水的爪痕。一条生命,要经历多少风吹雨打,才会如此的沧桑?而这些,在我眼里,都被所谓的距离一笔勾销了。我终于开始相信,距离越近,真相越容易遭到篡改。岁月无情地否定了我早先那个天真的结论,到底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刀,对准了我的父亲。我的心像被利器猛地扎了一下。仿佛有很多东西穿过我的身体,那么缄默,那么迅捷,那么顽固,让我猝不及防。
那段日子,我和父亲心照不宣,都不再提烟筒的事。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用过那把烟筒。父亲和生活斗了一辈子,就像一个看守瓜地的农人,手持镰刀棍棒,严防偷瓜贼的到来。现在他老了,没有力气再斗了。
白天,我和妻子出去上班,父亲和母亲呆在家里。有时候,在我准备出门的那会,母亲跟到门外的走廊里,小声提醒我,你爸的烟没了。或者说,酒没有了。烟和酒买回来,母亲默默地看着父亲吸烟,看着父亲坐在饭桌前举杯喝酒,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脸上竟多了一抹笑容。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它最终让母亲宽恕并理解了她身边的这个男人。
秋天的时候,我接父亲来县城,这是母亲离开后的第二个年头。
父亲没有赞同也没有拒绝,任凭我把他扶上车,替他系上安全带,像个听话的孩子。
一路上,我把车速放慢,走一段报一个地名,文市、楼前、澄潭江、大瑶、荷花,这些地名都是父亲熟悉的,搞集体时他担石灰经常从这些地方经过。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唤醒父亲结满蛛网的记忆。
父亲一边听着,一边嗯嗯地点头,短暂的茫然过后,浑浊的眼睛里掠过一线明亮的光。他指着路边的一座桥说,这里我来过啊,到筚溪塅担石灰就从这里过。他心里那道闸门突然打开了,往事像水一样清澈地流来。你看,那是渡槽,去你表叔家就要过渡槽,你跟我去过的。父亲把身子往后靠了靠,那时候好啊,十几个男劳力喔嗬喧天,每个人担一百多斤,也不晓得累,有一回担子在肩膀上,人就睡着了。父亲说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父亲说的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有一次他和上屋的巫光南一起去担石灰,到家时天快要亮了。一路迷迷糊糊地走着,突然醒来发现过了廖家坝,快到蒋家坪了,这等于弯了六里多路。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都被村里人当笑话讲。当时,两个人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当然没真抽,主要是真抽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哑巴吃黄连,掉过头来,闷闷不乐地往回走。从老家到县城的路上,父亲没停过嘴巴,我默默地听着,不时插一嘴。我很为父亲高兴,希望借此把父亲从昨天拉回到现实中来。
父亲腿脚不稳,他走动的时候,扶着墙、凳子、床、沙发。这些平常的东西,都成了父亲安全的依赖。即使扶着这些东西,父亲还是不放心,一步一摇,像机器人一样。有时候我扶着他,一再叫他不用担心,他嘴里答应着,好,好,那我晓得咯。眼神却犹疑不定,脚很不情愿地伸出去,在地上点一下又缩了回来,像在试探着什么。在他看来,他这个儿子也不是绝对的可靠。他怀疑身边的这个世界,不再是以前那个世界。在他的感觉里,周围的一切都是摇晃的,充满危险的,随时有可能轰的一声塌下来。
我住的是一套老房子,设计上存在缺陷,卧室离卫生间有点远。我特意为父亲准备了一个塑料桶,倒些水在里面,这样可以减小气味。我告诉他不用去厕所,就用这个桶子。父亲以为我在哄他,他说这不好吧?在他看来,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我说有什么不好呢,这样多方便。他还是不相信,想再确认一下。他指着桶子,用强调的语气说,就是这个桶子吧?我说是的,父亲终于放心了。我对父亲说,这个桶子就放在这里,你不要去动它,早上我会拿去倒掉。父亲再一次点头,表示明白了我的意思。一连几天都相安无事,我相信父亲是明白的,并非大姐说的那样。
有一天下晚班回家,走进父亲的房间,发现桶子里的尿全倒在了地上,房间里就像一个水池子一样,整个屋子布满了尿骚味。爸,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动吗?我心里一急,声音不由比平时大了许多。大概我很大的声音吓到了父亲,他嗫嚅着说,我,我看见你搞不赢,就想帮你倒一下。不要紧,我没倒在屋里,都倒在门前屋沟里了。我没有回话,屋子里一片阒寂。我们住在乡下老屋里的时候,洗脚水和洗脸水都是往屋沟里倒,哗的一声,就完事了。父亲是把这里当成以前的老屋了。见我不说话,父亲的脸色缓和了一些,没事,不要发火,等下你妈回来看了不好。我发现我的态度不对,赶紧说,爸,没事了。
我拿来拖把,把房间拖干净,再用清水洗一次,拿抹布抹干,然后点上一盘檀香,屋子里的气味小了许多。我突然觉得我想把父亲从昨天拉出来的想法是多么残忍。对他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在昨天,那里有一本存储着快乐和幸福的折子,可供他无限额地支取。
周末,我在家陪父亲。父亲显得很高兴,就算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忙这忙那,一句话也不说。我偶尔去看下书,父亲就拖一张椅子坐在我边上,我能听到他日益微弱的呼吸。他怕我不高兴,你看你的,我就坐一下,不妨碍你。可是一会,父亲就坐不住了,他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你给我扣下这个扣子吧?你有烟吗?我一根烟都没有了。其实,他的衣袋里就放着一包烟。我要喝水,你拿大杯子倒一杯。只要我动作稍微慢一点,父亲马上补上一句,语气也换了,用了一个“请”字。我请你帮我一下咯——印象里,父亲从不这样说话。他反常的客气让我心里涌过一阵酸楚,赶紧把书放下,一件件为父亲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有的是真做,有的刚做完,父亲就忘了,得跟他一遍遍解释。最后,父亲满意了,像我小时候拿到他给我的糖果一样笑起来。
有一天中午,因为头天晚上写东西到深夜,我想好好睡个午觉。我说,爸,我睡一会,要不你也睡一会吧。父亲说好。我把父亲安顿好就在沙发上躺下了。模糊中听到父亲的房间里传来很大的响动。我爬起来看到父亲站在窗前,他弓着身子,双手抓着防盗窗拼命地摇晃,防盗窗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大的响声,像冬天的风在死命地拍打,这情形让我想起关在笼子里的孤独而愤怒的豹子。父亲一边摇一边大声地喊,喔嗬——对门岭上有人吗?有人应一声啊。自然是没有人答应。窗子外面是一条大街,人和车汇成一条时断时续的河流。越过大街是僵硬的楼群,一直漫延到浏阳河南岸。父亲的视觉和感觉已经无法达成默契,他把这个城市的中心当成自己的老家了。在老家,山上劳作的人们确实是这样喊的,用喊声来驱赶疲惫和孤独。山隔得不近也不远,但喊声必须大过风和草木的声音,否则对方听不到。现在的父亲回到了原来的父亲,他在喊过去的自己。那个在山上伐木的自己,那个挑着一百五十斤谷脚步稳扎扎的男人,那个用一个通宵把石灰从百多里外挑回来的男人,那个一杯接一杯喝着烈酒的汉子。只是这时候的父亲,声音嘶哑苍老,阳光从窗子里漏进来,跌进他一头纷乱的白发。
我不敢去叫醒父亲,生怕他一回头,我的眼睛会出卖我。我努力找寻着能够逃离这无法忍受的现实的途径。过去,仿佛那是遥远的过去,没有什么事能难倒父亲。他赶着牛在月光下翻地,背着吃了生蚕豆中毒的大哥跑十五里路搭班车去县城,扛着被子和米送我去外乡上中学。他默不做声地做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懂得,在风雨来临的时刻,总有一棵可以倚靠的树,一棵庞大的不会倒下的树,他拼命打开枝叶,自己经历风雨。
想起前几天给父亲洗澡的时候,我为他抹上沐浴露,给他擦洗身子。时间在他雪白的皮肤上打上了褐色的斑点,我的手感觉不到肌肉的存在,面对着我的,几乎就是一副轻飘飘的骨架模型。他坐在凳子上,死死地抓着我的双手,就像翻滚的波涛中的一叶孤舟,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巨浪卷得无影无踪。
我的泪最终没有忍住。
今年端午节后,父亲越来越安静了,这是一种带着某种征兆的安静,让我的心跟着悬了起来。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就像一场战事的前夕,明明预感到危险一步步逼近,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
他懒得坐起来,懒得说话,懒得翻身,大部分情况下,用同一个姿势面对着世界。躺在床上,蜷缩着,像个睡在帐篷中的迷路的探险者,一半昏睡,一半茫然,看起来,生存或是消亡的前景都是一样的无关紧要。
柏拉图说,人生就是在练习死亡。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部内容重叠的哲学?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条生命残忍的轨迹。等到有一天,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将和父亲一样,成为某样东西的奴隶,就像禁锢在琥珀中的虫子一样。那个东西可以叫命运,可以叫时间,也可以叫衰老。只是那个时候,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六月的一个黄昏,父亲走了,他是无疾而终,在时间里耗尽了自己。屋外,夕阳刚刚散场,天还很闷热。田里的禾苗正在抽穗,菜地里,瓜菜一片葱茏。这些名叫庄稼的东西,和父亲相处了一辈子,就像父亲的孩子。从此,它们将和我一样的不幸。
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就在前一刻,他还微微地张开眼睛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然后安详地合上了眼睛。这是父亲的秉性,做什么都一声不吭,默默地吃饭,默默地干活,一天难得说几句话。到最后的一刻,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行事风格。
入棺的时候,我在父亲身边放了一瓶酒,不是啤酒,是五十二度的白酒。我喜欢那个喝着烈酒的父亲,滋的一声,一杯泛着白花的酒随着满满的力道直达脏腑。到这时为止,我已经是酒场上的常客,为梦想为感情醉倒过一次又一次。那年和女朋友分手回来的路上,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在路边的荒草地里睡了大半夜,醒来时看到满天越秋的星斗,低低地压下来,远处的田垄上连虫子的叫声也没有,只有一团团冒起的白烟,爬起来扶起落满冰凉的露水的单车,恍惚中泪在眼眶里打转。仅仅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父亲喝了那么多酒,我从未看见他流过眼泪。我与父亲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酩酊大醉时,总是关不住泪水的闸门。
在我还没学会抽烟喝酒以前,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不会打扑克,不会唱歌,不会下棋,除了烟酒,我不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按张岱的说法,父亲是一个不可交的人,直到那把胡琴的出现。那把胡琴是父亲一手做的,除了两根琴弦是买来的,其它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琴筒是一截普通的楠竹,膜是一块菜花蛇皮,柱子是一根小毛竹,弓是苦竹的鞭。弓毛本来是要用马鬃的,村里人连马都没见过,哪有马鬃呢?结果就用一绺山棕代替。这把琴简陋、粗糙、滑稽,就不应该叫琴。一个夏天的晚上,父亲坐在屋坪里拉琴,他拉的是花鼓调,声音连贯,顺畅,显然不是初学者的水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本色的琴声,清汤寡水,一马平川。琴弓在父亲的手里一来一去,却感受不到激越、高亢、呜咽、低回,那些凸起都被他一一削去,棱棱角角也被他磨平。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父亲拉琴,那次以后,父亲再没拉过,那把琴也不知所终。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拉琴并做了那把琴,我不得而知,大概是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以前。这个夜里,初为人师的我突然理解了父亲。那琴声是父亲梦想的出口,虽然那个出口小到不被我以外的任何人察觉,但就是再小,毕竟也是一个出口。有谁的梦想,原始阶段就在敞开的大平原上腾空而起呢?只是那个小小的出口也没给父亲留下,被接踵而来的柴米油盐春种秋收给堵死了。结果,父亲放下了琴,拿起了烟筒,端起了酒杯,一直到老都没有放下。烟酒,对于父亲,是一种药,一种安魂的药。
棺盖缓缓地盖上,我听到扑的响了一声,这是我和父亲的永诀。从此,我就是一个失去了庇护的男人,要独自去面对一个世界的风雨,尽管我早已有了应对风风雨雨的经验,但心里还是涌上来一种说不出的恐慌。
夜幕落下,墨色在屋场上涌动。大哥在父亲的棺木上点了盏灯,一个粗瓷碗装着植物油,一根草纸捻的灯芯搁在碗边。晦明不定的灯光,为父亲的亡灵,照亮通向天国的路。刚点上不久,一阵大风刮来,看这架势,这阵风是昨天的风的延续。昨天午后,一股飓风夹着漫天倾斜的雨点席卷了村庄,把对面山上一棵碗口粗的杉树拦腰折断,留下一个撕裂的树桩不祥地指向空空的天空。灯突然灭了,灭在这阵风里。大哥划着火柴再次点燃,在微弱的火光里,我看到了燃烧后那截灰褐的灯烬,举在风中,像我经过十字路口茫然四顾的时候,谁为我插上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