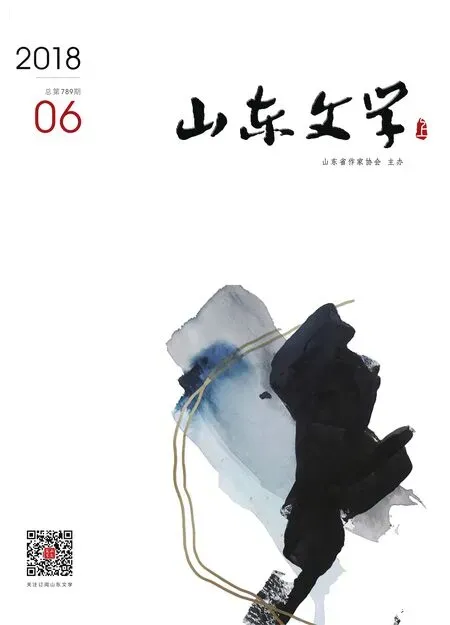青色草原博尔塔拉
吕仁杰
一
有这座城市之前,花和草肯定已经先抵达了,那是季节的风,将一粒种子吹到博尔塔拉大地上,孕育出生命,生根发芽,最终它们结亲繁育,有了成片的草原。风是羊群的舵手,是城市的方向,更是草原的生命使者。草,是春天最早生长的植物,风和草可以把一粒种子,带到屋檐瓦当的缝隙里,带到石头的苔藓上,带到怪石峪的沟壑里。
每天读书时,我会拿起一块石头替作镇纸,帮我压一下翘起的书页。这是一块天山青,形状极其像一只脚,它遍身灰白色,脚面铺满土黄色条纹,灰和土两种颜色叠加在一起,有一种久远的感觉,勾起我在博尔塔拉的日子。
它的形状确实像一只浓缩的脚站立着,虽然小,但总感觉有种强大的力量,站在北疆的大地上。我每天看到他时,就会听到北疆狂风暴雪的呼叫声,听到大地上野兽的奔跑声,也会感受到北疆阳光下的炙热和大鸟的鸣叫声。石头的纹理已融入我的情感和体温,变得不再冰凉。
在来新疆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查阅资料,想多了解这个陌生的地方。博尔塔拉我没有听说过,只有歌词里的戈壁滩和新疆舞,这个地名什么意思,我还没有弄清楚,但心却飘向那里。
博尔塔拉系蒙古语,汉意为“青色草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三面环山,西、北和南形成特殊的地理背景,中间是喇叭状的谷地平原。这里主要居住的是蒙古族,他们是一个豪放的民族,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四大组成部分。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依傍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时可以拆装的蒙古包,是草原的独特居住景观。
让我惊奇的是,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天山深处,有一种奇特的石头,长有人眼似的纹路。大自然的天斧神工,造就出的这种石头,呈青灰色,质地细腻光润,造型各异,如同玉一般,宛如青花瓷,当地人称为“眼睛石”,一块石头,是四亿年前大海的翻滚。
南北两侧的山地、中部博尔塔拉谷地,还有东部艾比湖盆地,组成了三大单元。全州最高点厄尔格图尔格山,在阿拉套山西端,海拔高度达4569米。东北部的艾比湖,却一下子跌落,海拔仅189米,它是全州最低的地方。阿拉套山之下,博尔塔河旁,有美好的传说。传说有着原始的美好,它如同一棵大树,在人们心中扎下根,一代代讲述着这个“故事”。
察哈尔蒙古西迁出发了,这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北疆地广人稀,沙俄趁势向远东不断地扩张,西面是哈萨克、布鲁特等强悍的游牧民族,当年的乾隆审察形势,感觉兵力不足,需要加强边塞的防御。伊犁驻军有一万七千多名,是正常驻防军的好几倍,对于政府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新疆的将领不断奏明朝廷,成为乾隆心中的难题。朝廷调遣内地八旗兵迁入北疆,察哈尔八旗兵是迁入北疆的第一批,北疆的换防兵则分批撤回。清政府专挑单身贫困者为选察哈尔兵,帮助他们还清债务,每人发放三十两银子,盐菜、银票照发,这对贫困的单身者来说是诱惑的。西迁后的察哈尔蒙古人,有田可种,繁育牲畜,生活富裕,对清政府充满感激之情,使得乾隆皇帝声望上升,得民心者得天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买了四百二十名察哈尔蒙古女孩儿、寡妇,送至新疆,将她们嫁给厄鲁特单身男子,他们结亲维护了新疆的稳定,消除了厄鲁特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我在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物珍藏馆中,看到一张乾隆帝的画像和《清代新疆察哈尔营》的连环画。察哈尔兵脚蹬长靴,左手持长矛,长矛带钩,可以用钩把敌人拉下马。右手拿弯刀,头戴白色皮毛,蒙古马看上去不高,但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这幅画看上去,查哈尔兵不是身披着盔甲,头戴铁盔,不是野战,倒像是骑射。图片证明了乾隆期间北疆的稳定和繁荣。
一幅图画,看到时间的变迁,“野地”失去野性,历史的痕迹消失不见。寻不到当年的情景,只有人们口耳相传,和资料上的记载,形成想象的空间。
二
“博尔塔拉”的地名和城市紧密联系,一个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高楼大厦、街道、纪念碑。每一处建筑形态的细节,民族的语言都贮满历史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一代代人相传,成为流进民族的一件重要的大事情。
你没有来过新疆就不知道新疆有多大,没来过博尔塔拉,就不知道有多美。一次经心策划的旅程,或是无意间经过,都会让你驻足,甚至停留。那是马背上的民族,羊群像春天的迎春花一样随处可见,脚印如同八月的棉花瓣,轻轻地和大地窃窃私语。在这里足够可以忘记城市,忘记不愉快。我相信,只要你经过,就会把你的心拴住,再也迈不开步伐。
二零一七年八月,是我第一次去新疆。百度上构画出来的大草原,和我眼前的不同,朋友的车子驶出地窝堡国际机场,和想象中不一样,眼前呈现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而是高楼大厦。川哥开玩笑说,这是从济南飞往济南。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并没有感到这座城市的陌生,而是从家乡飞往家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正在漫延,我担心草原会被它一天天吞噬。
八月的济南又潮又热,这个季节,从空调车里出来,会是一股热浪扑来,让你来不及躲闪。和我一同前往新疆的川哥,细长的眼睛,抿起两个深深的酒窝,调侃道,八月的济南是又热又浪,来到新疆是又干又爽。怪不得,我的朋友留在新疆不再想家,我似乎找到答案。
从地窝堡机场出来,阳光不温不火,一阵凉风从皮肤上擦过。朋友说,新疆不粘人,只心粘着心,这里的空气不单是想让你驻足,更会让你的体温留恋。
三
我从不同角度拍下一组照片,记录风雨苍茫的蒙古包,这是留给后来岁月的阅读。
文字和图片构成的画面,和想象中不同。蜿蜒在山间的电线开始变粗,黄绿相间的地板格开始变大。第一次到蒙古包,远远望去,犹如雨后冒出的小蘑菇,如同油画一般。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家,这一特有的文化模式,伴随着草原走过漫长的年代。
经过一上午车程,我们到达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蒙古族牧人穿着盛装,唱着长调,拉起马头琴,用蒙古族舞蹈,欢迎远方客人的到来。辽阔的歌声里面夹着青草的味道,传向远方。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山东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自然也是用美酒接待远方的客人。蒙古族虽没有山东的礼节多,但也历史悠久,他是多民族融合,大文化下产生的民族,有特殊的历史和讲究。
当远方客人来时,蒙古族会为客人献上白色的哈达,白色象征纯洁、吉祥,是蒙古族给远方的朋友,送上最珍贵的祝福。我们下车沿着小路走上十级台阶,一位美丽的蒙古族姑娘,身穿蓝色长袍,领口、袖口绣有回纹,象征平安的意思。她头戴银式别簪,精细华美,服饰风格和头部花饰、帽子,构成蒙族服饰的独特形式。她双手捧起洁白的哈达,给我戴上,白色哈达伴随我的黑色长裙飘扬起来。朋友摁动快门,记录下这一瞬间。
来博尔塔拉之前,我买了本《蒙古秘史》,读史料才知:哈达是远古中国的珍贵礼物“玉帛”的“帛”。在文献记载中得知:大禹大会天下诸侯时,配戴玉帛与会者万国。“玉帛”本来的意思是“在共尊帝王为家长的大家庭里,天下诸侯相互礼敬对方为兄长”,其背后的引申意思是“兄弟部族亲如一家”。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旦这一天,大汗统治领地,或掌有管辖权的要员,都给大汗进贡金、银和宝石等礼品,并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财源充足、享用不竭。
哈达有吉祥之意,它是一种语言,写在远古,更像一首歌,时常停下奔走的情感,寻找过去的情景。它的内容不是一天两天读完的,它吸引着漂泊的人,不顾路途遥远,急急赶来。
博尔塔拉热情好客,喝酒叫喝热,喝透,和季节有关,一年四季冷的时间比较长,喝热酒成为接待远方客人的礼仪。热不仅是热闹,它代表情意深厚,当它和酒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种文化。蒙古族朋友献上哈达,并奉上用银碗盛的奶酒,我学着他们的动作,接过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和地弹了一下,朋友告诉我这是敬天、敬地、敬祖先。当我的拇指压向食指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手指浸进碗中,酒液进入我的肌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我把酒液弹向天空和大地时,似乎完成了一种庄严的仪式。
一个动作传达出的情感和语言不一样,酒作为汉民族是用来敬客人的,但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酒又赋予了新的意义,蒙古族的酒是用来送祝福的。酒是情感的沟通,马背上的人们崇尚大地、山川、河流、树木、石头。
情感留在草原,记忆、想象和历史,将在那里碰面。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说,蒙古族人是粗野的游牧民族。然而,我眼前涌现出马头琴声的悠扬,和蒙古族人热情的微笑,感受到粗犷背后的细腻和柔情。如果说草原是他们的生命,音乐就是他们的呼吸。我坐在济南家中,往窗外望去,一只鸽子单腿站立在窗前,它犀利的眼神看到有人来到,拍着翅膀飞走。耳边响起草原上的马蹄声,白云、蓝天和镶嵌在绿色地毯上的金黄色野花随风摇动。
四
石头是大自然的作品,无奇不有,更有它的地域特点。谁又能说清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一块石头告诉你生命本来的真实,照出时间的年轮。
走进怪石峪,大门口用石头构成的牌坊,拉开神秘的面纱,它是由十几条天然形成的山谷组成的怪石群。怪石峪的石头之怪,也怪得有秩序,有的状如天狗望月、狮身人面岩、孔雀开屏、大象戏水、沙海驼峰、石猴护子、鲨鱼跃水,有的宛如古堡、亭阁,每块石头都有一个故事,你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拍下一组照片,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桌台上摆着一块石头,当初卖给我的主人,给它起名脚踏实地,这是我在怪石峪带回来的。我抚摸它,如同抚摩一个千古的故事。脚踏实地是一个大自然的雕塑,它的情感不是人工的,注入自然的血脉。石头是沉默的,它经历千年,甚至是亿年,目睹着北疆大地上的悲欢离合。它长满岁月的苔藓,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越来越珍贵。
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博尔塔拉。如果说,大海让我知道生命辽阔,那博尔塔拉那片青青的草地,告诉我大自然的神圣。站立在那里,我渺小得竟不如一粒尘埃。
一块石头,如配上底座,放在博古架上便成为一件艺术品,完成它的艺术创造,放在博物馆里,那将是历史的见证。
阎立本的《职贡图》中,外邦朝贡物品时,有象牙、羚羊,画中有三个人,手捧山石盆景,其中的一盆形状如灵芝,另两盆形态奇怪。这不是常见的石头,有了奇怪的形态,也赋予它特殊的寓意,说明喜好怪石之风已在唐朝盛行。
唐代诗人白居易,痴迷于怪石,他通过各种办法,得到两块奇怪的太湖石,视若珍宝,他日后留下诗曰:“奇应惭鬼怪,灵合蓄云雷。”他在玩石中,品味出人生的意义,石头奇形怪状,有自己的个性,令鬼神都觉得惭愧。怪石是美的,肌理清晰,层层渲染,呈现灵活的现象。文人赏石、玩石、品味石,从中品味骨气、生命和人生,石头也展现文人的孤傲之气。
郑板桥曾说:“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美玉出自顽石,怪石也是一种顽石。
石头是有风骨的,如果说太湖石温润、细腻、幽深,如婉约的江南女子稳重、端庄、安静的话,那么天山青,则是大方、勇敢、豪气。有山就有石,我们沿着天山山脉,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阿合提别科尔赞布拉克峡谷,有一条河流淌着,此时没有了咆哮声。这里是天山青的发源地,我挖开干净的泥沙,从河床上剥出一块颜色玉化的石头,上面有天山的眼睛,我的手触摸到它周边的纹路,感受三亿年前的温度。捡石头,成为一种乐趣,你会不停地发现漂亮的形状,好看的颜色,我不舍得扔手中的每一块。
我手里拿着这块石头,看上去表面粗糙,我用河水将它洗净,露出几道深浅不一的条纹,上面铺满梅花,我视为珍宝。这么大一块石头,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风暴,一点点地顶风前往,才在这里停留,并且等待与我邂逅,捡石头是随缘的。
一个荒岭下,裹着一个不被浸染的世界,石头是荒野的艺术。那一天,我把天山带回家,感受到天山不是用来攀爬的,而是用来仰望的。
五
草原部落,不只是牧人和牛羊的大迁徙,史料让我知道,这是一个随畜逐水草的民族。
博尔塔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塞种人的游牧地。《汉书》说,乌孙国东边与匈奴相连,康居在西北部,西邻则是大宛,南面就是城郭内的国家,向西方迁移时,大月氏打败塞王。塞王直取向南,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大月氏率兵攻占原塞王的地盘,后来乌孙王昆莫占有了大月氏的领地。匈奴打败大月氏后,顺利向西征服大夏,而塞王向南迁移,以后便分散为许多的小国。
已是深夜两点,若在济南早已进入深度睡眠,在这里,我还沉浸在兴奋中。雨细致绵密,我拉开窗帘,玻璃窗爬满雨滴,翻开从济南带来的《古代蒙古》,眼前浮现出塞王曾经征战过的地方。
经过一夜的细雨,我推开窗户,闻到一股青草的味道,它和夏尔西里有生命的不同。和我同住一间房的小姑娘,就像天山上镶嵌的一朵白云,清透得可以让我看到天山那一头,以及山上挺拔的植被。
清晨,史料装进脑袋,幻化成图片。带着期待,我们一行七个越野车,经过三个小时的山间小路,这里的山路不同关里,在关里的山路是可以看到后面车的,但在这里,跑慢了,前面的车就会停下等待,才能接上队伍。车子行驶在山谷中,天山青的发源地,阿合提别科尔赞布拉克峡谷,山路的颠簸,如同行驶在刚刚转场上来的马背上。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欣赏远处的风景。
大山中间的小路上,被成千上万只牛羊拦住去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的羊群,仿佛这才应了那句“风吹草低见牛羊”,马背上驮着干粮、水、蒙古包和牧人生活的必需品。草原上的这些生命,因为牧草,而被季节牵动着。我想起熊红久说,转场的牛羊是被季节牵着走的,它们对时令的把握要比我们人深刻得多。对于草原的了解,其实我们不会高过一只羊。
羊群脊背上露出坚硬的骨头,耸立起来,像骆驼一样。这么肥美的草原怎么会瘦成这样,朋友告诉我,因为牧人和羊群刚转场上来,不停地走,一年要转两三次,就像刚刚奔赴下来两万五千里长征。成群的牛羊跟随牧人赶去地窝子,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日,等到来年春天再次转场。
每年春秋两季转场的牧群都会经过这里,周而复始,每次持续十天或是二十天。远眺,山口处尘烟又起,一个族群,一户牧人赶着羊群和马背上背负的“家”,向山涧走来。它们踩着天山的石头,沿着丛生的杂草,在秋日里变成云朵。
据说,现在的转场,都改成用卡车运输牛羊,穿梭在大山之间。时间是无情的,它加快了城市的速度。我是幸运的,如此庞大的大迁徙,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生活在城市也有自己的悲哀,我们为什么寻找过去的历史?城市在不停地掠夺着记忆中的草原、蓝天和蒙古包。因为逝去,所以我们怀念。
情感留在博尔塔拉的山中,我在黄河岸边,在回忆里寻找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