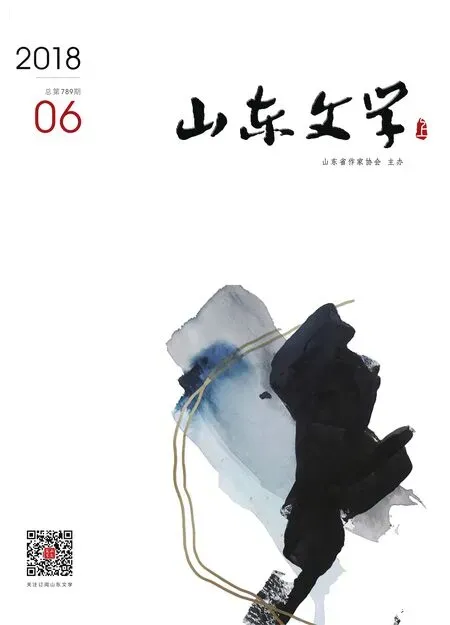西海固文本
程耀东
城与塔
与《诗经》里走来的这座城池相比,你长养在这个叫古雁岭的地方,时间并不久远。红色构建的骨骼,黄金锻造的肌肤,白银的线条分明在你的腰际,缠绕于身体上的每一级台阶,谁说不是这座城池留在光影里的记忆。伸向空阔的飞檐撑开你的羽翼,传送阴晴的风铃悬于时间高处,俯瞰苍穹的窗棂,在幽蓝的色彩里诠释着这座城池的苍老、坚韧、伟岸、阔达和雄浑。然而,为你遮挡风雨的依旧是黄土捏出的瓦片。
走近你,触摸你,在夜岚初上时分。
原本属于白天的喧哗、人声、脚步、镜头、闪光……此时已被城市出发的光影收敛,唯有清凉驻足于此。
树,自然是有的。桃树、杏树、杨树、柳树、云杉……算不上珍贵,却相互和谐着对方的生长空间。行走中,随意揪一颗拇指大的杏子,酸涩将人的记忆带回懵懂和混沌,也有是青春年代,不然,绝不会贸然造访。有青春,就不会没有秘密,此时回味,仿佛树林间飘散出的一缕暗香。
路是新修的,但过于平坦,就留给那些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以及饭后休闲的老人和孩子吧。我总是躲避噪杂,一个人在树与草的缝隙里找寻光亮的原点。草,自然不是人工的,如若是人工播撒,方显得有些娇柔、矫情和做作,与这片地域的性情和禀赋就有些格格不入了。
应该是今晚要到达的终点了,不然,他们不会说出:“这塔是固原标志性的建筑。”好在我不是游客、不是行者、更不是住一夜就起程的宿客,我是从这座城市的襁褓中长大的婴儿,母体的味道渗透一生。
目光在塔的身体上游走。红色、黄色、蓝色、白色以及黑夜下沉的色彩,不同方向柔和在它的面颊上,私占了半城风光。我的视觉似乎置于一种空幻,只好任其粘贴。
沿着台阶缓步,也不知道台阶有多少,高度肯定是有的,只是存放于每一个人的心里。光,也只有在夜的空洞里,才会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裸露,呈现它原始的纷繁和华丽。
而聚集于此处的人,总是不急不缓,目光与表情惬意在塔的周围,或者夜色里迟缓上升的微凉。声音自然是有的,但不是喧哗、噪杂、吵闹……而是窃窃私语,或梦幻般的呢喃在一圈一圈绕塔而上的光晕里,最后消散于夜色。风似乎很平缓,在暗淡里抚慰白天留下的疲惫和劳顿,抚慰千百年来从此处经过的人声和鸟语。风不会留下记忆,但会吹走时间。
绕塔腰一圈,眼睛被色彩斑斓的光线迷离,但绝没有迷失。雄浑的六盘山脉、蜿蜒的帝国长城、被废弃了的安西王府、不断迁徙的萧关城楼……这些沉睡在时间深处的地理坐标和历史符号,我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面对此时从城市的楼宇间出发的灯火,我只能想象她的过往。
坦诚地说,我眼前的这座城市,我不敢触及它的肌肤和骨髓,因为她的脉络流淌过的汉词实在无法计数。关隘、边塞、刀光、剑影、狼烟、烽堠、丝绸、驼铃、马蹄、诗歌、宗教……大凡帝国中心的每一次颤栗,这些强大的汉词箭镞一般,落于这片地域和地域上守护宁静的砖碟。
这时候,人声散尽,潮气上升,下沉的黑暗与灯光衔接的弧线上,星光不再微弱,如同我刚刚点燃的烟头。
在烟头的明灭里,我似乎看见一些人的身影,隐约在寂静的光线里。最先逆光而来的是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嬴政、刘彻、李世民、成吉思汗……他们三番五次地出现在这座写满荒凉的城头,为帝国的安危找寻更为坚固的石头。然而,当他们的步辇刚刚离去,紧随而来的便是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蒙古人、西夏人的马蹄和刀剑的寒光。
透过手指间徐缓扩散的烟尘,我的目光被一群煽情的诗人击伤在大唐的长安。这些名噪一时的诗人,将自己的名帖一次次地散发在萧关的大街小巷。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岑参、高适、王昌龄、李白、杜甫、王维……听听他们的名字,其中的一人微微跺脚,足以让整个大唐的诗坛颤抖。然而,他们以集体的力量发声于一座城池,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恐怕很难找出第二座了。我不知道是萧关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远播了萧关。这些从史书里抖落出的长歌短句,我读到的多是蒿草满目,芦草丛生的荒原,以及游魂萧关,尸骨遍野的惨烈。
依着水泥的栏杆,拍一张夜色中的城市。在黑夜的更黑处,镜头里显现得却不是斑斓的灯火,而是一个叫左宗棠的封疆大吏。这个晚清重臣,抬棺西征,遍插杨柳的同时,也没有忘却给这片土地播下“苦甲天下”的感叹。杨柳一年一度繁茂于萧关古道,“苦甲天下”的封条在时间的辙迹中日渐枯黄。假如这个前辈的灵魂尚在,今夜,我愿邀约此处。在这塔前,居高临下,面对一城辉煌,又该留下怎样的高歌与豪放?
树梢有了些许晃动,塔影也开始波动,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这尘世的光晕左右。在自己的阅读经验里,不断翻捡这片地域的过往以及人们冠以它的名字——大原、高平、萧关、固原、原州。在这些因时定制、代有异同的名字里,我不想去破解其间的密码,破解——只会留下更多的疼痛。
杏花开
这里是彭阳——杏花摇曳的彭阳。
触摸你酥软的肌肤,在一场温暖的碎雨扯开澄明的四月。春风使隐藏了一个冬天的苍黄远遁于视线以外,接踵而至的便是破土的鹅黄与淡绿。季节与农历在高原的背腹上开始彰显新一轮的妩媚,以及原本属于这片地域上的色彩和风姿卓绝。站在旷昊的蓝天之下,或者任何一道山梁上,极目远眺,搅动心扉的不仅仅是此时嫩芽初上的原野,还有这漫山遍野次第开放的杏花。
在黄土高原——在行走的高原人眼里,杏花便是春的使者。杏花开了,春就来了。不然唐人不会有“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句子。
百花丛中,你不算美丽。不及牡丹之富贵、荷花之清高、玫瑰之浪漫、百合之纯洁……你如同生你的土地,长养在朴实与自然之间。坚硬的骨骼、粗糙的肌肤、柔韧向上的枝条构成了你的表象。然而,就在这些并不细腻和光滑的枝条上,每一瓣红色、白色、粉红、粉白却以集体的力量绽放着招人的妖艳。依旧是一年一度的阳光,流泻在你的面颊之上,将你的玲珑写意在沟壑梁峁之间。
沿着山的海拔,梯田的曲线,破土不久的庄稼……这些蜿蜒在高处的杏花,将自己有序、无序地散落于苍茫深处。仰望,眼前是天空落下的一张粉红的帷幔,徐缓地下沉,不由自主的想象,将你带入时间无法过滤的梦境。站着,与一棵树对望。干净的花朵,安静的绿芽,淡淡的馨香……使你习惯了尘世与喧嚣的身体暂时有些无所适从。躺下,此时阳光正好,贴着草山,肉体被泥土芬芳。一缕细微的风划过树梢,花瓣飘落,飘在你的脸上,身上,或者手掌的纹路间。睁开眼,期间的一朵正好落于你的眼睑,但你绝不会感叹于花谢花飞飞满天的怅惘里。其实,飘落未尝不是一种美丽和辉煌。
站在高处,俯视。记忆中早年的山峦不知去向,只留下灿烂、妩媚以及包裹周身的韵致,致使我的文字无法访问你强大的盛开,也使我一次次失语于这满山遍野的雾一般的迷离。仅仅十来年,苍黄与苍凉被一种精神掩埋,纯真与秀美就绽放在母体之上。你不再含羞、矜持、掩映、藏掖……而是大方地裸露着性感的腰肢,接纳来自不同地域上的目光、闪光、肤色、语言、惊讶、感叹和弥留……彭阳——黄土高原腹地的一片地域,我原本就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呼出,声音在花海里显得那样微弱。
这些年龄不等、大小不一,或整齐、或寥落的杏树,被排列在这里,没有具体的种植者,也没有具体的看护者,在过往的季节的暗香里,迎来或送往了多少双脚印,仿若一年一度绽开的杏花,无从统计。一棵树,兀自孤独在一个避风的阳洼里,远远的,只露出半张脸,昭示着无处不在的春天的时光。时光在这里,不是欣赏者脚下煽起的尘埃,是树枝们向辽远的天宇扩散出的清新、恬淡、宁静和闲适。
细雨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没有注意。而这雨,不急不缓,给一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恰到好处的抚慰。倘若那个叫李清照的伟大诗人千年前来到此地,绝不会婉约出“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的句子。面对这样的灿烂和豪放,或许我们在宋词里读到的将是另一番意境。
山峦被淡淡的雨雾笼罩。人家屋檐上飘出散漫的炊烟,在雨雾与花雾之间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归宿。而院落周围这些正在享受雨滴滋润的花朵,偶尔会轻拂一下人的脸颊,而后微微摆动,似在挥别熟悉或陌生的身影。
绽放的依然是没有声响的杏花,飘散的依旧是馥郁的暗香。在一大片稠密的杏树之间,我看见一个女子,右手扶着一根枝条,左手拿了手机,不停地自拍,不断地变换着姿态。春天本应该属于花朵和女人,在这个远离喧嚣和浮躁的地方,她的肆意释放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此时,贵如油的春雨被阳光收敛。该是午后,那些睡足了午觉的人们,从窑洞里探出头,看着高远的蓝天和暖暖的春阳。在田间地头行走的他们,已经惯常了一季的花开与花落,对于往来的游人只是微笑着点一下头,也算是打过招呼了。这里不是高傲或者冷漠,是他们千百年来流淌的质朴与憨厚。泛绿的地埂旁,站着一个小姑娘,圆嘟嘟的小手在吃力地掐着杏花,她的身后,跟着一条纯白的小狗。
一个背着镜头的男人,疲惫于一棵树下,双眼微闭,任凭偏西的阳光在他的身体上肆无忌惮地游走。我的双脚致使我也有些动弹不得,只好学着他的样子。生活的琐碎与奔跑的欲望,将我们的身体缠绕于繁复,并不同程度地修改着行走的方向。只有将自己释然于这样的光景里,才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若没有时间的约束和几何线条的界定,我宁愿躺在这里,享受完这一季的花开与花落。
暖阳、青草、春雨、山野、梯田、庄稼、流水、人影……这些静止的或流动的物象,铺陈在千万朵的杏花里,每一个物象都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阳光西沉,我继续行走。在霞光与大野衔接的那一抹昏黄里,无数朵白色将自己敞开,飘在草尖上的花瓣与晚来的微风做着最后的告别,我行走的脚步也在这下沉的光照里终结。
此时,有云层从我的头顶掠过,祥和、轻淡,宛若暮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