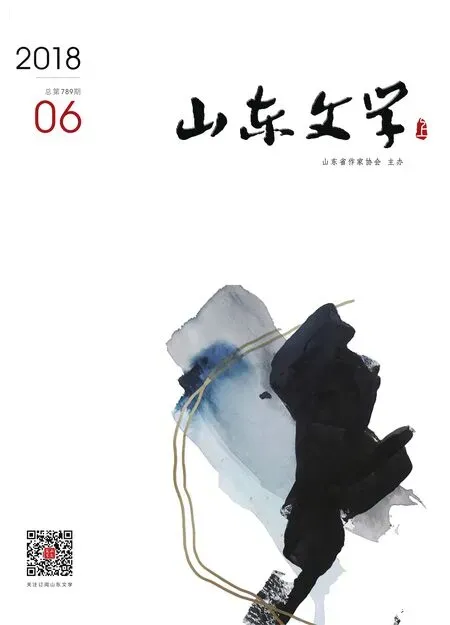新世纪儿童文学出版的新形态
李东华
直到上世纪末,中国的儿童文学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设立这个学科,也不被主流文坛认可。一个写作者只要跟“儿童文学”沾上边,那差不多相当于“幼稚”的代名词。最可怕的是读者对它的疏远:1998年《儿童文学》杂志发行量掉到6万册;江苏少儿社的文学期刊《未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文学期刊《巨人》《儿童文学选刊》停刊。很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本就不设立或者砍掉“儿童文学”编辑室,当时有句顺口溜描绘这个状况:“巨人”倒下了,“未来”没有了。然而,这样的窘境,在10年之后,到2008年左右,突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翻转:《儿童文学》《幼儿画报》等杂志发行超百万,《巨人》等纷纷复刊,此外,一些新的刊物在民营资本的运作下创刊了,比较著名的如《读友》杂志等,很多期刊都由月刊变成了旬刊或者半月刊。一些原本和儿童文学毫不沾边的出版社也开始积极介入这一领域,全国581家出版社,有523家出版童书。曹文轩的《草房子》10年间印刷了130次,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累计销售2000多万册。根据这些数字的今昔对比,基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新世纪前10年的儿童文学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读者,与惨淡经营的成人文学相比,此后儿童文学是“风景这边独好”,一路顺风顺水,到了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一标志性的事件表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不但被国内的读者所认可,也开始被世界读者和专家们所注目。发展至此,儿童文学无论是市场还是“走出去”以及艺术上,都成就斐然。20年,弹指一挥间,儿童文学这个弱小的孩子长大了,从被人忽视的“小儿科”长成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小巨人”。这其中究竟是出于侥幸和偶然,还是潜藏着对整个文坛都富有价值的启示?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这是缘于儿童文学有个天然庞大的市场。不错,我们国家有3.67亿的未成年人,但人口的庞大只是意味着潜在读者群是巨大的,这个潜在的读者群要转化为真正的文学人口,却是真正地考验了儿童文学的智慧与耐力。虽然过度的市场化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唤醒千千万万读者的阅读热情,我认为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得以翻身的最关键一环。而做到这一点,在我这个一直身处其中的人看来,是合力的结果。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关键词,我愿意用“情怀”来解释这20年间的巨变。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我们说上世纪90年中后期儿童文学遭遇了“寒流”,陷入了困境,这主要是指市场而言,并不是指儿童文学在艺术上的探索。相反,我倒认为这一段市场的低谷期却恰恰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创作的“黄金期”: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直接开启了后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校园小说的写作;曹文轩的代表作《草房子》在1997年问世;陈丹燕出版于1998年的《我的妈妈是精灵》至今都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原创幻想小说;此外还有郑春华的幼儿文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系列;而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北少社推出的“自画青春系列”更是开“低龄化写作”的先河,直接推动了新世纪后“青春文学”写作的分庭抗礼。在最寂寞的时候,儿童文学却开出了最美丽的花儿。文学史说到底是由一部一部经典作品构成的,所以作家们的定力是成败的关键。儿童文学作家有他的“傻劲”和“拙劲”,甚至是固执。面对种种诱惑,很少听到他们说要改行。这种一根筋走到底的个性,现在看来又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所以聪明人有可能被聪明所误,而傻人常常有傻福,这不是运气和偶然,而是上天对坚守的回报。现在,经常有些写作者说:“你们儿童文学市场真好,写儿童文学能赚大钱,我也要写。”能够因市场的成功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并不很大的写作队伍固然是好事,但为钱写作永远也走不远。记得当时有一次,我向曹文轩先生抱怨儿童文学所遭遇的歧视,曹先生很淡定地说:“随便别人怎么说,我们写我们的。”那时离他获国际安徒生奖还有十来年,那时他的作品传播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在深深的孤独中,儿童文学作家们也能一如既往地写作,因为他们有一种情怀,一种为孩子们写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试想,如果没有储存这些“家底”,当儿童文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拿什么作品给孩子们呢?岂不是无米之炊,空辜负了浩荡春风?
我们说搞儿童文学的人是理想主义者,但就我的观察,他们并不是空有一腔热血的空想家,他们是一群能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实干家。比如说少儿读物出版人,如何唤醒沉睡的市场是当时儿童文学面临的最大瓶颈,而出版人使出了“阅读推广”的大招。从作家们亲自跑校园,到层出不穷的专职的阅读推广人,它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具有前瞻意识的出版人也是儿童文学潮流的引领者,像21世纪出版社1997年在三清山的一次研讨会上打出了“大幻想文学”的旗帜,随后出版了“大幻想文学”书系,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幻想文学、幽默文学、大自然文学三面美学旗帜之一。而湖北少儿社则以一个地方小社,出版了“百年百部”书系,对中国儿童文学自“五四”诞生以来百年间的经典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是儿童文学界的“长城”一般的厚重工程。在“走出去”方面,不能不提2013年中少社在博洛尼亚书展率先在欧美展区设立了自己独立的展位,那一年曹文轩和高洪波两位作家随团参加了此次书展,这次书展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是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此后,“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我们以接力出版社为例:接力埃及分社已于2016年10月11日在埃及正式注册成功,总部位于埃及开罗解放广场附近。接力埃及分社是中埃首例合资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少儿出版界在阿拉伯地区首次设立海外分社的成功范例。截至目前,接力埃及分社首批计划出版图书共47种,其中26种阿语版原创儿童图书即将在埃及正式出版。在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中,接力埃及分社将继续推进阿语版图书的出版及发行工作,接力埃及分社第二批24种的阿语版原创图书已遴选完毕,并且已陆续在翻译过程中。接力埃及分社还力争与阿拉伯当地优秀的出版社合作,针对埃及和阿拉伯其他国家本土读者和市场的需求,共同开发适合埃及本土的幼儿园教材以及游戏益智类玩具书,争取用这些图书打开并立足于埃及及阿拉伯国家图书市场。此外,浙江少儿社也收购了澳大利亚一家专业的童书出版社。越来越多的少儿社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寻找到有效的路径。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能一一列举,但少儿出版人的智慧和努力是值得文学史记住的。像海飞、白冰、李学谦、徐德霞、张晓楠、张秋林、刘海栖、刘健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既有理想情怀又有战略胸怀的出版家们,改写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版图。那些在新世纪异彩纷呈的作家作品,小说如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我的儿子皮卡》;童话如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系列”、金波的《乌丢丢奇遇记》、汤汤的《到你心里躲一躲》等鬼故事系列、王一梅的《鼹鼠的月亮河》、陈诗哥的《风居住的街道》;散文如林彦的《门缝里的童年》、殷健灵的《爱——外婆和我》;诗歌如金波的《我们去看海》、王立春的《骑扁马的扁人》;科幻小说如张之路的《非法智慧》《乖马时间》;动物小说如沈石溪的《五只小狼》、黑鹤的《黑焰》、绘本如熊磊的《小鼹鼠的土豆》等等。这个长长的挂一漏万的名单,名家或新人,无一不得到出版人的助力。
儿童文学界人数不多,但可算是少而精,因为他们团结。而把他们最终凝聚在一起的,永远离不开党和政府在国家层面上的重视和扶持。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重视“三大件”,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可以说,从中宣部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到我所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都推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举措。这是一个国家的情怀。有人说,一个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态度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儿童文学成长得如此之快,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突然就长得高高大大,但是我们都清楚,它还需要补钙,需要更多的精品证明自己,为这个文体赢得尊严。今天,在儿童文学界内部,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认为已经进入“黄金期”。这种自信我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认可;二是以曹文轩先生获国际安徒生奖为标志,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可以把你托举到巅峰,也可能把你拖入水底。在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曾经成就儿童文学的市场,也可能成为某种桎梏。事实上,这几年市场环境好了,但过硬的好作品反而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对于儿童文学出版来说,“内容为王”才是未来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它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