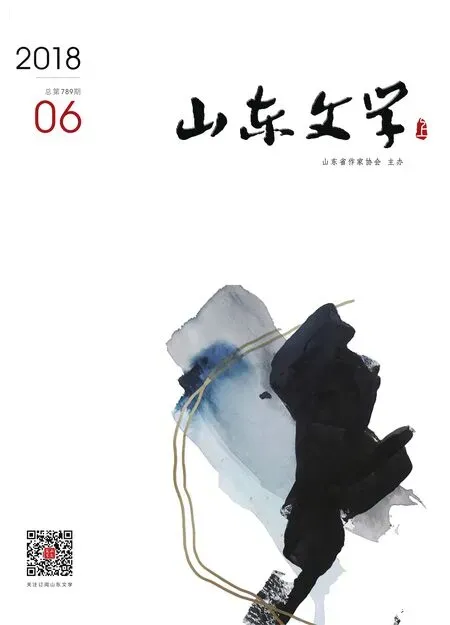网络时代儿童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董国超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两部重要的儿童学著作面世,一部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家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1982年),另一部是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2000年)。两部著作所关注的都是大众传媒对童年生活的影响。波兹曼在著作结尾,分析了童年被发现、童年文化的衰落、道德组织保护童年生态的能力、新媒体是否具备保护童年生态的潜能、家庭和学校对于保护童年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后,得出童年必定会被大众传媒所“淹没”的悲观结论。但是,也有令人欣慰的事情,波兹曼认为,会有极个别的社会成员,他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和“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波兹曼称之为“寺院效应”(the Monastery Effect)。在稍后问世的学术著作《童年之死》中,帕金翰尽管在开篇就提到《童年的消逝》,表现出对波兹曼的极大尊重,但是对“寺院效应”帕金翰并不认可,他认为:“我们再也不能让儿童回到童年的秘密花园里了,或者我们能够找到那把魔幻钥匙将他们永远关闭在花园里。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儿童免于接触这样世界的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
波兹曼和帕金翰所处的还是“前网络”和网络初始阶段,近10年来网络的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网络对童年的影响比波兹曼和帕金翰所提到的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媒,究竟会大到多少倍,恐怕现在还没有人会说得准。但是,两位学者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还要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童年是否真的会消逝?如果童年消逝,儿童文学如何找到立身之地?毕竟“儿童研究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前提,是建立儿童文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朱自强)。
当下国内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开始给予更大的理论热情关注网络对儿童文学的影响,我们能够在报刊杂志上读到《新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生产与传播》(胡丽娜)、《网络媒体时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许诺晨)、《网络儿童文学的正负文化价值透视》(侯颖)等研究论文,以及研究网络时代儿童文学应对措施的学术专著(《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谭旭东)等。在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主要的学术观点:其一,网络文化对追求诗意、追求完美的儿童文学产生了严重冲击,其平面化、碎片化、商业化已经导致儿童文学本质的扭曲,网络文化中暴力、色情、低俗等恶劣因素,甚至已经污染了儿童文学的艺术空间,毒害了儿童的心灵。因此,儿童文学需要“重构”与“突围”。其二,网络文化尽管存在弊端,但它丰富了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段,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影响,“网络儿童文学”是值得理论家认真研究的新领域。
把这两个观点与波兹曼和帕金翰著作的中心论点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当下儿童文学理论家所持的第一个学术观点,比较接近波兹曼的看法,其理论旨趣为,儿童文学面对网络文化的冲击,应该坚持操守,维护传统,在泥沙俱下的网络文化氛围中,营造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寺院”特质的儿童文学纯净世界;第二个观点类似于帕金翰的主张,论者认为儿童文学作家不能、也不应该自我封闭,要勇于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探索,利用网络文化提供的新的表现元素,“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具有时代特点的儿童文学审美世界的建构。概而言之,儿童文学作家是在“寺院”内营造纯美,还是走出“寺院”到尘世中冒险,是两种观点的主要区别之处。
守在“寺院”内也好,走到“寺院”外也罢,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在这一点上,持不同看法的双方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那么,问题来了,在网络时代儿童文学还是原来那个“儿童文学”吗?如果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再简单地谈“坚守”或“冒险”,是不是太表象化了呢?
关于儿童文学本质特征是否发生变化,答案应该是明确而肯定的。
我们发现,近10年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一部智能手机,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在商场、书店、学校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完成。网络中的文字所包含的信息量,远比文学提供的要多得多,譬如文学艺术中的主打门类小说,其传奇性和纪实性,与网络所蕴含的大量新闻信息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只剩下了令传媒读者陌生的叙事技巧。人们阅读传统的纸质叙事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而阅读手机微信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以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正在被边缘化。
与文学整体的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整体文学一部分的儿童文学事业却在快速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全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专业儿童文学出版社,现在专业儿童文学出版社已有28家,而且几乎所有省级和计划单列城市出版社都有专门出版童书的少儿出版中心,儿童读物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盈利手段。表面上看,儿童文学出版业的火热与整体文学的冷落形成对比,但是本质地讲,作为文学分支的儿童文学也存在边缘化现象,不过儿童文学的边缘化,表现为儿童文学更加明显、更加彻底地商业化、非文学化,是一种“艺术性质的边缘化”罢了。尽管中国的儿童文学已经取得了斩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大奖的辉煌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学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学活动,它日益融入到儿童教育之中,成为包罗万象的“童书”之一种,与家庭教育、学校教学、社会教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被纳入到全然功利性、彻头彻尾实用主义的儿童经济产业链之中。
这就是当下儿童文学在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况。在这种生存状况中,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忽视这种变化,泛泛地谈什么儿童文学应对网络文化的对策,或是前景展望,我们认为很可能会是隔靴搔痒。
对已经变化了的儿童文学本质内涵如何界定,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不想做形而上的理论研判和推导,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本质“悬置”方法,具体谈一谈网络时代儿童文学发展可能采取的策略。
一、抛弃精英意识,与通俗文学联姻
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形式,发生于五四时期,到现在也不过百年的历史。而在这百年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儿童文学被认为是“小儿科”,不被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就以高校的文学专业课程设置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全国中文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学校寥寥无几。90年代以后,随着朱自强、方卫平、王泉根、曹文轩、梅子涵等一批儿童文学理论家逐渐成为中坚力量,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才在高校中越来越推广普及开来。
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学术背景吧,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普遍存在着精英情结,总是希望以一种“纯文学”的姿态,让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把儿童文学归入到通俗文学之中,可能会让有些儿童文学业内人士觉得是对儿童文学的贬低。其实在欧美学者的理论视野中,儿童文学就被视为通俗文学(见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文化理伦与通俗文化导论》)。而且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儿童文学已然成为儿童经济、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此时还要再坚守“精英”的阵地,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把儿童文学定位为通俗文学,并不意味着对其艺术性质的贬低,恐怕没人否认J.K.罗琳的《哈利·波特》是通俗文学,但这并不影响罗琳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作为通俗文学的儿童文学,要求作家要更有意识地关注读者(不仅仅是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更加紧密地配合市场运作,创作出更加贴近儿童读者和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
二、观念更新,丰富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段
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网络时代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智能手机使每人都有机会尝试以往专业摄影师所做的工作,“有图有真相”是网络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儿童文学完全可以、而且已经实现了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融会贯通。“图画书”(绘本)近来在图书市场的热销,就是这种融会贯通的明证。
图画书不仅适合儿童阅读,同时也被很多成人所喜爱,图画书的思想内容既可以做儿童文学的解读,也可以做现代、后现代视野中的通俗文学解读。比如美国著名图画书作者莫里斯·桑达克的经典作品《野兽国》,作为儿童文学我们读到的是幻想、游戏以及童心童趣;而澳大利亚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克莱尔·布莱德福德却把它视为通俗文学文本,并在其中发现了往昔海外殖民冒险的后殖民意识(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及具有叛逆特征的狂欢精神(巴赫金狂欢理论)。
通俗文化中的主要艺术门类影视艺术,也与儿童文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罗琳的《哈利·波特》在全球影响如此之大,与通俗文化的大本营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不无关系。电视改编、各种儿童文学网站的推介,也对普及儿童文学知识、扩大儿童文学影响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回归人类童年,复活神话精神
儿童文学是陪伴个体生命童年期的艺术,神话是人类童年期的艺术,二者具有同质同构的特征,在网络时代儿童文学复活神话精神,是儿童文学可以采取的策略之一。
神话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幻想性和生命意识,这两点在神话中水乳交融,是神话具有永恒魅力的重要原因。“幻想文学”(Fantasy)作为一种儿童文学的艺术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才从日本儿童文学界翻译、借鉴过来,现在这种新的儿童文学艺术样式,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世纪交替之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还出版过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幻想”丛书。几乎与此同时,《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热销,更促进了幻想文学的发展。近十几年,幻想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翼,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当下很多幻想文学作品还缺乏深度,甚至一味的幻想而流于浅薄与荒诞。儿童文学应该借鉴神话创作的经验,在幻想中感悟人生、感悟生命的真谛。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根,在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引导读者领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感受生命的真谛,既是儿童文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四、关注家庭、关注亲情,以温暖拥抱童年
网络空间为人们的社交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社会成员,能够即时地、面对面地交谈。但是,网络毕竟是虚拟的,一块屏幕隔离了生命个体有温度的亲近,过度依赖网络,反而会使朋友和亲人之间产生疏离感。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网络之中,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儿童文学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家庭、关注亲情。倡导“温暖”的儿童文学主题。所谓“温暖”也即亲情与友情,这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的情感纽带,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应该提倡的伦理主题。
表现“温暖”是儿童文学最擅长、最具恒久性的主题,在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我们感悟最多的莫过于温暖。当下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细心观察儿童生活,为他们创作有感情温度的作品。儿童文学作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为下一代提供精品精神食粮的抱负。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品中的淘气男孩尼尔斯,在骑鹅旅行中感受到瑞典国土自然风光的美丽,了解了民族的历史和神话传说,历险经历也使尼尔斯从小淘气,长成为一个勤劳、温柔、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这部作品是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根据瑞典教育部的要求,作为一部学校地理教育读物而写的,正是这样一部“命题作文”式的儿童文学作品,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的责任感,以及作品中温暖的伦理主题。
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波兹曼和帕金翰所提出的问题:童年消逝或童年之死。从生理意义上说,童年永远不会消逝;从文化意义上讲,童年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会对儿童、对儿童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从目前来看,网络文化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更多机遇,有抱负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抓住机遇,坚定地站在孩子身边,与他们一起成长,迎接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