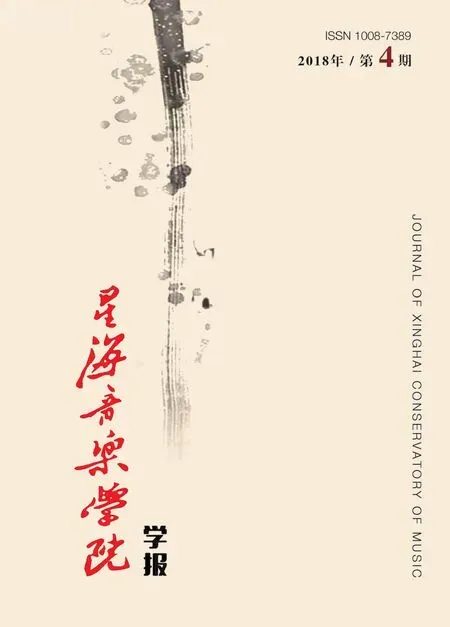粤派扬琴的调音对七平均律的启示
谢俊仁,黄振丰
一、七律扬琴“四盆”转换
自20世纪初,扬琴成为粤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当时所用的粤派扬琴为两排码的七律“蝴蝶琴”*吴迪:《粤派扬琴音乐之变迁》,星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4页。。有关这两排码扬琴的音阶,1920年丘鹤俦的《琴学新编》有详细解说:
扬琴字底(又名板线)通用者共四盆,一曰正线字底,二曰反线字底,三曰梵线字底,四曰苦喉线字底。四盘中以正线字底为最通用,若能习熟正线一盘,无论该调应用反线,或梵线、并苦喉线字底者,则可将字母变换,作正线而弄,其音调即与反线,或梵线、并苦喉线之调无异。故本谱之反线、梵线、苦喉线等调,均写正线字底,以便学者链就字底一盘,可作四盘之通用也。[注]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20年,第15页。
这即是说,“四盆”之间的转换,并不需要调校音高,而只需要转换音名。丘鹤俦在书内阐述了正线、反线、梵线与苦喉的“字底格式”[注]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20年,第29—30页。。同一组的音,在不同的“字底”的音名如下:

表1 四盆字底格式
根据这表,由于正线的“合/士”音程等同苦喉的“士/乙”音程,如果正线和苦喉两者的“士/乙”音程是相若的话,正线的“合/士”与“士/乙”的音程便相若;由于正线的“士/乙”音程等同苦喉的“乙/上”音程,如果正线和苦喉两者的“乙/上”音程是相若的话,正线的“士/乙”与“乙/上”的音程便相若。由此类推,如果正线和苦喉其他的同名音程皆是相若的话,结果便是“七平均律”。
二、七平均律的学术讨论
有关七平均律,在清朝已开始有学术讨论。康熙的十四律制,一反传统的十二律制,把传统七声改为等距七声;[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1013页。至19世纪,载武提出了计算七平均律的“连比例法”。[注]翁攀峰:《载武七平均律思想的初步探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7—25页。七平均律跟传统律制很不同,音阶没有大小二度和大小三度之分,七声旋律不同调式的音程结构,亦因此而没有分别。
至于传统粤乐是否使用七平均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黎田和黄家齐认为粤乐七律各相邻音的音程皆均等[注]黎田、黄家齐:《粤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陈天国更直接使用“七平均律”来论述粤乐和潮州音乐的律制[注]陈天国:《广东民间音乐的七平均律》,《中国音乐》1981年第4期,第7—8页;陈天国:《再谈潮州音乐的七平均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Z1期,第17—21页。。但是,不少学者并不同意这观点。陈威和郑诗敏的测音研究说明潮州音乐并不属七平均律,为轻三六与重三六共用的扬琴,他们的测音结果如下[注]陈威、郑诗敏:《潮州乐律不是七平均律》,《音乐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88页。:

表2 陈威和郑诗敏测音结果
牛龙菲认为所谓七平均律不是真正的平均[注]牛龙菲:《有关“七平均律”的问题》,《音乐艺术》1998年第2期,第6—13页、第33页;牛龙菲:《将“七平均律”易名为“七反律”的建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4—16页。,但可以用七个音之中任何一个音为主音来演奏同一旋律,故此,建议用“七反律”的名称,他还认为,由于各音程稍有差异,转调时,其调式色彩亦发生微妙的变化。陈正生认为,均孔笛能够翻七调,是靠“叉口”(指法)及“气口”控制,虽然不属三分损益律、纯律或十二平均律,但不是七平均律。[注]陈正生:《均孔管研究:中国民间管乐器的均孔不均律》,《交响》1998年第4期,第3—7页;陈正生:《“七平均律”琐谈:兼及旧式均孔曲笛制作与转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第26—28页。《粤剧唱腔音乐概论》的作者认为,粤剧传统音乐只是7音和4音偏差为中立音,[注]粤剧唱腔音乐概论编写组:《粤剧唱腔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35—45页。这与周仕深为高胡名家余其伟的测音结果相合。[注]周仕深:《粤剧音乐的调式》,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9—40页。周仕深的测音结果如下:

表3 周仕深测音结果
显示“合、士、上、尺、工”接近传统十二律五正声,而“乙、反”是中立音。
不过,20世纪初七律扬琴的律制,可能与上述测试不同。首先,粤乐的律制可能随年代而变迁;其次,演奏者能控制音高的乐器,例如均孔笛和高胡,在转调时,可以把音高微调,而扬琴的音高在演奏时则不能微调。故此,上述的测试结果未能排除20世纪初丘鹤俦《琴学新编》的论述,确是七平均律。
三、七律扬琴测音研究
七律扬琴律制的实际情况,可以作测音研究。不过,近代录音所用的扬琴,已不是两排码的七律扬琴,而是十二平均律扬琴;至于20世纪初的七律扬琴独奏录音,则很难找到。为此,本文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于2014年出版的《清音重闻》(广东音乐)唱片所收录的扬琴独奏《孔雀开屏》来作测音。此唱片的乐曲,均使用系内收藏乐器来演奏,《孔雀开屏》所用的两排码七律扬琴,原为丘鹤俦之物,[注]此扬琴后传粤乐大师吕文成,再由香港古腔粤曲名家李锐祖修复,并于2002年赠与香港中文大学。演奏者吴咏梅(1925—2014)为港澳两地资深曲艺名家,[注]吴咏梅2012年获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说唱”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人文学博士。20世纪40年代已活跃于乐坛,熟悉七律扬琴,她演奏此曲时已87岁。
我们首先把录音记谱,然后就每个在曲内出现的音,选择两个样品来测试,再计算两者的平均数。选择的样品必须是单独音(不是八度齐奏),其他的优先条件包括:时值较长;演奏得较清晰;较早出现。
如果两样品测试结果相差超过5音分,我们便再多选择几个样品来测试,再取平均数。测音工作由本文第二作者使用软件Melodyne来做。此软件可以直接提供测试样品的测音结果,而不需经人手调校,故此,测音结果不受主观因素影响。
(一)测音结果
《孔雀开屏》为正线七声乐曲,全曲总共使用了十五个音,其中的“仕”音只在八度齐奏时出现,故未有测试;而单独的“仩”音只出现了一次,只有一个测试结果;故此,共有十三个音测试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样品。测音结果相当准确,十三个音之中,七个音的两测试结果完全相同或相差1音分,两个音相差3音分,一个音相差4音分。只有三个音的两测试结果相差稍为超过5音分,需要增加样品。
以下的测音结果和分析,以“正线”音名按1920年《琴学新编》的低、中、高“字母”写法来记录[注]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20年,第26页。。

表4 是次研究测音结果
接着,我们列出各不同音程的音分。从以下各表可见,涉及“生”音的各音程,皆明显比其他相同音程小,这很可能表示,“生”在调音时偏低了。故此,本文的分析将不包括涉及“生”音的音程,并在表内把有关数据加上括号。
1. 二度

表5 二度音程
“伬/仜”刚好是十二平均律大二度的200音分。其余的音程,均比十二平均律稍小,部分接近七平均律的171.4音分。
2. 三度

表6 三度音程
最低的两音程明显不同,相差72音分,可以区分为大三度和小三度。其余的在大小三度之间,部分接近七平均律的342.9音分。
3. 四度

表7 四度音程
除了“仜/士”和“工/五”,各音程皆比十二平均律的纯四度500音分稍大,部分接近七平均律的514.3音分。
4. 五度

表8 五度音程
最低的两音程,以及“士/工”,极接近十二平均律的纯五度700音分,其余的音程,皆比十二平均律稍小并稍有参差[注]位于左边琴码左右两边弦线的中高音,属五度关系。由于扬琴的码是固定的,各个五度音程理应一样。但测试结果的中高音五度音程稍有参差,显示演奏者调弦时,把琴码左右两边弦线的张力调校得稍为不同。据杨竞明所言,由于琴码与弦之间的摩擦阻力,弦在码子两边的张力可以不一样。参见杨竞明:《怎样学习扬琴》,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年,第10—12页。,部分接近七平均律的685.7音分。
5. 八度

表9 八度音程
“仜/工”和“士/五”的音程比纯八度1200音分稍小,其余四对的音程比纯八度稍大。
(二)是否七平均律
从以上结果看到,扬琴低音部分“佮、仩、伬、仜、合”的律制,与中高音并不相同。两个五度音程“佮/伬”和“仩/合”,极接近五度律的702音分。三度音程“仩/仜”的385.5音分接近纯律大三度的386音分,“仜/合”的313.5音分接近纯律小三度的316音分,大小三度有明显的差别。两个二度音程“仩/伬”和“伬/仜”为187.5和200音分。故此,低音部分类似传统十二律制,而不属七平均律。
在中高音部分,则不少音程接近七平均律,不似传统十二律制,但是并非完全符合七平均律,各个二度音程稍有参差。当然,没有调音器协助,要调校天然律制以外的音程并不容易。不过,表内有个别音程非常统一,例如“士/乙”和“乙/上”的170和169.5音分,以及“上/尺”和“反/六”的174.5和174音分,均只相差0.5音分,显示演奏者调音很精确,而各二度音程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有意的。
再仔细分析,“尺/工”的186音分较其他二度稍大,接近纯律小全音的182音分,“工/反”的158音分则较细,接近中立音的150音分,两音程的差别虽然未及十二平均律的大小二度般明显,但足够让人听到后者较小,并符合传统律制“尺/工”音程比“工/反”音程大的概念。中高音部分各三度音程之中,最大和最小的是“上/工”的361音分和“工/六”的332音分,两音程的差别虽然未及十二律制的大小三度般明显,但足够让人听到后者较小,亦配合低八度的“仩/仜”与“仜/合”的关系。三度音程“士/上”的339.5音分,比“上/工”的361音分小,亦符合传统律制的概念。各四度音程之中,较小的“仜/士”和“工/五”属八度关系,显示这两音程与其他音程的差异是有意的。
故此,中高音部分的音程接近七平均律,但是,各音程稍有参差,不是完全平均,令正线旋律仍有传统律制的影子,不致完全脱离低音部分的律制。
四、律制分析
(一)高低音区律制不同的现象
高低音区的律制不同的现象,亦曾出现在旧制琵琶。19世纪华秋苹《琵琶谱》内的四相十品琵琶图式显示,一至四相之间以及一至三品之间属半音排列,三品以上,则属七律排列。[注]华秋苹:《琵琶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0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故此,吴咏梅把扬琴调至高低音区律制不同,并非独特,而是承接传统的。
(二)音程稍有参差的后果
扬琴中高音的律制接近七平均律,以此在“四盆”之间转换,似乎没有问题。不过,由于音程稍有参差,相同音名的音程在不同“字底”并不是完全相同,结果,转调后不同“字底”的一些音程之间的关系便不配合。特别是正线转到苦喉线之后,由于正线的“合”转为苦喉的“士”,苦喉的“士/上”和“上/工”音程分别为352和344音分,前者比后者稍大,与正线的“士/上”比“上/工”较小的关系并不配合。
(三)苦喉与士工线的关系
要分析这现象,首先要看《琴学新编》内苦喉和士工线的关系。《琴学新编》的《客途秋恨》一曲有苦喉段,[注]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20年,第242页。其旋律以正线字底来记录,骨干音是“合、乙、上、尺、凡”,下句结束音是“合”,等同现代粤乐对苦喉的理解。不过,假如改以《琴学新编》的苦喉字底来记录的话,正线的“合”转为苦喉的“士”,骨干音便是“士、上、尺、工、六”,下句结束音是“士”,属羽调;如此,按《琴学新编》的字底格式,苦喉即士工线。20世纪初中期,也有其他粤乐书籍谈及苦喉与士工线的关系。例如,1936年梅承杰《粤乐阐微》说“士工线即苦喉线”[注]陈守仁等编:《书谱弦歌:二十世纪上半叶粤剧音乐著述研究》,香港:香港粤剧学者协会,2015年,第113页。;1936年何修文《今乐指南》说“[乙凡腔]乙凡本士工线”[注]周仕深:《粤剧音乐的调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96页。;1957年陈德巨在《广东乐曲的构成》说“571245等于‘63’调的612356”[注]陈德钜:《广东乐曲的构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页。。
假如传统粤乐确是使用七平均律的话,便可以解释到“苦喉即士工线”这说法。不过,是次研究的测音结果显示,扬琴的调弦只是接近七平均律,而不是完全平均,以《琴学新编》苦喉字底格式来记录时,“士/上”比“上/工”稍大,跟我们对传统士工线的理解不相合。我们认为,这可以有以下两个解释。
首先,“合、乙、上、尺、凡”等同“士、上、尺、工、六”只是个概括的说法,只是描述七律扬琴可以在“四盆”之间转换,而不是说两者完全相等。当扬琴与其他不固定音高的乐器合奏士工线乐曲时,如果其他乐器把“上”音奏得稍低一点,令“士/上”比“上/工”稍小,而听众以其他乐器的音高为准,便有传统羽调的影子。陈威和郑诗敏说:
艺人们普遍认为,台上或台下,演奏起来都是跟随头手二弦……所以虽然历史上有过扬琴那样调弦,但它并未主宰音律,在以二弦为中心的弦诗乐演奏起来,各调中音与音的关系,一音数韵,许多音处于“活”的状态,从来没有被扬琴“死”的调弦所左右。[注]陈威、郑诗敏:《潮州乐律不是七平均律》,《音乐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88页。
其次,虽然丘鹤俦等把苦喉等同士工线,但这些以“士、上、尺、工、六”为音阶的士工线乐曲未必等同一般理解的羽调。《粤剧唱腔音乐概论》的作者便用“特殊的羽调式”来形容这情况[注]粤剧唱腔音乐概论编写组:《粤剧唱腔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44页。。笔者近年的研究显示,明代古琴谱,以及清代琵琶谱,亦有类似的例子:《松弦馆琴谱》(1614)内属羽调的《汉宫秋》[注]谢俊仁:《从〈松弦馆琴谱·汉宫秋〉看“苦音”在中国古代音乐的运用》,载谢俊仁:《审律寻幽:谢俊仁古琴论文与曲谱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35—139页。,其宫音与徵音的按音位置相比五度律的按音位置是偏高的;华秋苹《琵琶谱》(1818)内属羽调的《月儿高》[注]谢俊仁:《从琵琶曲〈思春〉到粤乐〈悲秋〉的乐调考证与传播变化》,《音乐传播》2016年第2期,第11—15页。,据乐曲前的音位图,其相位的“上”音是高半音的。
结果,由于“上”音偏高,两者的音阶均类似苦音的“合、乙、上、尺、凡”,只不过是采用了不同音名。但是,如果不加说明,这些“特殊的羽调”乐曲可能被人误解为一般的羽调,引起混淆。
1932年,丘鹤俦在《增刻琴学精华》收录了几首以正线“字底”来记录的乙反乐曲,[注]丘鹤俦:《增刻琴学精华》,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32年。但再没有用士工线这名词来描述这些乐曲,并说士工线“甚为少用”而没有列出士工线的“字底”。[注]丘鹤俦:《增刻琴学精华》,香港:香港亚洲石印局,1932年,第32页。这可能显示,丘鹤俦编写这本书时,不想再用士工线来描述苦喉,以免与“士/上”比“上/工”小的传统羽调混淆,而这传统羽调,才是他所说的“甚为少用”的士工线。这亦是现今粤乐界的主流做法。
我们推论,以上两种解释是可以并存的,即是说,当其他不固定音高的乐器与扬琴合奏时,可能会因应乐曲的调式而把乐音微调。如果乐曲的旋律倾向传统羽调,其他乐器可以把士工线的“上”音奏得稍低一点,令“士/上”比“上/工”稍小;如果旋律属苦喉(或“特殊的羽调”),其他乐器可以把“上”音奏得稍高,令“士/上”比“上/工”稍大,即以正线记录时,“合/乙”比“乙/尺”稍大,类似扬琴的音高,来突显苦喉的特色。如此,粤乐的律制是活的。其实,即使坚持采用“七平均律”这名称的陈天国,亦承认这是活的律制。[注]陈天国:《关于中国民族音乐乐律及演奏问题的两封信》,《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25页。
五、活的律制
这活的律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此尝试作初步猜想。众所周知,不少民间音乐,并不按照传统乐律理论,“乙”和“反”可以是中立音,其他的音也可能稍有偏差。当扬琴在明末清初从欧州传入中国后[注]吴迪:《粤派扬琴音乐之变迁》,星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0—29页。,由于扬琴是固定音高乐器,要适应民间音律,而又要应付转调,便把音律向七平均律靠拢,作为折衷办法。康熙十四律与载武七平均律理论的出现,为这本来是折衷的调弦办法提供了理论支持,音律便向七平均律靠拢得更近,最后出现了粤乐是七平均律的观点。但是,实际上粤乐七律并非完全平均,而是稍有参差,它保持了传统律制的影子,并可能会因应旋律的调式而变化。这活的律制不属三分损益律、纯律或十二平均律,但亦不是七平均律。它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民间艺人受环境因素影响而约定俗成。诚然,由于没有理论根据,不同民间艺人的调音习惯可以稍有不同。不过,民间艺人约定俗成的,应该是音律运用的整体方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音高关系。吴咏梅七律扬琴调弦的测音结果,正好为这整体方向提供了参考数据。
(一)律制的适合名称
由于粤乐七律是活的律制,各律之间的音程亦并非完全平均,会因应旋律的调式而变化,亦会因应个别艺人的习惯而变化,故此,“七平均律”并非适合的名称。陈天国列举了他使用“七平均律”的理由,[注]陈天国:《关于中国民族音乐乐律及演奏问题的两封信》,《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25页。包括七律乐器可以在同一件乐器上转七个调门,工尺谱八度内的七个音没有半音升降符号,以及老艺人没有半音升降的观念。但是,以上的理由,只说明粤乐的律制基于七律,与传统十二律不同,而不一定用“七平均律”。我们建议,“粤乐七律”是较适合的名称。环观其他律制的名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都可以统称为“十二律制”;康熙在《律吕正义》提出的律制,不少学者简称为“康熙十四律”。如此,我们并不需为粤乐的律制强加一个似是而非的形容词,简单称之为“粤乐七律”可能更好。
(二)粤乐七律的艺术意义
虽然约定俗成的粤乐七律没有理论根据,但这并不贬低其艺术意义,亦不成为“改良”律制的理由。一些非西方音乐,例如印尼的gamelan,其律制同样没有理论根据,但仍受世界各地的听众喜爱。如果粤乐改用十二平均律来演奏,习惯了七律的艺人和听众,反会觉得格格不入。故此,除非因为乐曲改编而需配合西方和声,演奏粤乐时源用传统七律,效果会更具地区色彩。
结 语
由资深曲艺名家吴咏梅调弦的七律扬琴的测音结果,显示低音部分的音律类似传统十二律制,中高音部分则接近七平均律,但是,各音程稍有参差,不是完全平均,令正线旋律仍有传统律制的影子。据丘鹤俦《琴学新编》,七律扬琴能够在“四盆”之间转换,苦喉即士工线。本文分析了苦喉与士工线的关系,推论当其他不固定音高乐器与扬琴合奏时,可能会因应乐曲的调式而把乐音微调。如果士工线旋律倾向传统羽调,其他乐器可以把正线的“乙”音(即士工线的“上”音)奏得稍低;如果旋律属苦喉(或“特殊的羽调”),可以把正线的“乙”音奏得稍高。这活的律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民间艺人受环境因素影响而约定俗成,不适宜强称为“七平均律”,简单称为“粤乐七律”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