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抑或领土:“民族国家之外”的遗产存续
——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与空间实践
赵 萱
以民族国家认同为载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构成了观察近现代耶路撒冷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作为三大天启宗教的共同圣地,耶路撒冷不仅处于世界宗教生活的中心,其古代文明形态更是以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形式得以保留和延续。因此,领土与圣地、边界与中心,抑或说国家建构与文明延续,业已筑起理解当代耶路撒冷以及巴以关系的两条路径。两种路径的相互交织,使得耶路撒冷既作为传统东西方对抗表述的对象与中东政治格局动荡的焦点,也成为人类社会多文明交融互动、全球流动普遍发生的现实投影。
一、圣地“领土化”:对于耶路撒冷一般性表述的解读
圣地与领土分别作为宗教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对应性概念,图绘了人们认知上的矛盾图景,二者的对立揭示出耶路撒冷有关文明与冲突的一般性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二元化论断却遮掩了丰富的日常表现形态。体现在民族国家与宗教文明看似两极化的观念背后,实际上却于内部具有连贯性,且在外部具有整体性;因而无力解释耶路撒冷日常生活中的交叠与模糊。具体而言,同时作为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耶路撒冷,在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中,其政治空间形态与其说存在着激烈的民族国家竞争,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为民族国家的缺位;其文化空间表达与其说是三大天启宗教结构性地鼎足而立,不如说是社会自然性的交织与分化。事实上,结构性视角与日常性视角的差异,指向了领土与圣地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一致性体现在无论是作为领土还是圣地,耶路撒冷始终被设想成为一个由政治或宗教中心向外辐射的、具有清晰边界的、均质与延绵的空间实体;[注]Satu Kivel? and Sami Moisio, “The State as a Space of Health: on the Geopolitics and Biopolitics of Health-care Systems”,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5, no. 1, 2017, pp.28~46.连续性则体现为有关领土的主权统治的理解,被直接挪用到对于圣地空间形态的解释中,其结果指向圣地的“领土化”[注]“领土化”概念在地缘政治和边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其内涵指向了在现代性进程中政治空间组织形式向民族国家形态转变,即从多权力中心、交叠的权力范畴以及不清晰的权力边界转向单一权力中心、同质性的权力范畴和清晰的权力边界。在这一空间组织过程中,传统的对于空间多样化的解释被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所取代,地理空间以及由此延伸的权力空间首先被看作是民族国家排他性支配的领土而存在,其被单独享有、规划和安排,从而建立现代空间秩序。参见Paasi, Anssi, “Boundaries as Soc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Regional Studies 33, no. 7 ,1999,pp.669~680.(territorialisation)。人们对于耶路撒冷宗教文明之间斗争与延续的理解,势必嵌套在主权统治之间的竞争与接替的僵化模式中。[注]宗教本身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事物,却需要转化为一种一致和连续的形态放置到民族国家框架下去理解,从而与民族国家形成同构性,这本身就是民族国家“领土陷阱”的独特表现形式。参见John Agnew,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 no.1, 1994, pp.53~80.在上述看似对立实则接续的路径下,耶路撒冷作为圣地之文明延续问题,总是不得不与作为领土的国家建构问题纠结在一起。因此,耶路撒冷通常同时解释为政治上其尚未确立的民族国家归属所引发的危机与文化上遗产形态的“濒危”,前者的缺位造成了后者在延续上的困顿。[注]由于在民族国家“领土陷阱”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以及文明的延续需要通过领土化的方式来实现,从而民族国家的“缺位”就会自动转化为文明延续的“濒危”。John Agnew,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 no.1, 1994, pp.53~80.但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耶路撒冷遗产存续的真实面貌,反而流露出一种“国家中心主义”与“领土中心主义”下的遗产保护理念。
援引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世界遗产的定义与描述,世界文化遗产在历史、艺术和科学角度上应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但同时其在国家领土内,作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不应以损害“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为前提,遗产保护“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注]参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第四条。即一般由主权国家提请,并由该国进行管理和保护。因此,在对于文化遗产的通常理解中,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主权实践紧密相连,其作为文化遗产即便内涵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比如宗教文明遗产),但依旧需要具体的民族国家作为其存续的合法代理人,否则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文明内涵,反而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和共享。在这里,圣地的“领土化”既成为某种理解宗教文明遗产的方式,也被作为一种保护和管理文明遗产的重要手段。
在此视角之外,当我们从一个日常性的角度出发,就需要继续追问,存在主权争议的耶路撒冷,或者说耶路撒冷遗产保护上的民族国家缺位,是否只可能造成负面性的结果,即由于无法恰当地安放于主权框架之内,从而也无法恰当地于世界范围内呈现。笔者认为,虽然民族国家的缺位的确给耶路撒冷的遗产保护,尤其是老城的维护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争议,但也正因为缺位使得耶路撒冷老城的遗产存续表现为另一种模式:没有民族国家对于文化遗产事务的一整套计划和干预,反而更能依靠一种生活化而非“领土化”的方式对遗产加以呈现。后者代表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源于外部施加的“识别、分类与治理”,[注]Charlotte Epstein, “Embodying Risk: Using Biometrics to Protect the Borders”, in Risk and the War on Terror, Routledge, 2008, pp.194~210.前者则依托于日常生活的自然延展、分化与交错。[注]其并不单纯被视为一个主权决断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吸纳更多的参与主体,从而呈现出主权之外的、丰富的日常生活面向。参见Anssi Paasi, “Boundaries as Social Processes: Territoriality in the World of Flows,” Geopolitics 3, no.1, 1998, pp.69~88.如果说,以往以领土嵌套圣地的遗产保护模式是以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基础,从而将耶路撒冷的国家缺位现状问题化,[注]圣地“领土化”本身就是遗产呈现的一种主要模式,并且由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权力空间的优先性而获得合理性,甚至往往标准化为遗产保护的唯一呈现方式。那么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视角则尝试将这一“问题化”再问题化,通由外来者的姿态去审视当民族国家缺位时,遗产形态如何得以言说与实践,从“领土化”之外的生活化场景去寻求新的遗产呈现方式。这一方式的形成无法由民族国家发起,也不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而是来源于日常生活,同时也引导着日常生活的延续。对于耶路撒冷的遗产保护,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民族国家缺位”所造成的困境,但是也能够设想于“民族国家之外”:在耶路撒冷老城的斋月之中,在“苦路”与“巴扎”之间,在“哭墙”之下,那些处于“民族国家之外”,从而尚未被识别、分类和整合的文化遗产形态,其揭示出文化遗产延续的另一种可能,也将提供重新理解巴以冲突的新思路。本文将基于2012~2013年、2017年耶路撒冷的田野调查,通过对耶路撒冷老城不同区域及其代表性遗址的民族志研究,探讨民族国家缺位下的遗产呈现方式。
二、作为世界遗产的耶路撒冷老城
耶路撒冷地处地中海东岸的犹大山区,丘陵和溪谷构成了耶路撒冷主要的自然地貌,天然的城防与狭小的空间使得耶路撒冷的基本空间格局早在数千年以前便已确立。19世纪中叶以前,耶路撒冷的城市面积仅限于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如今依然被奥斯曼时期敦厚的城墙所包裹,即耶路撒冷老城。该城墙修缮于1536~1541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I the Magnificent)统治时期,被誉为耶路撒冷建筑史上的伟大成就。奥斯曼帝国晚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浪潮刺激大量离散在外的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欧洲殖民扩张促使众多基督教朝圣者造访圣地,同时阿拉伯家族也在本地迅速繁衍、迁徙,耶路撒冷城市人口成倍扩张,权力形态日渐丰富。自19世纪30年代到1917年奥斯曼帝国解体,仅犹太人口便增长了20倍,城市的空间格局向西和向北延展,大量居民区和公共建筑也在这一时期于城墙内外修建,例如住宅、学校、医院和宗教场所。[注][以色列]丹·巴哈特:《耶路撒冷建城史》,王 俊等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2~175页。耶路撒冷从相对单一、同质的近东民族聚落,转变为族群结构复杂、社会记忆多元、文明遗址层磊的世界城市。
1920年,英国正式委任统治耶路撒冷,城市进一步扩张,初具现代意义的市政体系,位于老城西部的耶路撒冷新区逐渐成型。1948年,以色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宣告成立,第一次中东战争随之爆发,被联合国定义为“国际独立主体”的耶路撒冷被战后的停火线切分为东西两部分,处于东侧的耶路撒冷老城为阿拉伯国家所控制。[注]余国庆:《联合国有关决议与耶路撒冷问题》,《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整座耶路撒冷,久经战火的耶路撒冷在市政层面上实现“缝合”[注]Mark B. Salter, “Theory of the Suture and Critical Border Studies”, Geopolitics 17.4, 2012, pp.734~755.(suture),并开启了新一轮的复兴和改造,其中以圣殿山地下西墙隧道的开凿最为令人瞩目。1980年,以色列立法宣布耶路撒冷为“永远不可分割”(complete and united)的首都。同年,由约旦方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请,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于1981年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入选理由为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遗址为三大宗教所共享,[注]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耶路撒冷老城及城墙”一项被标注为: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 [site proposed by Jordan] ,特别标识了该遗产由缔约国约旦申请,而在当时以色列并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这恰是对耶路撒冷古代文明史的整体承认与全盘接纳;1982年,基于潜在的开发破坏和已有的现实威胁,再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约旦提请,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的耶路撒冷老城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的矩形城池格局,由当时的城墙所环抱,现存8座城门,城内共划分为圣殿山以及4个居民区,分别是穆斯林区、基督徒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直观的感受是老城由拥挤的房屋和嘈杂的市场组成,成为多种宗教、多个族群共同生活的场所。据统计,在这仅1平方公里的老城内便约有220处历史建筑物保存至今,用一位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城居民的话来说:“老城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故事。”
不难看出,经历了数千年的争夺后,耶路撒冷老城于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最终以世界遗产的形态被保留,但却是以一种求而不得的圣地“领土化”的方式完成的。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耶路撒冷老城便由以色列政府实际控制,被视为其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施予主权管辖,但老城内圣殿山所在的核心区域却由耶路撒冷伊斯兰瓦克夫(Jerusalem Islamic Waqf)和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管理,延续着阿拉伯穆斯林的社会生活。[注]赵 萱,刘玺鸿:《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人类学解读——从国家的遗产到遗产的文明》,《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正式给予巴勒斯坦正式成员地位,以此重申对于东耶路撒冷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的一部分,而耶路撒冷地位也应在该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协商解决。[注]Implementation of 35 C/Resolution 75 and 186 EX/Decision 34 Concerni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the Occupied Arab Territorie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unesco.org,2018年7月17日。尽管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决议与申明不能看作是关于任何国家主权合法性的认定,但耶路撒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正是出于这种遗产共享与政治切割之间的尖锐矛盾,数千年的权力与宗教之争,不仅演变为当前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主要形态的巴以冲突,并且通过遗产争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约旦的“提请”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立场”,透视出老城的遗产保护已经与阿以之间的国家斗争纠缠而难以解开。但是各方企图将圣地“装入”领土的愿望,又因为耶路撒冷合法主权的长期缺位而难以实现。有关国家的单方面举证与联合国对三大宗教共享事实的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实际控制与各类文化遗产在管理上的分化,都显示出遗产保护上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皆来源于民族国家竞争所带来的实际缺位,但是却很难由民族国家的重新确立或者再次切割而加以解决。
在此情境下,作为一名外来者,走在耶路撒冷老城,曲折的街市、穿梭的人流和狭窄的街道,往往让人们无法清晰辨别方向,更加难以系统化地感受和辨识老城的文化遗产形貌。在“领土化”的理念下,这种于遗产景观中的迷失,往往需要通过民族国家的干预加以清除,以便清晰及体系化地向外界展现和传递其内涵。但是,如果接受视角变更,从本地居民与大众社群的日常生活出发,那么这种外来者的迷失却能收获另一番风貌。在下文中,笔者将分别从老城当地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提取“民族国家之外”的遗产形态。
三、耶路撒冷老城的空间实践:日常生活中的遗产呈现
(一)“到阿克萨去”: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世界
耶路撒冷老城内生活有逾3万名阿拉伯穆斯林,绝大多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除穆斯林区外同时遍布老城的各个居民区,但耶路撒冷本地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地是位于老城以东3公里的橄榄山地区,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橄榄山一带的多个阿拉伯社区,当地人习惯将其称作“村落”。
对于本地阿拉伯穆斯林而言,有关老城的意象几乎全部浓缩在围绕阿克萨清真寺所延展开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是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神迹而建造,其赋予了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城的崇高地位,失去阿克萨清真寺等同于丢失了圣地。在日常表述中,前往老城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当地人习惯将“清真寺”一词省略,直接简称为“阿克萨”(Al-Aqsa)。在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体系中,阿克萨清真寺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可以在相关《圣训》中查实。例如针对三大圣寺,穆斯林应当整理行装,前往拜谒。[注]参见坎斯坦勒拉尼注释《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因此每逢周五上午,橄榄山地区便开始有三五成群的阿拉伯穆斯林乘车或徒步前往老城。狮子门是穆斯林进城的主要入口,穿过城门向南一转便是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圣殿山的入口之一,进入圣殿山需要通过两道检查,第一道是设置在圣殿山外的以色列军警岗哨,他们主要抽查入寺者的身份证件以确保是否穆斯林身份,并会要求背诵《古兰经》开篇章;第二道是在入口处的阿拉伯人检查点,他们会将怀疑为非穆斯林的入寺者挡在门外,考察宗教信仰知识,除背诵《古兰经》开篇章外,还会询问大小净的顺序以及礼拜的主要内容,以此辨别穆斯林身份的真实性。而在会礼(节日时间)等重大礼拜期间,礼拜人数可达十万之众,亦能突破百万,以色列所设置的安检点甚至会相应削减或撤除,以便穆斯林进城。[注]赵 萱,刘玺鸿,“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人类学解读——从国家的遗产到遗产的文明”,《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因此,阿克萨清真寺虽处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却依旧保留了穆斯林的圣地色彩,其内涵溢出了“领土化”的圣地。
这种在以色列的“领土”(直接的主权统治)之上践行“圣地”(延续的信仰生活)的行为,不仅出现在阿克萨清真寺这类宗教时空之内,也深入更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影响到外来者感知本地阿拉伯社会的方式。本地人常说“斋月里不会有人挨饿”,但事实上斋月的核心内容却是围绕斋戒的体认。斋月期间许多人会选择暂住在圣殿山内,而清真寺所属的瓦克夫将为入寺者免费提供晚餐和早餐,这些餐饮都是免费的,并且数量可观。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尽管指向了穆斯林群体,但也囊括了所有外来者。许多本地人家会在家中备好食物,携带锅碗瓢盆与人分享,甚至走在老城的街头与陌生人一起享用。笔者的一位邻居曾经在斋月里一次性赠与笔者7人份的大盘鸡肉米饭,他认为:“我们必须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如穷人,不论他是什么宗教什么民族,尤其是在斋月里。”实际上他本是临街一家小型饭馆的老板,多次招徕笔者进店,由于笔者一度经济拮据,从未进店消费,每次路过都感到尴尬,但到了斋月期间,他主动提供食物,用锡纸包好,让他的儿子在店门口观察笔者是否返回。同样,笔者的房东经营着楼下的一间阿拉伯咖啡馆,在斋月期间得知笔者要在家中招待朋友,便免费赠送了笔者两支水烟,用以宴客。如果说阿克萨清真寺是在民族国家缺位的情境下让世界得以“观看”一种活态的遗产存续,即清真寺继续被沿用;那么斋月期间对外来者的慷慨,就使得世界得以“接触”一种自然延展的遗产存续,即宗教文明的“身体化”[注]Jason Dittmer and Nicholas Gray, “Popular Geopolitics 2.0: Towards New Methodologies of the Everyday”, Geography Compass 4, no.11, 2010, pp.1664~1677.传递。如果说在阿克萨清真寺的案例中遗产还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尽管这种观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民族国家的规划,那么斋月的例子则进一步将遗产的延续和保存从“观看”转向“接触”。通过一种身体上的交接和满足,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文明遗产最终以一种日常化与生活化的方式传递到了外来者的手中。这一遗产的日常形貌源于历史延续和社会自发,不仰赖于任何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也不为任一政治主体所有,绝大多数的社会个体皆参与其中,共同言说、塑造和展演耶路撒冷老城,不论其是否被命名为遗产。
(二)隐匿的苦路与分割的教堂:基督徒的圣地叙事与实践
耶路撒冷老城中的街市密集,被紧邻的房屋和拥挤的巴扎所填充,许多街巷极为狭窄,铺满了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伴随着数十年来无序的旅游开发和商业改造,更显杂乱,哪怕是本地人也会时有迷路。而在这样一些看似混乱和无序的街道中,却存在着一条由多个站点、多个建筑串联的曲折复杂但是却又为人所熟知的路线,这便是基督教中的“苦路”(Via Dolorosa)。在基督徒的描述中,苦路是当年耶稣基督背负所走完的悲痛之路,共由14个站点组成,记录并纪念耶稣生平最后的一段路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1731年,当时的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确认了苦路上耶稣曾经停留过的14个标志性地点,取代了此前流传的多个版本,但苦路从来不是一条真实、完整的道路,而是一条从靠近狮子门的地方开始,穿越喧闹的穆斯林区,结束于圣墓教堂之内的路线,14个站点散布其中。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本地人并不能清楚地说出苦路14站的具体所在位置,但却有一批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士身穿中世纪式样的长袍,背负一人高的木制十字架穿梭于老城内,向随行者讲述每一站点的来由。
沿着基督徒的叙述在老城中探寻,苦路的第一站,也就是起点,位于狮子门内穆斯林区的一所阿拉伯语学校附近。据传这所学校的位置就是当年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府所在地,旁边建有定罪教堂,纪念耶稣受审,被彼拉多判决死刑。第二站毗邻第一站,是为纪念耶稣背上十字架,受到罗马士兵的鞭打和嘲弄,建有鞭笞教堂。前两站的教堂皆为天主教方济各会于20世纪初修建,不过据近代考古发现,事实上真实的总督府位置存有较大差异。向西继续前行百米再向南转,临近路口处便可到达第三站,相传是耶稣初次跌倒之处,但在《圣经》四福音书中并没有相关事迹的记载,如今建有一间亚美尼亚天主教会教堂,1948年在波兰天主教骑士团的捐赠下得以重修,因而也有人称之为波兰教堂。第四站紧挨第三站,是为纪念耶稣在此见到母亲玛利亚,建有亚美尼亚天主教会的圣母玛利亚教堂。继续前行,进入喧闹的巴扎,在一处向西的路口处可到达第五站,是为纪念一位叫西门的人在此替耶稣背负十字架,如今是一间方济各会的祈祷室,墙上还有一个石印,相传为耶稣扶墙休息时的手印。继续向西行走便是第六站,是为纪念一位名叫贝洛妮卡的少女曾在这里用手帕为耶稣擦脸,耶稣的面容印在手帕上,虽然这一典故流传甚广,但福音书里没有这块手帕的记载,建有贝洛妮卡修道院,同时也被认为是贝洛妮卡的故居。第七站是在穆斯林区的深处,相传这里曾是圣经时代耶路撒冷的审议门,耶稣的罪状书钉于城墙上,耶稣在此第二次跌倒,建有一间方济各会教堂。转入一条向南的岔路可抵达第八站,是为纪念耶稣曾在此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不要为我哭泣,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建有圣哈拉兰保斯希腊正教会修道院。继续南行在一个向西的拐角处便是第九站,是为纪念耶稣第三次跌倒,现建有一间埃及科普特教会教堂。随后继续西行才终于进入老城的基督徒区,沿苦路的第九站朝西南方向前进便可到达圣墓教堂,第十站到第十四站分别位于教堂从门口至大殿的不同位置,纪念耶稣被剥去衣服、钉上十字架、受难、收敛和入墓的全过程。
苦路作为耶路撒冷基督教文明遗产的重要一部分,如今也成为耶路撒冷旅游的重要内容,但是苦路却至今没有被修建成一条单独的“路”。这种苦路的“无路可走”一方面来自于不同教会在援引经文、朝圣方式和站点方位理解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路”线上的莫衷一是,比如许多基督徒会选择中间专门的站点进行祷告,而并非依照既定的次序进行,或者前往他们所认可的其他地点朝圣,以纪念耶稣的十字架之路;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苦路穿越了穆斯林社区,被嘈杂的巴扎所掩盖,鳞次栉比的店铺和热情奔放的阿拉伯店主兜售着各个宗教的纪念商品,他们的商铺和摊位覆盖了原有的或者可能的“路”线,唯有各站点的教堂标识出方位。苦路所形成的基督徒叙事和巴扎所形成的穆斯林生活交织在一起,两者的日常表现却并非相互分离,而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交织的方式呈现叙事的多样性:苦路内部叙事的多样性以及苦路与巴扎之间叙事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使得城市空间和遗产形态具有了多层次性。
苦路的第十站到第十四站全部位于圣墓教堂,教堂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管理模式。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始建于公元4世纪海莲娜皇后圣地朝圣时期,以纪念耶稣受难之名修建,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历史上为基督教各个教会和教派所争夺,现由3个教会(拉丁礼罗马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希腊正教会),6个教派(罗马天主教会、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埃及科普特教会)共同管理。由于历史上争斗不休,1757年经国际仲裁组织判定,以当时争端发生时各个教派所控制的范围确认为永久范围,教堂内大小财物全部登记造册,哪怕一枚钉子,进而实施共管。1853年,俄国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政府应法国的要求将希腊正教会所属的一部分区域转移给了罗马天主教会,于是奥斯曼苏丹再次颁布法令明确共管区域,不得发生新的转移。但是纷争始终没有停歇,1920年,两位教士竟然因为门前一级台阶的分属问题而遇害,起因是教堂门前的院子属于希腊正教会,而大门一侧的楼梯属于亚美尼亚教会,争执的焦点在于最后一级台阶属于院子的延伸部分还是楼梯,为此两派争执不休。正是因为圣墓教堂的空间极具敏感性,所以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七个派别参与管理教堂,这便是阿拉伯穆斯林家族,他们掌管着教堂唯 一 一 把 钥 匙 近1千年。1187年,伊斯兰军队的统帅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重夺耶路撒冷,为防止穆斯林破坏教堂,将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当时的侯赛尼家族,以保护圣墓教堂。因此,侯赛尼家族和努赛贝家族这两个阿拉伯穆斯林家族成为基督教圣地的保卫者,且得到各教派的承认。时至今日,每天清晨4点,两大家族的代表需要和几大教会的牧师进行合作开门的仪式,先由侯赛尼家族成员或委派的代表开锁,努赛贝家族随后推开一扇门,再由轮值的基督教会人员推开另一扇门,其他教派在旁监督,每天晚上7点依相反的顺序关门上锁,钥匙继续由侯赛尼家族保管,周而复始。圣墓教堂正是在这样反复无常、四分五裂的权力关系下保存至今。
复杂的教派斗争历史形成了当下交错的教堂管理模式(6个教派加上两个阿拉伯穆斯林家族),反过来也正因为这样的教堂管理模式,我们才能够真正瞥见基督教的历史分化进程与作为整体性的基督教文明的内部多样性。同样,这样一种“瞥见”是在国家缺位下实现的。即由于圣墓教堂这一世界遗产尚未被“领土化”,所以其依旧保留了一种多中心的权力形态,而不必成为某个国家或某一种宗教、某一个教派的单独遗产。这种复杂的管理模式的维持虽然是持续的宗教斗争的结果,但是通过一个不可完全切分的空间(管理权限可以被切分,但教堂本身作为圣地不能被切分),将不同教派甚至是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按照“历史使命”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命令”继续其对遗产的保护。不同教派以及不同宗教的共存,往往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的魅力之所在,但并不是一种主权安排下的共存,而是一种自发的共存。苦路的“无路可走”与教堂的“四分五裂”,在民族国家主权统治视野下可能是危险的来源,但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却使得交错的历史不至于被某种单一的权威性叙事所埋没,同时也在这种混乱与失序中保持着交互的活力。
(三)面朝哭墙:犹太人巴齐医生的故事
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第二圣殿,犹太人也开启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弥散时期。当时犹太教圣殿区域唯一留存下来的、没有被毁坏的部分只剩下圣殿西侧的挡土墙,这面墙也成为今天犹太人朝圣、祷告和恸哭的重要场所,因此被称作“哭墙”(Wailing Wall)。哭墙见证了犹太圣殿的存在,是犹太人最为重要的圣地。同时自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以来,它也是犹太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每逢节庆,不论是犹太青少年的成年礼,还是大屠杀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等国家节日,哭墙前方的广场上都会举办庆典仪式。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便对哭墙一带的建筑进行大规模修建和改造。例如开凿哭墙隧道、修缮会堂和犹太民居,甚至铸造第三圣殿所需的金灯台,安放在哭墙对面的高台上。而作为圣殿山的西墙,哭墙的另一面则是伊斯兰的禁地。因而不论是在宗教还是政治范畴,哭墙两侧似乎揭示出两个水火不容的世界,哭墙广场是老城内少有的各个入口都有以色列军警把守,需要进行安全检查的地方,哭墙隧道更是需要门票才能入内。
在上文中,阿克萨清真寺与圣墓教堂以及两者延伸出的斋月和苦路可以归纳为无需甚至拒绝国家主权力量介入的空间,那么哭墙则有所不同,其更能体现一种相反的努力,即民族国家对圣地“领土化”的尝试。哭墙作为犹太文明的遗产以及大离散的历史见证,其本身的内涵远远超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以色列的时空范畴。为了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其直接体现为圣地与领土之间的整合,相较于阿克萨清真寺与圣墓教堂,哭墙一方面上升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象征——新入伍的以色列士兵需要在哭墙前面宣誓;另一方面则作为推动圣地“领土化”的基础——阿克萨清真寺之下的哭墙隧道为同一水平空间的不同垂直区域,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圣地内涵。地面上是圣地对“领土化”的拒绝,地面下则是“领土化”以圣地的方式扩张。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提供哭墙遗产呈现的全部内容,更为日常化和生活化的面向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巴齐医生是一位90多岁的犹太老奶奶,她于以色列建国前夕从美国来到耶路撒冷老城,一住便是半个多世纪。笔者第一次遇到巴齐医生的时候是在橄榄山顶的咖啡馆门外,笔者曾主动上前询问,没想到她居然是一位来自老城犹太区的犹太人,经营一间靠近哭墙的家庭旅馆。她上山的目的是为了看望一位老朋友哈吉易卜拉欣以及咖啡店的一位店主阿拉伯基督徒阿卜杜拉。笔者当时多少有些疑虑,“您一个人来橄榄山不害怕吗?”巴齐医生笑着说橄榄山上有许多她的朋友,这次来这里的目的是,此前哈吉易卜拉欣在资金上遇到困难,向她借了5万谢克尔,今天他把钱还给了巴齐医生,这着实让笔者感到意外。阿卜杜拉称赞巴齐医生就是一部“活字典”,她在耶路撒冷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什么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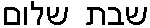
毫无疑问,巴齐医生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她从美国移居到耶路撒冷,独自一人在哭墙附近经营家庭旅馆,充分说明了她对于耶路撒冷的情感,是一位犹太教徒对于圣地的执着,但这份执着并没有完全被纳入一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偏执中。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可以不怀任何怀疑地在遍布巴勒斯坦人社区的橄榄山间行走,并与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结交,大胆地借钱给他们,这已超越了通常人们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误解。从巴齐医生鼓励笔者前往哭墙去领早餐的案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他者的宽容并不只是巴齐医生的性格特质,而是哭墙作为犹太文明遗产本身所具有的内涵。那位将早餐分享的犹太人可能错误地以为笔者是一位犹太人,所以十分自然地分给笔者食物并道以祝福。但是,这种“错误”恐怕要比“正确”地识别出一个犹太人更能彰显哭墙的精神实质,这就是“供养有需要的人”,而没有对是否为犹太人做出限定。哭墙当然可以在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中成为一种“领土化”的符号和武器,但是也可以成为与他人建立友谊和分享食物的媒介。环绕着哭墙的不仅是以色列的军警和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标识和叙事(隧道、金灯台),还有巴齐医生的旅馆以及与陌生人分享免费早餐的世界各地的信徒,他们的存在使得哭墙作为遗产,总能迈出民族国家的主权统治模式。
四、讨论:“民族国家之外”的遗产存续
阿克萨清真寺、圣墓教堂以及哭墙,这些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得到了保留和延续,更是由于民族国家的缺位而展现于“民族国家之外”。这里不单只是作为逝去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以活态形式保留的简单讨论,而是尝试回答遗产如何被呈现这一问题。前者与遗产的具体内容相关(如何让遗产的内容不会消失),后者则是一个遗产形式的问题(遗产的内容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与阿克萨清真寺相联系的斋月通过“身体化”的方式让伊斯兰文明遗产得以传递;与圣墓教堂以及巴扎相叠合的苦路,以“无路可走”的形式,让基督教的多元化历史叙事和与穆斯林生活相互交织的现状得以同时保留;与哭墙相连的安息日早餐,以与陌生人分享的方式,凸显出犹太复国主义主题之外的宽容和开放。我们当然可以设计并提供民族国家干预的标准形式。例如修建博物馆、印制相关书籍、设计相关旅游路线来呈现同样内容的事物,但却无法给予人们最大的心灵触动。在民族国家单一权力中心的覆盖下,遗产需要服务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而走向单一化的叙事,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国家对遗产的排布过程中,众多的参与主体不得不被边缘化,或者只能按照同一叙事进行展演。耶路撒冷老城的民族国家缺位,虽然给遗产保护带来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遗产保护模式中时,才显得急迫和棘手(世界上最珍贵的遗产却位于一个主权争端暂时无法解决的地区)。当我们回到老城的日常生活,这种民族国家缺位却在诸多问题之外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遗产依旧受到保护,即便不是在民族国家的财政直接支持和统一规划之下,遗产内涵依旧得到了传递。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缺位下的遗产存续要更为合理,而是强调民族国家缺位下遗产依旧能够找到新的延续方式,遗产的存续并不必然只有一种方式。
民族志展现出的生活化方式是日常的、随意的、自然的甚至是凌乱的,但是却让更多的主体进入遗产的存续中,每一个群体的故事并不妨碍另一个故事的出现,甚至那些看似矛盾的事物和现象可以在同一空间并存。不同于圣地“领土化”所追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遗产保护和呈现方案,耶路撒冷老城的维系是由众多的权力中心在非意图的情况下共同实现的,其并不否定冲突在耶路撒冷的存在,而是强调冲突本身也能成为统一与同构的一部分。[注]Helga Tawil-Souri, “Uneven Borders, Coloured (Im) mobilities: ID Cards in Palestine/Israel”, Geopolitics 17, no.1, 2012, pp.153~176.
从这一民族国家之外的遗产存续扩展开来,巴以冲突是否可以出现另外的面貌?自2017年以来甚嚣尘上的耶路撒冷定都问题再次将圣地嵌入到领土之中。首都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具有排他性质,是唯一的,如同我们所谈论的遗产保护中的单一权力中心;在此思路之下,耶路撒冷只能属于一部分人而排斥另一部分人。在作为领土的耶路撒冷被反复争夺并造成了无数流血事件的历史与当下中,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三大天启宗教在老城相对和睦地相处,主权管理与清真寺空间并行,巴扎与苦路交错,巴齐医生的穆斯林朋友圈,这到底应该看作是民族国家势力相互争夺的结果,还是民族国家缺位的结果?笔者看来既都是,也都不是。民族国家势力在耶路撒冷的角逐使得谁都无法实现绝对的压制,从而相互争夺客观上转化为一种缺位,不同势力之间为了继续争夺,不得不与他者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这样的“无奈”之下,圣地本身就不再是被争夺的领土,耶路撒冷的现状虽然类似于一种妥协,但是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可能性的开端。从老城的遗产形态中,我们观察到在单一权力、单一叙事与单一归属之外的另一种表达。这一方式或许无法直接移植到巴以冲突的问题解决上,但是却给出了启发与反思的空间:如果说遗产的存续不一定要采取“领土化”的方式去保护,那么共同体的存续是否一定要以民族国家为前提,而深陷于“领土陷阱”之中?在领土与主权之外耶路撒冷为我们提供的东西还将很多,换言之,耶路撒冷已不仅成为了某种问题(纠缠于其民族国家归属),也将成为一个新的提问(是否需要民族国家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