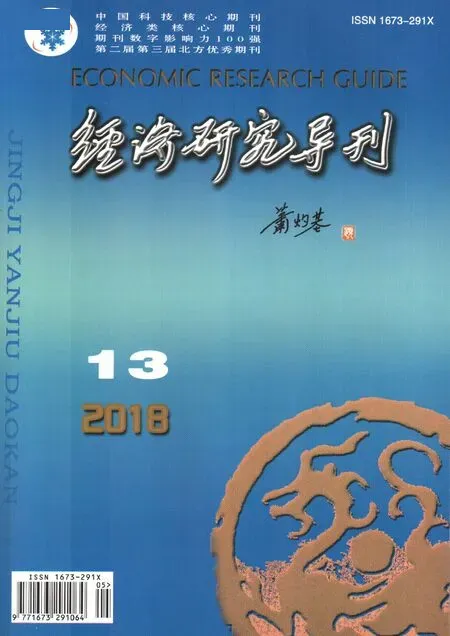公共危机中网络舆情管理的应对措施研究
韩 怡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8)
社会心理学认为,舆论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对个人和群体具有约束力。随着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网络舆情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1]。它的生成不外乎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产生”的,现实中的人物或者事件经由网络示众,然后引来网友“围观”,并在网络迅速扩散,进而会有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跟进形成热点舆论事件。另一种是“间接产生”的,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中,存在令人生疑或者不足为信之处,于是各方在网络上发问、质疑、求证甚至是纠正,引起讨论并在网络世界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网络舆论事件。
目前我国现有的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大致分为四个主题:突发事件、社会关系(如医患、城乡关系等)、国内热点问题(如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等)以及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的对外关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网络舆情有其特有的生命周期,往往会陷入死循环之中。因此,无论是否“有患”,网络舆情管理都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情管理的特点
1.网络舆情管理的界定不明确。研究学者认为,网络舆情管理可以分为一般事件的网络舆情管理和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管理。但是,根据网络舆情管理的主体、流程以及技术的不同,网络舆情管理的界定又应当重新分类。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并延续成网络热点舆情问题时,应对舆情的主体是谁?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技术处置它?网络舆情管理的对象是谁?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2.网络舆情的引导易失当。首先,政府舆情管理的官本位倾向,体现在现有的舆情应急管理更多强调部门内部的信息流转,对政府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涉及较少[2]。大多数政府部门仍秉持旧观念,认为对传统媒体和公共危机的舆论就应该主动地控制和打击,“自闭式”地进行单方面的信息传播以及被动接受。其次,当公共危机时间产生,网络热点问题出现、公众渴望了解问题的真相时,若主流媒体如果信息发布不具体、语焉不详,就容易导致网络舆情的产生,甚至会引起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稳定。此时,公众会把政府的言论当成网络舆论的终点,如何不偏不倚地做好发言是一个难题,像“不明真相”“情况未知”等容易产生联想的词汇更应该慎用。
3.政府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难调和。学者弗里曼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受一个目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3]如果政府与社会公众在某事件中有共同的目标,在网络舆论的处理上有利益相关性,那么舆论导致的影响和后果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某些公众故意制造、夸大网络舆论,期望通过网络舆论为自己发声或获取某种利益,但这恰恰可能违反了政府所要追求的社会公正的道义。政府追求的道义与公众追求的利益之间往往是很难调和的。
二、网络舆情管理主体的形成
1.政府——“第一人”。随着网络发展,网络舆情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络舆情也在社情民意的上情下达中扮演重要角色,更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党政部门非常重视网络舆情所表达的民意,出台的政策更加将网络舆情的良性沟通提升了一个高度。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民众心里,通常将政府跟舆情联系到一起,会出现“引导”“控制”等词汇,表明政府是经手网络舆情的“第一人”。网络舆情形成强烈的“倒逼”效应,更是要求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阳光政府、回应型政府[4]。
2.网媒——“风向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范围广、速度快,近几年兴起的“议程设置”更使得这些受众广的网媒在网络舆情应对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信息传递给受众的形成过程中能够过滤主要信息并将自己的观点扩散给受众,形成了信息传递的分级传播(一般是两级传播)。若不加约束,极易引发网络次生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风向标,网媒的自律和自我管理对网络舆情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网民——“后备军”。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SNS社交工具的兴起,互联网用户急剧增多。以网民为代表的群体在网络舆情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出于从众心理和自身感性的支配,超六成的网络用户会对公共危机事件长期关注并在网上进行评论或转发,还会对网络舆情进行夸大渲染抑或理智回应。网民的社会阶级、文化素养、群体规模都会对网络舆情造成影响,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网民的价值取向、利益差距、追求真相的标准以及道德的贫富差距[5],都会导致网民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见解分歧化。
三、网络舆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的“被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管理内容和主题的多元化造成舆情发展的方向不明、态势不清,这对政府的舆情判断和处置带来了很大的难度[6]。政府本应在舆情管理上占领先机,然而信息不健全、言辞的不恰当让其陷入被动的境地。由于舆情信息搜集的不及时、欠准确,检测技术的不先进,网络舆情政府的被动回应,忽视了与网民、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很容易在网络舆情引导中丧失话语权。
2.网媒的舆情疏导转为带头质疑。网媒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应充当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纽带。但有时情况正好相反,举例说明,在2015年的“天津港爆炸事故”后,网媒针对当地多家媒体集体“失声”和天津卫视仍然放热播韩剧的行为大肆报道,从之前配合政府进行舆情疏导到此后的带头质疑,不仅未起到舆情管理的作用,反而为次生舆情的产生提供话题。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网媒应充分发挥其纽带功能,通过网络平台安抚网民情绪、消除网民质疑起到舆情疏导作用,而不是带头质疑和大肆渲染,造成网民与政府矛盾加剧。
3.网民的道德绑架。在网络上的发言是“有主张,少论据”,易于情绪化[7]。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挫折与攻击》一书中提出,挫折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公众(网民)感觉自身利益被侵犯了或者感到将要受到某种威胁,他们就会在内心深处聚集不满情绪,网络是他们最好的宣泄口。在网络舆情管理中,道德绑架是一种群体性的泛道德化批判行为,一旦网民受到不良引导或是自身不理性的宣泄,将带动更多的人跟他们一起反抗。
四、网络舆情管理的正确应对
1.强化政府的舆情应对和网络治理能力。对于公众而言,“无可奉告”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回答。好消息胜过坏消息,坏消息在某种时刻胜过无消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产生之后,涉及危机的各政府部门应掌握第一手信息,主动回应,保证信息的更新和及时辟谣,面对各方的诸多质疑,应坦然面对并表达决心。同时,提高网络舆情的检测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追踪机制,对舆情谣言的制造者源头追责;加强网络宣传教育,增强网民明辨是非的能力,不信谣、不传谣。
2.规范网媒的职业操守和信息传播能力。网媒作为向网民传递信息的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因未加核实信息和为了信息的浏览量造成了网络舆情扩大、公共危机升级,不仅使政府公信力下降,还容易使得社会陷入恐慌之中。网络舆情产生之后,网媒更应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作为政府与网民之间的桥梁,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确保信息发布的真实准确,体现“以人为本”[8]的人文关怀理念。
3.倡导网民的理智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都以倡导用户自律和自我管理为突出特征。在倡导自律之外,各国政府还采用经济手段、技术手段、法律规范等方式,针对不同内容的话题和不同的参与程度,实施有区别的应对[9]。这给了我国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很大的启示,对于某些低俗、色情议题必须采取痛下杀手的方式;对于表达政治主张的议题,在没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情况下采取包容的态度,倡导“自律”为主的开放式管理。
五、结语
网络舆情治理借用政治学中的“治理”概念[10],强调舆情管理的多元性及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在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管理上,政府既是网络舆情讨论的主体又是引导、管理舆情的主体;网媒既是信息传播的中转站又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网民既是网络舆情的“发声人”又是舆情解决的监督者和主力军。我国在公共危机舆情管理的应对上经验不足,导致网络次生舆情屡有发生。因此,要重视政府、网媒和网民之间的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规避其负面影响,这对当前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婷,徐德美.公共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引导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7,(2):7-8.
[2]Freeman R.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rategic Approach[M].Pitman,Boston:MA,1984.
[3]彭知辉.政府视域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及反思[J].情报杂志,2014,(9):93-99.
[4]张勤.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信任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14,(4):40-44.
[5]徐铁光.网络舆情管理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J].伦理学研究,2015,(2):118-122.
[6]张润秋.网络经济价值二重性的引导与消解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3.
[7]孙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8]李纲,陈 浩.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图书情报知识,2014,(2):111-119.
[9]薛瑞汉.国外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的主要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9):106-111.
[10]李昊青,兰月新,侯晓娜,张琦.网络舆情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J].现代情报,2015,(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