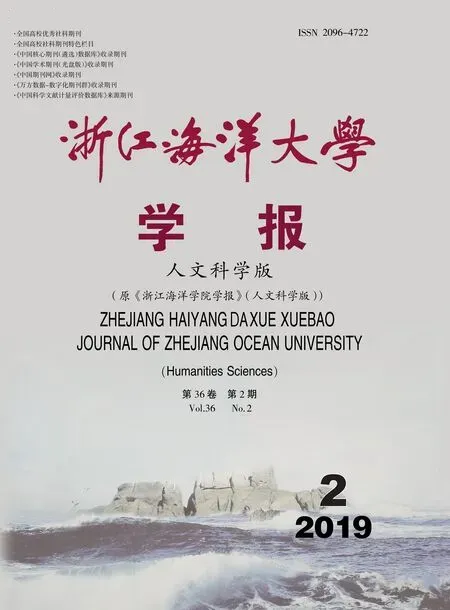朝鲜汉籍海洋古文献《漂海录》与《乘槎录》对比研究
黄 昊 秦锦清
(1.浙江海洋大学 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舟山 331022 ;2.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漂海录》为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所著,全书共计五万余字,以汉文书写。记录了时任济州岛三邑推刷敬差官的崔溥为奔父丧,自济州岛乘船往全罗道,在朝鲜济州岛海域遭受风暴袭击之后,与随行的属吏及护送兵卒一行四十三人历经十四日漂泊后于浙江台州登陆,在通过明朝政府的身份甄别后,由官方全程护送自台州陆路至杭州,改水陆经京杭大运河至北京,最后由辽东至鸭绿江返朝前后四个半月的行程始末。《乘槎录》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朝鲜文人崔斗灿所著,全书共计三万余字,同样以汉文书写,记录了崔斗灿受姑父之邀前往济州岛游览,乘舟返回全罗道归程途中遭受风暴袭击,历经十六日漂泊后于浙江舟山登陆,由清各级官府全程护送自舟山至杭州,行舟京杭大运河至北京,经辽东渡鸭绿江返朝前后六个月的行程始末。
一、海上历险经过比较
两位作者的遇险起因十分相似,船只的出海港口均为朝鲜济州岛的候风港口别刀浦,遭受风暴袭击的地点均为朝鲜济州岛至朝鲜全罗道航线附近。从遇险船只所载人数来看,两人所乘船只大小形制大致相当(崔溥船载四十三人,崔斗灿船载五十人)。漂流的起因均为遭遇狂风骤雨,为避免船只倾覆,自行砍断桅杆导致船只失去动力,不得不随波逐流。崔溥一行漂流时长为十四天,崔斗灿一行漂流时长为十六天,在这段漫长的漂流煎熬中,两人都曾陷入淡水缺乏、人心浮动内外交困的危机。面对困局,两人所采取的求生措施与应对困境的人生态度却并不相同。
(一)淡水缺乏的解决措施
(二)精神世界的不同追求
在漂流经历中的舟人,除却对物质生存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外,在精神需求方面也采取了各种行为以慰藉自身。如崔溥舟中安义曾提议:“尝闻海有龙神,甚贪,请投行李有物,以禳谢之。”⑦虽然崔溥并未采纳,但舟人皆曰:“人有此身,然后有此物,此物皆身外物。”于是“争检有染衣物、军器、铁器、口粮等物投诸海”。⑧无独有偶,崔斗灿也曾有“为文告于天,又为文告于海王、船王之神”⑨的行为。可见当舟人陷入险地而又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脱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寄希望于神明的庇佑,这虽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却也是一种对求生渴望的反映。但崔溥认为与其求助于虚无缥缈的神明,不如节约有限的物资,凭借自身的努力,谋求生路。在这一点上,两人有着较大的分歧。
(三)安定人心的应对表现
面对舟中的人心浮动,两人采取的行动截然不同。在崔溥所乘船只陷入漂流的前期,舟中为护送崔溥而随行的底层军卒怨愤情绪较重,以下言论较为具有代表性:“济州海路甚险,凡往来者,皆待风累朔,至如前敬差官在朝天馆,在水精寺,通计凡三朔以候,然后乃行。今此行,当风雨不定之时,不占一日之候,以致此极,皆自取也。”⑩意在抨击崔溥为奔父丧,匆忙启程,未候风期的行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还有言曰:“势已如此!取露治船,11虽竭心力终亦必亡。吾与其用力而死,莫如安卧以待死。”“长寿哉!此船也。等至于破,何不速破!”12显露出部分舟人自暴自弃,消极等死的心态。对此,崔溥对曰:“我奔初丧,情不可少留,人或有劝之行。为人子者,其可顷刻濡滞乎?汝等之同我见漂,实由于我,然势亦使之然也。况好生恶死人情所同,汝等岂无欲生之心哉?舟或破碎或沉覆则已矣。观舟今坚致,未易至破,若不遇石屿,能修补刮水,幸或风定波怡,则虽流至他国可以得生。今汝等亦有父母,有妻儿,有昆季、亲戚,皆望汝生,畏其不寿。汝等不念其情,不爱其身,徒以咎我之心率相解体,自归死地,惑之甚者!”13此言既反驳了部分军卒的愤懑言论,同时也鼓励了消极军卒的求生欲望,暂时稳定了人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船只再次遭风暴遇险时,甚至连中层属吏的心理防线也近乎崩溃,“莫金、巨伊山皆哭泣”,“安义大哭曰:‘吾与其饮咸水而死,莫如自绝!’以弓弦自缢。金粟救之,得不死”。面对此等情形,崔溥问领船、梢公:“舟已破乎?”曰:“否。”曰:“舵已失乎?”曰:“否。”崔溥随即回顾巨伊山曰:“波涛虽险,事势虽迫,舟实牢固,不至易败。若能汲殆尽,则庶几得生。汝实壮健,汝又往首倡汲之。”14于是再次鼓动舟人汲水自救。
而崔斗灿在面对舟人惊慌与窘迫情绪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心态则与舟中旁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乘槎录》中有如下对话:“其夜恶浪大作,船板皆鸣。余仍惫卧成眠,鼾鼻如雷。金君以振蹴觉曰:‘风色如此,何暇稳眠?’余曰:‘风色如此,不寐何为?’”15这段崔斗灿与舟人金以振的对话,反映出其相对镇定的心态与随遇而安的性格,甚至在风波稍定后,“见朝日自海底出,欲上未上之际,红波白浪,照耀万里,亦忧中之乐也。仍吟《赤壁赋》一篇,继之以诗”,16更突显其文人式苦中作乐的豁达态度。与崔溥在舟中扮演的决策者不同,崔斗灿在舟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这一差异,是因两船人员组成结构不同所导致的。崔溥所乘为官船,阶级分明,从属关系明确。崔溥在船中地位最高,是一行人的领导核心,因此船只遇险见漂,他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救险、鼓励舟人奋力求生的重任。但崔斗灿所乘船只为民船,舟人构成复杂,有平民、士子、商贾等。崔斗灿自身不过一举人,并无足够的威信与地位来领导众人。舟人彼此并无从属关系,因此仅在遇险时能够团结一致,奋力抢险,待船只安定后,面对之后的漂流境况各人的表现便各有不同。但崔斗灿在危急时刻提出的建议依然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日且昏黑,舟人大惧,计不知所出。船主梢工皆聚首号哭,男女并五十人齐声痛哭。时出身河应龟在傍,有膂力者也。余连呼应龟斧樯去鸟,斫尾去鸱,舟人齐出汲水,终夜有声”,船只初遇风暴时,崔斗灿命人砍断桅杆避免倾覆。“是时,船中所载公私马并五六匹,船只荡漾,左倾则左重,右倾则右重。舟人始有解马投洋之议,而私商爱其马,船主爱其船价,颇有相持之意。然余则以为好生恶死之心,物我所同,故姑无可否矣。至是风势益急,船几覆没。余以伤人不问马之义,决意投洋,船只小定”,17船只再次遇险时,为维持船只平衡,崔斗灿决议将周中公私马匹投海。总之,尽管两人身份地位、角色扮演各不相同,面对困境采取的行为措施各异,但总体来看都是各自漂船舟人得以幸存的关键人物。
二、甄别管送经历比较
两人登陆的第一地点均为浙江舟山。不同之处在于崔斗灿在舟山海域为渔民所救,弃船搭渔船至普陀山登陆受到寺僧接待,并传报地方官府救助。而崔溥一行在下山(今舟山市岱山县)遭遇海寇,被劫掠一空后,再次登船漂流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陆,且在登陆之初期被误认为倭寇遭到羁押。可见崔溥相较与崔斗灿的历险经历中,除了天灾,更有人祸,历险经历更为波折。
(一)身份甄别对比
通过比较两部文献中的记载可知,两人获救后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主要表现为崔溥一行人一度被误认为倭寇遭到羁押,随后受到了严格的身份甄别;而崔斗灿的朝鲜漂民身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官府的认可,并给予了漂民待遇。
在沿海局势相对紧张的明代,崔溥面临的甄别过程十分复杂,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桃渚所,由于带队抓捕的桃渚卫千户陈华先入为主的判断,认定崔溥一行人为倭寇,即使崔溥以所带官印、马牌、文书自证身份,依然被认为是其劫掠朝鲜人所得,因此在桃渚所进行的第一阶段甄别较为严苛,由把总松门及备倭指挥同知刘泽主持,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姓名、官职、住居、产物、诗书、礼乐、衣冠等方面。松门及刘泽的问询“汝国与日本、琉球、高丽相通乎?”显示他们并不知道高丽王朝为李氏朝鲜所取代的事实,误将两者视作两国。反映出浙东沿海的下层军官缺乏对朝鲜的基本认知,这一点与辽东一带经常接触朝鲜贡使的地方武官大不相同。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查,通过对一行人语言、衣冠、行为的观察,基本洗清了崔溥一行人倭寇的嫌疑。随后一行人被送往绍兴,并接受第二阶段的甄别。主持者为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宗、巡海副使吴文元、布政使司分守右参议陈潭,调查内容为朝鲜历史、都邑、山川、人物、风俗、祭祀、丧礼、户口、军制、田赋、服饰、刑名、地理等方面。离开绍兴后,一行人前往杭州接受最后阶段的甄别,主持者为镇守太监张庆、按察提调学校副使郑大人(崔溥事后忘记姓名)、布政使徐圭、按察副使魏福。张庆根据景泰年间出使朝鲜的倪谦所注《朝鲜纪事》,问询崔溥有关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朝鲜官员的官职,以为佐证,崔溥对答无误。提学副使则详询了崔溥朝鲜科举制度及所涉经书事宜。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形成了上报北京的报告,方认定崔溥一行人为朝鲜漂民的事实。
崔斗灿接受的身份核查仅有一个阶段,即在定海县治由知县沈泰开进行甄别,《乘槎录》中载“县主沈公泰开,座陈威仪,引三人问情,余随问随答,指陈情槩。是日行犒赏,各种肉品甚盛,饥隶皆饱,始有生气,喜可知矣”。后两日又“使客杭州吴申浦主席,行宾主礼”。18主要问询了朝鲜的山川风俗与科举制度,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甄别。
(二)管送对比
在甄别确认了两人的漂人身份后,当地官署对两人的管送方式也存在着差异。崔溥一行人即便在通过身份甄别后,依然被严格地限制人身自由,滞留期间日常活动都处于监控之下。禁止其在境内自由行动,也禁止社会人士前来探访。因此他们平时仅能接触明朝的各级军政官吏,而与当地其他社会人士缺乏交流。在遣送过程中,每日严格按照既定路线行进,风雨无阻,如《漂海录》载:“到连山驿。是日大雨。翟勇谓臣曰:‘我大唐法令严整,少有迟缓必止罪责,今虽大雨不可复留。’”19同时依然不被允许与当地社会人士接触,也无法深入了解行进路线地区的社会风貌。
同时,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教学体系不成熟,教学目标不明确,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导致毕业生难以对口输出,教育产出和实际成效不高。其次是教学中缺乏实践环节,导致课程脱离实际,课堂脱离工作环节,工程教育教师的授课方式更看重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依靠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和考试环节主要围绕教材进行,导致学生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最后是教师欠缺对学生的引导,仅仅是教师讲什么,学生记什么,这样严重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也降低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相反崔斗灿一行人,在接受简单的甄别之后,所受到的人身限制相对宽松。这使得崔斗灿能够在定海及杭州两地滞留期间,与当地文人士子笔谈交流,唱酬诗文,甚至在定海期间得以受邀前往士子竺世臧及学官金士奎家中参加宴饮,面对崔斗灿“而但远人离次,必骇物听,未敢承教”的顾虑,当地士人则表示“有官人带去则无碍”。20可见人身限制的宽松程度到了超乎崔斗灿想象的地步。因此《乘槎录》中可见大量对江浙建筑与民居内部摆设式样的细节描写。在杭州期间虽然被限制出行,使其游览西湖的心愿未能得偿,但也未限制外人探访。因此崔斗灿的接触人群除了地方政府官员外,还有大量闻讯前来交流探访的当地文士,双方通过笔谈的方式增进了解甚至唱和诗歌,交情匪浅。在崔斗灿一行人离开定海前往杭州以及离开杭州沿运河北上之前,都获得了当地文人的送别与馈赠,除了必要的衣食之外还有粉纸、吴扇、印章、诗集、书画、笔墨、烟草、药材等,甚至还有因担心崔斗灿水土不服,而提供“鞋底泥和百沸汤饮之”一类偏方建议,足见当地文士热忱之情。相对宽松的人身限制,也使得崔斗灿比崔溥更有机会游览返朝途中的名胜古迹,这也是其一行返朝时间相较崔溥一行更长的原因。
(三)差异缘由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崔溥相对崔斗灿而言,接受的甄别更为严苛,管送期间受到的人身限制也更为严格。而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明清两朝在海洋政策与沿海环境上存在着差异。崔溥漂海事件发生于明弘治元年(1488),而崔斗灿漂海事件发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明清两朝虽然都存在海禁政策,但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的性质与目的也不相同。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起施行,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御倭寇与海盗的侵扰。尤其在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新兴大名混战的战国时代,社会阶层激烈动荡。大量战败的大名及武士、浪人为谋出路选择到中国沿海地区与当地的海盗、流寇相勾结,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以致明朝沿海倭乱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为应对倭乱而制定的明朝海禁政策,有着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除在地方普遍施行的卫所制度外,沿海还设有巡海副使与备倭都司,作为沿海各省抵御倭寇的指挥机构与机动军事力量。在崔溥漂海所处的弘治初年,地方卫所尚未如明末时期一般废弛,且倭寇猖獗的沿海环境使得沿海卫所警惕性相对较高。所以崔溥一行登岸不久便被海门卫桃渚所的屯户发现,并按倭寇例遭到抓捕,同时接受了初步的身份审问。受明朝地方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立政治制度的影响,崔溥所接受的甄别来自多个有司衙门,存在反复甄别的现象。
而清朝海禁政策的起因是为了遏制沿海人民接济南明及台湾郑氏的反清势力,故而在康熙二十二年平台之后曾一度开放海禁,虽然后续几经反复,但大致处于弛禁状态。尤其在乾隆朝后,政策目的发生改变,由近海防御转变为贸易保护,成为了孤立主义性质的海禁。且在收复台湾后,清朝的沿海环境较为安定,地方官署不存在“舶来皆是倭寇”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想法。因此崔斗灿一行人受到的甄别要简单得多,受到的人身限制也较宽松,行止自由度也远高于崔溥一行。
三、运河沿途描述比较
崔溥及崔斗灿的遣返回国经历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的回国路线大致相同,均为自登陆地前往杭州,经由京杭大运河水路至北京,继而陆路经辽东过鸭绿江返朝。但他们在各自文献中,对运河区的描述重点却各有不同。
(一)描述对比
《漂海录》对沿途的记录十分详尽,且南北详略大致均衡。对运河区的描述,侧重于运河主干支流、自身水利设施及沿河城池规模、建筑规制等。尤其对运河区沿途的渡口、桥梁、闸堰、塘坝、驿站、铺递等交通设施有详实的记载,举文中一日所记为例:“县距江岸二三里许。又过黄浦桥、华渡铺、蔡墓铺、大板桥、步青云门、新桥铺,至曹娥驿,驿丞徐深也。驿北有坝,舍舟过坝,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越岸又有坝,坝与梁湖巡检司南北相对。又舍舟过坝,而步西二里至东关驿。复乘船,过文昌桥、东关铺、景灵桥、黄家堰铺、瓜山铺、陶家堰铺、茅洋铺。夜四更,至一名不知江岸留泊。”21非但一日如此,《漂海录》每日行程记录均十分详尽,即便有不知名的江河水利也描述在册,部分记载甚至未见中国本土文献,对今人研究明代运河及漕运情况有着独特的价值。除了对运河的水利设施着重记录外,崔溥还对沿河的军事设施与城防态势均有所描写。如“行至海浦,有兵船,具戎器,循浦上下,示以水战之状”,“门皆重城,鼓角、铳熥声震海岳”,“至宁海县之越溪巡检司。城在山巅,军卒皆带甲列立海旁”等等,同时对地方卫所分布皆记录在册:“过淮安府……又其间,有凤阳中都、凤阳左卫、龙虎右卫、龙江左卫、豹韬卫、豹韬前卫、淮安卫、大河卫、镇江卫、高邮卫、扬州卫、仪真卫、水军左卫、水军右卫、府军前卫、泗州卫、邳州卫、寿州卫、长淮卫、庐州卫等。淮南、江北、江南诸卫会于此,造船厂俱有。”22
由于崔斗灿在江浙滞留时间较长且印象上佳,而北方多处于赶路途中且与朝鲜景致相当,因此《乘槎录》在沿途的记述上有南详北略的特点。与《漂海录》不同,在对运河区的描述上,《乘槎录》侧重于对运河两岸的人文景观描写,而对运河自身的水利设施、运营状况着墨不多。让我们确信其行程仍在运河上的文字往往只有每日放船与目的地,如“鸡鸣放船”“放船至京口浦”“夜二鼓开船”等等,对船行沿途的桥梁、河塘、堤坝一律欠奉,至行程的后半程往往每日仅剩余日期、天气、开船时间与驻泊地。但对于沿途经过的名胜古迹往往多有描述,如“放船至京口浦。晋人所谓‘酒可饮,兵可用’之地也……波流之广,可四十里,而中流有金山寺,乃韩世忠破兀术处也,一名昭关,伍员遇渔丈人处也。其上有姜太公之钓台云”,“东门外有会稽山,山下有禹穴,西门外有汉高士严子陵之祠,意其谓七里滩也。府中有柱书曰:‘松菊今彭泽,山川古会稽。’然则彭泽亦会稽地也。夫以一县之地,想象千古往迹。禹穴无底,即玄圭告功之遗迹也。越兵栖山,乃勾践尝胆之古地也。谢安之东山,右军之兰亭,西子之浣纱溪,皆系此山之下”。23甚至亲往游览,如“到长清县之崮山站,上泰山谒玉皇庙,赋诗一绝”,“因留良乡县。县有古寺,寺有千手佛。其傍圣母娘娘行宫”。24除对运河区人文景观的描写外,对运河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也有不少描写,如“我东治田之制,除水田外,黍稷之属,并栽一处。或豆田种秫,秫田种豆,而中国则不然。秫田专种秫,豆田专种豆。又多种玉秫,处处相望,我东所谓江南秫也”,“挽船入瓜州城,城中始有茅屋草舍,而良田沃土,连畦接畛,污湿宜稻,高燥宜秫,亦衣食之乡也”,“到齐鲁,始有龟蒙诸峰连延横亘,地又多石,车不得行。市井村落,甚似吾东,五谷之早晚亦如之”,“自济南省以来,千里无山。土尚多秫,又有黍、稷、木绵之饶,但无秔稻。且多牧场,羊猪之属不可胜数,而马畜蕃息,成群阡陌”25等等。
(二)差异缘由
1.成书时间差异
这里我们所说的成书时间并不是指两者在历史上成书的先后顺序,而是指两部文献成书在作者历险返朝始末中的时段差异。《乘槎录》为崔斗灿于浙江定海获救后,即开始记录,每日一篇直至返回辽东为止成书,多事则详少事则略,这也是《乘槎录》为日记文体的原因。而《漂海录》虽然也采用了日记文体逐日记录,但并非崔溥自登陆获救起便开始书写记录,而是在返朝之后,由朝鲜上层授意,凭借记忆与从员的记录、回忆在八天内著述完成的。因此《漂海录》中对全程描述的详略程度较为均衡。
2.管送形式差异
前文我们对比了崔溥与崔斗灿二人的管送情况,可知崔溥一行受到的限制远多于崔斗灿。由于行进路线为提前制定,行程时日有严格安排,因此崔溥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在一条线上,观察的视角也同时被限制于运河本身与沿途目力可及的范围。而崔斗灿的行程仅有线路预设,无明确的时间安排,且对其人身限制宽松,行动自由较高,活动空间并不仅限于线。这使得崔斗灿能够了解到沿途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状况。
3.成书目的差异
《漂海录》是崔溥返朝后受命而作,属于朝鲜官方内部参考材料,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有朝贡的义务,但明朝对朝鲜贡使的朝贡路线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导致朝鲜对明朝的了解局限在燕辽一带。崔溥因海难于浙东登陆后,返朝途经了明朝的运河区,而这一地区鲜少为朝鲜所了解。因此朝鲜统治阶层迫切希望通过崔溥的《漂海录》了解明朝东南沿海及运河两岸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这也是《漂海录》在运河区的记述中还涉及地方军政的原因。
《乘槎录》为崔斗灿获救后,对自身遇难经历、获救及返朝遭遇的一种记录,没有额外的目的性,属于私人日志。崔斗灿出生于士族家庭,但自父辈起便已不再出仕,仅以诗书传家,作为一个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朝鲜士人,对于史籍中所载典故,常心向往之而不得见。因此崔斗灿更愿意在返乡途中抓住难得的机遇游览。故而《乘槎录》在运河区的描述多有人文景观的描写。
综上所述,两部文献存在内容互补的关系。以《漂海录》为线、《乘槎录》为面,可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运河区的整体状态。
四、劫后归国感受比较
在沿途的见闻记录上,两部文献都作出了江南富庶、淮南次之、淮北再次之,直至京师方又见繁华的表述。可见明清两代运河两岸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南北差异。
崔斗灿返朝后对《乘槎录》有一个简短的追录,回顾了自济州历险至重返故土的经历,尤其对江浙一带结识的中国友人念念不忘,表示“诸公之恩,尤不可忘也”。并在追录中对运河南北差异作出了结论性的比较:“自定海至扬州,多瓦屋,且多锦绣,多绝色。自扬州至济南,履屋或以秫茎,或以芦竹。男女衣裳皆褴褛,率多麻绵。自济南至新城,亦如之。其间虽有河间等地,古称繁华,而今不足观。岂地有盛衰,俗有污隆欤?所居第宅,皆土屋也。良乡以后,是附京之地,故物色稍稍可观矣。言语容貌,亦皆不同,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者也。”26明确表达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优于北方的论断。除却南北发展的实际差异,这也同崔斗灿在南方备受礼遇而在北方经历断炊困苦的个人感受有关。除了对运河南北的比较外,崔斗灿还从房屋、衣服、稼穑、墓制、车船等方面将在中国的见闻同朝鲜自身情况进行了对比。总体而言,《乘槎录》多以个人情怀与见闻感受为主。
崔溥返朝后的记录偏重于对明朝弘治初年各项新政的分析与总结,这既与其身为朝鲜中层官员的身份立场与眼界角度有关,也受限于接触人群多为明朝官吏,笔谈内容多涉及朝政有关。崔溥一行通过自身见闻与笔谈所得,感受到了一些弘治朝新政的新气象,如宪宗好佛道而孝宗抑佛道;宪宗好珠玉而孝宗崇节俭;宪宗多弊政而孝宗严法令等等。弘治元年为明孝宗登基的第二年,其在位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各项与成化年间有异的政策导向已经显现。朝鲜统治阶层便是从崔溥多方得知的这些新政气象为依据,预见了明朝短暂的弘治中兴,为朝鲜之后的宗藩朝贡政策方向提供了导向。总体而言,《漂海录》多以国家政策与政治感受为主。
通过两部文献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同为朝鲜漂民记录自身经历的域外汉籍,但是作者在海上历险、甄别管送、运河描述、归国感受等各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差异。《 乘槎录》作为一部私人日志,内容涉及清朝嘉庆年间,返朝途径区域的民居建筑、文人面貌、地方名胜、运河交通、农田稼穑情况,以及与地方文人唱和的大量诗歌,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文人尤其是浙东文人的精神面貌与思想境界。文献兼有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是研究清代运河区社会状态的珍贵文献。而《漂海录》作为一部有官方内参性质的文献,保有大量对明弘治初年运河运转状况、地方军政、社会民生、新政导向等方面的详实记录,是研究明代运河状况及弘治新政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资料。两部文献所记录的区间大致相仿而时代不同,侧重点各异,存在互补关系,对研究明清两代运河区的发展状况及漂民遣返政策均有其独特的借鉴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