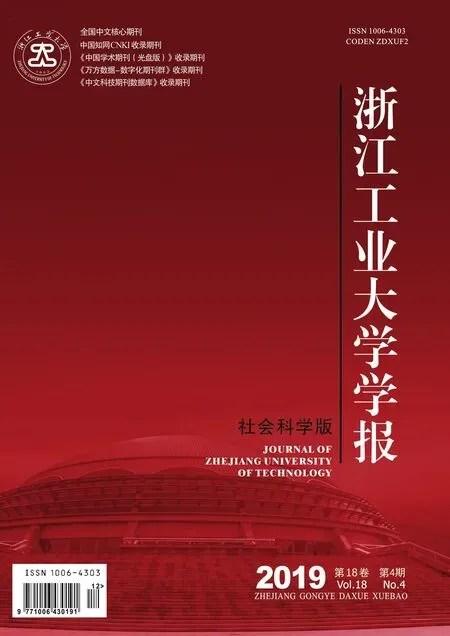《枯木禅琴谱》释论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在古琴音乐发展史上,由于师承、地区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琴派。广陵派始自清初扬州,上承明末虞山派,下启清末金陵、诸城、九嶷等琴派,对清代以至当代古琴艺术有重要影响(1)可参见刘明澜:《论广陵琴派》,《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第48-54页;戴微:《传人,传谱,传派——广陵琴派的历史沿革和艺术风格》,《音乐研究》1991年第2期,第47-54页;戴微:《江浙琴派溯流探源》,上海音乐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琴派诞生于琴乐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琴派、琴人、琴谱、琴学等方面有诸多成就,“广陵派五谱”集中体现了这些成就。这五个琴谱分别是清初徐常遇的《澄鉴堂琴谱》(1702年初刻于响山堂,后又重刻于澄鉴堂)、徐祺的《五知斋琴谱》(1722年)、清代中期吴灴《自远堂琴谱》(1802年)、晚期秦维瀚的《蕉庵琴谱》(同治年间)和释空尘的《枯木禅琴谱》(1893年)。
释空尘(1834—1908?),又名云闲、枯木禅,于光绪年间(1893年)编著了广陵派最后一部琴谱《枯木禅琴谱》(2)关于空尘研究,可参见司冰琳:《〈枯木禅琴谱〉研究及作者考证》,《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1期,第11-13页;《〈枯木禅琴谱〉内容与创作琴曲研究(上)》,《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65-72页;《〈枯木禅琴谱〉内容与创作琴曲研究(下)》,《音乐研究》2008年第3期,第33-36页。。笔者以《枯木禅琴谱》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在广陵派琴谱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发展,并对琴谱题名的佛学内涵加以阐释,在此基础上阐发其“以琴喻禅”理论的内涵,以就正于方家学人。
一、《枯木禅琴谱》对前代琴谱的继承发展与文化背景
(一)《枯木禅琴谱》对前代琴谱的继承与发展
空尘在凡例中自言琴谱为广陵流裔,全谱八卷,卷一、卷二关于琴德、指法、转调等方面的论述大多根据《五知斋琴谱》所述稍加阐发,少有创见,第三卷至第八卷兼收正、外调琴曲32首,曲目除《渔樵问答》外皆出于之前广陵诸谱,以《五知斋琴谱》为宗,数篇出于《自远堂琴谱》,而对于师祖《蕉庵琴谱》却未见提及,卷八收录琴曲7首均为空尘和尚所创作。
从该谱的记写情况来看,对比于《五知斋琴谱》中详细地前言、后记与旁注,《枯木禅琴谱》相对简约的多,但在曲谱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零星见到诸如“慢起”“跌宕”的演奏提示,可见其吸收了《五知斋琴谱》对琴曲演绎的细腻追求。
广陵派诸谱对琴歌的态度稍有区别,《澄鉴堂琴谱》收录的琴曲直接删除了歌词,认为影响音乐表达;《五知斋琴谱》则存文以备览,以求更深入理解曲意;《自远堂琴谱》也认为琴乐以音为重,繁琐的歌词令音乐拘滞重涩,所以把文词附于章节之末。而这些观念来自王坦琴论。王坦在《琴旨·有词无词说》中虽强调有词方可成声,但他和严澂一样,对后世一字对一声的填词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谱入《大学章句》《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归去来辞辞》《腾王阁序》《秋声赋》《赤壁赋》诸篇,每篇之字若干,每操之声即如之循字配音,绝无咏叹摇曳之致”[1],这些批评非常客观。可见他们并非反对琴歌,而是反对这种一字一音的机械做法。《枯木禅琴谱》继承前代诸谱观点,存词以达曲意,该谱收录了《平沙落雁》《胡笳十八拍》《怀古曲》《思贤操》《莲社引》5首有辞之曲,仿效《五知斋琴谱》的做法,将文词附于谱后。
《枯木禅琴谱》的部分内容又颇有创见。如卷一之《音声论》《辨音十六则》,卷二之《著作琴曲要略》《历代圣贤著曲名录》等论述都为编者多年精研琴学的心得,《著作琴曲要略》从音乐的一般特征出发,探讨了创作琴曲时须先说明主题,琴曲演奏时应以古淡舒简为要,这些其实是对广陵派琴曲特点的总结。另外,比较此谱《历代圣贤著曲名录》与《五知斋琴谱》之《历代圣贤名录》会发现有所不同,在某些考证方面,尤其是佛学相关的琴曲记录,《枯木禅琴谱》所记更为详尽,而最有创见之部分则在于琴谱的佛学意蕴,详见第二、三部分。
可见,《枯木禅琴谱》是广陵派琴谱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于前代琴谱,如《五知斋琴谱》和《自远堂琴谱》多有继承,但作者作为琴师与僧人的双重身份,使琴谱具有了别样的气蕴与内涵。
(二)僧人习琴的文化背景
古琴发展历史中,琴僧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但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僧人习琴多有阻力,一是传统琴人以“琴不妄传”为由,拒绝僧人习琴;二是佛教戒律对于僧人习乐的限制。
一方面,明清以来,在僧人弹琴数量逐渐增多的同时,儒、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开始在琴论中大量出现,古琴谱中的“琴不妄传”之语集中体现了这一现象。如明代琴谱《太古遗音·琴不妄传》:“释氏之学,出于西胡夷狄之教,僧者乃夷狄之门。琴乃中国圣人之教,岂容沙门而乱雅哉?”[2]这个观念在华夷之辨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甚嚣尘上,裹挟影响了一大批的琴人。另一方面,就佛教戒律而言,传统僧尼十戒中便有“不歌舞观听”。《梵网经菩萨戒本》卷二亦说:“亦不得听吹贝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不得作,若故作者犯轻垢罪。吴支谦《佛开解梵志阿颰经》即谓:‘沙门不得咏吟歌曲,弄舞调戏及论倡优’”[3]。唐初道宣撰《量处轻重仪本》中“不听畜物”第三、五条有详细说明,《唐六典》卷四中也有禁止僧尼作音乐之规定。但事实上,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佛教音乐也蓬勃发展。在盛大的供养法会上多有歌舞庄严,征诸经藏,法会音乐的描写在佛教诸经中俯拾即是。
既提倡又反对,看似矛盾,实非矛盾。禁止习乐,是担心乐之为音,扰乱修道之心神。但又不否认如果音乐运用得当则具有礼敬诸佛、劝导人心和理解经义的现实功能。《大智度论》卷九三即谓:“是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易化,是故以音声因缘而供养佛”[4]。《法华经》《高僧传·唱导》篇皆有以音乐供养三宝,具有教化之功的内容。可见,佛经中虽有僧人不习乐的戒律,但并不排斥音乐在弘法时的工具之用及教化之功。
(三)“攻琴如参禅”的理论发展
随着历史发展,参与音乐活动的僧人日渐增多,他们或精通音律,或擅长器乐,多数有着僧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唐宋以后,禅宗流行,随着文人士大夫参禅修行悟道之风的盛行,儒与佛、士与僧的充分接触与交流也赋予琴乐独特的理论和艺术表现。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宋代琴人成玉磵,他在《论琴》“攻琴如参禅,岁月磨炼,瞥然省悟,则无所不通,纵横妙用而尝若有余。至于未悟,虽用力寻求,终无妙处[5]”中对琴曲的领悟,即如果没有对意境的深刻探求与领悟,一味苦练,达不到妙处。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提出了“声音之道可与禅通”[6]的理论,并举琴史上著名的俞伯牙受成连启发而海上移情之典说明:“音在于是,偶触而即得者,不可以学人为也者”[6]。伯牙在浩瀚无垠的自然界中获得启悟,精神瞬间升华,泯灭了物我界限,心中之道与自然之道完美交融,达到了音乐审美的最高境界。这种心路历程与禅悟类似,禅宗无论顿渐,皆是在境与意会的刹那间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与琴中静心求道、实现万物之超脱实属同一途径。
就宗教层面而言,既然乐与道通,那么自然可以把琴乐当作弘扬佛法、参禅悟道的工具去学习。释空尘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习琴的。他在琴谱自序里言明自己有四位老师,牧村长老为禅师,赵逸峰为道士,丁绥安与乔子衡为儒生,其思想当亦有兼容并蓄的底色。释空尘在四位老师相继谢世之后,携琴访道,历燕齐楚越,在虚心求教的同时勤访秘谱,终于在1893年辑成刻印《枯木禅琴谱》八卷,为广陵派琴谱的发展划上圆满的句号,与前四部琴谱相比,因释空尘作为僧人的学识修养与审美意趣,使琴谱从题名到内容都具有明显的佛学意蕴。
二、“枯木禅”题名释义
释空尘又名云闲,号枯木禅,琴谱命名为《枯木禅琴谱》,虽有以自号名琴谱之意,但空尘似乎对“枯木禅”“枯木”情有独钟,在自序中提到琴为乐之圣器,斲以枯木,《自述诗》中也有“枯木禅中养性天”之语,卷八自创曲中还有一首《枯木吟》。结合释空尘少习儒业,后投迹空门,并曾师事僧人、道士和儒生的习琴经历来看,空尘应当精通内典,而且对于儒、道典籍也比较熟悉,其思想或亦有兼容并蓄的底色。在刊刻琴谱前后,空尘正驻锡于虎丘,而虎丘禅法渊源有自综合数种因缘,空尘以“枯木禅”为琴谱之名,当另有深意。
(一)“枯木”典之源
“枯木”之典源出大梅法常禅师,唐代黄檗希运禅师也曾言“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7]。此处重在讲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心之虚空无求,但悟禅道并非止于此,而是以比喻的说法阐释假若心果能如枯木石头、寒灰死火之时,则“少分相应”,即入门悟到浅层次的真谛。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五灯会元》卷六的“婆子烧庵”公案中有更详尽的说明:“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8]。婆子烧庵赶人表面是嫌弃禅师的修为,或也是在点化禅师,禅师“枯木倚寒岩”当是打去妄念、无情无欲的空寂境界,这只是入门浅悟,禅宗修行讲究明心见性,打去妄念并非无情无欲,不思不动,而是蕴含着真性的无穷妙用。
在禅宗史上,尚有“枯木众”“枯木堂”“枯树逢春”和“枯木偈”之典,但与“枯木禅”之内涵类似的典故是“枯木龙吟”(3)现存有唐琴名枯木龙吟,连珠式,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出自唐代曹山本寂禅师与石霜禅师(据《传灯录》记载,“枯木众”与“枯木堂”之典亦与石霜禅师有关)。在《五灯会元》《古宿尊语录》和《指月录》中皆有记载,内容稍有不同:“僧问香严:‘如何是道?’香严曰:‘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香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石霜曰:‘犹带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石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骷髅里眼睛?’师曰:‘乾不尽。’……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8]
(二)“枯木禅”的内涵:真空妙有
此公案讲“道”的境界及“如何悟道”。血脉当指内在之心性佛性,枯木里龙吟当是指空寂之中巨大的生机,血脉不断,即自性分明,骷髅里有眼睛,就是乾不尽,利他因缘不尽,若无眼睛,便与枯木石头寒灰死火一般,智光不到;若无喜识,亦如寒潭死水样无法利益众生。“意谓绝灭一切妄念、妄想,至大死一番处,更甦生还来,而得大自在”[9]。据佛教基本理论,万事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成,而因缘因时因地皆有不同,是以万事万物呈现无常性空之态,而这种空中并不死寂,恰如慧能所说:“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10]。可见,禅宗之“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包容万有;而且,正因其“空”,才能容纳万有。是以禅宗中的“枯木”“枯木禅”“枯木龙吟”之典都含有真空妙有之意,即苏轼《送参廖诗》所言“空故纳万境”之意,即通过止息妄念,恢复活泼的自性妙用,真空妙有、枯木逢春才是枯木禅的实质。空尘和尚在琴谱中多次提到这一典故,无不从这一角度着眼。
(三)以“枯木禅”喻琴德
从琴谱各序及杨葆光小传中可知,释空尘晚年曾居于虎丘,而虎丘一系禅法始自宋代的绍隆禅师,六祖惠能门下悟道者共四十三人,各化一方,晚唐至北宋初期,共分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五宗,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歧两派,合称五宗七派(或称五家七派),为唐朝以后的佛教主流。上文已述,出于百丈怀海门下的黄蘗希运禅师曾用“枯木”之典,而临济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创立临济宗。临济宗传至石霜楚圆(986—1039年)门下,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虎丘禅法一系传自临济宗杨岐派下,以南宋时期虎丘绍隆为开山祖师。南宋绍兴初年,绍隆到虎丘讲经,一时众僧云集,声名大振,逐步发展为一座规模宏伟的著名佛寺。空尘和尚出家于虎丘,后又长期居住于此,取枯木禅以为名号,或渊源有自于此。
空尘和尚在《自序》中曾言:“琴者,乐中之圣也。斲以枯木,系以团丝,圣人之示天下法者,为能修身养性,以助治理也”[11]。《琴德论》中曾述及琴为圣人所制,其功能可以修身助化,其形制可以通天地,圣人借此宣其大道,是以琴德最优。琴以枯木制成,为何有如此功能?《枯木禅琴谱》中德辉和尚的序言有一段解释:“且夫枯木,死物也,弃之则日渐朽败,取之仅供一爨耳。忽遇巨眼,知为良材,运以斧斤,施以丹漆,饰以金玉,佩以弦徽。或置诸庙堂之上,或藏诸岩穴之间,无所处而不当。其发为音声,乃能入性命之微,通造化之妙也。如此,倘所谓大死而后大活者,非欤?”[11]德辉和尚从琴之制而言,认为树木枯尽才能成为琴材,遇上制琴者的慧眼妙手,可焕发生机,成就琴缘,是以枯并非死,而是涅槃,可入性命之微,通造化之妙,这两句其实也是空尘对琴德的具像化描绘,以空化有,以死化生,得活泼自性,正合枯木禅实质。
可见,释空尘以“枯木禅”为琴谱命名,取其枯木逢春、真空妙有之意,而琴乐由枯木弦丝遇慧眼巨手而焕发生机类似,都是以死化生,得活泼自性,且具修身助化,宣示大德之功。这一点空尘在阐释“以琴说法”时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三、以琴喻禅
(一)以琴喻禅:以琴理体悟禅理
空尘虽然有复杂的思想底色,但佛学信仰无疑是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成分,他认同“乐与道通”,以琴乐为修道悟禅的重要媒介,强调:“我教中之蒲团禅板,何异修身养性之道,证之琴德,奚有二哉?自梵僧居月善琴,继以颖师、聪师、维公、义公,咸以琴理喻禅,见于旧简者不可以数计”[11]。列举历史上有名的琴僧及其“以琴喻禅”之理,认为通过琴理可以体悟禅理。
空尘的这个观念与他的朋友们颇有共鸣,德辉和尚在琴谱序中称赞他能做到“琴禅合一”,而竹禅和尚为琴谱所作序言则直接以“以琴说法”为名,并进一步解释:“大道无相,闻声而入,衣钵流传,因人说法。今云闲上人,深悟琴学三昧,其住世行道,得教外别传之旨”[11]。直言空尘和尚以音乐为悟道之机缘,是另一种形式的“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禅宗用语。一般把佛陀言句传授者称为教内之法,而直以佛心印于他心者称为教外之法。而“教外别传”特指不设文字、不立言句而直传佛祖心印。达摩的《悟性论》对此有详细解释。其同门徐熙更是在序文中以“琴以谱传,禅从琴寄”八字概括此谱之特征,认为释空尘深谙禅学要旨,又对琴道有透彻领悟,还有娴熟的琴艺技法,是以能传播琴学,并由此得禅悟之理。
(二)“以琴喻禅”体现之一:缘起理论
具体而言,“以琴说法”或曰“以琴喻禅”在琴谱中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琴乐产生的缘起理论。德辉和尚在序言中谈到这一问题:“木无声也,必张以弦,弦亦无声也,必弹以指,然则此声从木生乎?从弦生乎?从指生乎?质诸云公,请为下一转语”[11]。探讨声乐起源,与苏轼诗不谋而合:“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2]
此理论在佛教经论中也多有论述,如《大般涅槃经》卷二六为了论证一阐提并无佛性而以箜篌为喻,《大智度论》卷九九有类似表述:“复有箜篌譬喻,有槽,有颈,有皮,有弦,有柱,有棍,有人以手鼓之。众缘和合而有声。如声亦不在众缘中,离众缘亦无声,以因缘和合故有声可闻”[5]。这是佛教的缘起理论,认为世界万物不是凭空而有,也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因缘和合的结果,诸法皆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因缘聚合才有果。琴乐是琴弦与妙指,当然更有主体的精神意趣三者和合而成。徐青山的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的琴乐生成论,即具有明显的缘起论影响痕迹。无论苏轼亦或德辉和尚都在强调木、弦、指数者因缘合和才产生妙音。相较而言,《大智度论》单纯论音,以箜篌乐音为例,说明其音不单在柱、皮或槽,也不单在手,而是所有因素的刹那间因缘聚合。《大般涅槃经》则借声音的因缘聚合离散来说明佛性亦复如是。
(三)“以琴喻禅”体现之二:元音、心与有形之音声
“以琴说法”亦体现于《音声论》中关于元音及其与“心”的关系的论述。《音声论》开篇用了《金刚经》的一个偈子:“‘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其义何其深哉!”[11]此偈出自《金刚经》的“法身非相分”,旨在言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尽虚空、遍法界无一物堪称法身,所以法身不可假借外物而观,最后佛以四句偈为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五色焕眼而非形,八音盈耳而非声,偏谬为邪愚,邪隔不见”[13]。即言执着于有形色、声,只能误入邪道,与空寂之性相违,正确的做法应该立足自性,不生不灭,非空非有。
此处空尘感叹此四句偈含义幽深,音、色并举,偏重于音。借用此偈强调不可执著于有形的声音,而应该探究声音的本质,在他看来,声音的本质通于自然之道:“盖音声之道,含虚无复姤之机,达来除变化之理”[11]。复为阴极阳生之卦,以喻人身静极而动、阳气初生之际。姤为阳盛阴生之卦,以喻人心动极而静、阴精自生之时。其自然之道无静无动,无始无终,亦空亦幻,但在这其中又蕴含着蓄势待发的希望,这音声空尘称之为“元音”,它“通乎天地有形之外,蕴乎喜怒哀乐之前,生于心而节于外”[11]。圣人造琴瑟制律吕的目的就是“倡天地之元音,俾人心一归于正”[11]。圣人制乐,首重教化之功。而雅乐则是元音诸调和合的理想之乐:“至于雅乐,元音须声调翕如,方可成曲,但劝除淫哇之声,去杂乱之节,其取音用意当性静心诚,虽曲有悲欢离合而音自中正和平”[11]。并引用庄子之语为结:“虚无澹泊,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也”[11]。因此,释空尘在《著作琴曲要略》中以“古淡”及“节奏舒简”为琴曲最理想的风格。
空尘之论虽重元音,但亦不废弃有形之声,因只有有形之声音才是人心感受自然之道的媒介,感受的主体则是《音声论》中百般强调的“心”:“寔由心为之通,声为之感,气为之调,然后被于物之响应而成也”[11]。这个体悟的过程可以逆推:“凡物皆气,凡气皆声,凡声皆心”[11]。万物均由心生、心感,“释空尘引用《金刚经》语,并不是要彻底抛弃有形的音声,而是要通过这音声来超越有形,达到空灵纯净的佛境……音乐离不开有形的音声,但我们不能执着于有形音声,不能被有形的音声所迷惑,不能为其束缚,成为它的俘虏。……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心’,包括如何通过音声又超越音声,也全靠‘心’来完成的。正是‘心’,才是禅宗音乐本体论的根基和枢纽”[14]。而空尘在《音声论》中也重点讲了这个不生不灭、非空非有之心,而音与色都是刹那间生灭变化的,是外相,是以不可执著的,但又不能离开外相而求其大道,如同言意关系一样,言是得意之津梁,不可或缺。在《著作琴曲要略》中更是以“乐曲以音传神”开篇,详述五正二变七声是如何表达曲之深意:“谈乎人事物类而无所不备,其为音也,出于天籁,生于人心,凡人之情,和平爱慕悲怨幽忿,悉触于心,发于声,亦即此七音也。因音以成乐,因乐以感情,凡如政事之兴废……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动物情也”[11]。这段表述是传统美学中典型的“物感”理论,即因物感心,心动而产生艺术作品,通过艺术作品的欣赏理解又可以探知明了万物之理,文论中多有此理论,如《毛诗大序》《文赋》及《文心雕龙·物色篇》中都有相关论述。
这里有形之音亦是悟道之津梁,是以空尘才会在琴谱中不厌其烦地陈述弹琴的各种技法、琴音特色以及琴曲风格等,都是对有形之音的描述。如《指法纪略》重在言如何弹好琴之三声:散、泛、实(按),从与左右手相配到距岳山远近再到甲肉之运用皆有言说。而《琴声十六则》则是对如何弹奏琴声的十六种风格有详细地描述,婉转曲折,深切入微。
由此可见,释空尘在《枯木禅琴谱》中寄寓了他的琴学理论及禅理体悟,认为二者有互通之处,因为声音产生的缘起理论及元音与心的关系,所以可以琴说法,寄禅于琴。但对于古琴音乐而言,有形之声音又是“心”悟理不可或缺的媒介。
总之,《枯木禅琴谱》是释空尘一生心血所系,作为广陵派的最后一部琴谱,它对于本派前代琴谱,尤其是《五知斋琴谱》和《自远堂琴谱》多有继承,同时因为释空尘僧人与琴师的双重身份,琴谱也体现了他对于佛学与琴学辩证关系的思考,使琴谱从题名到内容都体现了“以琴说法”“禅以琴寄”的特殊意蕴。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