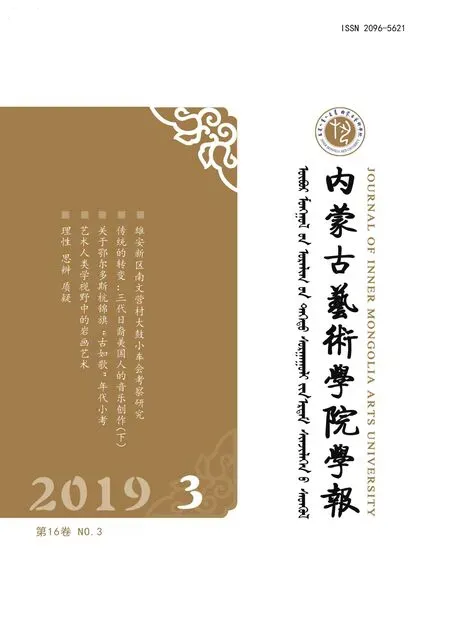近年来中国电影书写历史创伤研究
储双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民族国家对自身经历过的政治浩劫、大规模屠杀、战争等历史灾难及其留下的创伤总是耿耿于怀、难以忘却。因为“历史创伤”建立在(政治上)确认犯罪者群体——通常是在国家层面——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们是“在对话中形成的”,并且不是“固定的构成”。而确定“历史上的不正义”又是根据对普世人权的认识,那么“历史创伤”的现象也证明了历史是与政治、法律和伦理相互依存的。由于“历史创伤”和“持续时间”的问题,历史学科的特定概念“客观性”也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时间上的距离就被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经过时间,有偏见地“党派性”(和有偏见的行动者)——比如宗教、政治等等——才能消失,为“超党派”的视角也就是“客观性”的视角打开道路。历史主义的距离概念和历史概念在实践上没有区分清楚。[1](26-27)荷兰历史学家洛伦茨的这段论述对客观叙述历史创伤提出了超党派视角、时间间距以及对话性等要求。
事实上,大家普遍认为,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时间间距越长就越能准确地表达其意义,也才越能凸显其价值性的存在。换言之,只有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 才能为理解历史本身提供一种更为接近价值和意义的契机。唯有如此,脱离了当时时代限制的历史本身的意义才能被生成;而对于同时建构着历史的历史本文而言,意义的生成同样需要拉开时间的间距。伽达默尔认为:“对一个本文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Ausscho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促使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间距,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2](343)伽达默尔的“时间间距理论”阐释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为了达到对历史创伤的正确理解,必须要克服与历史之间的时间间距的障碍。相反,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提供了富于建设性的可能性,我们对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有永无穷尽的发现就是借助它实现的。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对伽达默尔的“时间间距理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间距必然会造成人类记忆的断裂。他认为:“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3](28-29)时间间距带来认识论的断裂,也会造成历史的缺失,但是这种断裂也使得电影创作者情感立场上可以保持相对客观和冷静。电影创作者总是寻找各种机遇和契机,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之上进行一次再书写和重新建构。电影上映后,针对影片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有些感兴趣的人往往会针对自己所能找到的相关史实去重新认知和梳理,挖掘影片遗漏了什么重要历史信息,虚构和添加了哪些人物和事件、细节,做出了哪些取舍,这些体现了创作者怎样的创作观念和表达意图,对历史本身是否提供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新鲜表述。这些都驱使电影创作者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态度,获得对历史更有效的建构和诠释方式,或者说更能够得到最大范围的观众的认可。
一、大屠杀题材:有无人类和人生终极命题的追问
对于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世界影坛上出现了很多部正面讲述南京大屠杀或以其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历史电影。除了中国主导拍摄的《屠城血证》、《南京1937》《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以外,还有中外合拍的《黄石的孩子》(2008)、《拉贝日记 》(2009)。每次历史叙述都在不断探索或者说不断更新原有的叙述视角,力图做到某种超越,就是这种差异化的书写丰富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维度和方式,从而让公众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更为丰满、清晰。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对这一很难让国人采取宽容心态的严肃题材,如何更加从容地走向国际影坛,被更多的外国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横亘在下一个要拍摄南京大屠杀的创作者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可能《辛德勒的名单》为这类题材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较为合适和贴切的指引。
《五月八月》《栖霞寺1937》《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都选择历史见证者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讲述二战史上日本法西斯制造的这桩灭绝人寰、罄竹难书的血腥屠城惨案。从叙事视角和表达方式来说,《五月八月》《栖霞寺1937》是将中国人作为受害代言的主体,即以中国人在战争中的亲身遭遇为主轴,带领观众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全城实行大规模屠杀的历史真相,真实地感受这场不容否认的人间悲剧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殇痛,调用人的良知与本能去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扼杀和摧残。其中,影片还展现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寺庙僧人与凶残暴虐的日军进行了一场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不同于前两部影片,在叙述角度上做了大胆尝试,分别以日本士兵角川、十三个金陵风尘女子和美国冒牌神父约翰的见证视角,面向国际社会承担起再现历史、反思战争的功能和责任。
两部影片都表现了一些惨烈悲壮的战斗场面,以此表明这是血性抵抗之城。尽管有大量国民党将士弃城溃逃,仍然有一些不愿意投降的士兵坚决留下来喋血守城,在这座沦陷的死城里的街头巷尾与日军展开了无望而惨烈的殊死抵抗。陆川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有南京的记者问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有什么看法上的改变。我说两年前我觉得这是一座屈辱之城,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也是一座抵抗之城,也是一段不屈的历史。”陆川表示:“支持我们走下去的是,不希望大家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只有40 万的数据,而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脸,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抵抗之城,不是我们编造的,而是真实的历史。我觉得一个民族很难期盼每次灾难来的时候都有救世主,我们的民族70 年都是靠自己,我们民族的抵抗从来没有停息过。”张艺谋在影片上映前就向外界透露,与严歌苓的原著小说相比,影片《金陵十三钗》中加入了表现中国人浴血抗争一条故事线索,“需要表现中国人的血性、不屈不挠的精神。”两部影片破除了以往种种关于南京屠城惨案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存在的那种对“不抵抗中国人”的片面描述。它们都以个人记忆的叙述方式承载起官方正史之外的民间叙事,展现了这段屈辱历史中中国军民为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斗争的场景,建构关于抵抗、牺牲、团结的民族神话。在这场大悲大恸的民族灾难面前,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处在危急关头,两部影片皆借重具有开放意识的人文精神,并以闪亮的人性光辉和坚强的生命意识,来彰显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生生不息的坚韧与顽强。可见,两部影片竭尽全力地挖掘历史的隐微之处,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起到激发民族责任感的作用。
从《五月八月》中天真纯洁的中国孩子、《栖霞寺1937》中与世无争的中国寺庙僧人,再到《南京!南京!》中的受过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日本士兵角川,直到《金陵十三钗》中的13 个金陵风尘女子和美国冒牌神父约翰的传奇组合,充分体现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在叙述视角和立场上从主观到客观的调整轨迹,以及希望这类题材影片由国内走向国际的受众范围变化。《南京!南京!》把日本军人设置为影片的中心人物去发现和揭示,一方面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确实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战争伤害数字确凿;另一方面,日军角川直面大批中国军民的屈辱和死亡之后灵魂深受震荡乃至拷问的视角,无疑为影片确立了赎罪与宽容的主题,而这是建立在中方以主动换位思考或宽容来假想性地赢取日方赎罪的思维逻辑之上的。虽然从占领者的视域观照南京大屠杀更显客观,以其目光看到中国军民的反抗也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叙事视角和立场向日军位移,也导致建立在血腥残暴的屠杀场面之上的民族情感和信念认同的真空。这也是影片上映后引起争议的某种原因。《金陵十三钗》以“商女”们挺身而出舍死取义,以及美国入殓师约翰完成从流浪汉到真正神父的人生角色转换,阐明了救赎与自我救赎的主题。血腥的野蛮屠杀唤起了见证者的斗争意志,从懦弱走向坚强,获得精神洗礼和道德新生,这种由污点走向亮点的心灵蜕变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电影创作者不遗余力地去对这段沉重历史予以真切再现,并对这场血腥战争进行沉痛反思,某种层面上也折射出了电影创作者对这场历史灾难的道德良知以及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和历史责任心。对于这类题材影片来说,对历史的再现是为了让人们获取关于战争的苦难历史,投身灾难和创伤的反思,将民族仇恨和伤痛牵引和延伸至民族复兴、和平。单纯地对屠杀者残酷暴行进行控诉和批判,或者说对被屠杀的无辜生命寄寓同情和体恤之心,都不是影片创作的根本初衷。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战争和人性予以深刻反思,冷静、克制、自信地审视侵略过我们的敌人,唤起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无限向往,才是反映人类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的最终目标。
国际影坛上描述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题材的电影有《苏菲的选择》(1982)、《辛德勒名单》(1993)、《美丽人生》(1997)、《钢琴家》(2002)。其中,尤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名单》最负盛名,该片不仅痛苦地呈现了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波兰境内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戮,又安静地告慰了逝去的无辜亡灵,给人以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升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犹太裔美国导演,在听说波斯尼亚种族清洗行径和大屠杀否认者的无耻言论后,决定将幸存下来的辛德勒的犹太人波德克·菲佛伯格见证的感人事迹搬上银幕。当时正值新纳粹主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开始日渐抬头,此片的题材极为敏感,而且许多电影人都认为没有商业价值。事实证明,这部以黑白摄影为主调来揭露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恐怖罪行的影片,摈弃了斯皮尔伯格以往热衷的特效,在思想严肃性和艺术表现力上都达到了中上水平。影片尽管没有直接表现德国纳粹在最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110 万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场景,但通过拉克拉科夫市“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的屠杀便可窥一斑。
德国纳粹党卫军司令官阿曼·苟斯认为,犹太民族在任何统治中都趋向于容忍,数千年来被到处驱逐还是委曲求全,这次他们可是劫数难逃,德国纳粹党卫军可不会像古罗马帝国那样仁慈。党卫军司令官阿曼·苟斯生性残暴,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阳台上端起枪支瞄准犹太劳工射击取乐,然后伸个懒腰去洗漱。他在德国投机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的启发下有所感悟:权力是指当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杀人而不去杀人。当皇帝对罪犯说“我赦免你”时就是权力。阿曼·苟斯赦免了犯错的犹太女佣海伦,但他还是未能饶过犯错的犹太马夫。他对知识分子出身的犹太女佣海伦十分依恋,但他还是不能超越等级和种族观念去爱她,内心依存的些微人性仍然战胜不了邪恶的魔鬼的力量。导演试图通过阿曼·苟斯对犹太女佣既冷酷又怜爱的痛苦情绪,来揭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对德国人的异化,也反映了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病态和畸形。当一列列装满犹太人的火车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当一个个犹太家庭默然吞金、病人含笑服毒、孩子躲在下水道时,当一位红衣女孩穿梭在一个个被枪毙的犹太人群中而自己也倒下时,当一车犹太妇孺因调度失误而开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而被剃头淋浴时,影片将大屠杀的意义已经不再简化为弱者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而从道德层面的谴责提升到现代文明的盲目性和荒谬性。
影片《辛德勒名单》的精妙之处,一方面在于采用辛德勒开列犹太人存活的名单这一叙述视角切入沉重的大屠杀题材,亦即辛德勒用自己所有财产打通关节贿赂纳粹军官,购买犹太人的活命;另一方面在于影片对人类和人生的终极命题进行了探讨和追问,并给人以永恒方向的指引。既让人直面法西斯屠杀无辜种族的血腥历史,又引领人从痛苦和梦魇中走出来得到心灵慰藉。这是值得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历史电影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二、反侵略斗争题材:基于情感、态度、文化价值观的多视角
甲午中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中国当下影坛反映这类题材的影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台湾导演洪育智执导的《一八九五》(2008)和魏德圣执导的《赛德克·巴莱》(2012)为代表的多方位展现台湾土著居民反抗日军统治的影片。二是以《一九四二》(2012)为代表的冷静克制地表现抗战时期千百万河南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和国民政府冷漠对待灾难的影片。三是以《铁道飞虎》(2016)为代表的“主旋律+动作+枪战+喜剧”叙事模式的抗战影片。
《一八九五》讲述了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日本近卫军团在甲午战争后准备接收清廷同意割让的台湾之际,遭遇到客家仕绅吴汤兴召集的台湾义民军为保家卫国奋勇抵抗的故事。原本是接收,但因台湾人民自发的大规模反抗,变成了一场战争。影片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抒发了台湾人民对清廷战败台湾被迫割让日本的沉郁悲愤、壮怀激烈之情,同时又渗透出一种声嘶力竭的悲恸、绝望和无助,犹如影片开头处吴汤兴淡淡地叙说自己的身世——父亲在自己孩提时代不告而别。整个故事讲述得十分冷静克制,对义军撤退、寻求粮食支援等战斗和牺牲场面表现出高超的控制能力。影片的情感表达尽管含蓄曲折,但能让人感受到浓郁忧愤、深沉蕴藉的家国情怀。
影片《赛德克·巴莱》力求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台湾日据时代由当地赛德克族发起的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雾社事件,因多角度的叙述视角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魏德圣在该片中引入了角色对角色、镜头对角色、观众对银幕多重注视的结构,而非压迫性地让观众被动地认同某一种文化价值观。小岛源治是少数善待台湾原住民的山地警察,起先他竭力化解赛德克部落间因争夺猎场而引发的冲突,而当妻儿被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麾下的勇士杀死后,转而威逼利诱屯巴拉社一同围剿马赫坡社。莫那三十多年来见证赛德克族在险恶的日据时代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明知这是一场求死的战争,但唯有为灵魂的自由而战,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进入祖灵之家。猎头族将出草取来的敌人首级作为礼物献祭祖灵,这种血腥的活祭方式,其实是在向祖灵或神明表达无限的虔敬之情,以及对其卓越的狩猎能力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勇士拒绝卑躬屈膝的文明而宁愿选择骄傲的野蛮,不战死便自尽,用生命来换取图腾印记的文化与信仰,使整部影片洋溢着雄性气息和硬汉精神。在青年莫那取头颅血祭祖灵、三百勇士抗击日本人的猛烈反攻等暴力场景中,影片用兴奋型叙事来制造眩目的形式美感,让观众享受野性难驯的快感而淡化伦理观念。在三百勇士血洗雾社公学校、为了血祭祖灵而自相残杀等暴力场景中,影片则用冷静型叙事来揭示人性的残忍与黑暗,调动观众在目睹屠戮时所诉诸的伦理观念。夹在日本人威胁与族人期望之间,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不被文明认同的花冈一郎、花冈二郎,是从小受日本教育、取日本名的赛德克巡察。他们对身份归属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台湾人抗日也亲日的复杂情结。争取民族独立就必须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反抗日本又不得不踏上反抗现代性的道路。这就是寻求民族独立与实现现代性在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两难困境,一种渴望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而又无法从传统中获取支援意识的焦灼心态。可见,影片给观众提供了辨识小岛源治、莫那·鲁道、花冈兄弟等角色的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渠道,但不会要求观众忠顺他和他的文化价值观。
影片《一九四二》以逃荒地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美国记者和传教士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古老的中原河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导致三千万灾民在饥荒中颠沛流离、踏上逃荒路。原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在叙事上以调查体的形式展开,影片却将其改编成了一部全靠外力推动找不到或者说几乎看不见强有力的精神出路的苦情戏。在白热化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之下,在卖儿鬻女的没有尽头的逃荒旅途之中,尤其是置身于当时政府冷漠、腐败及蔑视人民生存的时代之中,影片结尾处展现出来的人性温暖或曰人的尊严就显得极其微弱。老东家亲眼见证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在饥民浩荡、哀鸿遍野、绝望无止的逃荒旅途中以各种形态惨死后,褪去了原先身上那种封建地主的市侩和狡猾,焕发出人性的善良和崇高,在片尾处与失去所有亲人的陌生小女孩互认为爷孙相依为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多舛命运和深重苦难,普通老百姓在那个社会动荡、灾害频繁的环境下对艰难生活、无奈人生只能咬牙忍耐而无力抗争。令人遗憾的是,影片只是将日本侵略军征伐劫掠让灾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置若罔闻、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上访被驳回、传教士力量有限、贪官趁火打劫……种种史实制造的悲惨的人间炼狱景象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虽然片尾处闪耀着些许人性的光辉,但是并没有指出一条对于饱受战乱、饥荒蹂躏的灾民具有强大的救赎力量的康庄大道。
《铁道飞虎》用动作喜剧片的商业外壳包装了抗日战争题材,凭借动作、幽默、明星对红色经典影片《铁道游击队》进行了重新改装,意欲重现《智取威虎山》的商业成功。把侵华日军弱智化、漫画化,使小人物的实力和能量夸张化,显然有违历史真实。一些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戏剧性情节,其中虽无特别令人难以卒睹之败策,却或多或少地有损于影片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这不是说历史剧不容虚构,而是说虚构的人物情节未能熨帖地融入历史图景之中。相对而言,《智取威虎山》在各类反派形象塑造上更为出彩,并以此衬托出战斗的艰辛与不易。以娱乐性作为出发点固然无可厚非。《铁道飞虎》竭尽全力地使用各种动作创意、笑料包袱和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再现的却是《铁道游击队》生逢的20 世纪50年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国际影坛上,不乏有一些经典之作让战争与幽默成功对接上,无论人物的外在行为是多么的过火和癫狂,但影片毫无例外地皆立足于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该片的主题是小人物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留给观众的只是隔阂很深的抗日激情。距离原作60 年的现在,经典翻拍如果还不能让观众在大笑之后咀嚼出真实而又沉重的历史大味道,表达一种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生命意识,那么就可以说是迷失或者说背离了它的本义。
美国战争片大多趋同于以重大战役作为背景来描写人物命运,而中国战争片侧重于展现某一重大战役。前者在结构上以写人为主,通过战役和战斗场面来烘托和渲染人物性格;后者在结构上以写事为主,较详尽地记录了某一重大战役发生的前因后果、重要历史人物关系和性质。不过,即使是以描写某一重大战役为主的好莱坞战争片,它都虚构出一条关于爱情或人性的主线,让虚构人物参与到战役过程中去,从而使得其所反映的历史精神容易为人吸收。因而,常常会出现虚构的历史人物成为主角,而真正的历史人物倒成了配角。对于二战题材,美国电影的主要创作趋向表现为:一类是以《拯救大兵瑞恩》(1998)为代表的“历史灾难+救赎”的叙事模式。关注战争的受害者,是影片的起点。终点则是美国是一个崇尚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的国度,控诉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的暴政和对其他国家的压迫。另一类是以《英国病人》(1996)、《珍珠港》(2001)为代表的烽火爱情的叙事模式,将虚构的主线推到历史的前景位置,由奇观惊悚组成的历史灾难旅程浓入当代人的心灵之中。在中国影市异常火爆的《血战钢锯岭》(2016)恰恰将两种叙事模式作了很好地结合。
这类美国影片明显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回归和重振旗鼓,注重塑造出平民英雄在巨大的历史灾难面前所焕发出来的永不屈服、坚韧不拔、开拓进取、英勇无畏的精神。它们往往会采取平民代入法,从平凡小人物视角观察历史事件,改变了以往讲述创世纪英雄的宏大叙事,而以个体化体验的方式叙述。自20 世纪30 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对法西斯持“中立”立场,因而长期以来遭受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质疑。这类影片的拍摄意图就在于为此作出各种辩解,塑造美国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旗手身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拯救大兵瑞恩》、梅尔·吉布森执导的《血战钢锯岭》,都极为逼真地重现了当时战斗场景的惨烈与残酷。尤其是《血战钢锯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上等兵军医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予以人性化呈现,非常传神,让人觉得有理有据,觉得可信。当历史事实对个人命运造成泰山压顶之势时,导演用“浓入”法,当历史事实对个人命运若即若离时,导演则用“淡出”法。前者的用意是透视诺曼底登陆、冲绳战役留下的心影心响;后者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二战的历史背景。最终就是为了揭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表达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
电影书写历史创伤总是力求自己在叙述方式做到独特,在情感表达上追求新颖。正是因为每部影片往往会追求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同一历史事件,给观众以不同棱面的阐释,进而为观众提供具有饱满度、深刻性的历史认知。不过,无论采取怎样的叙述视角,提供怎样的新思考和新认知,都要紧紧抓住人类终极关怀的观照,并给以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信仰承诺。只有对那些给民族国家造成心灵创伤的历史事件赋予人类终极之追问,并给出一个合理或者合乎情感的诠释,才能让观众走出历史创痛,更好地面对自己和世界。也就是,影片无论是采用回忆的结构还是通过虚构去建构或组织起一个历史世界,最终的目的是让观众从影片所营造的创伤性世界中逃脱出来,进入到一个有着相对熟悉和安全的规则的社会秩序之中。这才是优秀的历史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