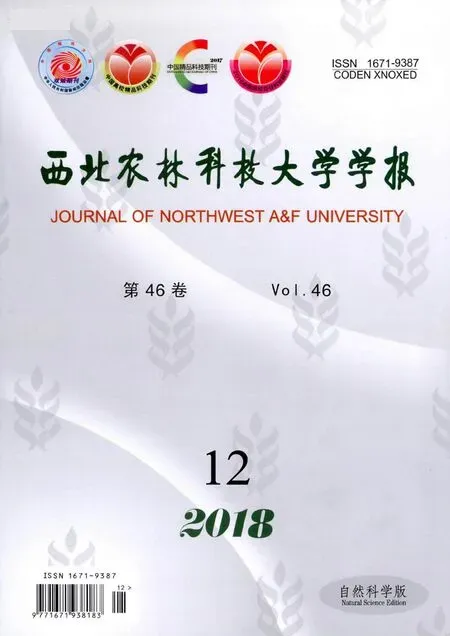华南虎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生物学特性研究
范克伟,余 佳,杨守深,傅文源,林开雄,黄翠琴,戴爱玲,林青青,郑 琳,林宏彬,王 娟,邓阿丽
(1 龙岩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2 福建省家畜传染病防治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 龙岩 364012;3福建农林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4 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福建 龙岩 364201)
大肠杆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细菌,一般不致病,但有一些血清型或具有某些毒力因子、毒力岛的菌株具有致病性,并能引起人和动物共同感染,是人畜共患病重要病原[1]。目前根据大肠杆菌的致病特性将其分为3个主要亚群:共栖菌或非致病性大肠杆菌亚群、引起肠道感染的致病性大肠杆菌亚群及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exraintestinal pathogenicEscherichia.coli,ExPEC)亚群,其中ExPEC亚群包括引起人和动物尿道感染的大肠杆菌(UPEC)、新生儿脑膜炎大肠杆菌(NMEC)、败血症致病菌和禽致病性大肠杆菌(APEC)[2]。研究表明,ExPEC具有广泛的宿主谱,不同ExPEC亚群可侵袭或破坏宿主的防御系统并在机体内多种组织增殖,提示ExPEC的病型更为复杂,如禽致病性大肠杆菌(avian pathogenicEscherichiacoli,APEC)可引起禽类的多种疾病, 常表现为心包炎、肝周炎、腹膜炎、气囊炎、输卵管炎、滑膜炎以及败血症等症状,是目前严重危害养禽业的传染病之一[3-4]。通常认为分离自禽类的多数大肠杆菌血清型只对禽类有致病作用,而对人和其他动物不会引起感染。但Tivendale等[5]研究发现,APEC也可引起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疾病,表明APEC亦是人兽共患病的潜在病原体。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主要毒力因子包括黏附素、铁螯合蛋白系统、耶尔森杆菌素、血清增强存活因子、外膜蛋白、大肠杆菌素、温度敏感血凝素、溶血素、志贺毒素等[6]。
华南虎亦称“中国虎”,属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动物,也是中国特有的虎亚种。目前华南虎种群的近交系数高、群体小,且对华南虎现在流行的传染病未见流行病学系统调查[7-9],这对其种群繁衍非常不利。近年来,我国不断有圈养华南虎感染疫病的报道[1,7,10],表明疫病已威胁到我国华南虎群的繁殖保护工作。2016年3月,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出现一只不明原因急性死亡华南虎幼虎,为进一步调查该幼虎急性死亡的原因,无菌采取死亡幼虎的肺、肝和肠道等组织病料进行细菌分离鉴定,并对分离菌株进行了16S rRNA基因扩增、生化试验、药敏试验以及毒力相关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以期为该病例的确诊及我国圈养华南虎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料来源
2016年3月,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送检一只75日龄急性死亡的华南虎幼虎。该幼虎死亡前1天,表现出精神沉郁、不爱走动、嗜睡、拉黑色软便等症状。对死亡幼虎进行病理剖检发现:血液较为稀薄;病变主要集中在消化道,从胃开始整个消化道内有大量焦油样的黑色内容物,进一步观察发现胃黏膜表面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溃疡灶,小肠各段肠黏膜脱落,并伴有严重的充血及出血现象;大肠至肛门各段肠黏膜也呈现明显的充血、出血及脱落现象;脑膜充血;胰脏出血;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及气管均未见明显的病理变化。
1.2 主要试剂及试验动物
伊红美蓝琼脂(EMB)、麦康凯、营养肉汤、SS琼脂平板、鲜血琼脂平板,均购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药敏纸片、革兰氏染液、微量生化发酵管,均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DNA分子质量标准(DL2000)、LATaqDNA聚合酶、2×GC Buffer、dNTPs、通用型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pMD18-T克隆载体,均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DH5α感受态细胞,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BALB/c小鼠,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1.3 引物设计与合成
参照文献[11]合成细菌16S rRNA 通用引物,参照文献[12]合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鉴定引物,对分离菌株进行PCR鉴定;参照文献[13-14]合成针对大肠杆菌ST、eaeA、EinV、CNF1 4个毒力基因的引物;参照文献[4,6,15]合成其他13种大肠杆菌毒力相关基因的引物,并对分离株的毒力基因进行PCR扩增检测。上述引物序列详见表1,均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表1 大肠杆菌鉴定及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的引物序列Table 1 Primers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virulence related genes of Escherichia coli
1.4 细菌的分离培养
无菌采取死亡幼虎的肺、肝、脾、肠等病料组织,划线接种于鲜血琼脂平板、麦康凯平板、SS琼脂平板培养基上,37 ℃培养16~18 h;挑取单菌落进行革兰氏染色后镜检,将可疑菌落在麦康凯平板上分区划线,37 ℃培养16~18 h;再次挑取具有大肠杆菌典型菌落形态的单菌落分别划线于伊红美蓝琼脂、麦康凯和SS琼脂平板, 37 ℃培养16 h后进一步纯化。用葡萄糖、果糖、麦芽糖、乳糖、甘露糖、蔗糖发酵试验,枸橼酸盐利用试验,尿素酶试验,吲哚试验,VP 试验,硫化氢试验等对分离细菌作进一步鉴定。
1.5 分离菌株的16S rRNA PCR扩增与序列分析
参照TaKaRa公司通用型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说明书,对分离菌株进行DNA提取,采用表1中16S rRNA通用引物进行PCR扩增。 PCR反应体系总体积25 μL:DNA模板1 μL,2×GC Buffer I 12.5 μL,dNTP 4 μL,上、下游引物各1 μL,LATaq酶0.25 μL,用ddH2O补至25 μL。PCR反应程序为:95 ℃预扩增5 min;95 ℃ 1 min,58 ℃ 45 s,72 ℃ 1 min,33个循环;72 ℃延伸10 min。PCR产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将目的片段经胶回收后克隆至pMD18-T载体中,送Invitrogen公司测序。利用DNAStar 7.1和MEGA 6.0软件将测序得到的基因序列与GenBank公布的各株大肠杆菌16S rRNA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并构建系统进化树。
1.6 分离菌株的PCR鉴定
采用文献[4,11]的禽致病性大肠杆菌鉴定引物(表1),对分离菌株进行PCR鉴定。PCR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同1.5节。
1.7 分离菌株的药敏试验
用灭菌生理盐水将分离菌株制成含菌量为1.0×108CFU/mL的细菌悬液,涂布于LB营养琼脂平板上,按照药敏纸片扩散法,参照CLSI(2015年)手册对头孢噻肟、头孢噻吩、庆大霉素、恩诺沙星、四环素、强力霉素、卡那霉素、多西环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甲基异恶唑、氯霉素、氨苄西林、链霉素及呋喃唑酮共15种常用抗菌药物进行药敏试验,测定分离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1.8 分离菌株的小鼠致病性试验
参照文献[16],采用平板计数法测定分离菌株的菌落形成单位(CFU),然后将培养物稀释至1.0×109CFU/mL。选取 6周龄BALB/c小鼠24只,其中攻毒A组6只小鼠,经腹腔注射稀释后的上述分离菌培养物0.1 mL/只;对照A组6只小鼠,采用同样方式注射等体积无菌营养肉汤作为阴性对照;攻毒B组6只小鼠,采用灌胃针灌服稀释后的上述分离菌培养物1 mL/只;对照B组6只小鼠,采用同样方式灌服等体积无菌营养肉汤作为阴性对照。观察记录各组试验小鼠的死亡情况,并及时对死亡小鼠进行解剖和病原分离。
1.9 供试小鼠病理组织切片的制作与观察
无菌采取死亡小鼠心、肝、脾、肺、肾和肠道等组织病料,置于体积分数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按常规方法依次进行冲洗、脱水、透明、浸蜡、包埋、切片、烤片,经H.E染色和加拿大树胶封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组织病理变化。
1.10 分离菌株的毒力基因检测
参照文献[13-14]的方法,对分离菌株基因组DNA的ST、毒力岛eaeA、EinV、CNF1毒力基因进行多重PCR检测,在GenBank上进行BLAST分析;参照文献[4,6,15],对分离株的其他13种大肠杆菌毒力相关基因进行PCR扩增检测,PCR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同1.5节。
2 结果与分析
2.1 细菌分离及形态特征
对采集的死亡幼虎组织病料进行细菌培养,其中肝脏及肠道组织样品中均分离到1株表现相同的菌株,该菌在伊红美蓝琼脂(EMB)平板上呈现黑色菌落且带有金属光泽,在麦康凯琼脂培养基上形成粉红色圆形、边缘整齐、有光泽的菌落,在SS琼脂平板上菌落呈红色圆形、光滑、边缘整齐;经革兰氏染色呈阴性,为无芽孢短小杆菌(图1),将该分离菌命名为FJ/Tiger2016。生化鉴定结果显示,该株细菌符合大肠杆菌的生物学特性(表2)。

图1 分离菌FJ/Tiger2016的革兰氏染色结果(×100)Fig.1 Gram staining result of the isolate FJ/Tiger2016(×100)

项目 Item结果 Result项目 Item结果 Result葡萄糖GLU +尿素酶URE-果糖FRU +吲哚试验IND +麦芽糖MAL +明胶液化试验GEL-乳糖LAC +硫化氢H2S -甘露糖MAN +VP 试验VP test -蔗糖SUC -MR试验MR test +枸椽酸盐CITR -
注:+.反应阳性;-.反应阴性。
Note:+.Positive; -.Negative.
2.2 分离菌株的16S rRNA扩增与序列分析
2.2.1 16S rRNA PCR扩增 以分离株FJ/Tiger2016 的DNA为模板,利用16S rRNA通用引物扩增分离株16S rRNA全基因序列,结果在1 500 bp左右有1条特异性条带(图2),与预期片段大小相符。序列比对结果显示,该分离株为大肠杆菌。
2.2.2 16S rRNA的序列同源性与系统进化树 将FJ/Tiger2016 16S rRNA测序结果,与GenBank中登录的其他25个大肠杆菌分离株16S rRNA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对,结果显示FJ/Tiger2016与其他参考菌株16S rRNA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98.5%~99.7%。其中与禽源分离株(AB272358)的序列同源性最高,为99.7%;而与鸭源分离株(EF620921)及鸭源分离株(EF620925)的同源性最低,为98.5%。系统发育进化树分析结果(图3)显示,26个大肠杆菌分离株共形成2个较大的遗传分支,鸳鸯鸭源分离株(HM194880)与其他分离株的距离都很远,单独处于一个分支,其余菌株位于同一大分支。

M.DL 2000 DNA Marker;1.空白对照;2.分离株的PCR扩增产物M.DL 2000 DNA Marker;1.Blank control;2.PCR products from the isolated strain 图2 分离菌株16S rRNA的PCR扩增结果Fig.2 PCR amplification of 16S rRNA of the isolate

图3 大肠杆菌分离株FJ/Tiger2016与其他来源参考菌株16S rRNA的系统进化分析Fig.3 Nucleotide sequences based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16S rRNA between the FJ/Tiger2016 and other strains
进一步分析发现,FJ/Tiger2016与人源分离株(NZCP016497)、鼠源分离株(NZMBNX01000003)、禽源分离株(AB272358)及鸭源分离株(EF620926)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遗传小分支,亲缘关系较近,但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异性或物种特异性。
2.3 分离菌株的PCR鉴定
以分离菌株DNA为模板,利用禽致病性大肠杆菌鉴定引物扩增分离株phoA基因序列,结果(图4)在约720 bp出现1条特异性条带,与预期片段大小相符,表明该分离菌株为禽致病性大肠杆菌。

M.DL 2000 DNA Marker;1.空白对照;2.分离株的PCR扩增产物M.DL 2000 DNA Marker;1.Blank control;2.PCR products from the isolated strain图4 分离菌株phoA基因的PCR扩增结果Fig.4 PCR amplification of phoA gene of the isolate
2.4 分离菌株的药敏试验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分离菌对15种待测抗菌药均表现为敏感,其中对头孢噻肟、头孢噻吩、环丙沙星、恩诺沙星、左氧氟沙星、四环素、强力霉素、磺胺甲基异恶唑、卡那霉素、氯霉素、氨苄西林、链霉素和呋喃唑酮较敏感,对庆大霉素和多西环素中度敏感。
2.5 分离菌株对小鼠的致病性
2.5.1 临床症状、组织病变及病原分离 攻毒试验结果显示,攻毒A组6只小鼠在攻毒后5 h内全部死亡。剖检可见小鼠腹腔内积液,胃严重膨气,肠黏膜水肿、充血严重,心包淤血,肺脏严重出血,肝脏肿大,脾脏淤血(图5)。同时,从死亡小鼠腹水、肝、心血分离到的菌株,经鉴定与攻毒菌株相同。而对照A组6只小鼠均无异常。攻毒B组6只小鼠攻毒后无明显的临床症状,至攻毒后7 d均未出现死亡。
在对攻毒小鼠剖检时,在小鼠肝、心血等均未分离到菌株。对照B组6只小鼠也均无异常表现。上述结果表明,该分离菌株通过腹腔接种对试验小鼠具有较强的致病力,5 h内攻毒小鼠全部死亡;但通过灌胃接种的方式攻毒小鼠均未出现死亡,因此怀疑该分离菌株有可能属于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ExPEC)。
2.5.2 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对攻毒A组及对照A组小鼠进行病理解剖,分别采取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等组织,用体积分数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制作组织病理切片。病理切片镜检结果显示,与对照A组小鼠相比,攻毒A组小鼠心脏组织中心肌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心肌纤维间有大量的红细胞(图6-A);肝脏组织中央静脉及肝窦内有大量红细胞,大量肝细胞发生变性,胞核溶解,空泡化(图6-B);脾脏组织内淤血严重,脾窦内有大量红细胞及炎性渗出物(图6-C);肺脏组织出血、肺泡壁增厚,肺泡和支气管内充满了大量的炎性细胞、红细胞浸润及炎性渗出物(图6-D);肾脏组织中可见大量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脱落,肾小管官腔内及小管间有大量红细胞及炎性细胞,肾小球出血,部分肾小球萎缩甚至消失(图6-E);肠道病理切片观察可见肠绒毛大量坏死、脱落,并伴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为主的病理变化(图6-F)。

A-F.分别为攻毒A组小鼠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肠道;A′-F′.分别为对照A组小鼠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肠道A,A′.Hearts;B,B′.Livers;C,C′.Spleens;D,D′.Lungs;E,E′.Kidneys;F,F′.Intestine;A-F.Pathological section results of the infection groups;A′-F′.Pathological section results of the control group图6 分离菌株腹腔注射攻毒小鼠不同器官组织的病理切片观察结果Fig.6 Pathological sec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organs of mice after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the isolate
2.6 分离菌株毒力基因的检测
采用多重PCR对分离菌株进行致病基因检测,发现该菌株含细胞毒性坏死因子1(CNF1)毒力基因,特异性条带大小约为550 bp(图7)。产物经胶回收后送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与GenBank中CNF1毒力基因(AF483828.1)的同源性为99%。致病性大肠杆菌ST、eaeA、EinV毒力基因的PCR结果为阴性。
利用PCR方法对分离菌株是否含有13个毒力基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死亡华南幼虎分离菌株含有irp2、fimC、luxs、stx2f、iroC、tsh、pfs、ompA和fyuA9个毒力基因(图8)。对其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将测序结果在GenBank 上进行比对分析,显示均为目的片段,这些基因与其致病作用有密切关系。

M.DL2000 DNA Marker;1.分离株PCR扩增产物;2.空白对照M.DL2000 DNA Marker;1.PCR products from the isolated strain;2.Blank control图7 分离菌株毒力基因CNF1的PCR扩增结果Fig.7 PCR amplification of CNF1 virulence gene of the isolate

M.DL2000 DNA Marker;1.Negative control;2.irp2;3.fimC;4.luxs;5.stx2f;6.iroC;7.tsh;8.pfs;9.ompA;10.fyuA图8 分离菌株9个毒力基因的PCR扩增结果Fig.8 PCR amplification of nine virulence gene of isolate
3 讨 论
华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虎亚种。近年来随着我国濒危虎群繁殖保护工作的开展,虎数量明显增加,但疫病对圈养华南虎的危害也在不断增大[1,7,10]。大肠杆菌是动物肠道内最重要的微生物之一,根据血清型不同,某些致病性大肠杆菌能引起畜禽、野生动物和人共同感染,给经济生产、人类健康、野生动物保护等均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被视为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菌[17-20]。此外,大肠杆菌病的流行暴发,也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的健康繁衍。
3.1 华南虎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分离鉴定
本研究对死亡华南虎幼虎多个器官组织进行了细菌分离鉴定,结果从其肝脏及肠道组织中分离得到1株细菌,根据形态特征、培养特性、生化试验及16S rRNA序列分析结果,确定该分离菌为大肠杆菌,命名为FJ/Tiger2016。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在华南虎饲养过程中经常饲喂活禽,为了解该菌株的感染来源,本研究采用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特异性鉴定引物对该分离菌株进行了PCR鉴定,结果显示FJ/Tiger2016属于禽致病性大肠杆菌,表明其感染来源有可能为家禽。
目前对大肠杆菌病主要利用抗菌药物进行预防和治疗,然而常用抗生素的滥用,使得病原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且不断产生新的耐药菌株,造成某些抗生素临床应用效果较差。虽然野生动物不常接触抗生素,但其耐药性不容忽视[21]。对临床上分离到的菌株,必须进行药敏试验,选择高效敏感的治疗药物,方能较好地防治该病。本研究选用15种常见抗菌药物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FJ/Tiger2016未表现出明显的耐药性,对选用的抗菌药均表现敏感,因此多种药物均可作为临床治疗该分离株引起的致病性大肠杆菌病的候选药物。
3.2 华南虎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致病性及其毒力基因检测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FJ/Tiger2016的致病特性,本研究开展了小鼠致病性试验和禽致病性大肠杆菌(APEC)毒力相关基因的检测分析。小鼠致病性试验结果显示,FJ/Tiger2016经腹腔接种时,对试验小鼠具有较强的致病力,小鼠攻毒后5 h内全部死亡。病理剖检及组织病理切片观察结果均显示,该分离株对死亡小鼠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等多个重要组织器官,均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病理损伤,这也可能是造成该华南虎幼虎急性死亡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发现当采用灌胃接种时,至攻毒后7 d攻毒小鼠均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表明该分离菌株为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ExPEC)。禽致病性大肠杆菌(APEC)属于ExPEC亚群,且近年来有研究表明,APEC除可引起禽类的多种疾病外,也可引起包括人在内的多种哺乳动物疾病,为潜在的人兽共患病病原菌[5,22],上述结果表明,APEC已对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大肠杆菌的致病性与其毒力因子关系密切。大肠杆菌毒力因子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毒素、粘附素、外膜蛋白、铁转运系统等[23-24]。毒力因子的存在与毒力大小决定了所致疾病的种类和严重程度。FJ/Tiger2016的17种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其同时含有CNF1、irp2、fimC、luxs、stx2f、iroC、tsh、pfs、ompA和fyuA10种毒力相关基因。其中fimC编码的蛋白是Ⅰ型菌毛生物合成过程中所必需的蛋白, 是检测Ⅰ型菌毛的标志,与细菌的黏附、入侵和繁殖有密切关系,APEC中Ⅰ型菌毛的检出率比在非致病性菌株中高;iroC、irp2和fyuA均为APEC铁摄取系统蛋白编码基因,而获取铁的能力是APEC发挥毒力的关键,其中irp2和fyuA是构成耶尔森菌强毒力岛(HPI)的2个重要毒力基因,负责从靶细胞摄取铁[25]。不管是什么血清型,大约70% APEC中含有HPI[26]。tsh为自主转运蛋白,是禽源大肠杆菌中一个重要的致病因子[27];ompA为外模蛋白(OMP)编码基因,可以介导细菌定殖、侵袭和免疫逃避[28];luxs和pfs参与合成密度感应系统中的信号分子AI-2,通过信号分子AI-2 调节毒力基因的表达;stx是产毒大肠杆菌(STEC)的主要毒力因子,stx2f与禽源STEC相关性较大;CNF1是一种分子质量为115 ku 的蛋白毒素因子,能够固定地激活Rho家族GTP酶RhoA、Rac和Cdc42,其引起的细胞毒性主要是由于异常的Rho激活和随后的Rho降解[2,24]。白灏等[4]对56 株APEC分离株毒力基因的检测结果显示,fimC、pfs、ompA、luxS4个基因的检出率超过90%,为APEC保守基因。陈文静等[29]对65 株鸭致病性大肠杆菌分离株进行14种大肠杆菌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表明ompA、pfs和luxS3种基因高度保守,在分离菌株中的检出率为100%,iss、iuCD、tsh、fimC、cvaC和iroC基因的检出率达到72%以上。这些毒力基因与APEC的致病性、耐药性等均密切相关,而本研究中FJ/Tiger2016同时含有上述多种毒力基因,暗示其可能具有很强的致病性,与对小鼠的致病性试验结果一致。
3.3 华南虎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系统发育分析
基于16S rRNA基因的同源性比对和进化树构建结果显示,FJ/Tiger2016与GenBank 中其他25个大肠杆菌分离株的同源性在98.5%以上,其中与禽源分离株(AB272358)的序列同源性最高,为99.7%。与人源分离株(NZCP016497)、鼠源分离株(NZMBNX01000003)、禽源分离株(AB272358)及鸭源分离株(EF620926)亲缘关系较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遗传小分支,表明分离到的禽致病性大肠杆菌FJ/Tiger2016可能来源于禽类,但又具有成为人畜共患潜在病原菌的可能。
4 结 论
分离到华南虎源禽致病性大肠杆菌FJ/Tiger2016,该分离菌株为具有较强致病力的肠道外致病的禽致病性大肠杆菌,表明禽致病性大肠杆菌已对我国圈养华南虎造成了一定的威胁。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该分离菌株可能来源于禽类,但又具有成为人畜共患潜在病原菌的可能,因此在华南虎饲养过程中应引起重视。本研究结果为探究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致病机理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我国圈养华南虎大肠杆菌病的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