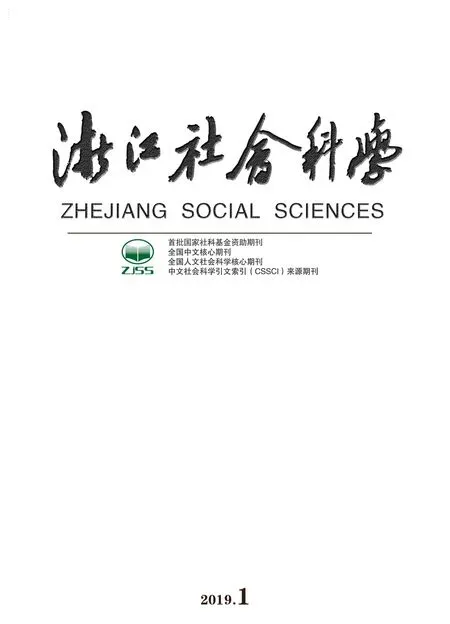尼采的幽灵:鲁迅“反启蒙的启蒙”思想
□ 高力克
内容提要 鲁迅借鉴尼采及欧陆“新神思宗”哲学批判“19世纪文明”之“众数”与“物质”的偏至、倡言“重个人”与“非物质”、呼唤以“英哲”“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以其尼采式的批判现代性的“反启蒙的启蒙”之“新启蒙”,在晚清启蒙思潮中独树一帜。尼采政治上的反启蒙主义和哲学上的启蒙主义,构成了其“新启蒙”之“反启蒙的启蒙”的悖论。鲁迅的尼采式启蒙思想既具有现代性批判的前卫性,亦难免“反启蒙的启蒙”的思想困境:“天才”与“庸众”的对立。一方面,他崇尚尼采“超人”式的“贵族激进主义”,主张“重个人”、“排众数”;另一方面,他又希冀以“超人”式“大士天才”为社会之桢干,树特立独行之风,以改造国民的奴隶性。这样,他就难以摆脱“天才”与“庸众”二律背反的困境。鲁迅“重个人”、“排众数”的尼采式个人主义与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目标的矛盾,也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的分歧所在。严复、梁启超“陶铸国民”的“新民”是一种培育公民意识的政治启蒙,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新人”则是一种人性改造的精神启蒙。鲁迅所追寻的“新人”典范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公民,而毋宁是一个后现代的“审美乌托邦”。论人格的等级,严梁的“新民”属于“中等的东西”,而鲁迅的尼采式“新人”则属于“最高的东西”,二者以陶铸国民的“低调的启蒙”与人性解放的“高调的启蒙”,相映成趣。鲁迅晚年从尼采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其“超人”幻灭后反抗空虚的新求索。马克思以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填补了鲁迅幻灭后孤独“个人”的空虚。
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早年负笈东瀛习医,后弃医从文,投身以文艺疗救国人精神的启蒙事业,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不朽的启蒙时代文学杰作,开中国现代文学之先河。
晚清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器物西化和维新运动的制度西化的递嬗。1907年,游学日本的杨度综合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目标,倡言军事工商立宪并举的“金铁主义”。青年鲁迅反思晚清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他认为,兴业振兵和立宪国会皆属文明的枝叶而非其本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治标不治本,而文明之本根在人,“立人”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由严复和梁启超引领的“开民智”、“新民德”的清末启蒙思潮中,“中国尼采”鲁迅之启蒙思想,以其以浪漫主义批判现代性的“反启蒙”色彩和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独树一帜,成为近代中国“新启蒙”的先驱者。
一、现代性批判:众数与物质之弊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现代文明拜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双元革命”之赐。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了现代西方之民主政治与商业社会的兴起,演成19世纪文明之“众数”与“物质”两大潮流。古今文明之转型,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大众社会的平庸化、同质化和商业社会的物质主义,遂成为现代性的两大偏弊。
现代化是一个由英国发轫而向世界扩张的全球转型过程。由于东西方的时代落差,西方现代性问题与中国转型问题属于不同的时空语境。在20世纪初的清末中国,“民主”与“物质”两大潮流正方兴未艾,席卷神州。在立宪派与革命派中,议会民主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尽管二者有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的路径分歧。而流亡欧美的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则承洋务运动之余绪,推崇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力倡“物质救国论”,以抵制革命潮流。
在清末思想界,鲁迅是最早关注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者。1907年,这位26岁的留日学生撰《文化偏至论》,翌年发表于东京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这是一篇青年鲁迅反思西方现代性而探索新启蒙的代表作。受尼采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鲁迅对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众数”与“物质”之弊有着敏锐的认识。他指出,19世纪的一大潮流是“众数”或“众治”。从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复至法国大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①民主化的大众社会扫荡了贵族,但其平等主义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以多数压制少数独特者的群众霸权,以及社会的同质化和道德习俗、精神趣味的平庸化。
物质主义为19世纪的另一大潮流。近代以降,宗教衰落,思想自由,科学勃兴,技术发达,至19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煤铁汽电广泛应用于军事制造交通,“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②随着工业革命后现代商业社会之物质文明的兴盛,崇尚物质生活的物质主义大行其道,成为世界“除魅”以后的一种新的世俗价值观,这种物质崇拜导致了现代人之精神的枯萎和生命的异化。
鲁迅以现代性反思的视域,审视19世纪文明之得失,洞察民主与商业社会的偏至:“众数”与“物质”克服了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之旧弊,又导致了现代性之“多数人的暴政”和物质主义的新偏。
对于20世纪的新文明,鲁迅寄希望于欧陆“新神思宗”。在他看来,19世纪末欧洲思想变迁的新趋势是尊崇个人和标榜精神的“新神思宗”的兴起。“新神思宗”以矫正19世纪文明而起,其“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③
反观中国西方化的革新运动,鲁迅指出其食洋不化而不辩西方文化偏伪的迷思。西潮东渐“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鲁迅批评维新运动盲目追逐偏伪的西方19世纪文明而“由旧梦而入于新梦”的迷误,他主张,中国改革“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④
鲁迅崇尚个人主义,但他深知“个人”观念在中国移植之难。“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⑤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深入人心,社会民主之倾向大张,凡个人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的趋势,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荡无高卑。平等理想诚美,但其篾弃个人殊特之性,则流弊所至,将使纯粹之文化精神更趋于僵化。“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⑥19世纪大众社会的凡庸化,物极必反,则先觉善斗之士出而倡言个人主义:斯蒂纳倡“极端之个人主义”,叔本华“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克尔恺郭尔疾呼“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易卜生则主个人主义而“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
鲁迅最推崇的欧洲个人主义思想家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他盛赞尼采及其超人哲学:“若夫尼耙,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⑦鲁迅服膺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反对“抑英哲以就凡庸”,而主张“置众人而希英哲”,期待“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⑧
鲁迅服膺的欧陆“新神思宗”的个人主义,是一种非物质主义的精神个人主义。他指出,与个人主义一样,非物质主义亦由抗俗而兴。唯物之倾向至19世纪后叶其弊益显,一切事物无不质化,精神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舍主观之内面精神。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停滞,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黯淡,此为19世纪文明之通弊。于是新神思宗兴,崇奉“主观与意力主义”,匡纠流俗,其功有洪水方舟之伟。“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质言之,主观主义“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⑨尼采、易卜生等人皆以主观主义力抗时俗,克尔恺郭尔则以主观性为真理准则和善恶标准。19世纪末,人格理想有古今之变。惟有意志超群的勇猛奋斗之才,艰苦卓绝,才能最终实现其理想。如叔本华主张意志为世界之本体,尼采希冀意志绝世而几近神明之“超人”,易卜生则呼唤万众不慑之强者。“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⑩鲁迅推崇的“意力主义”,即以尼采权力意志哲学为代表的19世纪欧陆唯意志论哲学。
鲁迅对现代性的批判,以浪漫主义的“审美现代性”反对民主工商文明的“社会现代性”,即张钊贻所谓以“文化现代性”反对“实用现代性”,其问题意识在文化而非政经制度。因而,他介绍和倡言欧陆“新神思宗”浪漫主义哲学文艺,而对欧洲彼时的政治经济思想并无措意。
二 “立人”与“改造国民性”
鲁迅深刻反思批判了西方19世纪文明之重物质轻精神、以众数斥个人之偏弊,并倡言精神个人主义以矫正之:“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⑪鲁迅以超越西方19世纪文明而求索20世纪新文明的世界视野思考中国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必须避免重蹈现代西方之文化偏至的覆辙,取“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之方针。彼时,杨度倡言的“金铁主义”在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其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大成,主张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与立宪主义。追随梁启超立宪主义的杨度,曾与鲁迅同年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而在鲁迅看来,“金铁国会立宪”所追求的军事经济政治现代化,皆为文明之枝叶而非本根。鲁迅的“非物质”、“重个人”的启蒙主张,基于对晚清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反思。
鲁迅以现代性批判和世界文明的宏阔视野反思晚清现代化运动,批评新思潮盲目追随西方文明而对“物质”与“众数”顶礼膜拜的迷思,“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⑫鲁迅指出,欧洲19世纪文明凌驾东亚,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及其末流,流弊自显。而新神思宗力挽狂澜,补偏救弊,其可“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⑬
鲁迅所期许的20世纪文明,将是以主观之“意志”为基础的新文明。他相信,20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而与19世纪之文明相异趣。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20世纪之新精神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志以辟生路。
鲁迅跨越时空,以现代性之视域思考中国转型问题。他通过反思19世纪西方现代性之偏弊和借鉴“新神思宗”之个人主义,提出了其“立人”之启蒙主张。他认为,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不改革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但所以匡救之新文化,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亦于忧患无补。因而中国既要顺应世界潮流而改革旧传统,又要防止西方新文明之偏至,改革需要超越中西古今的开放的心灵。“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⑭鲁迅的改革方案是,借鉴欧陆新神思宗的个人主义,启发国人之自觉,以使沙聚之邦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
在鲁迅看来,青年往往厚西薄中,主张以欧化代传统,而于欧洲19世纪末新神思宗等新思潮漠然而不措意,仍盲目追求现代西方之“至伪而偏”的“物质”与“众数”。在他看来,“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⑮
“立人”是鲁迅反思晚清现代化运动而独树一帜的改革主张。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竞言武事,”“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⑯而在鲁迅看来,追求西方的军事工业商业宪政,皆枝叶之求,而欧美之先进,“根柢在人”,故中国的革新亦“首在立人”。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鲁迅首举“人”之大旗,揭示了人的解放之启蒙主题。鲁迅“立人”的目标是“致人性之全”的“新人”,其路径则是以文艺转移性情,而“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问题是青年鲁迅探索的中心问题。1902年,鲁迅负笈东瀛,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习医。受严复与梁启超的影响,国民性问题成为留日学生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鲁迅受严梁思想和“国民性”思潮的影响,又读到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之气质》,而开始求索国民性问题。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常与同乡好友许寿裳讨论人性与国民性问题。据许氏回忆:“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二)的探索,便觉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⑰鲁迅和许寿裳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诚与爱,而其最大最深的病根是奴隶性。改造国民性的根本目标,就是克服国人的奴隶性,而实现个性的解放。
而“改造国民性”的方法,就是文艺启蒙。鲁迅认为,中国民众的精神受小说戏曲影响甚深,因而文艺可以引导国民精神。他后来回忆:“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变社会的。”⑱鲁迅早年在东京翻译弱小民族的抵抗文学,以及五四时期 《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的创作,即其“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实践。鲁迅后来忆及其写《狂人日记》的初衷:“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⑲
新文化运动是鲁迅文艺启蒙的黄金时期。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退潮,鲁迅仍坚持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在他看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⑳
三、鲁迅与尼采:“反启蒙的启蒙”
鲁迅的启蒙思想深受尼采的影响。他初抵东瀛,就受日本尼采热的影响,而喜读尼采。1918年他用古文翻译过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其作品《狂人日记》、《热风》等颇具尼采的风格,故有“中国的尼采”之号。关于鲁迅与尼采的思想联系,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钊贻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㉑
尼采是 “后现代主义哲学之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尼采用以权力意志为基础的生命哲学取代理性主体的形而上学,实现了“从现代之准备性阶段向现代之完成的过渡”。㉒尼采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审美主义的批判,诚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尼采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的框架,”“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㉓
尼采崇尚“贵族激进主义”的个人主义。他认为,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㉔“生命就是权力意志。”㉕由于权力意志的强弱,人类社会天然存在少数的命令者与多数的服从者。命令者与服从者分别代表了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基督教是否定生命的最有害的奴隶道德。尼采所谓“主人”与“奴隶”只是性格类型,更符合他的意图而不至于被滥用误解的用语是 “高贵者”与“奴性者”,抑或“贵族品质”与“奴隶品质”。在现代社会,古代那种野蛮的主人——奴隶制度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更加精神化的主奴关系:“奴隶”是受束缚的精神,“主人”则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精神超凡脱俗,总是不懈地为高贵事物而奋斗,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创造性潜能。㉖现代民主社会延续了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对尼采来说,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奴隶”(受束缚的精神)拥有一切权力,而“主人”(自由精神)则丧失了权力。这是群体对个体的完全胜利。而那些通过为人类创造新价值和新可能性而进行领导的“命令者”却愈益稀缺。顺从的群体本能被最好地继承了,并且以牺牲命令的艺术为代价。现代社会愈来愈接近于彻底压制任何变异的或越轨的事物,偏离规范被视为邪恶。对于现代社会,每个越出正轨者皆是乖谬者,而所有乖谬者都必须被拉平。顺从是残忍地被强加的。㉗
对于现代性导致的危机,尼采寄希望于 “超人”:“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㉘“超人”表征具有战斗力的自由精神,他超越了奴隶道德,而为极端的权力意志所驱使。“超人”是人类未来的拯救者。“上帝死了。我们需要在这颗行星上,在这个宇宙中保全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将人兽置于控制之下,需要给我们自身的深层的生命力套上扼具以使之服从于高贵的目标。”㉙>尼采强调:“‘超人’一词被用来表示一个至高的发育良好的类型,这种人对立于‘现代’人,对立于‘好’人,对立于基督徒和其他的虚无主义者——该词出自查拉图斯特拉这个道德的毁灭者之口”。㉚>查拉图斯特拉宣告“超人”的来临,他“感到自己就是一切存在者的至高种类”,“在这里,在任何时刻,人都被克服了,‘超人’概念在此成了最高的实在性——在无尽的远方,迄今为止人类身上被诩为伟大的一切东西,都处于‘超人’之下”。㉛
尼采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毁灭者,也是新价值的创造者。尼采指出:他的《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这本书(1886年)从根本处讲乃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包括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也包括现代政治,同时指出了一种最不现代的对立类型,一种高贵的类型,一种肯定的类型。在后一种意义上,本书便是一本贵族(gentilhomme)教科书——‘贵族’这个概念比人们一向所见的更具精神性,也更为彻底。哪怕只是经受这个概念,人们精神上也必须有大勇气,人们必须不曾学会畏惧……时代引为自豪的所有事物,都被认为是与这个类型构成矛盾的”。㉜现代性批判与贵族精神,构成了尼采哲学的“贵族激进主义”精神。
尼采哲学有两个面向:一是否定的面向,“重估一切价值”,批判基督教与民主制,批判否定生命意志的“奴隶道德”;一是肯定的面向,呼唤“精神大贵族”,即“超人”。尼采哲学的两歧性,表现为他对启蒙的暧昧性,他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位旗手伏尔泰和卢梭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出身于波兰贵族的尼采厌恶“卢梭的18世纪”和其平等主义,却将“精神大贵族”伏尔泰引为同道。尼采于1878年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在这本扉页题辞“献给伏尔泰,纪念他逝世百周年”而标榜“一本为自由精神的书”中,尼采写道:“伏尔泰首先是一位精神大贵族(grandseigneur):而我恰恰也是这种精神大贵族。”㉝尼采生命哲学的根本宗旨,是生命意志的升华和强化。这也是其扬伏抑卢的根本原因。
尼采哲学的启蒙之敌与启蒙之友的两歧性,构成了其反启蒙的辩证法。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将其归为“尼采的新启蒙”。 德国学者黑勒(Peter Heller)认为,尼采反对“卢梭主义”这“一种革命性的、极端乌托邦的平等主义。”“伏尔泰的名字也许仅仅是一个广告,目的是推出尼采自己牌子的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的特征在于,其倾向的确与18世纪旧启蒙运动的倾向相反”。㉞黑勒把尼采称为崇尚精英特权的“自由的贵族化个人”。㉟
孙周兴对尼采“新启蒙”之反启蒙与启蒙的二重性作了进一步诠释:尼采是政治上的反启蒙主义者,哲学上的启蒙主义者。“或问: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尼采明显反18世纪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又显然在主张一种超越道德和革命的、弘扬个体生命强力的新启蒙,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哲学的。两者构成一种纠缠不清、难以消解的现代性矛盾和分裂,甚至令今天的学人(知识分子)都无以解脱。在哲学上看,政治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必定是不彻底的、局部的、成问题的;而在政治上看,哲学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又不免沦于反动和极端(反革命、反民主、反平等之类)。 ”㊱
尼采哲学是一种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启蒙”。18世纪启蒙的基本精神是理性、自由、平等。而尼采“新启蒙”的要旨则是生命意志、精神自由、高贵性。自由精神、个体价值、反基督教,是尼采“新启蒙”与18世纪启蒙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尼采声称要追寻被卢梭“革命乐观主义”葬送的进步进化的启蒙精神。他反对大众,崇尚贵族,把特立独行者的创造视为文明进化的必要条件。特立独行者的创造导致变异和进化,而大众只能压制天才,扼杀创造。基督教道德是颓废者的道德、奴隶道德,它压抑强者,扼杀创造,以逆淘汰阻碍进化。平等化的现代民主社会亦同样如此,它只能产生颓废的“末人”。因而崇尚个体意志自由的尼采,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启蒙主义者、反民主主义者。此即尼采哲学“反启蒙的启蒙”之两歧性。
鲁迅东渡日本后,受明治后期方兴未艾的尼采热的影响,开始关注并喜爱尼采。彼时,中国知识界除了王国维和章太炎外,对尼采甚少措意。严复和梁启超介绍的西洋新学,多以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为主,主要为17、18世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斯密、康德,或19世纪的密尔、斯宾塞、伯伦知理等。鲁迅则注重19世纪末最前卫的文学哲学思潮,尤为浪漫主义以及唯意志论哲学。尼采是一位诗人和“文学型的哲学家”。鲁迅尤为喜爱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翻译了其序言。他盛赞尼采崇尚“大士天才”的个人主义,希冀以尼采式“超人”作为其“立人”的典范。
鲁迅的启蒙思想具有强烈的尼采色彩。其以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批判现代性之“众数”与“物质”、以尼采式“超人”为“改造国民性”的“新人”典范的启蒙思想,其以尼采反启蒙思想为中国启蒙之思想资源的两歧性,以及其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与尼采哲学“反启蒙的启蒙”理路如出一辙。尼采反对基督教和卢梭,视其道德主义和平等主义为弱化个体生命意志的颓废者道德。鲁迅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由于其对生命意志的弱化。他崇尚尼采,则旨在以其“超人”刚毅不挠的超绝生命意志扫除国人的奴性,唤起国人的自由精神。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深受尼采“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思想的影响。尼采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他阐扬希腊神话中表征“主人道德”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反对基督教否定生命意志的“奴隶道德”。在尼采看来,生命即“权力意志”,“主人道德”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它以强力、肯定生命、具有价值创造能力为本质特征。而“奴隶道德”则是否定生命意志的颓废道德。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亦集中批判国人的奴性心理,他把奴隶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主要病症。
在《灯下漫笔》(1925年)中,鲁迅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㊲
关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在 《论睁了眼睛》(1925年)中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㊳
在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的小说杰作《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影响显而易见。尼采曾把地球视为一个疯人院。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则是一个被“吃人”的礼教戕害的精神病人。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扬从“虫豸”到“人”到“超人”的进化论。鲁迅笔下的“狂人”则表达了从“虫”到“野蛮人”到“真的人”的进化论,他以“真的人”取代了尼采的“超人”,作为对“吃人”的“野蛮人”的超越。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3)中,鲁迅谈及其《狂人日记》受果戈理和尼采的影响,并且比较了他和尼采的进化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㊴
在《阿Q正传》中,鲁迅旨在写出现代国人的灵魂。阿Q的愚昧、怯弱、贪婪、麻木、自欺欺人、欺软怕硬,是奴性的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四、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批判:先知与困境
当清末启蒙学者还在寻求“富强”、拥抱“自由”、“平等”、“民主”等欧洲启蒙价值时,鲁迅已经慧眼独具地关注欧洲19世纪文明之“众治”与“物质”的偏弊,并引入19世纪末欧陆最前卫的批判启蒙的“新神思宗”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揭示自由与平等、物质与精神的悖论,反思中国启蒙和现代化的方向问题,并提出了“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之深刻的中国启蒙议题。这种极具前瞻性的世界视野和现代眼光,使鲁迅在晚清新思潮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位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先知。在一百年后的21世纪,鲁迅穿越时代的思想洞见愈益凸显出其深刻性。
独立的个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个性解放”是弘扬主体性的启蒙运动的核心主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家族主义和皇权主义盛行的古老宗法社会,个人附属于“家国天下”共同体,从未获得独立的价值。鲁迅“重个人”的主张,借鉴尼采等的“新神思宗”哲学,揭橥“个性解放”的启蒙主题,呼唤特立独行、反抗时俗的“超人”和“精神界之战士”,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伦理革命的深刻意义,这使其成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者。
关于民主社会的“多数人的暴政”、平庸化和同质化,早在尼采之前,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已有深刻洞察。与崇尚卓越的贵族文明相比,民主社会是一个平庸的大众社会。托氏预见了民主时代的来临,也洞察了民主的深刻悖论:“多数的暴政对民情的影响大于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妨碍了伟大人物的成长”。㊵民主社会难以避免平等与自由的冲突。“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㊶民主社会的平等化必然导致平庸化。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㊷出身于诺曼底贵族世家的托克维尔男爵并不掩饰他崇尚卓越的保守主义情怀:“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并存,巨富和赤贫并存,最聪明的人和最愚昧的人并存的时候,我总把视线离开后者只看前者,而且前者使我看起来喜欢。”㊸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托氏留下了他关于“平等”的哀婉悲观而意味深长的忠告:“现代的各国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㊹
托克维尔的朋友、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想代表约翰·密尔亦所见略同。他在《论自由》中警告:“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展,完全是受这个蹊径繁多之赐。但是,它之保有这项惠益,也已开始是在一个减少得可观的程度上了。它正朝着那种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断然前进。托克维尔(M.de Tocqueville)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曾评论到今天的法国人甚至比前一代的法国人是怎样更加彼此相象了。我看若说到英国人,还可以在远远更大的程度上来作这同一评论。”㊺密尔对现代社会之凡庸性主导一切的同化趋势忧心忡忡。他认为,个性是创造的源泉,天才永远是少数人,他们总是更富有个性,甚至具有与众不同的怪异性格。而大众社会的时代趋势是同化。政治、教育、公众舆论都在促进同化,并形成一种大群与个性为敌的势力,以致使个性愈来愈难以保住其根基。“现在遍世界中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到现在,个人却消失在人群之中了。……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势力”。㊻密尔强调,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制政府,不论在政治行动方面或者在公共意见、品质以及心灵情调方面,曾经升高或能够升高到平凡性之上,除非多数人接受具有较高天赋和教养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指导。“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㊼
鲁迅对民主社会“众数”之多数专制、同质化和平庸化的深刻批判,与托克维尔和密尔异曲同工,虽然其批判的西学资源并非托密二氏之保守的自由主义,而是19世纪末以尼采为代表的欧陆“新神思宗”的“主观与意力主义”。在民主思潮方兴未艾的20世纪初清末思想界,鲁迅对民主独具慧眼的批判格外醒目。
然而,鲁迅的浪漫主义毕竟不同于托克维尔和密尔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对于民主,鲁迅之中国帝制时代的保守主义与后者之西方民主时代的保守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时代落差显而易见。托密二氏对民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顺应民主的历史趋势,对民主取利避害,与民主共存。而鲁迅则持非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民主观,这使其作为一位中国启蒙者的政治观颇显暧昧。
托克维尔指出:“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㊽“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㊾托氏对民主的态度是:迎接不可抗拒的民主时代的到来,对民主加以引导,以取其利而避其害。对于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来说,尽管他对取代贵族社会的民主社会充满保守主义的哀婉感伤,但他却宁愿把与自己贵族观点相对立的平等视为上帝的旨意。“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而美丽。”㊿托氏的现代主义立场超越了其贵族的保守视野。“贵族制国家的体制所固有的一切弊端和美德,与现代人的性格格格不入。”51对于民主的弊端和危险,托氏既感到恐惧,又怀有希望。他相信这些民主的弊害可以克服和避免,“我越来越坚信,民主国家只要愿意干,还是能够建成高尚而繁荣的社会的。”52
与托克维尔一样,密尔虽然对民主的弊端和危险多有批评,但他仍是代议制民主的坚定辩护者。他的名著《代议制政府》(1861年)使其成为代议制民主的经典理论家。他认为:“由人数上的多数掌权比其他的人掌权较为公正也较少危害。”53纯粹民主制难以实施,因而,“一个完善政府的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54为防止民主的“多数专制”,密尔主张“参与”与“才能”并举的原则,以达致人民主权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显然,鲁迅并不熟悉托克维尔和密尔对民主的辩证思考。而他所欣赏的尼采则是民主的敌人。尼采“贵族激进主义”敌视民主的理由,是民主是庸众即奴隶对大士天才的征服,它泯灭高贵卓越,扼杀创造性,导致生命意志的弱化。尼采崇尚贵族、反对大众的政治思想是反启蒙的。鲁迅的尼采式启蒙思想亦难免其“反启蒙的启蒙”的暧昧性。
鲁迅借鉴欧陆“新神思宗”哲学批判“19世纪文明”之“众数”与“物质”的偏至、主张“重个人”、“非物质”的启蒙思想,固然具有反思现代性之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前瞻性,但现代的欧洲病与前现代的中国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当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民主和物质主义的现代病时,中国这一古老的农业帝国正为专制与贫穷所困扰,民主化和工业化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两大目标。以反抗欧洲现代性之 “重个人”、“非物质”的“新神思宗”为救治中国病的药石,显然忽略了工业欧洲与农业中国的时代落差。
鲁迅的尼采式启蒙思想的一大困境是 “天才与庸众”的对立。尼采个人主义寄希望于“大士天才”即“超人”,主张以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鲁迅服膺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反对“抑英哲以就凡庸”,主张“置众人而希英哲”。英哲与庸众势不两立,少数英哲的出世以多数庸众的牺牲为代价。当鲁迅追随尼采而呼唤“超人”式的“大士天才”,以改造国民的奴隶性而促其觉醒时,他不能不遇到“天才”与“庸众”、“主人”与“奴隶”的悖论。按照尼采,“主人”与“奴隶”以生命意志的强弱而势不两立,颓废的基督教和民主社会皆为奴隶对主人的反进化的征服。而“超人”的出世,则是“主人”的胜利和“奴隶”的末日,即“奴隶”压制“主人”之人类历史的终结。
鲁迅的尼采式启蒙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他崇尚尼采“超人”式的“贵族激进主义”,主张“重个人”、“排众数”;另一方面,他又希冀以“超人”式“大士天才”为社会之桢干,树特立独行之风,以改造国民的奴隶性。这样,他就难以摆脱“贵族激进主义”之“天才”与“庸众”二律背反的困境:因为“天才”与“众数”势不两立,“众数”或奴隶的解放即“天才”的末日,而反个性的“众数”社会又是鲁迅所反对的。因而归根结底,鲁迅“排众数”、“重个人”的尼采式个人主义与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目标自相矛盾,这也是鲁迅的现代主义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的分歧所在。鲁迅“人国”的国族主义关切毕竟不同于“超人”的贵族激进主义之个人自由理想。“天才”与“庸众”的张力,贯穿于鲁迅思想的始终。五四以后,正是“天才”的幻灭,才使鲁迅把目光转向“庸众”。
鲁迅的启蒙思想继承了晚清严复、梁启超阐扬主体性、批判奴隶性的思想。严梁认为,专制导致奴性,启蒙的目标是“陶铸国民”,以国民代替臣民,这一人格转型的路径是教育启蒙与地方自治。鲁迅继承了严梁批判奴隶性的思想,但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则是以文艺转移性情为路径。严复“陶铸国民”的启蒙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制度相配合,其新“国民”的典范为英国式的公民。梁启超承严复“开民智”思想之余绪,其“新民”的宗旨亦为培育英伦式的现代国民。梁氏闻名遐迩的 《新民说》倡言 “国家”、“公德”、“自由”、“权利”、“义务”,不啻为一部现代公民的教科书。如果说严梁“陶铸国民”的“新民”是一种培育公民意识的政治启蒙,那么,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新人”则是一种人性改造的精神启蒙。鲁迅“立人”的“新人”典范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公民,而是浪漫主义文学哲学的“大士天才”,其理想人格是尼采式的“超人”。这种特立独行、意志超群、超凡脱俗的“天才”与严梁倡言的布尔乔亚式现代“国民”格格不入,民主社会的“新民”毋宁是尼采“超人”所要超克的庸俗堕落的“末人”。因而,鲁迅追寻的“新人”毋宁是一个后现代的“审美乌托邦”。套用托克维尔的语言,论人格的等级,严梁的“新民”属于“中等的东西”,而鲁迅的尼采式“新人”则属于“最高的东西”,二者以陶铸国民的“低调的启蒙”与人性解放的“高调的启蒙”,相映成趣。
五、从尼采到马克思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现代社会的形成伴随着个人的“抽离”(脱嵌),这一暗含在轴心革命中的“伟大的抽离”,与我们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的确立和增长有关,这样的社会存在赋予个人空前的首要地位。我们起初的自我认识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中,我们基本的身份是父亲、儿子或部落成员。只有到后来,我们才逐渐认识到自己首先是自由的个体。因而,个人的“伟大的抽离”是道德—社会秩序理解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使我们完全从宇宙和社会的神圣性中抽离出来,由此成为单一的个体。55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公共领域、主权人民的兴起形成了以国家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这场个人独立的革命,提高了人们对大社会的归属感。它使人们从狭隘的群体中分离出来,但并没有把人们置于一种专顾自身利益的孤立之中。一个充满着私人关系的等级社会完全过渡到一个非私人化的平等社会。56作为一个道德理念,现代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中断人们的归属感,而是把自己想象成属于更广大而更无个人色彩的实体:国家、运动、人类社群。这种变化意味着从“关联的”身份转向“范畴的”身份。57
泰勒所谓个人的“伟大的抽离”与新社会秩序归属之辩证的“现代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而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式个人主义则不然。标榜“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的尼采,反对自由民主制度,追求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而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斯蒂纳的“个人无治主义”亦然。尼采崇尚意志自由的个人主义固然与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一脉相承,但其反民主的政治倾向则是反启蒙的。在尼采之缺乏“个人”与“社会”辩证性的激进的精神个人主义中,从传统社会秩序“抽离”而又拒斥现代社会秩序之归属的“个人”孤立无依,“超人”的虚渺理想并不能克服“个人”的孤独和虚无。
鲁迅是清末最深刻的个人主义者,其个人主义比其师章太炎 “大独必群”的个人主义远为激进。鲁迅的尼采式“贵族激进主义”之精神个人主义,也有别于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
鲁迅崇尚的“大抽离”后独立而无所依傍归属的 “个人”,是孤独的个体。短篇小说 《孤独者》(1925年)表征着鲁迅作品根深蒂固的“孤独者”意象。小说主人公“孤独者”魏连殳(一个小城镇知识分子),经历了觉悟—孤独—绝望—自虐的精神过程。其人生的悲剧在于,“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58
这篇写于新文化运动退潮后的1925年而收入鲁迅作品集《彷徨》的《孤独者》,毋宁是五四后“彷徨”的“孤独者”鲁迅本人的精神写照。经历了“大抽离”而解放的独立的个人,割断了传统的天人纽带和共同体联系,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个体,现代人的孤独亦随之而来。鲁迅信奉斯蒂纳式“个人无治主义”,他对许广平承认,高长虹“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是安那其主义者。”59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来说,“孤独者”的焦虑挥之不去。相比较,信奉民族自由主义的梁启超所追求的“新民”,则是个体脱离家族羁绊后再归属民族国家的“国民”,其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辅相成。梁氏不是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故他并无鲁迅的孤独。五四后,鲁迅的孤独、彷徨、虚无、绝望,既源于新文化运动退潮和传统巨大的守旧力量,也源于其怀疑现代性而启蒙理想渺茫的无所适从。鲁迅启蒙的孤独困境,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其既反传统又反现代性的“反启蒙的启蒙”的思想困境,二是其尼采式“超人”乌托邦的虚渺,三是其反庸众的精英立场,四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文艺启蒙收效之难。在晚清和五四的启蒙者中,这种启蒙的孤独是鲁迅独有的,梁启超与陈独秀并无此孤独。梁氏“新民”的思想魔力俘获了一代知识人,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可见一斑。陈氏1915年秋创办《青年杂志》,其旨在青年动员的十年启蒙计划,不到四年“新青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重拾世纪初在东京受挫的青年时代的启蒙理想,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并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不朽的启蒙文学作品,批判吃人的礼教,剖析国人的灵魂,开中国新文学之先河。五四以后,随着《新青年》阵营的分化和新文化运动的退潮,鲁迅陷入彷徨之中,并逐渐怀疑和疏离尼采思想。
学界一般认为,鲁迅的思想转变始于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4.12事变”,依据是鲁迅自述彼时其告别了进化论思想。其实,鲁迅在新文化运动落幕的1923年60已开始疏离尼采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李大钊、陈独秀相继改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新青年》启蒙阵营随之分化。1923年,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一改早年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转而强调经济的重要性:“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61鲁迅一改早期浪漫主义之“非物质”的唯心论,转而置重“钱”和“经济权”。而且,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亦不免怀疑,“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62
同时,鲁迅不再坚持早年“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他在《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中强调:“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就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63鲁迅改变了早期以天才改造庸众的精英态度,从崇尚“天才”到重视“民众”。
这表明,五四以后,鲁迅摈弃了其早期启蒙思想之“非物质”与“重个人”两大宗旨。这预示着他从尼采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1928年,鲁迅在主编《奔流》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转而以阶级论代替人性论,并改变了轻视多数的精英主义立场。在《习惯与改革》(1928年)中,他指出:“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64
耐人寻味的是,19世纪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哲学富有一种癫狂气质。无独有偶,鲁迅推崇的“新神思宗”哲学家尼采和斯蒂纳的生命皆以癫狂告终。叔本华亦生性孤僻怪诞,其父死于癫狂溺亡。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尼采和斯蒂纳的唯意志主义归为浪漫主义,并揭示了二者以癫狂为归宿的思想原因。他指出,斯蒂纳的思想困境导致其最终在疯人院度过余生。“类似的思想同样也在煎熬着尼采,这位更伟大的思想家,不过,他在某些方面也和施蒂纳相似。从这里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就需要交流。……只要存在常规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同价值就是必需的。只要存在共同价值,就不可能说一切由我来创造。假如发现任何先定之物,我就一定要打碎它;发现任何结构之物,为了使我的自由想象天马行空,我就必须摧毁它。就此言之,由它的逻辑结论来看,浪漫主义的确以某种精神错乱告终。 ”65
晚年鲁迅终于告别了其自留日时期以来所深爱的尼采哲学。他在《拿来主义》(1934.6)中写道:“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之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66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3)中,对于“尼采的超人的渺茫”,67鲁迅指出:“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 ”68鲁迅认识到,尼采的“超人”难免癫狂的虚渺幻想,“超人”的幻灭除了带来癫狂,只有空虚。鲁迅从尼采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就是其“超人”幻灭后反抗空虚的新求索。马克思以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填补了鲁迅幻灭后孤独“个人”的空虚。
晚年鲁迅告别自己所属的 “中产的智识阶级”,转而冀望于无产阶级:“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69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鲁 迅 :《 文 化 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184、185、185、185~186、186、187~188、188、189、191、181、182、191、192、193、180 页。
⑰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⑱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⑲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第393页。
⑳ 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㉑ 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㉒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9页。
㉓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21页。
㉔ ㉕ ㉘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 116、182、127 页。
㉖ ㉗ ㉙ [美]埃里克·斯坦哈克著,朱晖译:《尼采》,中华书局 2015年版,第 109~121、121、125 页。
㉚ ㉛ ㉜ ㉝ [德]尼采著,孙周兴译:《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60、123、131~132、91~92页。
㉞ ㉟ [德]黑勒著,田立年译:《尼采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奥弗洛赫蒂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221页。
㊱ 孙周兴:《尼采与启蒙二重性》,《同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㊲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 1 卷,第311~313 页。
㊳ 鲁迅:《论睁了眼睛》,《鲁迅全集》第1卷,第331页。
㊴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 6卷,第 189、190页。
㊵ ㊽ ㊾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295、4、8 页。
㊶ ㊷ ㊸ ㊹ 50 51 52 托 克 维 尔 :《论 美 国 的 民 主 》(下 ),第621、883、883、885、884、884、885 页。
㊺ ㊿ 47 [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78、70、71 页。
53 54 [英]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55页。
55 56 57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林曼红译:《现代社会想象》,译林出版社 2014年版,第 44、57、132、138 页。
58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100 页。
59 鲁迅:《书信致许广平》,《鲁迅全集》 第 11卷,第485页。
60 周策纵以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新文化运动落幕的标志。
61 6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71、274页。
63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75、276页。
64 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174~175页。
65 [英]以赛亚·伯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44页。
66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1 页。
67 6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189、190、206 页。
69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151 页。